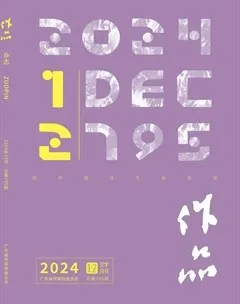蜗牛壳(短篇小说)
推荐语:孙婷婷(云南财经大学)
我是从诗歌开始看到彭紫城的,诗歌和小说双重写作者的身份让他的小说语言有独到之处。他的小说青春气息浓烈,这样文艺的文字似乎不属于这个时代,却让我这个80后很有熟悉感,在我们的大学时代,这样的文字是常见的。他书写青春的疼痛感,在暧昧的语境和矛盾的叙述中书写沉迷于梦魇的阴暗以及贪恋虚荣的扭曲灵魂。这是充满勇气的写作,他不仅是面对还要探索内心的隐秘与黑暗,既描写深渊,也从深渊中凝望。文字充满了探索,蜘蛛、蜗牛、蛞蝓等的隐喻充斥着小说,编织了弗洛伊德式性别身份认同的寓言。无法忽略小说中对身体触感的陌生化捕捉,潮湿、破碎、清冷的空气、泥土,文字的组合传达出强烈的氛围感。
如果看到他的其他小说,会发现彭紫城已展现出写作的野心,云来镇、大乘村、张云来,生活在现代性的都市,但是在文学中构筑乡村与小镇青年。但这种空间并非乌托邦或者逃避,而是充满追问地在一点点搭建和探索,并渴望被看见,如同小说中的人活在不可靠的叙述中却有着强烈的自我探索和被看见的希求。我也希望彭紫城继续写下去,珍视而不局限于自身的独特风格,去不断探究文学世界的无限可能。
自打我开始感受一种名为记忆的东西,我的内里就沉重了起来。一只蜘蛛织成的银白色巢穴,当坠落的时刻,蜗牛就掉落在缝隙的凹陷处,不出意外的话,胶状的身体会因为水分的流失而萎缩,直到变成干枯的碎片,木屑一般的,被吹散,齑粉,或许会被大地收集,成为绿色的苗,被稀释,转化。
而蜗牛壳会保留更久,像一个脓疮般吸附在雨的表面,碾压过后,一切都碎了。
你和我的距离就是蛛网的形状,圆网形状的云来鼓楼在摇摇晃晃的步态下,我从大乘村到云来图书馆的路径,从云来镇最北边一直向南走,到鼓楼的北门入口。
下过雨的街道,一股草木和雨水的气味,熏得我喘不过气来,这让我想起了你身上的味道。也是这样深沉的木头的味道,我记得你那只蜗牛壳一般的短发,不礼貌,评价,可是,你表露出赞同的口吻。黑色的螺旋就这样旋转,镶嵌在了你白皙的皮肤上。
人的脚密密麻麻地踢踏在肮脏的路上,由于相同颜色的裤子,那些腿交织在一起,就如同蜘蛛的八条腿。泥泞跳到裤腿上,打湿了向上卷起的裤脚,你当然也可以这么想,这是一幅抽象画,某一位画家拜访此处时,也许会将这个素材转化为更值钱的东西。
我时常会猜测,我仅仅是你的消遣物。
你责骂我,拆开了书外面的塑料封皮,解释不在于它是否真实,而是在于一个人是否愿意相信,较为说教的口吻,你是一尊巨大的蜗牛,把我牵制在黑暗的幽冥中,地上散落的话语你一点点拾起来,雨天时,它们全部被粘贴在白色大理石地板上。
你有时候对我说:
你过得很好,因为你早已经忘记了什么是好了,大约在某个青年时期的早晨,一干二净。
你推荐给我一本恐怖漫画,恐怖,仅仅对于未知,现在,对你来说,最恐怖的是生活本身。你的形象有时我会和漫画里的主角弄混,你们有着一样的短发,有着一样白皙的皮肤,有着一双硕大的眼睛,黑宝石一般刺痛自卑的痼疾。
对于早晨,空间总是更加广阔,空气更加清冷,这是你的奥德赛,这是图书馆,这是白色砖块堆砌起来的白色城堡。
午后的阅读,往往是梦境与文字交相辉映的,有些时候会很难分清影子和光的距离。
你说你是从云来的最南边逃过来的,你说你受不了村子里晃来晃去的男人,张云来,你说,他已经与整个村子合为一体了,甚至是名字。
等到秋天,外面都变成黄色,你就回去。
等到冬天,路上没有那么多来来往往的行人,你就彻底离开云来镇,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在云来外面。
我不得不承认的是,我无法接受你的告别,正如我无法接受没有壳的蜗牛,蛞蝓,它们是同一种东西吗?也许明天,我会在百科类书架上找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后来只找到了蛞蝓和蜗牛冬眠的不同:蛞蝓冬天直接钻到地下,寻找合适的温度,一直在地下待到来年春天。而蜗牛钻进壳里,用黏液封住蜗牛壳口,留下一道缝隙,等它嗅到生的气息,就重新回到这个世界。
雨还在下,从云来的最北边一直走到图书馆,我的鞋上沾满了泥巴和草的碎屑。泥土与地上的石砖摩擦,就像踩在果冻上。
我在软软的泥土上,看见雨和光一齐拓印出蛛网的形状。
鼓楼的暗红色木门上被黑色的漆涂上了一连串电话号码,办证,疏通管道……还有一些寻人启事、招工简介、征婚启事,我对这些东西感到好奇,雨水把劣质的墨水晕染得像一幅水墨画,但我还是看到了上面是个女人。
我继续向前走,来图书馆,并非因为它存在的形式是以书为载体,而是我不知道去往何处,一直向前走,向梦借以生存的经验,梦里的步伐会更快一些,行走的状态,也许来自好奇的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了你的脸,但我知道你不仅仅存在于我的梦里。
让雨淋淋你的郁闷,蜗牛在雨后会看见更多。但你没有听从我的建议,你一直在书店里游荡,穿着那件绿色的围兜,扭动着头上的那顶黑色蜗牛壳状头发,沉入寒冷的纸张。
我有时候想,你至少会出去晒晒太阳,像野猫一样偷偷地四处溜达,趁没人在意的时刻,你至少会去看看新开的商店,就在街上,不进去,远远地观望着,可你唯一的归宿只有图书馆,与整个世界隔离开来,默默地在黑暗深处睡去。
有时候,天气是晴朗的,也许是雨后,也许是雨前,空气有一点点潮湿,灰尘尚飘浮不起来,掉落在地上,发出黏土的香气。这样的时候,我很少去书店,你那时会离开吗?大概率你依旧守候在条形码旁边,周旋在人来人往的借书人之间。只是后者是我的揣测,我见你的时候,你一直坐在书旁,而不是那张刚进图书馆就能看到的桌子旁,那里总是坐着一个粗鄙的女人,她好几次咒骂过借书的人,这也许是她的计策,这样借书的人会少一些,她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给她自己。
我从来没有和我周围的人谈起过你,关于你的眉毛里的黑痣,关于你蜗牛壳般的发型,关于你的绿色围裙,关于你高挑的身材,关于你像芭蕾舞般的走姿穿梭在书架之间,我什么也没和周围的人说过。
我记得你给我推荐的意识流、元叙事、人称变换的作品,我还记得你最喜欢魔幻现实主义,那时候这个词还没被大家那么多次地使用,每次用到这个词,仿佛是我们之间的谜语,每解开一次,都会有种从迷宫的层层叠叠中找到一个没人发现的暗洞出口的感觉。
模糊是我们的同义词,有些时候你不小心抖掉了一些较为准确的事,断断续续地,我只记得张云来这一个名字了,所以下意识地,我会把这些事全归于他。
你说你不应该和我说大人的事,我说那你就不应该给我推荐恐怖漫画,那是大人才应该看的,你说不是你推荐的,你只是把它拿给了我,是我自己选择看的。
你现在哪去了呢?我来过图书馆好几次打听你的事,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胖女人也不在了,很多时候,疼痛的消失比幸福的消失来得更加容易感受到。
我有时猜测,你被图书馆里潜藏的巨型蜘蛛捕捉进了另一个空间。我并不是无端猜测,我把这个猜测和你遇到外星人的经历联系在了一起。
雨天又来了,我撑着一把锈迹斑斑的伞,摇摇晃晃地向图书馆走去,因为大风把地面上脆弱的事物都刮得摇摇晃晃。这次的雨,是在路上开始下的。我又看到那张寻人启事了,它的一半已经被另外一张寻找孩子的压在了下面,就好像这个人连同启事一道被新的失踪压在了下面。
就像是赴约一般,与明天见面,而昨天,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你继续讲述你的故事,我们躲在图书馆的最深处,这样就没有人听得到我们的声音。
外星人,这时,你终于愿意把这件事说出来了,时机已到,而时机是对自己妥协。你深知,有些事,需要讲述出来,这件事才真正地发生,否则它就存在于虚无,靠近假的那一头。
这些雨在路灯的照射下显现出形状,而光的体态也被雨衬托出来了,晶莹虾的形状,和你说的UFO的射线一般,我此刻期待这股光线也能将我吸收进那个古铜色的飞行器。你强调它的形状正如云一般,他们剪着和你现在一样的发型,你的发型也是他们剪的,蜗牛壳形状的梦境收集器,同时兼具共享的功效,我不相信。
更多的雨水把我的黑色裤子打湿,即使打着伞,风依旧把雨舀了一瓢泼在了我的腿上,这是因为云来是在坝子里,风通过狭管,更急。我不相信,换句话说,我希望有一段如你一般的旅程,这至少能证明我不普通。
你说你被挑选的理由也许就是太过普通,等你再长大一些,你会慢慢适应平凡,从青年时代的疯狂进步,向山顶进发,一直到中年,你在山顶看到更高的山,然后开始质疑乐观主义,不过再爬一阵子吧,你说。
有时候,图书馆的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下我们俩和门口那个凶巴巴的女人。她听到我们的对话,警告我们,称我们的声音填满了整个图书馆,你说,是孤独、雨水、平凡和年复一年的日子填满了这里。
回家和来图书馆,我通常会选择不同的路线,回家我会走一条人更少,更多的桉树、法国梧桐、蓝花楹、草地的路,它经过公园,路上有更多的蜗牛。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动物,它们同时拥有恋矢和生殖孔,货架上的百科全书还描述到它们剧烈的刺插运动。好奇扭曲了我的大脑,我颤颤巍巍地捉起一只蜗牛,羞耻感也涌了上来,从鼻腔一直延伸到我的眼珠附近,我似乎感受到了蜗牛黑和黄的色调,连同雨水一起把我和泥浆包裹起来。
你说那个时候张云来两只手被两个人架着,一个人叫沃妞,一个人叫沃仔,他们是外星人。不只张云来见过他们,蜗牛博物馆的保安也看见了他们,是他联系收容站的人把你送回来的,距离是两千公里,他脚上还套着那双塑料拖鞋。那天下午,他还出现在田埂上,挑着扁担,挂着两个黑色圆桶。子夜一点,世界最大的蜗牛博物馆的保安发现了他,保安报了警,警察把他送进收容站,收容站站长亲自联系了云来镇的领导,把你从上海接回了云来。
你说起那两个人的面容,国字脸,以及粗犷的眉毛和薄薄的嘴唇,这些似乎是漫画男主角的面容,我怀疑你把他们弄混了,你压根也没见过,是吗?那淡黄色的黏液旁边配的是日文,人形蜗牛,即使是这样,我还是记得那张脸,晶莹的皮肤和那双高高凸起的眼睛柱。
那本漫画里的另一个主角长着一模一样的脸庞,这不由得让我怀疑这是否是作者的怠惰,蛞蝓少女,而寻找的壳,正是少女的头。
一切似乎渐渐清晰了起来,至少对于迷宫一般的图书馆来说。
被送回的张云来向云来镇的人讲述了这个故事,镇上的人对于他的荒唐经历提不起一点兴趣,直到电视台的到来,人们又开始关注起张云来。电视台的专家以及主持人通过观察他的饮食起居,并没有发现什么,但最后他们签订了一份协议,你下意识地觉得这是补偿,你收下了。
这个故事终于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梦游症,这是一种常发生于压力较大的成年人的病症,成因较为复杂,与患者的童年睡眠经历有关。
记忆就是这样沉重起来的,你向我解释说,如此这般,吐丝,结网,然后将一整个螺旋形状的记忆包裹其中。
张云来讲完沃妞、沃仔的故事之后,村里的人只是笑话他,仅此而已。但他因此而被电视台采访之后,村里的人开始躲着他,即使大家都看到了专家的解释。
有时候,下起大雨来,大乘村所有的泥土地都松软了起来,我还是会打着伞出去,把蜗牛捉住,然后放在酸奶盒子里,透明的那种盖子,可以透过淡蓝色的塑料光泽看到蜗牛。有时候蜗牛一动不动的,有时候它一直向前爬,即使前面什么都没有。我看着蜗牛咀嚼青草的模样,似乎我拥有了它,我驯服它,就好像在驯服我的恐惧。
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钟面上显示的时间是十二点,天上淅淅沥沥的雨水打湿了周围摩天大楼的墙壁,沃妞和沃仔拉着他的手,贴着红色墙壁一直往前走。他们那时穿的是什么衣服?有一道类似于苏州园林似的巨大圆形铁门,这里应该是入口,它已经关闭,所以继续向前,一栋类似于土楼形状的钢材和玻璃为材料的建筑,直到出现一座已经生锈的楼梯,他们爬上楼梯。沃妞和沃仔似乎在密谋什么,他们告诉张云来一直向上走。
我告诉你这一切是因为我已经分不清这是你曾经和我叙述过的,还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抑或我的梦,你一面说这是曼德拉效应,一面告诉我更多有关张云来的事。
你告诉我张云来小时候总是围着他母亲转,有时他甚至是嫉妒,当他父亲与他母亲过于亲密时,他会显得焦躁不安,当他的父亲离开时,他松了一口气,仿佛母亲是他自己的。
后来他又发现,他对母亲好奇的点,不在于占有,而是好奇母亲的生活核心,进而他就可以模仿。他欣赏起母亲纤细的腰和手臂,欣赏起母亲因为劳累而累赘在头发里的汗珠,发现母亲从集市上买回来放在抽屉里一直没用过的指甲油,发现母亲有一双鞋子后面过于高的根。
再到后来他在家偷偷把母亲的发箍戴在了头上,这让他感到自在,类似于净化。在原有的混乱的秩序里,他发现了最普世的一条,于是他用这种感觉碾碎了一切混乱,把蜗牛的壳磨碎,倒在了土壤的上面。在时间的耕耘后,新的秩序在诞生,在暧昧的语境下,他惊人地发现这一切打破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打破了阴阳平衡。但或许打破这个词不够准确,或许这是一种平衡。
有一瞬间,他设想过,他也许能同时拥有胡须和乳房,同时拥有阴茎和阴道,就像是蜗牛同时拥有恋矢和生殖孔。
这样诡异的话语让我再次恐惧起来,或是说愧疚起来。那天我为了给蜗牛透气,划开酸奶塑料盖子,我划了一次,没开,两次,没开,三次,刀划开了塑料盖子,划开了蜗牛壳,划进了蜗牛的身体里,我立马把刀拔了出来。我没有想到蜗牛壳会那么脆,许久之后,我都没有缓过神来,蜗牛一动不动地躺在酸奶盒子里,仿佛博物馆里的雕塑。
我原本打算把蜗牛埋葬进土里,再给它竖立一块墓碑,上面就写:纪念我的宠物蜗牛。但我始终没有勇气再碰那个酸奶盖子了,这给我一种错觉,那只蜗牛会在我不关注的时间里自愈。我再一次注意到这只蜗牛是很久之后收拾桌子,我发现那个酸奶盒子里布满了蛛网,它只剩下壳了。
临近你离开的那几天都没有下雨,却下了几次冰雹。我越来越分不清记忆、梦境和你的叙述,但我渐渐明白了什么,我又去图书馆了。细碎的冰雹砸在我的身上,比雨清晰一些。鼓楼里闪烁的灯光被隐藏在了树林里,红色的漆掉落在路边野狗的尾巴上,几个孩子嘴里吐露出幼稚的词,还有一个更大些的孩子坐在板凳上,身子靠着另一张板凳和作业本上睡着了,一个扎着两条辫子的老奶奶正牵着一个背红书包的小女孩。大家在冰雹里都慢了下来,还是说,那时已经是另一天了?我的鼻涕流了出来,我一直用手擦。我低头看的时候才发现,那是鼻血。这个时候我真希望下的不是冰雹,而是雨,这样就可以洗刷掉污秽,一切又都可以重新开始。
我径直走向了我每次都会路过的广告牌,我记得在一个男人的寻人启事、一个餐馆的招聘启事、一个重金求子的招人启事下面,有一个蜗牛壳状头发的女人,那就是你不是吗,张云来?我一张一张地拿下来,我看到了那张已经被风化了一半的寻人启事,幸好,可以认出是谁,但,那却不是你,那个人也不叫张云来。于是,我又把撕下来的每一张纸贴了回去,我向图书馆跑去。
你已经离职了,那是我又去了几次还是找不到你之后才发现的。我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秋天来了,你说,等到秋天,你就回去,我不敢问那个凶悍的胖女人你是否就叫张云来,只是,我有时在梦里黏黏糊糊地搅拌起那些记忆,沃妞、沃仔是你告诉我的故事吗?那个蜗牛博物馆里陈列了我死去蜗牛的雕塑,我成为那个摇摇晃晃的男人,摇晃在云来镇的每一个角落,摇晃在雨水里。后来我像漫画主角一样长出了恋矢和生殖孔,爬来爬去。梦是欲望的满足,梦是个体的无意识,梦是童年的放大器,梦是我终于在寻人启事里找到了你的面孔,我高兴得爬到图书馆找你。
路上透明的黏液被雨冲刷,却没有消失,就像蛛网一样,它依旧挂在鼓楼红色的木门之间。图书馆里也有蜘蛛网,我一直关注蜗牛,却忘了潜藏在角落里发光的眼睛。我被凝视,你告诉了我最后一个故事,你说你背后也有一个蜗牛壳,现在你要永远生活在壳里了,而那个壳,现在就在图书馆里,在某一本书的文字里,在梦和回忆交织的地方。
可我还是希望找到你,秋天的雨变小了许多,但是持续的时间却更长了,我习惯不打伞。像温水煮青蛙一样,小雨总是更容易淋湿行人,银针般掉落在棉质的衣服上,渗透,慢慢把衣服变成地图,指示着我到你所在的村庄,下德著村,公交车会经过。我计划明天出发,明天的数量和昨天一样多,但我还是记得那一天。
我准备了一个背包,我放进去了那本恐怖漫画,还放进了那瓶酸奶和蜗牛壳,我把塑料盖子盖上了。除此之外,我还带了一个苹果,我准备路上吃。
我期待着前往下德州就像我期待着前往那片梦中的白桦林,那片白桦林就在你的村子里,和那里的蜗牛一同生长。
出发的前一天,我梦见你的波波头,张云来,你为什么混迹在那群你所说的外星人当中?你有意地隐藏在其中,但我还是发现了你,通过你身上深沉的木头的气味。多年以后我常常诧异于我是如何在梦里闻见味道的。你们拉着我的手,朝白桦林深处走去,我看见椭圆形的飞行器,肥皂般的质感,从中散射出的光芒照亮了整片林子。你们的手在传达给我信息,告诉我顺着那束光走,不要回头,我同时注意到你们的手没有指纹也没有任何纹路。
顺着光束的暖意,我最后瞥见白桦林慢慢从木头的质感慢慢变软,从圆棍状逐渐扩成圆网状,蛛网,它们回来了,即使我的蜗牛只剩下壳。沃妞和沃仔还是把它从我的背包里拿了出来,他们打开了塑料盖子,我醒了。
我没有带伞,我被你和梦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虽然梦是那么轻,像一块纱布,层层叠叠,最终压制住全身,类似于秋天的雨,细碎的银针逐渐把全身打湿,层层的纱布碾压了整个内里。
清晨的车站就在我的面前,车就这样来来回回,每个清晨你都可以找到,在对应的时间。倘若你问我持续了多久,我不知道,我只是看见车站站牌生锈的边框和新补上去的蓝色油漆。
车上比我想象的人多,他们大多操着本地口音。车里的热气与车站的清冷形成对比,我把湿漉漉的身子挤进车厢,挤进我陌生的语境。我看见车厢里一个妇女正在给孩子喂奶,她的右手边坐着一个身上布满水泥白点的迷彩服装的男人,看上去很疲惫,他的鼾声仿佛不来自这个秋雨绵绵的空间。
我选了一个靠后的座位,遥视。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个词的?遥远的视界,我们大部分人的大脑的开发程度不到10%,所以说你是否在这之上,我感受到了你,你就在那片白桦林中,就在下德著村。
我还感受到了云来的未来,觉察到今年的夏雨比往常更猛,秋雨比以往持续的时间更长,由此预测冬雨也会来,甚至是雪,上一次下,是七年前。遥视,我看到接下来的几年会依然如此,他们现在把这归因于拉尼娜和厄尔尼诺,可是之后呢?有声音告诉我,甚至是整个空间,到那时候,我们将会是冰河世纪的受害者,很多都会是。是沃妞和沃仔吗?张云来说,他们来自四维世界,他们投影到了我们的时空,运用脑电波与我们交流。交流,仅仅是我们的表达,更准确地说,应该叫传输,单方面的,类似于自来水厂的水从我的水龙头里流出来,我的嘴巴就含在龙头上,感受水流。
苹果的清新让我从遥视的奇妙体验中回过神来,旅途将继续。
“下德著村,到站的乘客请下车”并不是电子语音,云来的公交已经太旧,是司机提醒熟睡的乘客而大吼一声。
我下车就踩到了潮湿的泥巴,地上散落着橘子皮和被吮吸过的甘蔗,白桦林就在眼前了。类似于谢幕后的演员和导演,我此时感到不真实,伴随着虚无感。
细绵的秋雨现在抚摸着破碎的广告,关于治疗不孕不育、阳痿、梅毒。声称药到病除,我真希望这是真的,这样,也许秋雨的萧瑟会少一些。
白桦林在呻吟,或许是因为蜗牛陆陆续续钻进了土里,打扰到了树的根。相互的侵犯,我们和云来的关系也是如此,相互纠缠,相互混合,直到形成一种惊人的相互共生关系,但从更深层看,不论是蜗牛还是我对于树根和云来镇来说,更像是一种入侵。
一路上,我一边向过路的老奶奶和老爷爷询问张云来家具体的位置,一边寻找适合我的蜗牛的壳埋葬的地方,我更愿意将它埋在离我较远的下德著村。有些泥路不太好走,特别在雨的浸湿下,显得更加粘脚。
你就在前面了,你即将离开,因为冬天即将到来。天气预报说,今年将会难得地下雪,雪将掩埋一切,掩埋所有不理解,待到来年春天,你已不需要理解,你需要——新生活。
我敲响了你家的门,门上写着“期颐偕老”,这是多少年前的牌匾了,散发出老木头的气味,和你身上的木质香气互文。你打开了门,我又看见那头蜗牛形状的短发,你已然知道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
那就这样吧,我拿出了你曾给我推荐的恐怖漫画,我决定送给你。
“那你已然知道关于我们相遇的所有了。”
是的,我已然知道,要不是漫画的开头介绍过作者,我甚至怀疑作者是你,沃妞和沃仔,潮湿的雨季,蜗牛博物馆,遥视,冰河世纪,蜗牛和蛞蝓,此时的你像我最初认识的你一样,像一只巨大的蜗牛,将我压得喘不过气,当然,关于你在村子里的其他,并没有在漫画里出现,你说你就要离开,到时候你可以随意着装,没有一个人认识你。
你告诉我你曾经形成了这样一种生活:醒来,在紧张地收拾后疾步走进学校,坐在座位上,观察着清晨,有时你会观察太阳,一直到中午,太阳出现,吃饭,然后进入下一段观察,观察午后的微风,观察题目,观察同学。你说你无法参与其中,直到你发现了类似于蜗牛般同时拥有恋矢和生殖孔的愿望之后,你觉得生活真正开始起来,而不是依附于之前那些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事。
身边的人都带着不可思议的眼神,他们觉得这一切打破了他们的常规,他们鄙视、指责,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将无法理解他们本身的生活,无法再继续装瞎,仿佛这才是他们的生活核心,盲着一直向前,直到这样黑暗的世界得到了其他人的追随。
有时,你说生活需要蜘蛛,蜗牛掉落到蜘蛛网的陷阱之中,开始回忆起一切,忽然觉得记忆的沉重,它们忽然觉察起很多更重要的事,而他们的死居然如同一件稀松平常的普通事。没关系,他们的胶状会逐渐被吞噬、蒸发,而壳会留下来,这就是蜗牛与蛞蝓的区别。漫画的结局也会发生的,你说,洪水将导致成千上万的蜘蛛爬向更高的地方,它们也存在自救,蛛网连接在一起,可能会包裹整一片秋天。云来镇近来也有暴雨预警,白桦林将变成真正的蛛网吗?我们看见,远处一小群蜘蛛正在朝我们这个方向跑来,我打开背包,将我的蜗牛安葬于此,应该说——蜗牛壳。
责编:周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