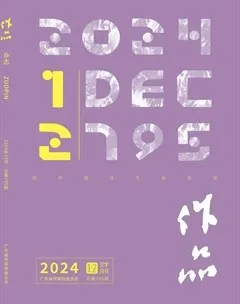挑到天上去(短篇小说)
1
戊寅年春天,我变成“挑二哥”,从长江边的云安小镇出发,挑盐前往湖北利川。为节省时间,没走东门,而是选择一些比较直截的街巷大路(名字叫“大路”,其实只有三四尺宽,除去右边铺一行石板,其余全是土)。这时,路上只剩一些脖颈处摇晃大铃铛、驮米口袋、被人吆喝进出城的老黄牛。
横行述先桥,坐渡船过江,翻过赶场坝最后一座石板桥,越过一道深谷,接着则是沿鱼背河一条三里上下相当险绝的陡石梯。可以看见岳父岳母的老屋子。它也睁着鱼儿眼睛看我。鱼背村在我眼前散开去。
快到“水寨”处,迎头碰见一队车马行伍。他们一歇下来,有的找祠堂、茶铺、酒栈的板凳安坐屁股,有的牵几匹光背瘦马到河中饮水。对他们来说,目的地滨江小城“云安”已近在咫尺。我与之擦肩,从头到脚蒙一层尘土。
而后遇到一个头发蓬乱的家伙。我们相互连正脸都没瞧一眼,在我看来他太危险,而他觉得我太困惑,这就好像两国勇士狭路相逢,在他眼里确实透露出恶意,他与你同样有妻儿,同样心里祷告,所以同样紧握腰带上的匕首。所幸的是,我和眼前这个家伙最终井水不犯河水。
月光被身后遥远的月亮地挡住,又一小列队伍急急忙忙从身边走过。除了靠沉重脚步和喘息声打招呼,我们彼此都没有过多交谈。
我挑扁担,提橘灯,沿流水淙淙的溪壑转了几转。石梯路越朝上趋,丘壑越觉深邃。君不见砍不完、锄不尽的杂草灌木!把汗湿我牛衣的盐巴卸下,我独自坐在鱼背山顶。此刻,云安已被万千山岭吞进深腹。
2
万物沾满露水。我继续朝川楚夜空出发。经过长久煎熬与疾驰,就像一头苟延残喘的老麋鹿,汗水直流,四肢虚软,随时躺下来休息,置天为床。夜空中无数星星在头顶扩散至整个荒野,就像碎乱的珠玉,构成富丽广博、光焰万丈的宇宙。面对这一切,我边前行边奉献我所有高歌、半吊子歌、半吊子调和长途跋涉时的呼唤与长啸,仿佛万物能听见我,理解我,包容我,融化我。
现在我脚边谷壑开阔。谷底江水流淌,如同一柄发光的长剑。山坡披戴的暗云,半遮半掩遥远山脚的村镇与树丛。注意听,深谷中还传来枪声。那土地上,有端坐于马背的士兵,追命的枪声惊扰江河,连射声、点射声、爆炸声……
“吃得,饿得,走得,做得,挨冷得,挨热得,这是云安人的口号。”大哥说。
思绪如同陨落的星辰,在漫无边际地潜游。想象中,看见这个世界的中央:在我家那座土房黑暗的角落,那里,藏有父亲的烟卷、母亲的鞋垫……我相信那小小角落支起的永恒,我知道这大地,这街道,这地面,这江水和生命的影子都神圣。
随后便是不见人户的行走。满冈乱石如群羊。
终于,一个村落从天而降。停下脚步,扒着门缝张望,进到一户点“瓜瓜花”般灯焰的人家去要点吃的。屋里有一对老夫妻,孤苦伶仃,以放牛羊为生。两个老人欢迎我,给我麦子饼和粥,讲他们儿子被送到遥远的上海打仗,又靠近炉火念《四十二章经》,还想让我也念。然而,我不习惯念经,于是当两位老人闭眼祈祷,我轻轻推开柴门走了。
深夜,我睡到村外一个麦垛里,闭上疲惫不堪的眼睛。
我居然梦见自己在闪烁的灯火中沿黄州第二大道行走。路过一些茶楼,成群男人全都手举酒碗,抬头辨听远方枪炮之声。男孩们在马路上玩耍,撞到我身上,我缩肩膀,挑着重重的盐巴,继续前行,表现得很坚强——去哪里?前方的终极灯火是什么?
3
“小弟娃,路不好走哦!”清晨醒来,刚跋涉不久,就转身看见一个人边吆喝时甩尾、垂涎、负担老盐的黑骡子,边用树枝指着脚底盐水溪的丝线。
“要挑到‘天上’去!”他一挥手便说。
路到底有多不好走?我紧紧抓住一根老藤,给他和他的战马让路,任由石块跌落谷底。他呢,也不管我爱不爱听故事,竟自作主张摆起经来:
“据说唐代,从鱼背村到‘天上’就‘滩石险恶,难于沿溯’。一位名为翟乾佑的天师,痛心百姓运盐劳苦,作法将管辖沿途险山的十五条龙全部召来,命令它们将险山变为平路。一夜之间,十五里险山有十四处化为平地,只有一处依然如故。又过了三天,一条龙化作一位娉婷的女子出现在翟乾佑面前。她对翟乾佑说:‘我之所以不把险山变为平地,是想帮您救济众生!您知道,云安一带的穷苦百姓都靠挑担运盐维生,如果险滩变平,船可以通行,这些穷人没活干,会饿死冻死的!’听了这番话,翟乾佑恍悟。他再次下令,将沿途险山恢复原状……”
“看到没?”他继续自顾自说,“对门那座山就是‘天上’。”
他把树枝当鞭子,将云安喻为“川盐济楚”的生命线。说战争期间,“川盐济楚”有两条路:其一从云安入江,到湖北由陆路转运至鄂西南及湘西一带;其二沿江下行至湖北香溪,转陆路运到鄂西北。云安是两条线的起点,也是川东地区的盐业重镇。日军正是发现这一点,才数次对云安进行空袭,企图切断盐脉源头。
“轰炸一过,爬得动的,又跑回来继续干活。”
我听着,气喘吁吁。没想到这位骡子匠、这位摆经先生已赶着他的骡马远远消失于半空。
我面朝“天上”,鼓起眼睛寻找,但一仰头,头上的草帽都掉了。
4
山中传来吟吟声。我开始以为是虫鸣,捡几块石头四处扔扔,也没发现有虫子栖身。这声音缓缓吟唱,像在空中,不可捉摸。细听,如同许多人的和音,总缭绕我。等我歇气,就又没了。我挑扁担将背中的盐巴分担,它又重现在耳边。我恐怕是耳鸣,索性走快些。半夜时分,远近寂寞幽谷空无人影,莫非它源于我的恐惧心理?
这一种难以追随的曲调,听不清唱词,却觉得熟悉。我决定转过眼前山弯去看看。四面峻岭清静,只有山中风涛,再就是偶尔一处溪涧哗哗。溪边有个临时竹棚。竹棚外哪儿会有人?吟唱声不知不觉消失了。
我继续爬行,听见它又吟唱起来,像大悲痛之后趋于平静却无法抑止的忧愁,随风流淌。
“虽然是山高水远,平步中九曲回肠。二更天灰阁孤光,猛抬头破屋半间残墙……”
刚听清两句歌词,却什么声音也没有了,沉寂得令人恐惧。可多少有点快意,终于证悟这并非我自己由于恐惧而生出的心病。
歌者只在此山中。
果真是个手拿火把的瘦男子在唱!我发现时,他已闭口,正蹲在溪边啜饮溪水。串串回音仿佛与他毫不相关,还在悬崖间传播,还在满世界寻找寂寞之耳。
“小兄弟,”他也发现了我,“这盐水溪是不是要流进下面的鱼背河?”
“你怎么知道?”
“我尝出来的。”
他告诉我他叫狄牙,挑满满两木箱宝贝:瓜,果,草鞋,男人的强盗烟,女人的雪花膏,洋火,菜刀,手链,西洋镜……要什么有什么。只要能碰到人户,就找机会兜售,已经行走四方多年。于那些大宅第,他就像一只点缀荒凉的候鸟,一年不只来一次。
没想到在这样的荒野还能碰到同伴。山夫只见压樵担,岂知带酒飘歌儿?
于是,他挑黄木箱子,在前面带路,我帮他拿照明火把。我们结伴行走在幽谷。
5
夜来过岭忽闻雨,今日满溪都是花。再次醒来,从树枝间望见零散天空,亮得有些刺眼。又是自由晴朗的一天,鸟儿在歌唱。我满心欢喜,恍惚看到古老巴国祖先蹲坐在蓝色天空棕色山峦柔软土地边。狄牙已经站到我身旁,卷起叶子烟,像一只高大烟囱吐纳炊火。
“继续走吧,青光白天了。”他说。
这是一个属于艰难苦恨幻觉的白昼。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
从溪边过,从洞边过,从茅屋边过。路上所见,全是一种荒凉情形。草堆旁忽然一朵红花。斜坡上忽然满是马桑果、地果。老僧已死去,只见耸立的新筑佛塔。两条爬行的蛇。一只伏在路旁见人来便惊讶飞去的野鸡。半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三座清代石桥,名为“无夺”“无伐”“无暴”。一堆白骨。一群乌鸦。
在长长弯弯的山路间行走,原不能有所恐惧:横尸倒地的流浪汉,执刀拦道的贼,有毒的花草,乘人不备袭人的猛犬,盘踞山洞中的豹子猫,全不缺少。这些东西似乎无时不与过路人为难。
天佑我们在一切灾难中沿大路走去。这时节我们正过一条小溪,两岸极高。溪上一条独木桥,行人通过时便吱吱呀呀作声,山腰有猴子叫唤。水流涓涓。远处山雀飞起肃肃振翅的声音仿佛也能听见。
溪边有座灵风庙,石像上悬挂红布,庙前石条过路人可以歇气。槛外双瀑泻石涧,跳珠溅玉,冷入人骨。
我们还要穿过一片旷远的山中空地。四处可以看到一丛丛马桑、黄荆条、蓍茅草、飞廉,它们细长的枝茎挺立山坡,野花野草被斜阳照得亮闪闪,在虚化中增大轮廓,仿佛军队为巡逻在原野上设置的哨兵。
山坡陡峭,出现一座座狭长的白色楼房。
“看见山顶老寨子了吗?”狄牙提起扁担,轻轻拨开云雾,指着远方告诉我,“那就是清水土家村。他们下面有条石笋河,河边有口龙缸。”
从那个方向传来数声枪响,一声接一声,四周山崖引起无数回音。
“会不会是游击队?”我问。
“那是猎人打猎呢。”狄牙说。
夜色迷闷,听到有村人警告,不要击打更鼓,说庙后山中多虎,闻鼓则出。我们又误入幽谷,狼奔鸱叫,竖毛寒心……
“山男”“天狗”“天邪鬼”幽谷响……“穷奇”来回旋转飞舞,把树梢、树枝、树叶刮得连轴转……旋风最里面的“穷奇”,生有两把镰刀模样的羽翅……
我们继续上路,仿佛与先辈同行。果然手持火把,承担咸涩,翻山过河。道路崎岖幽深,而月亮底下大山深处,再无任何顾虑。
狄牙一路唱歌,歌声传得深远,逝去的亲人们都能听见:
【杏花天】虽然是山高水远,平步中九曲回肠。二更天灰阁孤光,猛抬头破屋半间残墙。
吾闻壮夫重心骨,古人三走夜路孤。隙月斜斜刮露寒,一枝难稳又惊乌……
这样的歌要在山里唱,月下听。唱到最后不知是谁在唱,谁在听。听到最后只有你在唱,我在听。
故人与影子,真实与亡魂,合为一体,在前面引路,这样的路再远也很近,再难也容易。而走着走着,烟云袅袅,雾气随远处龙缸、悬崖底下暗河缓缓升腾。
6
无涯无际的神秘山脉正不动声色,召唤四方客们到它谜一般的深谷幽壑里去。狄牙和我不由自主听从这种召唤。没刻意选择道路,又走整整一天,又走整整一夜……走到不知道已走了多少天,不知道已走了多少夜。星星透过松树树冠,仅仅为我们两人照亮。世间一切都沉沉酣睡。
狄牙说,随便沿哪一条路走,你都会被引往某个溪谷,站到一条溪流的深潭边。
破晓前,我们果真重逢弯曲的盐水溪。它笼罩在浓雾里。拨开云雾,如同直上青天向五老招手。手捧溪水洗双眼,回看群山万朵玉芙蓉。
我们在岸边生起篝火,坐在一旁,久久默听盐水流过时遥远的岁月回音,以及后来猿猴响起的哀愁啼哭。我们一声不吭抽烟,直到东方吐出一抹异常柔媚的淡红色朝霞。
“就这样坐他两千年多好啊!”狄牙说,“把小锅儿拿出来,我们煮茶喝。”
雾从峡谷峭壁奔涌而出,席卷一切,遮住太阳。天凉下来,甚至耳边不远处盐水溪也像山顶上的雾一样凄迷。在惹人生畏、狭窄泥泞的峡谷道路上移动,死亡或龙或所有神秘之物,都在下面的深渊凝视我们。狄牙边奋力寻路,边传授经验:
“走山路,兄弟,莫慌,那些路不会动,动的是你。”
随之而来的则是狄牙极其认真、严肃,俯身向深渊跪拜。他投一块肉下去,云海慢慢翻卷。前方衍出好多可攀手攀脚之野藤。
“只要你够虔诚,此地的龙就会为你摆一摆尾。”
我们终于从云海平面冒出头。我们折回山腰,取道一座山的顶端。我踩到一块松动的磨刀石,于是就开始和这块大石头一起顺一处岩脊滚下山坡,没想到引起山崩、垮崖,石头朝我底下可怜的狄牙砸去,雷鸣般从他头顶越过。我俩几乎丢了性命。我夹紧双腿肌肉控制继续向下滚动,就在高崖边缘抱住一棵马桑树止住滑落,狄牙也在一口倾斜的山洞里躲住坠石。此后,我俩为取回行囊、盐巴、扁担,好几次侥幸脱险。这绝对是生死关头。然而我们成功了,顺利抵达安全的大垭口。
它以几条弯曲岔路、一场猛雨、一座孤单山门寺、一盆免费“巴人茶”的见面礼,拥抱并且接纳了我们。有诗为证:
山门寺外逢猛雨,林黑天高雨脚长。
水去云来归梦远,应寻此路是潇湘。
7
庙里住有两位出家人。虚幻的孤独山路在寺院变得真实具体,具体到一根弦——于兰法师在晚课敲响木鱼,木鱼声微弱、纤细,却甩尾摆脱千军万马,震撼两颗脆弱而又茫然的心灵。就餐时,他微笑着告诉我们,自己是高阳人,十五岁就出家了。他提供给我们的肴膳,多是诸花,而香气达于内外。庭中有玉树一株,围可合抱。于兰法师常在树下打坐。花开满树,状类古玉。每一瓣落,锵然作响。捡起来看,如赤瑙雕镂,光明可爱。不时有异鸟飞上枝头鸣叫,毛金碧色,尾长于身,声等哀殊,感人肺腑……
晚上我们同睡一间僧房。法师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独自在床上参禅。虽然我也见过云安一些法师拿禅师棒尖声叫喊的形象,但还是觉得这位于兰法师器识更沉秀,内心更安然。
要睡觉时,狄牙问:“法师,寒雨如此,怎么过夜?”
“睡吧,不要忧心。”
我们就寝。隐隐中只见于兰法师从怀里掏出三角碎瓦数片,在灯上烧。随后就烧旺了,满室皆暖。夜里半睡半醒,雨早已停歇,也不知是做梦呢,还是现实中发生的事,一只白虎从窗外月光下的青青菜园跳进屋来。我和狄牙吓得魂飞魄散。但它只是蹲在于兰法师床前。法师纹丝不动,仅仅用手轻抚虎头,老虎便俯首帖耳。俄而,这只大虫就离去了……
另一位于护法师则年轻得多,看起来像是于兰法师的徒弟,一晚上都不见踪影,第二天清晨才又突然出现。大垭口有一股清涧,路过之人都靠它洗漱。早上有个货担郎把水弄脏,水立刻干涸,不久就绝流。于护法师站在泉水边徘徊,连连叹息:
“如果你枯竭,我们该何去何从?”
说完清流就又重新洋溢,泉水也源源不断。他打一大盆甘冽清泉,我实在憋不住,想去求证,却被他递送的新鲜香醇“巴人茶”堵住喉咙。只有“咕咚咕咚”啜饮声以及泉水珣珣声以及鸟儿啁啾声以及路人谈笑声以及两位法师木鱼声回荡。
清亮阳光开始照耀山门。狄牙对像影子一样站在晨曦中的于护法师说,我们要去利川。小法师听后大吃一惊,紧紧盯住身材瘦弱的我,似乎要把我从外到里看个透心亮。最后,狄牙轻手轻脚放下两把牙刷、一盒葵花种,我则留下一包盐走出山门寺。
8
在川楚边界的高山地带赶路,你会发现岔路增多。遇到好些朋友,我们不知不觉会聚,组成一支小小队伍。这是一支奇怪的队伍,有破衣烂衫沉默者,有挑箩背筐健谈者,有跛脚外地人,有持刀流浪汉,有行色匆匆的本地人,有提酒壶的老顽童,有拖儿带口的移民,有和我一样背盐的少壮,当然更多的,是像狄牙那样四海为家此路穷的货担郎。
“爬过前头那个坎坎,就是野人洞。”一位吆骡子的大姐说着话,就上了我的前。
我还记得自己边走边琢磨:时间与骡马并肩前行,从骡马疲倦而忧郁的眼睛,就知道时间已有多老……
我双手抓住扁担头,给大姐和骡子腾路。她的老伙伴背驮雪白瓷碗,露出布袋的部分在阳光下时时闪光。顺她惊恐眼神望远去,我意识到我们已沿龙缸狭路,快要爬到齐跃村土司山野人洞。
“冉广竹歹得很噢!”队伍里有人回应。
不知不觉,人们和牲畜开始放慢脚步,就好像缓缓降下来的风势。
“野人洞阴风极盛,一个人不敢经过。大家跟紧点,要相互照应。”
队伍行进速度逐渐变慢。所有眼睛熟悉流浪的岁月。七曜山顶峰近在咫尺。它赫然耸立,荒凉而孤寂,呈现出蜀道的原始威慑力。这位古老巨人在它那突出的云雾国度里板着脸孔。
川楚孔道必经之路——野人洞——就像所有蜀道长蛇的七寸。我们时时感到毛骨悚然。我们知道,人们攀爬过的许多树丛之后,都可能埋伏着三五个棒老二。他们食量大如虎,一头牛的脊背肉,一顿就吃光。据说前天夜里,蜷缩的野蛮人一颗子弹打穿一名醋商的草帽,中弹者照样继续前行。另外有人补充,上周另一个酒鬼,子弹打得浑身漏酒,嘴巴都烂了。
“真是恶魔!”
我们听到无数消息。从四方客的谈论中,我们慢慢拼接出,冉广竹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深心,他的双手,他的魂魄,都沾满鲜血。为逃脱被抓壮丁的命运,他把保长的头顶踩成飞机场,带人不断四处劫持“肥猪儿”,是个对任何伤害他、冒犯他、侮辱他、怠慢他的行为进行残酷报复的恶棍。
他把清水土家长得最好看、歌唱得最好听的女孩叶春雪抢去当压寨夫人。此前,他多次听人欢喜赞叹叶春雪美丽,命令村长让他开开眼。村长忘了村里当初曾有人掉包,替这个魔头引见其他女孩从而招来杀身之祸,居然满口答应。
村长在叶春雪家摆下宴席,第二天让她在席上露面。宾客人数不多,冉广竹坐在叶春雪旁边,见到她竟目瞪口呆,心想自己活这么大还没遇到这类笑弯秋月、羞晕朝霞的女孩,任何别人为把这样一个女人弄到手而干出无论如何背信弃义、卑鄙无耻的事来,也是情有可原。从清水回来,冉广竹已经迷恋她。第二天一早,他就领一帮人冲下老寨子,掳走叶春雪——吻她并讲江湖话,将她搂抱在怀。
冉广竹是棒老二中的棒老二,是棒老二的克星。他曾占领据说是最凶恶的某个大王的山头,焚毁附近村落,把全部山民驱赶到自己的领地,杀死武将,将对头关进笼子。军师前来议和,此大王过一个月才得以生还,鼻子、耳朵都被割掉。冉广竹吩咐这个不幸者,转告附近其他山大王,如果不立刻送来规定的银票、鸦片、枪支、牛羊肉,并亲自上前跪拜,他将用同样的方法处置他们。最后他亲手杀掉五个山大王,割掉他们的鼻子、耳朵,附上他的问候,送给利川文化馆长。
“眨眼间,”给我们讲这件事的人意味深长地说,“一群野狗已经在舔那五个大王流在地上的血了。”
整座七曜山郁郁葱葱,树木扶疏,浓荫密布,斑斑斓斓,宛若梦境。自打听说我们中曾有人遭到伏击,我始终对树木疑神疑鬼,仿佛每棵树后面都躺着一个死者。最后,众人在一个大石沟的转折处停住歇气。那里有一股小小清泉,被人称作“一碗水”,意思是无论春夏秋冬,里面永远都有一股和碗差不多大小的泉水流出。看着起泡、水肿的双手,我躺倒在崎岖山路,把衣服撩起来擦汗,没想到它已被盐水泡得轻轻一扯就烂作几条口子,于是我索性赤裸上身。狄牙看见了,从他的箩筐深处找到一件女人的红衣服让我换上。
“各位好啊!”不知从哪里冒出三个身材强壮的男人。其中两个高点的,嘴里含烟斗,另外一个矮点的,仰脸在喝长颈瓶里的酒,搞不清楚是纪念散伙还是庆贺欢聚。
还来不及看清这一伙人,他们已拿起身旁的武器,慌忙向我们冲来。
“你们大概找了很久?”他们说,“这里没有桥,没有船,也没有仙车,你们想凭空跨过野人洞,是不可能的。”
“棒老二的根子埋得很深,”有个家伙走到我身边,把穿女人衣服的我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仿佛我们终于露出真面目,犹如妖魔钻出魔瓶,他继续说道,“尽管官兵动用了铲子、铁锹挖他们的根,结果反而把自己的手弄破。”
“你们最起码,也应该——”另一个人指出,“带一两件防身的武器。看我们的行头:每人都有一把三个枪筒的火枪,腰杆里还别着手枪。——如果火枪哑了,手枪还能应急嘛。”
“我带着连鞘的匕首,还挺锋利。”第一个说话的家伙接着说,并从腰里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来,在手里摆弄。
“老三,把刀放回去。”第二个人说,“你看这位先生脸都吓黑了。他还小,见不惯这种凶险的武器。棒老二最容易从他们手中把钱抢走,今天遇到我们是他们的福气。明白吗?”他转脸向我,接着用眼神一一扫射我们十多个人,“把钱交给我们保管吧,大伙儿,这样才最安全。”
对话到此中断。我记得他刚说完“这样才最安全”,一切就都完了。只听到枪火声响。这种声响,没有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都受到震荡——我自己也成为枪火声响的一部分。
幸好枪声熄灭了。但声响久久停留在脑海,双臂和双腿筛子似的颤抖,好像背后有人摇动我。
9
最终我没有饮弹。
没有任何人饮弹,只是我们脚边的石头和泥土炸了一阵。等形势平息,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山崖边一队人马身上。可以望见他们戴着铁帽,可以分辨出普通士卒与当家的。
也可以望见旗帜在扭摆。最前面,是一对骑高头大马的男女,他们口含冰糖,眨眼间,已侧拉马身,转步回头,并肩离开。
先前被他们挡住的金色阳光重又出现,继续往我们肌肤里沉浸。由于背光,他们的印象,于我而言当然只能是剪影。
接着有若干提枪者冲到我们身边,将那三个家伙绑走,犹如绑走天神祭品。若不是高地下面的河谷可以听见心惊胆寒的三声枪响,我们定会长久站在原地比赛憋气。
我们面无表情,没有哪个会如此失魂落魄。
最后只剩下我们这十多个四方客。人群中开始从窃窃私语,变得口气缓和,再到热火朝天:这就是大伙儿说的棒老二头目?这就是人们争相传颂的那个“冉广竹”?另一位就是美女叶春雪?
此前谁也没见过那根旷世奇竹,只能猜测。我们和这群神秘人马之间,隔着一条神秘界限,这仿佛是一条分隔生者、死者的界限。所有人都察觉到了。可当越过这条界限,非但没有什么可怖,反而变得越发沸腾、越发活跃起来。
之后的路途,我们下意识已形成少壮自觉走前后,老人、女人、身体虚弱者走中间的情形。我们奔走,怀有野兔从狼犬群中逃离之感。
很快在荒野青山间攀援。我边爬,边回头环顾整片七曜山脉,觉得它不再可怕,就随口唱起:“虽然是山高水远,平步中九曲回肠。二更天灰阁孤光,猛抬头破屋半间残墙……”在狄牙这些伟大歌曲唱到最澎湃时穿过狭窄山路。
似乎幸运来得毫无缘由,只听狄牙大喊:
“大水井,大水井!”
所有人才回过神来。生命中的一切似乎重又变得美丽。我甚至开始畅想起这场惊心动魄的疯狂之旅,甚至走得更远,想起我所经历的所有疯狂之事。真是不可思议。
那位赶骡马运瓷碗的大姐,放声吆喝“歇气——歇气——”,并拿出自己的老酒庆祝。我们坐在山路边,一人轮流满满喝一口,还共享各自的食物。有人手指脚下远处轻雾笼罩的野人洞,笑道:
“怪不得那会儿感觉有人给我扇风,当时我屁眼儿都吓紧了。原来这就是阴风!”
“现在安全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挑炭老伯,他长吁短叹,同时递给我一块麦芽糖。
我仰面躺下,发现头顶伸展、覆盖着巨大桐树枝柯,浅紫色花朵缀满枝头,在我们这些流亡者看来,显得那么怪诞、虚幻、富丽、诡谲,令人艳羡。我缓缓起身,捧起瓷碗大姐的酒,学父亲那样,仰脑壳朝天喝。这一切都发生在宁静蓝鸟栖息的巨大古树下面。
太阳透过树叶的棋盘格子,往我们肩头抛下一片片闪光的小圈装饰,似金币在跳动……
世界刚刚苏醒过来了。接下来的时间,四方客们不停分路道别。
10
又只剩我和狄牙两人。白天我们走在荒野,没人看得见;到紫罗兰色夜晚,就徜徉在野性星宿的统驭下……冷风从旷野吹来。
利川要到了,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尽管拿火把,点松明,仔仔细细翻来覆去找,还是找不到“利川”。我们站在一棵枯树下抬头找路。前面的路曲曲折折,好像通往古老楚国。我们决心往回走,放弃利川。道路似乎永远延伸。
四下里漆黑,回头爬五里,终于看到远方一片微明中出现房屋轮廓。是一座门口悬挂五个大灯笼的院子。
我和狄牙取下流浪汉专属的两块手表——一只太阳,一只月亮——准备露宿荒丘。
但我还是选择厚着脸皮去敲门。
门当然没开。门后一个声音传来。
“哪个?”
“我是云安的,挑盐到利川。他是个货担郎。”
“有啥事?”门后声音继续甩出。
“您好,打搅,可不可以借宿……?”
“借不到!”重得像落石。
我被这些话砸得不轻,打算拉走狄牙。
但见这个家伙按兵不动,向我眨眨眼。只听他故意漫不经心、煞有介事,大声嘟囔。
“兄弟呀……”他在门口细细摆开扁担,动作仿若在整理床铺,“看来今晚,我们只能在这根扁担上睡了……”
刚把我们拒之门外的大户人家果然好奇。对方半开门,想看看我们如何表演这一幕:一根扁担怎么睡两个人?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们就已钻进屋内消失不见,如同两条扎进泥土最深处的黑泥鳅……
11
我是太阳出来一枝花,
说句真言谢主家。
男的收拾包袱衣裳,
女的收拾针头线麻。
我是一步就跳上马。
……直到卧榻远去消失不见,次日清晨,我们才放声大笑。也正是在这些痛快笑声中,我们抵达柏杨。口渴难耐。
再次敲门。一个女子端出清水来。我们喉结嚅动。交还她白净瓷碗,交还得那样缓慢,仿佛整个下午都在这时间内流逝。
我和狄牙继续拖细长身影一步一步踏上渺茫路途,徒留女子及她的家在远远疏林中隐没。
12
利川终于到了。没有大伙儿眉飞色舞谈论的那般神奇,也没有那些故事中提到的那般恐怖。这只是一个交付盐巴的小城,也只是一个意味着离别的驿站。
许多人站在驿站送别亲友,四周都是告别的歌。树摇摆,唱万千沙沙之歌。我把我的地址誊写给狄牙,他从脖子里取出一块玉递给我:
“留个念想。”
我实在拿不出什么,就把我的扁担送给他。我们已分开行李。
“冷吗?”最后我问。
“风冷。”他望风捕影。
我看见他挑担子转身离去前,眼中一层薄雾。他看见我眼中困惑的晨霭与群山。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