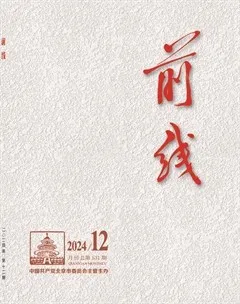森森戍堡 烟火人家
202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镇石峡村乡亲们的回信中,肯定了他们自发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并依托长城资源走上了致富之路的做法。石峡村是长城孕育众多村镇中的代表。作为屯兵城池和指挥中枢,长城沿线的军事城堡扼守山川要隘,肩负着守卫家园的使命。当长城军事作用弱化之后,原先军事色彩鲜明的戍堡逐渐演变为充满烟火气息的村镇。新时代,有更多如石峡村一样矗立在长城脚下的村镇,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千年古镇古北口
“南控幽燕,北捍朔漠”,古北口镇位于古北口长城关口处,自古就是华北平原通往东北平原和内蒙古的交通要冲,素有“燕京门户”“京师锁钥”之称。唐代因其位于幽州(今北京)之北,得名“北口”。五代以后称“古北口”或“虎北口”。宋代“澶渊之盟”后,古北口驿路是宋辽使者往来必经之路。金元时期北京成为国家都城,古北口军事地位更加突出。在金代迁都北京时,古北口等关隘的屏障作用成为北京作为国家都城的一大有利因素,“山峻相连,近在都畿,易于据守,形势雄伟”。
明代迁都北京后,古北口成为一处雄关险隘。古北口城“南控大石岭,西界潮河川,为古北要冲地”,古北口路参将驻扎此城。清代古北口是连接北京与承德避暑山庄的咽喉,康熙、乾隆等皇帝多次途经古北口。直到近现代,古北口仍然发挥着屏障北京的作用。1933年的长城抗战,古b0fd96f8cdd644c5f2fb8cf870eb6ff9dc1ecf8583bdc8a491e1dacb8ee5a291北口之战为“激战中之激战”,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广大爱国将士,同仇敌忾,血洒长城,其忠烈精神已与古北口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
战争年代,古北口烽火连天;和平时期,由于古北口连接南北的交通优势,这里成为中原与塞外物资集散中心。南方的丝绸、布匹、茶叶、瓷器,塞外的牲畜、皮毛、药材等在此汇集。辽代辽圣宗统和四年(公元986年),驻古北口官吏曾违反朝廷税法,滥征商旅,受到处罚。清末民初时,古北口已有多条大街,商铺数十家,是名副其实的商贾云集之地。
作为长城文化带上的千年古镇,古北口镇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人文景观与历史古迹。当地流传谚语“古北口三宗宝,七郎坟、令公庙,琉璃影壁靠大道;一步三眼井,两步三座庙”。杨令公庙、财神庙、药王庙、古御道等古迹俯拾即是。尤其杨令公庙始建于辽代,是辽王朝为纪念宋朝名将杨业而建立的祠庙,代表着中华民族对忠义精神的公共认同。千年历史长河中,无数先贤圣哲、达官显贵、豪杰志士、文人墨客曾在古北口驻足,使这座军事重镇在豪迈之中亦显儒雅之气。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北宋使者刘敞出使契丹时取道古北口,拜谒杨令公庙,留诗缅怀:“西流不返日滔滔,陇上犹歌七尺刀。恸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两鸿毛。”清朝,康熙皇帝赋诗:“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时平不用夸形胜,云物秋澄斥堠闲。”描述了古北口雄关险峻奇绝、林壑清幽之景。
进入新时代,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生态修复、乡村振兴等工作的开展,千年古镇古北口面貌一新。长城脚下的纪念地、民俗村等,与长城本体串联起一条“古北口红色探访路线”。人们在红色旅游中,回望历史、铭记先辈,体验当地丰富的长城精神与文化资源。历史悠久的长城文化,源源不断地为古镇提供了新活力。
固若金汤永宁城
永宁古城位于延庆东部,属今延庆区永宁镇。在明长城防御体系中,它是塞外至八达岭长城“层层设防”的重要环节,扼守宣府、延庆、四海要路,与延庆城一东一西,遥相呼应,对于保障京师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永乐皇帝北巡,驻跸在今永宁城西北15里的团山,发现这里“厥土旷沃,群山环峙”,于是“迁民以实地,命官以莅民”,在西部设置了隆庆州(今延庆区),在东部设置永宁县(今延庆区旧县镇团山村),次年又设置永宁卫,驻扎军队。“永宁”之名,取自《尚书》“其宁惟永”,寄托着对于永远和平安宁的美好向往。
永乐以后,随着天寿山皇陵的营建,明王朝认为“祀莫重于陵寝,戎莫重于畿辅”,将陵寝安全与国都安全看作是同等重要的国之大事。为加强皇陵防御,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阳武侯薛禄统兵在天寿山以北修筑城池,将永宁县、永宁卫由团山迁移至此,同时将原本驻扎居庸关的隆庆左卫也迁了过来,以增强防御力量。这一新修筑的永宁城肩负着保卫皇家陵寝、屏障京师安全的职责,“为陵京肩背,至要害也”。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永宁城设参将署,成为明代延庆东部地区最高军事指挥中心。
阳武侯薛禄所筑永宁城,周长六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辟四门——东曰迎晖门,西曰镇宁门,南曰宣恩门,北曰威远门,4座城门都建有瓮城。城内布局严密,城中央建巍峨高耸的玉皇阁。登临其上,可以俯视整座城池,瞭望城池四周。玉皇阁东西两侧并排建有钟楼和鼓楼,以阁为中心向外辐射形成4条大街,东曰善政、西曰广武、南曰阜民、北曰拱辰,街口均建有牌坊。大街尽头与环城马道相交,以大街为中心,鱼骨状分布着三十余条胡同。这些胡同名称也有着鲜明的军事色彩,如左卫胡同是因为隆庆左卫治所在此得名;卫后巷是因位于永宁卫北边得名;仓胡同、北东仓胡同、南东仓胡同皆因存放军粮、牧草而得名。
永宁城自建城始,既是军城,也是延庆东部地区文化中心、商贾集聚之所。明嘉靖《隆庆志》载:“四牌楼一月六集,三八日为市。”即一个月有六个集日,每逢农历三、八日是集市。入清以后,永宁的军事防御地位逐步下降,军事和行政管理机构逐步裁撤,军事、政治中心色彩淡化,文化和经济中心地位更加凸显。道光年间,胡先达等永宁士绅捐田集资,创办缙山书院,周边地区寒门子弟免费读书,以育人才。缙山书院大门两旁对联——“开卷攻书解惑释疑有劳夫子;学成报国承前启后还望后生”,蕴含着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学成报国的期望。
近年来,永宁依托古城独特的古韵风貌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探索古城治理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引入文艺演出、非遗展示、文创产品研发等,现代潮流与传统烟火气息互为补充与支撑,将古城底蕴与文旅发展紧密结合,古城焕发出内外兼修的崭新活力。
古村新颜石峡峪
石峡村位于今延庆区八达岭镇西南,是由明代石峡峪堡发展演变而来的古村落。石峡峪位于居庸关西北,其山间小路可容骑兵通过,从而绕过八达岭长城。因此在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中,石峡峪一带有着较高军事价值,不少长城段落是属“极冲”或“冲”的军事要地。
石峡村所在的石峡峪堡,是明代石峡峪一带长城防守的枢纽。根据《四镇三关志》记载,石峡峪下辖“糜子峪口等隘口三处,边城一十六里”。石峡峪堡建于明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距今已有440余年的历史。有南北两门,北门门额为“石峡峪堡”,南门门额为“迎旭”。城墙原本高大坚固,内墙黄土夯筑,外墙青砖包砌。现存南城门城垛拐角及西侧十余米长、两三米高的堡墙。最高军事长官为石峡峪守备,并在城堡内建有石峡峪守备府。作为京师西北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环节,在石峡峪一带流传着李自成闯关的故事。传说李自成进攻北京,打到八达岭,苦战多天,久攻不下。当地老者献计绕开八达岭而取山间小道,直至石峡关。守将唐英中计离关,李自成乘隙攻破石峡关长城,然后奔袭居庸关,又从背后攻破八达岭,由此大明皇都的北大门陷落。石峡关长城因而被传为“闯王破关处”。这个故事虽然与《明史纪事本末》记载的李自成取道柳沟破关有所出入,却在一代代人的讲述和《三疑记》等戏曲的演绎中流传,成为长城脚下民众有关长城历史的集体记忆。入清以后,由于石峡峪重要的军事价值,清政府仍然派兵驻防。乾隆年间编纂的《延庆卫志略》记载:“石峡峪在(居庸)关西山内,设百总一名,带兵巡防。”不过从这一记载也可看出,此时石峡峪军事地位已经下降,最高军事长官降为了百总。石峡峪堡作为军事堡垒的色彩逐渐淡去。
近年来,石峡村依托长城资源,打造精品民宿、发展休闲农业,摸索出一条乡村文旅发展新路径。因长城而建,因长城而兴,被群山环绕的静谧古村正生机勃勃地走进新时代。
长城沿线大量古村古镇,积淀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古北口、永宁镇、石峡村的发展,是长城脚下传统聚落发展的代表。长城保护为沿线古村古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多元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新图景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如何依托长城沿线山水与雄关的特色,在守护长城、传承长城文化的同时,通过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实现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还需要不断探索、持续推进。
(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北京老城地名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与保护应用研究”〈项目编号:21DTR04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洪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 金蕾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