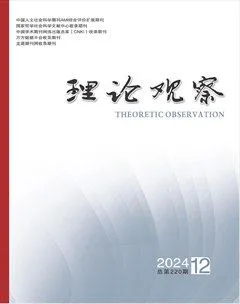论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及其测量
摘 要:多词单位是语言的基本构筑材料之一,母语者的语言知识很大程度上亦由各类多词单位的主动和被动知识构成。因此,二语学习者有必要掌握大量的二语多词单位知识,尤其是二语多词单位的隐性知识,以达到在语言交际中灵活运用的目的。有鉴于此,二语多词单位的习得与测量理应成为二语习得与外语教学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对影响二语多词单位习得的诸多因素进行简要分析,并结合相关研究阐述了学界用以测量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的实验范式(如眼动跟踪、自定步速阅读、启动范式),以期引起研究者和语言教师对这一领域的进一步关注与重视,推动相关研究的不断细化与深入。
关键词: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眼动跟踪;自定步速阅读;启动范式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12 — 0126 — 05
一、引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使用很大程度上是程式化的(formulaic),其中存在大量长度不等、结构各异、功能不同的多词单位(multi-word units)[1]。早在1925年,英国语言学家Harold E. Palmer就已注意到多词单位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多词单位是构成语言的基本单位之一,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掌握多词单位不仅有助于扩大词汇量,还能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利性。近些年来,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外语教学领域均开展了对母语和二语中多词单位的研究[1]。学者们一致认为,一个人的母语知识很大程度上由多词单位的主动和被动知识所构成。由此,二语学习者若要达到或接近本族语者的语言水平,就需要掌握大量的二语多词单位知识。本文对二语多词单位习得的影响因素进行简要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研究,阐述了几种有助于对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进行测量的实验范式,以期进一步引起学界对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研究的关注与重视,推动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习得与测量研究的深入发展。
二、二语显性与隐性知识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语言知识分为显性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隐性知识(implicit knowledge)两类。二者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热点,也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外语教学工作者颇感兴趣的问题[2]。显性知识指的是人们能意识到且能表达出来的规则知识,而隐性知识是指人们能使用但表达不出来的知识[3]。
上世纪80年代,显性-隐性知识的接口问题开始成为二语语法教学研究争论的焦点之一。无接口说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接口,习得的知识体系是学习者在实时交际情况下使用的唯一的语言知识来源,而学得的知识体系则主要起到监控所习得的语言知识输出的作用。弱接口说和动态接口假说则更贴近教学实践,认为显性和隐性知识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接口,但这种接口是动态的、变化的,取决于具体的学习情境和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在二语语法教学中,显性和隐性教学均有其优势和局限。显性教学注重语法规则的讲解和练习,有助于学习者掌握语法规则,但可能忽视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境和语感的培养。隐性教学则强调通过实际语言使用来培养语感和直觉,有助于学习者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下习得语言,但可能难以保证学习者对语法规则的准确掌握。因此,如何平衡显性和隐性教学,有效促进显性和隐性知识之间的转化和融合,成为了二语语法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学界趋于一致的观点认为,发展隐性知识是语言学习的终极目标。由此,只有当某种教学方法能够产生隐性知识或至少有助于隐性知识的习得时,这样的教学方法才有实际应用与推广的价值。
目前来看,在二语多词单位(如搭配、短语/词组、半固定表达、习语等)的教学和学习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显性知识的习得,即通过课堂教学、规则讲解和刻意练习等方式获得的、学习者能够明确意识到的语言知识。相比之下,对隐性知识的发展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将显性与隐性知识的发展路径进行比较的研究更是稀少。这可能是因为显性知识具有明确的规则和结构,更容易被测量、量化和教授。而隐性知识则更加复杂和抽象,它来自于学习者的个人经验和直觉,难以被直接观察和测量。然而,隐性知识在二语多词单位的学习中同样重要。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加自然地理解和运用语言,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流利性。因此,对隐性知识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与显性知识的发展进行比较,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二语多词单位的学习过程,为教学实践提供更有效的指导。由此,开展对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的系统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二语多词单位习得的影响因素
二语多词单位的习得富有挑战性,有若干因素影响着学习者对二语多词单位的习得。首先是母语迁移(L1 transfer)的影响。母语迁移是指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受到母语知识和经验的影响。当母语与二语中的多词单位在结构、意义或用法上相似时,就会产生正迁移,有助于二语多词单位的习得;而当二者存在差异时,就会产生负迁移,干扰二语多词单位的习得。例如,Wolter和Gyllstad的一项研究发现,相较于非搭配(non-collocation)和两者语言中不一致的搭配(incongruent collocation)来说,高水平二语学习者对于一致搭配的可接受性判断速度更快[4]。
其次是语言输入(language input)的影响。语言输入的频率和丰富性对二语多词单位的习得具有重要影响。有些研究也验证了频率对于多词单位习得的重要性。例如,Durrant和Schmitt通过一项限时命名任务(timed naming task)发现,在句子语境中对二语形-名搭配的多次接触要比单次接触时,被试的线索回忆(cued recall)表现更好[5]。对阅读过程中多词单位的视觉加工研究也发现了此类频率效应(frequency effect)。例如,Siyanova-Chanturia等人的研究发现,与二项式短语(binominal phrase)的倒置形式(reversed form,如*groom and bride)相比,本族语和非本族语被试对二项式短语(如bride and groom)的阅读存在加工优势[6]。
第三是知觉突显性(perceptual salience)的影响。不同于口头语篇,在书面语篇中多词单位缺乏知觉突显性。换言之,在书面文本中,多词单位不具有明确的形式标记(formal markers),且有些多词单位形式上不连续(如not so...as...),这就增加了学习者对多词单位进行识别、加工与习得的难度。因此,学习者经常注意不到语篇中出现的多词单位,转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单词的识别和加工上。例如,Bishop在一项涉及二语阅读者的研究中发现,学习者往往注意不到语篇中的多词单位[7]。根据Schmidt的“注意假说”(Noticing Hypothesis),不被学习者注意到的信息就不可能从“输入”(input)转化为“吸收”(intake)而被学习者习得[8]。
第四是教学方法的影响。教学方法的选择对多词单位的习得有重要影响。例如,任务型教学法可以促使学习者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运用多词单位,而基于语料库的教学方法则可以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多词单位示例和用法。Boers和Lindstromberg将程式语(即多词单位)的教学干预分为三种,即“增强程式语意识”“运用词典或语料库”“强化背诵记忆”[9]。我国学者马蓉对国内外程式语教学干预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元分析[10],结果表明,“强化背诵记忆”的有效性和保持效果最好,“综合干预法”的有效性次之,而“增强程式语意识”和“运用词典或语料库”具有中等效应。
四、对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的测量
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诸多研究考察了被试在阅读中附带习得的词汇知识,包括多词单位知识,但严格来说此类研究仅测量了被试对词汇显性知识的获得。鉴于隐性知识在二语习得与使用中的重要作用,有必要深入考察学习者对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的习得,进而判断其能否在实时的聚焦意义的语言使用中提取并使用此类知识[2]。
二语隐性知识的测量方法众多,且各有优势与不足[11],但这些方法主要聚焦二语语法隐性知识的测量。从已有研究来看,二语多词单位的隐性知识可以通过眼动跟踪(eye-tracking)、自定步速阅读(self-paced reading)以及启动范式下的词汇判断任务(primed lexical decision task)等实验范式来测量。
眼动跟踪技术在心理语言学中的运用非常广泛,为研究者提供了深入理解人类语言处理过程和心理机制的重要工具。在多词单位加工研究中,眼动跟踪技术可以用来记录和分析学习者在阅读多词单位时的眼球运动轨迹,从而揭示他们在语言加工过程中的认知过程。具体来说,眼动跟踪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注视点。通过分析学习者的注视点,可以了解他们在阅读多词单位时,对哪些单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有助于揭示学习者对多词单位结构的认知和理解程度。二是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通过记录学习者的注视时间和注视次数,可以了解他们在处理不同单词时所需的时间和努力程度。这有助于评估学习者对多词单位的熟悉程度和加工难度。三是扫视路径。通过分析学习者的扫视路径,可以了解他们在阅读多词单位时的整体认知过程。例如,学习者是否按照预期的语法结构进行扫视,或者是否存在跳跃、回视等异常行为。在以往研究中,不少研究使用了眼动跟踪技术研究了程式语(即多词单位)的认知加工机制。例如,Underwood等人使用眼动跟踪技术研究了程式语的在线加工,结果显示,在阅读过程中,程式语的末尾词与出现在非程式语中相同的词相比得到注视的次数较少。这就意味着被试能够根据程式语中的前几个单词迅速预测其末尾词[12],从而表明被试能够快速地从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中提取有关程式语的知识(如形式、语义、功能等),具有相关程式语的隐性知识。Siyanova-Chanturia等人通过眼动跟踪研究发现,母语者和不同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对高频短语的阅读速度要比低频短语更快[6]。这可能表明相较于低频短语来说,高频短语在心理词库中更容易被激活,进而表明高频短语具有强度更大的隐性知识。
自定步速阅读任务(self-paced reading task)是另一种心理语言学研究中常用的实验范式,主要用于实时的语言理解加工研究。在自定步速阅读任务中,阅读者通过键盘按键来逐一呈现句子片段,并根据自己的速度控制对每一个句子片段的阅读时间。因此,这种阅读方式被称为“自定步速”阅读。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者可以记录阅读者对每一个句子片段的阅读时间,从而推测他们的理解加工过程及其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这种实验范式基于“眼-脑”假说(Eye-Mind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眼睛是认知的窗口,通过眼睛获取的信息会直接影响大脑的认知过程。因此,自定步速阅读任务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研究工具,用于探索阅读过程中的认知机制和心理过程。这一方法也被一些研究用来考察程式语的在线加工模式。例如,Schmitt和Underwood在其研究中要求英语本族语者和非本族语者完成一项自定步速阅读任务。研究者对比了程式语的末尾词(目标词)与出现在非程式语中的相同单词(控制词)的阅读时间,结果显示,目标词和控制词的阅读时间没有显著差异[13]。然而,Tremblay等人通过三项自定步速阅读实验(分别是逐词、逐块和逐句自定步速阅读任务)发现,相较于控制句子(即包含一般短语如in the front of the的句子),被试对包含词串(如in the middle of the)的句子加工速度更快[14]。Millar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正确的母语搭配,本族语被试对非母语式的搭配(non-nativelike collocations)阅读时间长得多。研究者认为,这些错误的学习者搭配(learner collocation)对本族语被试造成了更多且更持久的认知负荷[15]。换言之,本族语被试对母语式搭配具有阅读加工优势,体现出较强的隐性知识。
启动范式(priming paradigm)亦是心理语言学中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用于考察语言加工的心理机制。在这种范式中,研究者一般先呈现一个启动刺激,随后再呈现一个目标刺激,然后观察启动刺激的出现是否促进了随后出现的目标刺激的识别(也就是启动效应)。启动范式可以揭示出先前经历过的语言形式或语义如何对之后的理解或产出活动产生影响。它常见的类型包括语音启动、语义启动和句法启动。这些不同类型的启动范式可以用于研究语言的不同方面,如语音加工、语义理解和句法结构等。该范式能在不引起被试察觉(conscious awareness)的情况下研究语言的加工和使用,避免了复杂的、需消耗大量认知资源的策略性过程,这一特性使得它特别适合用来考察学习者的语言隐性知识。该范式以Michael Hoey的“词汇启动理论”(Lexical Priming Theory)为基础[16]。它主要解释了在语言处理过程中,一个词汇(启动词)如何影响对后续词汇(目标词)的识别、理解或产出的现象。这种影响通常表现为启动词的出现加速了目标词的加工过程,或者增加了目标词被选择的可能性。词汇启动理论基于词汇在大脑中的存储和激活模式。根据该理论,词语不是孤立地存储在记忆中,而是作为一个网络的一部分相互连接。这个网络中的节点代表词语,而连接则代表词语之间的语义、语音或形态上的关系。当一个词语被激活时,它不仅可以被识别和理解,还可以激活与之相关的其他词语。
搭配启动(collocational priming)作为启动效应的一种形式,受到搭配词共现频率的驱动,可以用来考察不同强度搭配的心理现实性(psychological reality)。搭配启动指的是在语境中,一个词(启动词)的出现会促进与其具有搭配关系的另一个词(目标词)的激活和识别。这种现象体现了语言使用中单词间的相互依赖和关联。搭配启动的研究主要关注单词间的搭配关系对语言理解和产出的影响。例如,当“tea”这个词作为启动词出现时,可能会促进与“tea”有搭配关系的词汇(如“cup”“drink”等)的激活,从而使其更容易被识别和产出。通过研究搭配启动效应,研究者可以深入了解语言使用者如何处理和运用单词间的搭配关系,以及这种能力如何影响语言理解和产出的速度和准确性。相关研究中,Sonbul和Schmidt[17]以及我国学者陆军[18]使用了搭配启动范式考察了二语搭配的隐性知识。例如,Sonbul和Schmidt[17]使用了多种测试方法来评估学习者在搭配学习后的收获,包括传统的显性测试(如形式回忆和形式识别)和创新的隐性测试(如启动)。该研究结果显示,尽管所有条件都促进了显性知识的增长,但没有一种条件显著促进了隐性知识的增长(通过启动测试所测量)。这表明隐性知识的习得可能更加困难,需要更多的语境暴露、自然交际和内化过程。
目前来看,针对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的研究尚为数不多,学者们更多关注二语语法隐性知识的测量与诊断[2]。未来研究可以运用更多的方法,如听觉模态下的末尾词判断、视觉模态下的末尾词启动等心理语言学方法,以及NIRS(近红外光学成像技术)等神经语言学[19]方法,对二语多词单位的隐性知识开展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例如,我国学者费晓东和宋启超通过NIRS研究了高级学习者对日语语块的加工机制[19],结果表明,随着所考察的日语语块语义透明度的逐渐降低,大脑中语法加工区域的激活程度由强变弱,揭示出高语义透明度的日语语块最有可能是语义分解加工,即学习者不具有这些语块的隐性知识。此外,二语多词单位涵盖多种类型,如搭配(如strong tea)、短语/词组(如in the morning)、半固定结构(如the more..., the more...)、习语(如rain cats and dogs)。这些多词单位类型在使用频率、结构完整性、语义透明度、双语同译性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势必影响学习者对二语多词单位的习得,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以上因素对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习得的影响。笔者建议,在未来的进一步研究中,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研究方法,针对特定类型的二语多词单位进行研究,不断丰富和细化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的测量研究。
五、结语
以往针对二语隐性知识的研究多聚焦于语法层面的知识,对二语词汇尤其是多词单位隐性知识的研究较少。这可能是由于语法知识具有较为明确的规则和结构,使得其显性和隐性学习差异较为显著,因此更容易成为研究焦点。然而,随着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二语词汇的隐性知识,尤其是多词单位的隐性知识。这是因为词汇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同样重要。而多词单位,如短语/词组、固定搭配等,更是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于二语词汇隐性知识的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学习者在词汇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和学习策略,同时也可以为二语教学提供有益的启示,帮助教师制定更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促进学习者的词汇习得和运用。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加强对二语词汇隐性知识,尤其是多词单位隐性知识的研究,以推动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和实践的改进。本文分析了影响二语多词单位习得的因素,讨论了眼动跟踪、自定步速阅读、启动范式等实验方法,希望能引起学界对二语多词单位隐性知识习得与测量研究的进一步关注,从而开辟二语多词单位研究的新方向。
〔参 考 文 献〕
[1]李更春.中国英语学习者程式语心理表征模式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1.
[2]李更春.二语隐性知识测量研究[J].现代外语,2021(06):839-848.
[3]李更春.二语显性和隐性知识测量方法新进展[J].喀什大学学报,2019(04):100-106.
[4]Wolter, B. & Gyllstad, H. Frequency of input and L2 collocational processing: A comparison of congruent and incongruent collocations[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13, 35(03): 451-482.
[5]Durrant,P.&Schmitt,N.Adult learners’retention of collocations from exposure[J].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010,26(02):163-188.
[6]Siyanova-Chanturia,A.,Conklin,K.&van Heuv-
en,W.J.B.Seeing a phrase “time and again”matters: The role of phrasal frequency in the processing of multiword sequence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anguage, Learning, and Cognition,2011, 37(03):776-784.
[7]Bishop,H.The effect of typographic salience on the look up and comprehension of unknown formulaic sequences [C]/NlINZx2ngHMkdAJybszFQLTx218FZrFWWQyFjs0J+sQ=/N. Schmitt. Formulaic Sequences: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Use.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4: 227-248.
[8]Schmidt, R.W. The role of consciousnes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J].Applied Linguistics, 1990,11(02):129-152.
[9]Boers,F.& Lindstromberg,S.Experimental and intervention studies on formulaic sequences in a second language [J].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2, 32: 83-110.
[10]马蓉.程式语教学干预有效性的元分析研究 [J].外语界,2020(03):80-88.
[11]李更春.二语隐性知识测量方法介评 [J]. 外语研究,2021(01):57-61.
[12]Underwood,G.,Schmitt,N.,& Galpin, A. The eyes have it: An eye-movement study into the processing of formulaic sequences [C]//N.Schmitt.Formulaic Sequences: Acquisition, Processing and Us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2004: 153-172.
[13]Schmitt,N.& Underwood,G.Exploring the processing of formulaic sequences through a self-paced reading task[C]//N. Schmitt. Formulaic Sequences:Acquisition,Processing and U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2004:173-189.
[14]Tremblay,A.,Derwing,B.,Libben,G.,& Westbury, C. Processing advantages of lexical bundles: Evidence from self-paced reading and sentence recall tasks [J].Language Learning, 2011,61(02):569-613.
[15]Millar,N.The processing of malformed formulaic language[J].Applied Linguistics,2011,32(02): 129-148.
[16]Hoey,M.Lexical Priming: A New Theory of Words and Language[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5.
[17]Sonbul,S.& Schmitt,N.Explicit and implicit lexical knowledge: Acquisition of collocations under different input conditions[J].Language Learning, 2013, 63(01): 121-159.
[18]陆军. 二语隐性、显性搭配知识特征研究——一项语料库数据分析与心理语言实验的接口案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03):1-9+112+159.
[19]费晓东,宋启超.基于NIRS证据的日语语块加工机制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1(01):91-101+160-161.
〔责任编辑:杨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