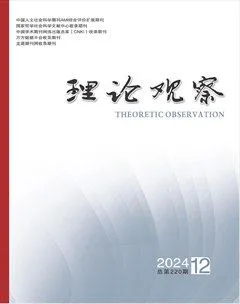实利与殖民的二重变奏
摘 要:《(满语)物理》教科书作为伪满政权实施奴化殖民教育的重要工具,体现着实利与殖民的双重特点。该教科书在编写原则、知识观、插图设计、实验设置与物理学名词使用等方面体现着唯实利主义的本体性特点。在唯实利主义的基础上,又在意识形态、语言政策、教科书内容三个方面体现出殖民主义的附加性特点。该教科书的编著并不是为了让学生掌握系统、科学、普遍的物理学知识,而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成为辅助伪满政权统治的“奴化人才”。
关键词:伪满洲国;《(满语)物理》教科书;实利主义;殖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12 — 0113 — 05
1932年3月1日,溥仪在日本的扶植下执政傀儡政权“满洲国”,自此,我国东北地区彻底沦为日伪殖民地。为了贯彻殖民主义教育方针,日本在接手东北沦陷地区教育权后,第一时间便从教科书入手,妄图重建意识形态逻辑,进行教科书的审查与编纂工作,将殖民主义思想与奴化思想全部融入教科书内容之中。以《(满语)物理》教科书为代表的理科教科书在殖民主义思想控制下,同样体现了服务于其资源掠夺的实利主义价值追求,使得其体现出实利与殖民的双重特点。
一、《(满语)物理》教科书的基本情况
(一)编纂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彻底控制了中国东北沦陷地区的教育系统。为了实现其“养成忠良之国民”的教育目标,伪满政权对原有教育系统进行了肆意地破坏与修改。首先,在组织机构设置方面,为了能够精确出版匹配其殖民主义思想的教科书,1932年7月,原伪民政部下设部门文教司升级为伪文教部,统管所有教育事宜,伪文教部下设学务司总务科掌管教科书编审事务。[1]后于1937年5月伪文教部被撤销,在伪民生部重设教育司,由教育司下设部门编审官室掌管学校教科书编纂、审查及检定事项。[2]其次,在学制设置方面,为了能够快速培养出供其使用的“奴化人才”,伪满政权于1938年实施新学制,废除原有中等教育的三三学制,并将初中和高中合并为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施行以实业教育或实务教育为主眼之国民教育。[3]再次,在课程体系设置方面,为了能够削减学生文化知识水平,减少文化知识的授课课时,学校课程中并没有单独的物理课程,而是将物理作为“理科”课程中的一门学科进行教授。[4]同时为了巩固殖民地位,在课程设置上将“汉语”改为“满语”,且将日语列为必修的“国语”科目之一。[5]导致掺杂着汉语及日语的“满语”文字充斥在众多教科书内容之中。最后,在教科书审定方面,为了加强对教科书意识形态的把控,新学制所用教科书必须由伪民生部大臣编著(国定教科书);如果著作者非伪民生部大臣,那么此类教科书则需经由伪民生部大臣进行检定(检定教科书)。[6]《(满语)物理》教科书正是在以上种种背景交织影响下的产物,在承担伪满政权所赋予的殖民奴化任务外,还体现着以培养服务于资源掠夺的实利主义人才观。在实利与殖民的交互影响下,使得该教科书具有其自身的本体性意义和服务于政治侵略所需要的附加性意义。
(二)各章情况
《(满语)物理》是“伪满洲国”实行新学制以后所出版的一本“新式”教科书,于康德七年(1940年)10月15日经伪民生部检定合格后,由伪满洲国法定出版社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出版发行,是一本“检定教科书”。该书由日本人松尾俊市和樱谷清次郎二人共著,适用于伪满洲国中学。全书除索引外共7章,分别为:绪论、物性、热学、力及运动、波动及音、光、磁气和电气,正文后附13页索引,主要是一些物理学名词的日文对照。《(满语)物理》教科书共274页,插图325张,问题131道,实验34项,小节201节。每章的分布情况各有侧重,第七章磁气和电气页数、插图数、小节数最多;第四章力及运动问题数最多;第三章热学实验数最多,各章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满语)物理》教科书的实利主义特点
1912年2月,蔡元培基于当时社会的新需求出发,率先提出了实利主义教育的主张,并将其列入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之中。[7]实际上,蔡元培主张的实利主义主要指科学教育或智育,从而构建了在教育中以传播科学知识和实业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可能。但是在伪满时期,实利主义教育却背离了此根本追求,带有极度的奴化殖民色彩以及功利化色彩。而教科书作为当时奴化殖民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不可避免的掺杂进了大量的奴化殖民内容。虽然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其主要以客观知识为主,通常来说比较难受到奴化殖民思想的影响。但物理学知识在世界工业化进程中的不断应用,使得其在促进实业技能提升中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作用,而正是基于物理学的这一本体性特点,为伪满政权通过实利教育来进一步推行殖民奴化思想提供了可能,也间接地促成了该教科书的唯实利主义倾向。
(一)实利主义编写原则的定位
伪满时期新学制的实施,对国民高等学校的教学原则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随着物理这一科目被划分入理科这一大类目之中,其编写原则也要服从学校教学的整体要求与理科教学程度的要求。在康德四年(1937年)所颁发的《国民高等学校规程》[8]第一章(教则)第一条中指出:
授与国民生活上适切有用之知识、技能,尤其有关实业者更宜注重,务须以实验及劳作,使之明确了解,应用如意……。
在第二章(学科目及其程度)第九条中指出:
教授理科应关于主要之植物、动物及矿物之一般知识,并关于物理上及化学上之现象及定律、机械之构造及作用、元素及化合物之知识之概要。
由上述要求可以发现,该教科书的编写立足于唯实利主义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此教科书只需教授“有用”的知识,即能够促进生产、生活的知识,而普遍性知识、系统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的教授以及这些知识如何教授并不关心;第二,此教科书注重的是技能的传授,掌握知识的多寡并不在考虑范畴之中;第三,此教科书只传授“一般知识”即可,并不注重知识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满语)物理》教科书在本质上就不是一本合格的教材,其只是伪满政权进行奴化殖民的一种工具,此教科书的编著不是为了让学生掌握系统、科学、普遍的物理学知识,而只是为了让学生能够成为辅助他们统治的“工具”。
(二)实利主义知识观的体现
物理教科书是传播科学知识的首要途径,在物理教科书中,科学知识渗透于教科书内容之中,主要体现为物理学名词、定律、概念、定义、公式、法则、规律等。[9]在唯实利主义的影响下,该教科书内容充斥着大量抽象的实用主义知识。
《(满语)物理》教科书在内容设计上看似通过对物理概念的阐释与界定、物理定律的发现与演绎、物理公式的归纳与推导等方式来传播知识。但实际上该教科书在“教授知识之概要”这一原则的指引下,舍弃了物理学知识的具体演绎、公式推导与规律总结,忽视了连贯系统的物理学知识的传授,从而保证有大量的版面可用于阐释实利知识。在该教科书的绪论之中,就明确地指明了物理学的实利主义作用[10]1:
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以研究物质的性质·音·热·光·磁气及电气等现象为主之科学。依着此科学的研究,可以明了此等自然现象。依着此科学的应用,可以发明蒸汽机关和电气机械等。
落实到物理学与自然现象的联系方面,该教科书列举了如水虫在水面行走或跳跃的现象、雪的结晶形状、在平静的水面投石所产生的现象、雷雨时先见闪光后闻雷鸣的现象、日食与月食现象等。落实到物理学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方面,该教科书列举了如水准器(水准仪)在查知水塔水面的应用;压缩空气在制动机、潜水艇排水中的用途;起寒剂(制冷剂)在制作冰糕时的应用;在移动重物时利用滚木来减少摩擦力的方法等。除此之外,又着重分析了风车、水车、听诊器、留声机、望远镜、照相机、罗盘、避雷针、电池、电灯等器械的工作原理。由此可见,该教科书只注重阐述能在生产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的物理学知识,置其他知识于弱势地位,进而最大限度地传授技能知识。
(三)实利主义的插图设计
插图作为文字内容形象化的一种呈现方式,是构成教科书体例中的重要部分之一。物理教科书中插图的运用对物理概念与规律的理解、培养观察能力与实验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11]纵观《(满语)物理》教科书的插图设计方面,除去实验配图、数据图、现象图、模型图、物理学史图外,尤其重视生产生活实际中实物图及原理图,从而强化知识的实利取向。该教科书插图中不仅包含水准器、连通器、比重瓶、探照灯、罗盘等实物图。也包含气压计、抽水泵、温度计、暖水瓶、冰糕桶、人造冰、空气液化器、天秤、飞机、蒸汽机、显微镜、幻灯、电影机、分光器、感应起电机、蓄电池、保险盒、电铃、电话机、直流发电机、电动机、无线电发送等原理图。以关注实利主义的插图设计对于渗透实利主义教育内容起着强有力的补充作用。
(四)割裂探索能力的工具主义态度
物理学是一门探索性很强的学科,这种强探索性体现在对未知科学领域不断追寻的过程之中。在物理教科书中,这种探索性主要体现在以物理实验为代表的科学实践过程,物理实验在学生科学方法培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科学方法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连接着科学假设与科学知识。[12]另一方面物理教科书中科学方法的训练是以实验事实为出发点,按照科学方法的内在逻辑呈现物理学概念与规律的建立过程。[13]
尽管《(满语)物理》教科书看似实验种类设置很丰富,即包括验证胡克定律、波义耳定律、阿基米德原理、库仑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欧姆定律、焦耳定律等经典著名演示实验。也涉及物体的浮沉、液体表面张力、液体的膨胀、气体的膨胀、流体的对流、固体的熔解(熔化)、液体的汽化、液体的沸腾、合力、平行合力(平衡力)、摩擦、重力加速度、横波、纵波、真空传导、音的媒质(声的介质)、光的直进(光的直线传播)、光的全反射、光的干涉、磁感应、水的电解(电解水)、火花放电等典型探究实验与测量实验。但这些实验均只停留在书本层面,并未设置深入实验室中的动手实验,忽视了实验对于学生探究能力及科学方法培养。体现出只传授最基本的物理知识,不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工具主义教育观。
同样,这种态度也体现在该教科书物理名词的使用情况之中。物理教科书中物理学名词的使用标准,不仅展现了作者编撰教科书和对待物理学知识的科学态度,更关系到读者对物理学知识的能否准确领会与迁移运用。虽然《(满语)物理》教科书通篇使用了大量中文与日文混杂在一起的“满语”,但对比该教科书中主要的汉语物理学名词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教育部出版的《物理学名词》可知,该教科书物理学名词使用并不标准(表2)。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名词不仅体现出口语化的倾向,如将音调称为调子。甚至将一些物理学名词简单地以物理学公式的简称命名,如将冲量称为力积,即力和力作用时间的乘积。由此可见,这种不谨慎的科学态度所传递的是不准确的知识,这也再次印证了其实利主义的教育态度,即传授物理知识即可,至于是否是准确的物理知识并不重要。
三、《(满语)物理》教科书的殖民主义特点
殖民主义是一套侵略和掠夺性的政策、行为方式和历史进程,它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侵略和掠夺世界弱小国家和民族并将它们裹挟进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过程。[14]教育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伪满时期中国人民并没有管理教育的自主权,而是以被动的方式由殖民者强行将其列入殖民主义中去。在殖民过程中,教科书作为教育活动进行的重要载体,不断地传递着殖民者的意识形态。殖民主义不仅赋予了教科书的殖民主义特征,更是将教科书带入其历史进程当中。可以肯定的是,《(满语)物理》教科书虽然不同于当时的文科教科书内容中对客观事实的大量篡改,但殖民主义一直作为一条明线牵引着该教科书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得该教书或显或隐地体现出殖民主义特点。
(一)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体现
教科书作为殖民的一种手段,无法规避侵略者对其意识形态管控。但《(满语)物理》教科书的意识形态体现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是由于该书主要传递的是以原理或规律为主要内容的客观物理学知识,但又不得不在这种客观知识中体现别有目的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东北沦陷地区教育的统治,伪满政权于1938年开始实施“新学制”,以此为基础制定的《学制要纲》明确地提出了其殖民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养成忠良之国民”。[15]这种所谓的“国民”并不是要将学生培养成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是要完全泯灭学生的中华民族精神从而将其形塑为彻底服从殖民统治的“满洲新国民”。[16]自此“愚民”政策实施之后,各级各类学校均冠以“国民”学校的称呼,体现出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满语)物理》教科书也正是配合该殖民教育目标而出版的教科书之一,在封面处就明确地印有“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字样,将“国民”一词牢牢地扎进学生的思想之中,从而服务于当时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除此之外,该教科书对不同“实业科”的学生进行差别化的教育,从而极力地压缩学生知识类课程授课课时。在该教科书目次页中醒目地印有教材分配上的注意[10]目次:
以商业为实业科的国民高等学校及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使用本教科书时,因理科的教授时间较少,对于本书的全部,宜简易教授,而可省略下列教材。
在省略的教材内容中,就包括比热的测定、光的干涉、电波等12项基础物理学知识内容。差别化的教学不仅使得物理学知识的学习更加不系统化,也侧面的加强了愚化学生的进程。
(二)殖民主义语言政策的体现
不论何时,语言本身都代表了特定的意义和价值,语言不仅是思想本身,更是一种思想工具。伪满时期,在教育活动中语言政策的殖民主义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国语称之为“满语”,强行将日语列入国语之中,从而使得“满语”在涵盖汉语的基础上充斥着大量的日语;另一方面是不断压缩汉语的教授课时且不断扩张日语教授课时,视日语为唯一的“高地位知识”。这种嫁接式的语言政策,破坏了汉语的语言文字纯洁性,让学生在学习中无时无刻地被动接触日语,从而最终达到通过语言同化来抹杀国家观念的殖民主义目的。
这种殖民主义语言政策同样在《(满语)物理》教科书中得到明确的体现,从教科书命名时刻意指明“满语”就可见一斑。同时,该教科书内容的各个方面都充斥着大量的日语,使得教科书语言表达混乱,削弱了教科书应有的学术价值。尤其是物理学定律和原理大量采用日语表述(表3),从侧面进一步加强知识学习与殖民语言之间的关联。
(三)殖民主义教科书内容的体现
如果说《(满语)物理》教科书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和殖民主义语言政策是通过显性和隐性方式共同展现的,那么该教科书的殖民主义意图则是通过明目张胆的教育内容来体现的。除去该教科书中大量物理学名词、物理学家及物理学定律等内容通过日文表达之外,该书在注重物理学知识与生活生产运用的基础上,夹杂着以“满洲国”为名号的殖民主义教育内容。如在讲解无线电话这一节中有如下内容[10]267:
例如对于远距离电信用的波长,定为……。我满洲国各放送局,亦各定一定波长的电波,所以想要听取某放送局的放送,必须选择该局所定的波长。
在这里,该教科书通过无线电话的运用从而联系到“满洲国”的无线电话的电波波长,以“我满洲国”为措辞强调学生的“国家观念”,凸显教材内容的殖民主义特点。
四、结语
教育作为个体意识和社会之间的中介,使得个体在教育过程中获得自身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一种独特认识与感知,从而构成该个体的意识,教育不仅传递知识,也“加工”人。在伪满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伪满政权将奴化殖民知识渗透到各类教材之中以巩固其统治地位,通过教授技能知识生产更多维护其统治的“奴化人才”。当这种知识植根于殖民统治的土壤之中时,使得《(满语)物理》教科书成为奴化殖民思想进行渗透与控制的重要工具。
〔参 考 文 献〕
[1]国务院文教部.满洲国文教年鉴[M].1932:6-7.
[2]国务院文教部.第三次满洲国文教年鉴[M].1937:2.
[3]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新学制大要[M].1937:14.
j67demy8TF1e6I1KWP/WKQ==[4]满洲帝国教育会.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G].1937:415.
[5]森田孝.満洲國の國語政策と日本語の地位[J].日本語2,1942(5):80.
[6]新学制之新教科书自新学期采用之新教科书编纂方针[N].盛京时报,1938.1.12(2).
[7]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中华书局,1984:130-137.
[8]国民高等学校规程[Z].1937.10.10.
[9]陈云奔,刘志学,王枭,王尊博.中国第一本现代意义物理学教科书——谢洪赉译《最新中学教科书·物理学》评析[J].科普研究,2018,13(05):79-86+105+111.
[10]松尾俊市, 樱谷清次郎.(满语)物理[M].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44.
[11]邹丽晖.高中物理教科书插图修订策略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9,39(09):94-99.
[12]何永红,王祖浩.我国科学教育急需厘清的几个关系[J].教育科学,2006(01):41-44.
[13]邢红军,张抗抗,胡扬洋,石尧.物理概念与规律的教学要求:反思与重构[J].课程.教材.教法,2018,38(02):91-96.
[14]周少青.几种民族理念的分析与比较[J].学术界,2015(01):61-73+323.
[15]学制要纲[J].满洲教育,1937(06):1-3.
[16]刘学利,张学鹏.制造“国民”——试析伪满洲国教科书《满语国民读本》[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14(02):54-57.
〔责任编辑:包 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