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光才:当下本科教育的困境与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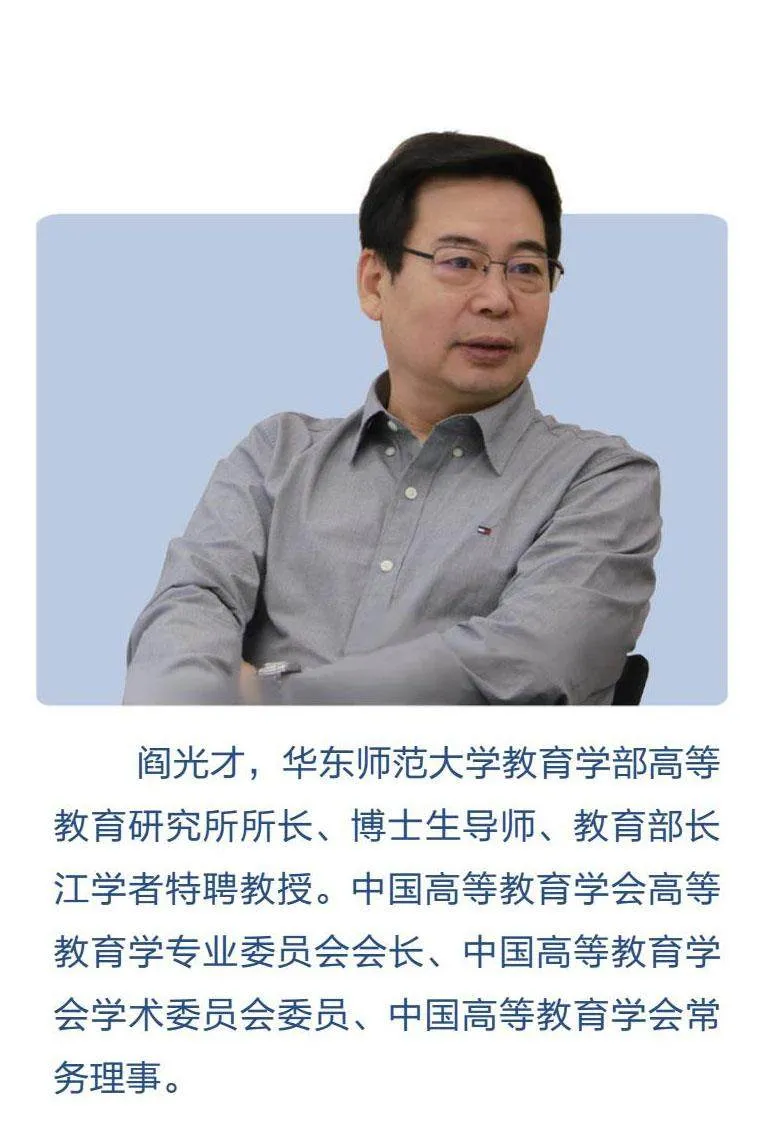
成绩、绩点、竞赛、考证、保研、求职……无时无处不在的竞争,引发了当今大学生中极为流行的“内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也让他们对眼前的忙碌与未来的预期多了几分彷徨和迷茫。现实中的本科教育实践,有着太多的纠结和张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在其新作《理解本科教育:学科与专业、课程与教学》中带领我们反思当下本科教育的处境,探寻本科教育的内涵与合理定位。
《教育家》:“究竟是我们的大学忘记了本科教育的使命,还是我们从来就对本科教育内涵随时代的流变而根本无法确认其合理定位?”您的《理解本科教育:学科与专业、课程与教学》立足这样一个问题情境的预设,对本科教育相关议题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考察和诠释性的理解。站在当下,您认为本科教育应如何应对时代之变、适应国家之需、满足人民之盼?
阎光才:在最为抽象层面上,本科教育的使命是恒定的,从中世纪至今,究其本质而言它就是培养人。但这种抽象的理解,内涵极为贫乏,因为时代在变,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也在变。在精英教育时代,本科教育无须关注学生的现实需求,甚至也可以漠视社会需求,在相对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或区隔格局中,人们也无须忧心于未来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然而,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今天,尤其是在由技术所引发的社会产业与劳动分工结构加速变迁的环境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学历贬值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经济波动起伏不定、社会岗位频繁变动,特别是如今人工智能为社会所有行业带来的冲击,种种不确定性让每个人的命运不再有往常的“定数”。由此而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文凭水涨船高且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我们的本科教育如何寻求新的定位以及培养规格和培养模式的变革,才能培养学生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竞争并不是一件坏事,它是社会发展活力所在,但是,如果竞争带有高度的同质性,在无意义事项上损耗过多的精力,它就成了“内卷”;不确定性也意味着风险,但风险本身是中性的,在有利于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祉且兼顾个体收益事项上的勇于挑战,它可能是有价值的创造与创新。但人们是否具有抵抗风险的能力,不仅在于社会的包容性,还在于我们的教育是否能够尊重个体禀赋与需求差异,养成学生挑战常规的底气和摆脱集体压力的勇气。
显然,为应对高度的同质性竞争以及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天的本科教育如果还固守传统的人才培养定位与模式,锚定既有的社会部门、产业与岗位分工,以相对刚性的培养方案,实行大批量流水线生产,不仅会加剧同质性竞争,弱化了人才培养对变动不居社会的适应性,还会因为个体潜质发掘不足、个性不彰,削弱学生应对不确定性的风险承担能力。
《教育家》:您在书中指出,“如果在培养结构上还延续传统的相对统一和批量生产模式,而不是探索多样化、弥散化乃至带有个人定制化的培养路径,人们担心的规模性本科生毕业即失业现象绝非危言耸听。”本科生培养路径的转变可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阎光才:摆脱上述危机或者未来潜在的危机,我想除了探索多样化、差异性与个性化的培养路径,别无他途。大学本科仅仅四年,期望以四年时间为每个人规划和确定未来人生的轨迹,甚至提供一生无虞的保障,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枉然。尊重个体差异、专长与偏好的培养路径,并非就是颠覆传统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理念,而是在注重可迁移的通用性能力与基本专业素养培养的前提下,思考如何赋予高校专业设置的灵活性,如何为学生创造更多专业转换、课程辅修或双学位等项目自主选择的机会,为学生的专长、主业之外的偏好、跨学科能力等拓展空间。人的潜质、个性与需求各有不同,只有顺应每个人的个性,而不是以标准与结果对齐的方式,才能让个体获得适合于自己的教育。个性化教育不是无序的,而是有其基本指南与要求的。缺乏自我主导能力与循规蹈矩者,可以遵循基本路线图,而不满于常规要求甚至想另辟蹊径者,则应为其自我探索与试错留有余地。自由选择不是放任,而是强化对等责任,唯有体验到自我探索之艰与自我责任之重,才真正有利于人心智的成熟,形成可以延伸至整个生命历程的可持续性自我主导与自我学习能力,从而获得应对未来工作与生活挑战的基本“装备”。
探索多样化、个性化与弹性化的培养路径,其目的不仅在于促成个体自由生长,而且也是摆脱统一规格批量生产导致同质性竞争困局,让个体在高度不确定性中探求最大确定性的现实策略。大学本科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应该相互开放,课程资源实现学校乃至校际的共享。同一专业,方向可以不同,即使同一专业方向,也并不应强求课程完全一致。这种尊重个体选择的差异性教育,并非专业与课程学习的碎片化,而是强调如何在尊重个体选择的同时,又能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保证学生学习的连贯性以及专业能力与素养培养的系统性。
《教育家》:2024年,我国开展了一场数量足够多、力度足够大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您认为如何做好学科专业设置的调整与优化?
阎光才:本次大规模的本科专业布点撤销与增设,无疑有其合理性。但是,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为何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来一次兴师动众的调整。追根溯源,我想根本问题还是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与办学体制。毋庸置疑,高校的学科与专业具有相对稳定性,外部社会产业结构与技术环境变迁的不确定性,彼此之间的信息非对称性与反馈存在时滞性,也意味着高校人才培养不可能与社会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保持无缝对接的耦合。但是,这并不代表高校就可以漠然置之。本科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如何利用知识与理论传授及其应用与实践,培养学生的素养与能力,包括价值观澄清、批判性思维、系统思维、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数理分析能力、跨文化视野、沟通能力和艺术鉴赏力等,这些通用素养尽管不能直接显现为可售性的市场技能,但它们是以不变应万变的“利器”,不会随时代与环境乃至工作场景的变化而失去意义,这也是本科教育之所以为“本”的要义所在。至于专业素养,它实际上也包括“软”与“硬”两部分能力或技艺,软技艺实际上属于专业的核心素养,其所指不仅是我们常言的“宽口径、厚基础”,也指涉专业的系统性思维与能力,因此,它是“宽”与“深”的有机统一。专业“软技艺”培养与训练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应对特定领域甚至跨越学科专业的适应性。专业“硬技艺”则指具体的专业知识、理论、技术与技能,它较为脆弱,其价值在变幻莫测的市场需求与技术加速变革环境中容易折损乃至过时和淘汰,这也是目前本科专业教育中主要问题所在。
因此,如何才能摆脱上述周期性的大范围专业结构调整困境,仅依靠政府部门不时的专业目录调整、强制撤销与刺激性的增设,未必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实中换个专业称谓,但课程结构与内容与以往大同小异的现象并不罕见。说到底,高校才应该是人才培养、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主体,其主体权力与责任并未得以确认与落实,或者说给了权力但接不住的问题始终存在。多少年来,我们一再倡导高校要面向社会自主办学,强调放权赋能,强化高校主体责任,但是这种机制不畅的“魔咒”始终难以打破。我认为只有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以及吸纳社会力量的参与,密切关注学术与技术、行业与产业发展前沿,高校才能以一种循序渐进和积累式的自我变革,走出动辄大破大立的周期律,实现其既相对稳定又与环境变迁之间保持相对协调的有序发展。
《教育家》:您如何看待“二本困境”?“二本”学生就业与发展的突破口或发力点在哪里?
阎光才:对于坊间各种“二本”的说法,我并不认同,“二本”这一指称具有典型的标签化色彩,它无非是指那些容纳高考落败者的众多地方普通高校特别是新升本科高校,所谓困境则是指其目前正面临的学术实力不及“双一流”、职业与技能训练又不及高职高专的尴尬境地。在此,或许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一下:第一,高考成败不代表人生得失,人的心智成熟有早晚,社会上大器晚成者不在少数;第二,普通本科机构有类别之分而不存在等级之别,机构层面的“类”,表现为人才培养定位或特色的不同,而同类机构内部的“人”,也同样存在“类”的差异;第三,ibu+KB23M3yR5WbNIMoSfw==我们所谓的拔尖创新人才,并非“双一流”高校的专属,其他普通高校同样可以成为拔尖人才的摇篮,它未必就是学术拔尖,而更可能是应用技术、职业技能的拔尖,一个社会的发展活力离不开思想与理论创新,但理论成果的转化更需要技术与技能高手乃至匠人来提供支撑。
摆脱当前普通本科高校的困境,寻求其学生就业与发展的突破口,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在机构意义上的类属定位是否能够真正到位?当前,在不断强化分类引导的政策框架中,我们提出所谓应用型或技能型等概念,姑且不论其界定是否清晰,仅就常识而言,专业应用能力与技能培养其实比理论人才的培养,更需要资金、设施与设备等资源的投入,也更需要其与社会行业产业之间的融通,包括专业实习与实践场所、技术、设施设备、资金与教师的相互开放与交流,问题是它们是否具备这些基础与条件?第二,在普通高校内部人的类属上,人们往往在自觉不自觉之中,将学生群体理解为需要统一“规训”而不是尊重个体差异的个性化教育。故而,现实中,培养方案刚性、必修课程杂多、强制性灌输教学和学生自主选择余地少,在该类高校中更为普遍也更为严重。此中存在的悖论是,如果该群体学习兴趣寡淡,那么如何才能调动其带有兴趣地学习?如果我们认为,该群体需要提高自我管理或约束以及主导能力,那么强制性规训与其中小学阶段的学习体验又有何区别?
因此,要提升普通高校学生的发展与就业能力,或许更需要尊重学生的个性,为其拓展专业与课程选择空间,以更为丰富的正式和非正式课程资源,发掘与培养其多样化的理论、技术与技能专长和偏好,形成有助于其生涯发展的自主学习、技术掌控与开发的能力与技能。说到底,机构的分类不能构成个体差异发展的“紧身衣”,不能成为否定学生自由成长与发展的借口。
《教育家》:学历通胀对我们的本科教育提出了哪些挑战?如何缓解学历通胀带来的教育焦虑和就业焦虑?
阎光才:学历通胀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普遍存在的现象,至于如何应对这种挑战,简单说,就是伴随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必须有培养体制与模式的结构性变革。概括当下世界各国经验,大致涉及如下层次:一是政府适当淡化代为高校规划与管控的观念,强化高校作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主体责任;二是本科培养体制趋向于弹性化,包括专业设置、培养方案、课程结构与培养过程的灵活性以及学制的弹性,重视学生可雇佣能力的培养;三是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自主学习能力与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至于如何缓解当前普遍存在的教育和就业焦虑,这是一个远超出高等教育本身的复杂议题,它有其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状态、人口结构、社会就业以及劳动保障政策与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也有其教育文化、人才观念与考试评价制度的归因。说到底,只要存在社会岗位资源稀缺或供需紧张,焦虑就在所难免。因此,如何缓解这种普遍的焦虑,让每个学生具备就业力而不是竞争力,获得有成就感的工作,感受有尊严感和有意义的人生,这既需要外部社会环境的全面改善,也需要如上所提到的本科教育与培养体制的结构性变革。
《教育家》:在书中,您特别强调了“可雇佣能力”,能否具体解释一下其内涵与培养方法?
阎光才:简单说,可雇佣能力是指个体获得工作、维持工作以及转换工作的能力,它贯穿于个体整个工作生命历程。不同的人以及人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能力需求是存在差异的。可雇佣能力包括通用性能力与专门性能力,或者是所谓的软技艺与硬技艺。贯穿人一生的可雇佣能力,无论是通用还是专门能力,其实大多并非在大学中养成,而是来自工作与生活。由此也就带来了一个难题,大学作为人生的一个关键期,究竟应该培养哪些能力?不同能力孰轻孰重?培养取向是指向近期就业还是兼顾未来职业人生?这些恐怕都不是简单且容易回答的问题。换个角度,立足于生涯视角来审视大学这段关键期,或许能够从中获得某些启示。对于刚刚脱离被监管的未成年人角色而又尚未成为真正社会责任承担者的大学生而言,给予他们相对自由的空间,允许他们自我探索和试错,自我确认能力所及、偏好与专长,形成可持续的自主学习能力,赋予他们自由选择及行为的责任担当意识,以帮助他们顺利实现由校园到社会即成人的身份与角色转换,这或许才应是本科教育的核心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