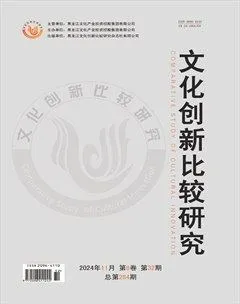从《卧虎藏龙》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命题,而影视传播是其中的重要方式。该文以电影《卧虎藏龙》为研究对象,从文化呈现、传播现状及构建路径三个方面,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新途径。在文化呈现方面,电影蕴含了丰富的“古典中国”想象。在传播现状方面,影片通过适配西方人的“前理解”、追求艺术真实、克服语言障碍等方法赢得了西方观众的认可,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在构建路径方面,提示中国文化出海应重视中国叙事、探索中西语境的转换及加强国际合作。《卧虎藏龙》上映20余年后,其成功经验依然值得借鉴,对其分析有利于中国电影探索新的文化传播模式。
关键词:《卧虎藏龙》;李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叙事;国际传播;文化意象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1(b)-0158-05
Explor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JIA Linl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25,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 significant issue in China's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with film and media playing a crucial role in this process. This paper takes the film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as a case study to analyze new approaches to sprea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broad, focusing on three aspect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 current state of dissemin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pathways. In term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he film embodies a rich imag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a". Regarding the current dissemination status, the film has gained recognition from Western audiences by adapting to their "pre-understanding", pursuing artistic authenticity, and overcoming language barriers, thereby achieving effective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on pathways, the film's success suggests that efforts to promote Chinese culture abroad should prioritize constructing Chinese narratives, exploring the conver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s, and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ore than 20 years after its release,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still offers valuable lessons. Analyzing its success provides insights that could guide Chinese cinema in exploring new models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Ang Le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narrat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image
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已形成趋势,文化的国际传播日益呈现出重要性,而影视凭借其可视化特点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上映20余年来,凭借其影响力,已成为在国际上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范本,因此学界对它的讨论一直保持着热度。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需要更多的影视作品面向国际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卧虎藏龙》的传播策略值得借鉴,中国电影也应该抓住机遇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海”作出贡献。
1 《卧虎藏龙》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呈现
李安曾说拍摄武侠片《卧虎藏龙》“除了一偿儿时的梦想外,其实是对‘古典中国’的一种向往”,“古典中国”当然要依靠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进行呈现。《卧虎藏龙》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前者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器物,可视、可感;后者为融入物质中的各种思想,可体会但无法触摸。不同的文化元素组成了一幅幅绚烂的电影画卷,向世人展现出李安有关“古典中国”的文化想象。
1.1 民居、服饰与器物
影片开始的镜头便是白墙黛瓦的江南民居,江南民居在中国近现代的画作中是常见的题材,颇能代表中国古民居的形象。影片中还有贝勒府等京城合院民居,古色古香,浸透着浓重的历史气息。电影中的服饰包括袍、衫、褂、裤、裙、旗装等,既符合故事的时代特点,又有些许现代设计,与角色设定相得益彰。主角李慕白无论是会客还是打斗皆是一袭长袍,非常符合飘逸的“大侠”形象。传统的器物更加多样,笔墨纸砚、家具、摆件等,都是标志性的传统物品。所有器物中,兵器最为突出,刀、枪、剑、锤等,种类繁多,其中青冥宝剑别具一格。剑这种武器历史悠久,先秦时期已经声名鹊起,而青冥剑又削铁如泥、锋利无比,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至高的权力。影片由青冥剑串起江湖中的恩恩怨怨,其也被镀上了一层神秘光环,是集中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具”。
1.2 武侠
“侠”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侠”与“武”自古便密不可分。明清以来,武侠逐渐成为小说的重要题材,正义之士拥有超绝的武功方能称为“侠”,恶人拥有至上武功只能提升“恶”的等级,与“侠”毫无关涉。现代的小说、电影把武侠推上了超现实主义的发展道路,李安不满那些过度夸张的武术表现,他访武术名家、读武术书籍,力图了解真实的武术。而真实的武术毕竟与电影表现不同,武术必须转换为电影的视觉语言才能吸引观众,尽管如此,李安还是在回归传统武术的道路上做出了尝试,以至于打斗场面没那么好看。电影故事设置在江湖、官府、世俗生活之间,德行高尚的李慕白与高超的武功合体,担得起“大侠”的名号。影片将李慕白设定为悲剧结局,这种安排也彰显出将武侠片从神怪化的道路上拉回来、重新融入传统现实生活的努力。可见,李安对传统的执着追求,这符合他对“古典中国”的向往。
1.3 思想文化
影片涉及的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儒、道两家,儒家思想较多地体现在人际交往方面,道家思想则与武术、剑术相关,在电影中的地位比较突出。李慕白和俞秀莲谈及闭关时的感受时说:“这次闭关静坐的时候,我一度进入了一种很深的寂静,我的周围只有光,时间、空间都不存在了。”这句话其实就是老子所说的“虚静”境界,庄子所谓“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可以说是对“虚静”的生动描述,“白”即光,也就是说虚静境界充盈着吉祥之光。影片中最高深的武功为玄牝剑法,剑法的名字来源于道家。《老子》第六章云:“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玄牝”若进行文化学、文字学的解释非常复杂,可以简单理解为万物化生的根源,而且化生的力量绵绵不绝。李慕白教训玉娇龙所说的“揣而锐之,不可长保”引自《老子》,意谓“显露锋芒,锐势难保长久”[1],后面说的“勿长、勿助、不应、不辩”也是从道家思想引申而来,用以说明敛藏锋芒、待机而动的道理。由于与武术密切关联,相比于儒家,道家思想对武术的影响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表现上更为典型。
1.4 独特的东方美学
李安说:“拍武侠片,除了武打还有意境。”意境是中国美学的术语,粗略来说就是情与境相合的产物。影片中的意境有江南村落的静好,李慕白牵着马行走在池塘边的石板路上,神情闲雅,仿佛从画中来;还有古意十足的庭院,俞秀莲与玉娇龙在玉府对坐倾谈,窗外小院绿树婆娑,中国建筑的“借景”审美彰显无遗……意境更多是与武相联系,如影片大量展现的轻功。飞来飞去的轻功本是超现实主义的东西,但轻功的灵动承载着中国武术的别样之美,尤其是影片中的竹林大战,动作之轻盈简直可以通于绘画的“气韵生动”,所以李安着力演绎。较早有关《卧虎藏龙》的研究文章都将其影像呈现等同于西方科技大片的“奇观”,但与大片奇观的硬朗不同,《卧虎藏龙》呈现的更多是柔美、静美,一种独特的东方之美。
影片中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还有很多,李安用它们很好地还原了“古典中国”的图景。西方观众面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的能够直接感知,如各种器物等鲜明的文化符号及独具东方特色的电影画面;有的只能限于肤浅的了解,如道家思想。无论如何,《卧虎藏龙》在西方的热映都是一次成功的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
2 《卧虎藏龙》的文化传播策略及其存在的问题
李安拍摄《卧虎藏龙》是实现他的一个梦想,并非刻意去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关于影片引发的文化效应,他“压根儿没想到自己会制造出这等状况”。当中国影片要面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观众,就必须克服文化差异、想方设法让西方人接受这部电影,这可以说是一种“并非策略的策略”。
跨文化电影的制作过程非常复杂,而从成片的传播效果看,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其传播策略。
第一,适配“前理解”。“前理解”是诠释学的术语,“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2],海德格尔的这句话可以视为对“前理解”的简单解释,“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即所谓“前理解”。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如果不顾及异文化的理解习惯或说“前理解”,很难获得成功。李安主要从两个方面适配西方人的“前理解”:一是整体的故事编排;二是人物行为的细节。西方影评人Blake Kunisch说李安“将戏剧技巧、阴谋诡计和浪漫爱情完美地结合”[3],“阴谋诡计”“浪漫爱情”是西方戏剧的常用题材,从这些题材入手能够很好地引起西方人的观影兴趣。细节方面,影片力避过于中国化的表现,以尽可能符合西方人的欣赏习惯。中国古典的爱情由于受到伦理的束缚,向来不能自然地释放,女子常常会表现出忸怩的姿态,而李慕白与俞秀莲、玉娇龙与罗小虎的爱情却表现得比较自然,省去了文化理解上的困难。
第二,追求真实。这里的“真实”主要指艺术表现的真实。西方艺术,无论是古希腊的雕塑还是文艺复兴,以至19世纪的绘画,走的都是写实的路子,并且得到哲学上的支持,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即显示出对真实的执着追求。中国文化也崇尚真实,而艺术表现却在形神结合的“意”上面不断用力。虽然西方现代各种超现实主义艺术不断涌现,但仍然在某些方面坚持真实取向,如异文化原生态的真实感。为配合西方人的这一追求,李安着力打造原生态的东方味道,除了前述传统文化的展示之外,人物容貌、声音及环境的刻画上都下了不少功夫。玉娇龙的饰演者章子怡脸上的斑点及青春痘均未遮盖;李慕白的饰演者周润发、俞秀莲的饰演者杨紫琼都采用了广式普通话的原声,未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配音;故事很多时候发生在夜间,灯光的设置恰到好处,没有破坏夜间的氛围……这些处理都有助于提供“古典中国”的真实感。
第三,克服语言障碍。语言的问题不只是翻译,对白是否有意思、是否能够配合剧情、能否被西方观众接受等都要考虑在内。李安自述对白“有文艺腔的、地道的、半文半白的、半中半西的,来路很多,是个混合体”,而恋爱戏和推理戏的对白更不好处理,对白设计好了,翻译成英文同样是一个大工程,“不是直译,而是照西方模式、以欧美观众能够接受的讲法及语法尽量传达相同的意涵”[4]。有研究者称《卧虎藏龙》的字幕英译是顺应性的翻译,这种翻译是一种“动态的顺应过程”“顺应于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双方的认知环境”[5]。这其实是翻译策略的学术化表达。
上述几种方法未必是专门传播传统文化的策略,它们可以适用于很多面向国际传播的华语影片。不过,《卧虎藏龙》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人的期待有机地融合起来并引起可观的文化效应,的确是一次成功的国际传播。这次传播摆脱了稍早国产影片如《红高粱》等迎合西方人眼光及所谓“东方性”的诟病,以一种古典美的形式将传统的中国呈现在西方人面前,受到广泛赞誉。但是为了赢得西方市场,制作方重点考虑了欧美人的理解与接受习惯,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中国文化的清晰度,如影片中一些官职、器物的名称无法准确翻译,文化习惯、文化思想难以有效传达等,这可以说是影片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就西方人的习惯不仅会降低文化清晰度,还可能引起误解。玉娇龙与罗小虎的爱情故事充满了自由、浪漫的气息,影片有意淡化伦理V801ujQQvRiMiunUQcmhhQ==纲常给玉娇龙带来的压力,突出她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契合西方人的爱情观与价值观。当然,中国的封建伦理并不值得夸耀,但如果不展示角色在伦理中的挣扎,有可能导致西方人误认为中国与西方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也不能充分显示追求自由的那份可贵。相对于文化上的模糊,误解更不利于文化交流;文化模糊可以通过不断加强的文化传播逐渐消除,避免让文化交流走入歧途。一部电影不可能面面俱到,《卧虎藏龙》掀起西方人的观影热潮,进而激发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本身具有文化传播的意义。
3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建议
《卧虎藏龙》上映后的20余年,中国电影市场不断增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海”在影视这一渠道上不断创新。在倡导文化交流的今天,中国电影应汲取经验,审视不足,积极探索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
3.1 抓住时代机遇,构建中国叙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显著,世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了解中国,中国也需要走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提炼”“构建”“讲好”“展现”都是围绕中国文化这一核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中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电影应抓住时代机遇,积极参与构建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叙事”和“故事”是什么关系呢?“在国际传播中,相较‘故事’侧重于‘说什么’,‘叙事’更侧重于‘如何说’。”[6]也就是说,故事侧重于内容,叙事侧重于方法。有学者指出,“制作一部匠心独运的中国优秀电影,需要的不仅是过硬的制作技术,更需要精益求精的极具中华文化特色的内容支撑。”[7]电影善于讲故事,电影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但电影叙事与中国叙事不在一个层面上,电影叙事是就具体故事而言,是微观的;中国叙事是就中国和全球发展而言,是宏观的。电影参与中国叙事的构建,是在文化传播的宏观层面参与,即寻求中国文化影视国际传播的总体策略,中国电影应在这一大方向上做出思考与应对。
3.2 明确文化差异,寻求转换路径
钱锺书谈到比较文学时曾说过一句脍炙人口的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8]东西方文化能够进行交流,的确存在着相同的心理基础,但二者的差异也显而易见,有时甚至难以跨越。西方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曾用一个有趣的比喻描述文化差异:“中国人在许多场合画了个鸭,我们却望见了一只兔子。”[9]抛开西方人自居优越感的“东方性”不谈,文化间的误解也常有发生,我们看西方文化也是如此。明确文化差异,就是重视差异,继而寻求转换之道。梅特·希约特在谈及丹麦电影的国际化问题时曾说到三种电影元素:一是完全民族性的电影因素、二是可转换的电影因素、三是国际性的电影因素[10]。三种电影因素的划分很有道理,前两种因素都是差异性因素,第三种因素则具备文化通约性。三种因素中,第一种因素不可转换,第二种因素可以通过恰当的转换被异质文化接受,因此最为关键,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化传播的效率。当然,在转换过程中,为了照顾异质文化的理解习惯,可能会降低本土文化的清晰度,这种矛盾靠一部电影不可能解决,《卧虎藏龙》即是如此。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传播不是一部电影的事,三种电影因素的比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电影的批量制作及文化交流的深入,第一、第二种因素的比例会逐渐缩减,文化的清晰度也会相应提高。
3.3 组建国际团队,制作电影精品
中国有很多电影是国际合作的结果,但这里所说的“组建国际团队”不只是技术合作或国际演职人员的加盟,而是为了实现文化传播目的,组建由具有国际视野或国际身份的编剧、导演、演员、技术人员等构成的团队。《卧虎藏龙》除了不具备明确的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之外,其团队基本符合这一要求。李安本身是华人,又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戏剧教育,熟悉西方电影市场的运作规则,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终于向世界提供了一部精品电影,展现了东方文化中的中庸内敛和西方文化所崇尚的自由勇敢之间的碰撞。当前,中国电影欲拓展海外市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需具备明确的文化传播目的,同时发挥制度优势,组织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在内的国际团队,从剧本到电影上映,用心经营每一个环节,矢志打造精品。所谓“精品”,当然不是一厢情愿地自我标榜。电影制作过程需要在制作者与受众、专家与普通群众之间架起桥梁,将文化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尽可能地消除在制作阶段,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能够将这种理解用电影语言传递给异文化的观众,真正实现文化的国际传播,这样的电影才能称为“精品”。此外,为了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清晰度,还可以在电影之外做些尝试,如对文化核心元素做一些先导性的解释。这种解释融入宣传片或者制作成文创产品与电影一起发售,能够培养观众的“前理解”,有助于提高传播效率。
4 结束语
任何一位电影人都不会拒绝更广阔的舞台。近几年,中国的玄幻小说受到西方网友的关注,国漫电影《大鱼海棠》《雄狮少年》《哪吒》等也受到热捧。而游戏《黑神话:悟空》横空出世,也吸引很多西方网友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中国电影应当借势推出相关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21世纪世界民族之林持续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 张靓蓓.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69.
[2]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06.
[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76.
[4] 张志辉.精彩绝伦的演绎:《卧虎藏龙》影评[J].大学英语,2001(2):39-40.
[5] 孙乃荣.顺应论视角下看《卧虎藏龙》的字幕英译[J].电影文学,2011(21):139-140.
[6] 郭金超,黄钰钦.以文化为桥,探索构建国际传播的中国叙事[J].新闻战线,2023(22):22-25.
[7] 关冠. 弘扬东方文化 垒砌精神高塔:试析《卧虎藏龙》多元文化内涵[J].文艺争鸣, 2019(12): 190-194.
[8] 钱锺书.谈艺录·序[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9] 郝大维,安乐哲.期望中国:中西哲学文化比较·导言[M].施忠连,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10]梅特·希约特.丹麦电影与国际认可策略[C]//鲍德韦尔,卡罗尔.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麦永雄,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713-716.
基金项目: 广东省2023年度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三进’背景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外语课程建设研究——以应用型本科高校为例”(项目编号:2023GXJK3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贾琳琳(1980,8-),女,湖北天门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语言与文化,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