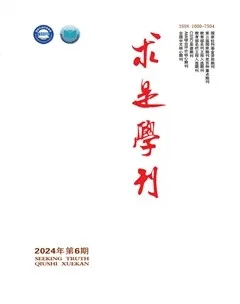帕菲特对人格同一性的反驳及其伦理意义
摘 要:针对其所整理的人格同一性经典观点,帕菲特在《理与人》中分别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一是如果遵循还原论观点,人格同一性就将成为一个无法提供具有实质意义答案的空洞问题;二是就非还原论而言,像笛卡尔式自我这样的精神实体缺乏充分的经验证据,反而有大量否定它的证据;作为“进一步事实”观点的支撑点,对经验主体的预设并非必要,因为非人称式描述是完全可能的。帕菲特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格同一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恰当类型的原因而产生的心理关联性和心理连续性,亦即其所谓关系R。他进而分析了这些观点产生的两大原因:一是原子式个人的预设,二是个人自我延存的自然愿望。帕菲特反驳的主旨其实在于伦理的层面。在《理与人》中,帕菲特的反驳实际上是针对作为自利论理论基础的原子式个人预设,进而批判西方主流伦理理论采取的个人主义视角。该反驳在《论重要之事》中的后续发展主要表现为对康德伦理学元伦理层面的批判以及对其规范伦理的修正。帕菲特的反驳不仅揭示了西方主流伦理学个人主义视角的内在问题,而且表明了它们在应对当代诸多重大现实问题方面都存在根本的缺陷。
关键词:帕菲特;人格同一性;经典观点;反驳;伦理意义
作者简介:阮航,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6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帕菲特的伦理理论及其当代效应研究”(20BZX112)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6.006
帕菲特(Derek Parfit)的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思想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其Reasons and Persons 甚至被认为“或许是20世纪关于人格同一性理论最有影响的著作”①。201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帕菲特以肖克奖这一哲学界顶级荣誉,其首要原因就是帕菲特通过分析和论证,得出了“人格同一性不重要”这一具有颠覆传统意义的结论,从而对人格同一性理论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②,这些分析和论证最基础和核心的部分在于对西方近代以来相关经典观点的反驳。那么要理解帕菲特的人格同一性理论及其价值,就有必要探讨其反驳的主要内容。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帕菲特的反驳作较全面的考察和评价,分四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交代帕菲特对其反驳对象亦即人格同一性经典观点的梳理;第二部分论述帕菲特反驳的基本内容;第三部分以问题的方式解读帕菲特反驳的思路和脉络;第四部分结合On What Matters 的相关内容,简要评价该反驳蕴含的问题意识及其伦理意义。
一、对反驳对象的清理
近代以来,人格同一性一直是西方哲学史上广受关注且引发持续争论的问题,①但人格同一性这个论题到底意味着什么?还不是很明确。帕菲特通过分析和区分,认为人格同一性实际上包含两个论题:“(1)一个人的本质是什么?(2)是什么让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的时间成为同一个人?什么是每一个人历时性的持续存在所必然包含的?”②帕菲特认为,第一个论题是关于质的同一性;第二个论题在直接的意义上是关于量的同一性,但其实也关涉质的同一性,因为(1)的答案对于(2)的答案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比如说,如果问题(1)的答案是一个人的本质在于其灵魂,那么问题(2)的答案可能就是:正是我的灵魂才让我在本周一和周五成为同一个人,我同一的灵魂是我持续存在所必然包含的。
帕菲特接着考察了近代以来人格同一性的经典观点,其中包括人格同一性的物理标准(PhysicalCriterion)、心理标准(Psychological Criterion),如笛卡尔式的纯粹自我(Cartesian Pure Ego)一般的精神实体以及进一步事实观点(Further Fact View)。鉴于前两种观点较为繁复,他通过讨论和修正,整理出各自的最佳版本。
按照帕菲特的整理,物理标准的最佳版本是:
(1)必要的不是整个身体的持续存在,而是大脑足够部分的持存,这个部分足以支持一个人的持存。今天的X和过去某个时间的Y是同一个人,当且仅当(2)Y的大脑有足够的部分持存,且现在是X的大脑,而且(3)这种物理持续性没有采取一种“分支”形式。(4)历时的人格同一性仅仅在于,像(2)和(3)这样的事实是成立的。③
(1)是质的同一性要求,(2)(3)是量的同一性要求,(4)则是强调(2)与(3)之间的内在关系。“分支”形式是结合帕菲特设计的“非常规的火星旅行”这一虚构情形来说的,其要旨在于说明,物理标准强调人格同一性之成立必须基于一对一的关系,而不能采取分裂(fission)的形式。
帕菲特对心理标准的讨论是从修正洛克经验记忆(experience-memory)的观点入手的,并区分出两个对于理解心理标准来说极为重要的概念,即心理关联性(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和心理连续性(psychological continuity)。按照帕菲特的定义,心理关联性是指特定的直接心理关联之成立,心理连续性是指强关联性的重叠链之成立。心理关联性虽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更为重要,但不是传递性的关系,因而不能作为人格同一性的标准。心理标准只能诉诸由心理关联性衍生的心理连续性,按照帕菲特的整理就是:
(1)当且仅当存在强关联性的重叠链,才存在心理连续性。当且仅当(2)X与Y在心理上是连续的,(3)这种连续性有恰当类型的原因,并且(4)不存在另一个与Y也有心理连续性的人,今天的X和过去的Y才是同一人。(5)历时人格同一性仅在于,类似从(2)到(4)的事实是成立的。④
其中(4)类似于物理标准中的(3),都属于量的同一性要求;对于这里的(3),按照对“何为恰当”的要求不同,心理标准可分为三个版本:心理标准的窄版本要求必须是常规的原因,宽版本的要求是任何可靠的原因,最宽版本则可以是任何原因。
帕菲特还指出,物理标准和心理标准之间的差异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大,两者反而有不少共通之处,均属于人格同一性的还原论观点(Reductionist View),其基本主张可概括为“个人历时同一性的事实仅仅在于某些更特定的事实之成立”①。还原论观点还可能提出某种针对非还原论的主张,即我们能够以某种非人称的(impersonal)方式来描述有关某个人存在的事实,而不必预设这个人的同一性。②还有一种还原论观点是二元论的,即要求同时满足物理标准和心理标准。通过拓展“事件(event)”一词的用法以便涵盖与信念、欲求等相关的心理状态及其变化,帕菲特将人格同一性的还原论观点概括如下:
所有还原论都会接受“(1)个人的存在仅仅在于:大脑和身体的存在,以及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物理事件与心理事件之发生”;一些还原论者会主张“(2)个人就是特定的大脑和身体以及上述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事件”;另一些还原论者会主张“(3)个人是某种实体,这种实体截然有别于某个大脑和身体以及诸如此类的一系列事件”③。
持有主张3的还原论观点看上去类似于非还原论观点,但在帕菲特看来两者存在根本的区别。④非还原论观点(Non-Reductionist View)可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个人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其典型代表是笛卡尔式的纯粹自我或精神实体;另一类观点认为,人格同一性是某种不仅仅在于物理连续性和/或心理连续性的进一步事实,帕菲特称之为进一步事实观点。
基于上述整理,帕菲特就明确了所要反驳的基本观点,并进而指出,他力图通过反驳这些观点达到四点结论。⑤其一,我们不是脱离我们的大脑和身体以及各种相互关联的物理事件与心理事件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其二,“我们的同一性总是确定的”这一观点并不为真。在某些情形中,人格同一性问题是空洞的。其三,任一时刻的意识统一性以及整个人生的统一性这两种有待解释的统一性,都不能通过如下主张来解释,即各种不同的经验是为同一个人所有的。其四,人格同一性并不重要,根本上重要的是由于任何原因的关系R。以下分别简要考察帕菲特的反驳。
二、对人格同一性经典观点的反驳
帕菲特首先要反驳的是人格同一性的非还原论观点,该观点的一个明确表达可见于里德(Reid)的如下表述:“我的人格同一性……蕴含着我称之为自我的那个不可分之物的持存。无论这个自我可能是什么,它是在思考、考虑、决定、行动和受苦的某物。我不是思想,不是行动,不是感觉;我是在思考、行动、受苦的某物。”⑥其要有二:一是自我是经验主体,而不是经验本身;二是自我的人格同一性蕴含着,存在某种脱离人们经验而独立持存的实体。第一点是还原论者也会承认的,第二点则为还原论者所否认。帕菲特由此指出,非还原论观点要能够成立,其关键在于论证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一是存在某种脱离我们的大脑、身体以及一系列经验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二是这种实体是持存的,具有连续性。但帕菲特认为,我们无法证实这种实体的存在及其持存。
第一,我们不可能诉诸直接意识,从经验内容来判断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独立的经验主体的持存。帕菲特设想了一个支线情形⑦来作理论说明。
[非常规的火星之旅之支线情形]地球上的我将在三天后死去。火星上仿我的复制体刚刚产生两个想法:“正在下雪。所以天气必定很冷。”但情况其实是这样的:我在小隔间按下绿色按钮的前一刻有“正在下雪”的想法。几分钟后,火星上我的复制体瞬间有意识了。他一有意识,就拥有了关于我生活的表面(apparent)记忆,尤其记得我刚刚有过“正在下雪”的想法。接着他想到,“所以天气必定很冷”。因此,我的复制体会认为,这两个想法都是由同一个思考者亦即他自己产生的,但实际上是,我产生第一个想法,而我的复制体只是产生第二个想法。
复制体在相信他有上述两个想法时所意识到的,只是其生活与我的生活之间的心理连续性,而不是某个独立实体的持存。同样地,我们在有一系列想法时所意识到的,只是意识流的心理连续性。他进而指出,如果有人声称意识到独立存在的主体之持存,那么他“意识到”的很可能只是对纯粹心理连续性的意识,或者是如洛克和康德所论证的具有心理连续性的一系列实体。总之,帕菲特认为,我们的经验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相信这些实体存在的理由。
第二,我们也不能根据经验来推断这种实体的存在。帕菲特认为,这方面最著名的主张当属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通过合理怀疑,推断出唯一无可怀疑的是怀疑者本人的存在,进而认为,每个思想必有一个思考者,并由此假定思想者必定是某个纯粹的自我或精神实体。这种笛卡尔式的纯粹自我意味着一种截然有别于大脑和身体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但帕菲特认为,笛卡尔的推断尤其是假定是有问题的。
其一,由思想的存在推出思想者的存在,这可能是讲得通的,但不能由此推出思想者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因此,帕菲特赞同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的如下观点:“我思故我在”尽管在前一种意义上为真,但可能在笛卡尔衍生出来的意义上产生误导作用;因为笛卡尔在此能够推出的主张应该是:“被思想的是:思考正在进行”,或“这是某个思想,因而至少一个思想正在被思考”①。
其二,由利希滕贝格观点所面临的反驳,帕菲特进而引出对另一类非还原论观点即进一步事实观点的反驳。利希滕贝格对笛卡尔主张的改造蕴含着,我们可以在无需指称思想者的情况下描述思想。帕菲特称之为非人称描述。当代一些学者如斯特劳森(Strawson)、休梅克(Shoemaker)、威廉斯(Williams)等认为,非人称描述无法解释我们精神生活的统一性,因为除非我们指出具有这些经验的那个人,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指出特定的经验或描述它们之间的联系。②其中威廉斯力图通过语义分析表明:非人称描述无法解释个人生命的统一性;非人称描述要是可能的,就必须表明,意识的统一性能够以不预设人格同一性的方式来描述。威廉斯进而主张,人格同一性不仅仅在于物理连续性和/或心理连续性,而且还在于某种不同于大脑、身体及相互关联的物理事件和心理事件的进一步事实。在帕菲特看来,这种进一步事实观点也属于非还原论,但它不是诉诸笛卡尔式的精神实体,而是通过要求意识同一性而诉诸经验主体的必要性或各种经验的所有者身份。
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是洛克用经验记忆的连续性来解释人格同一性的观点,③由此拓展就要求“心理的统一性由所有者身份来解释。按照这种观点,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通过把不同的经验归因于某人或经验主体来解释这个人的意识统一性。正是这同一个人拥有这些经验,才使得这些不同的经验得以统一”④。为了反驳这种进一步事实观点,帕菲特设计了一个虚构情形,其概要如下:
[我的物理考试]在参加某个物理考试时,我有两种方法去解答最后一题,但不确定哪一种更可能成功。因此,我决定让我的大脑分离10分钟,左右半脑分别运用其中一种方法来计算,然后重新统一我的大脑以便写下满意的答案。在实施过程中关于我的表面记忆有三点值得注意:1.在切断左右脑的连接时我的意识流也分离了,但这种分离是我体验不到的;2.在分离之后,我的一条意识流都意识不到另一条意识流正在进行另一个运算,而只能从另一条意识流所控制的手部运动看到这一点;3.可以设想,在将要重新统一大脑的时候我在每一条意识流中应该料到的是:我好像记得刚刚进行过两个计算,但在任一计算过程中没有觉察到同时在进行另一个计算。①
通过精心设计,帕菲特的描述突出了与他所要讨论的问题相关的要素。一是他假定在分离时存在两组独立的思想和感觉,因为每一条意识流都能够有意识地控制其相应的手,独立而互不干扰地运算。那么这种没有确定人称的意识流本身就具有意识的统一性。二是大脑的重新统一意味着,各自具有统一性的两条意识流可以像河流的支流一样重新汇聚,进而可以推想的是,若干组独立形成的思想和经验记忆同样可以共存,并统一于具有连续性的意识生活。三是帕菲特还认为,上述过程不仅是可理解的,而且是以非人称的方式描述的,那么这就蕴含着,我们不需要预设同一个经验主体的存在就可以解释意识统一性。总之,“我们不需要通过把这些经验归因于同一个人或者同一个经验主体来解释这种统一性”②。
第三,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支持如笛卡尔式纯粹自我一般的实体之存在,我们反而可以由此引出反对的论证。只要有证据能够支持如笛卡儿式纯粹自我一般的实体之存在,非还原论观点就可以成立。但帕菲特认为,没有任何足以支持这种实体存在的证据。
为此,他讨论了这方面最强的证据,亦即支持轮回重生信念的证据。比如说,某位日本女人声称曾是青铜时代的某个凯尔特武士,并且她保留下来的某些类记忆可以为考古队所证实。这种证据似乎支持轮回重生的信念,进而支持非还原论的如下观点,即存在某种精神实体式的纯粹自我。但帕菲特认为,即便类似的证据普遍存在,也不能证实轮回重生的信念,更得不出非还原论观点想要的结论。这是因为,这种纯粹自我既然是实体式的存在,那就应该是完整且不可分割的,亦即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不存在任何程度上弱化的可能性。但上述证据只是片段式的类记忆,只是部分记忆链条的重叠,而不是完整的记忆,只有后者才能支持轮回重生进而非还原论观点的某个纯粹自我。帕菲特进而反驳说,我们如果假定存在这种纯粹精神实体式的自我,那就会发现,这个假定与已为科学所证实的观点或经验相悖。我们如果相信该假定为真,那就不得不放弃诸多为科学或经验所证实的信念,比如说记忆以及心理连续性的载体是大脑这一信念,心理关联性可以在某种弱化的程度上成立的信念;又如按照这种非还原论观点,我们的身体就应该被视为纯粹精神实体的居所,从而发生我们与某个历史名人实际上是同一个自我的情况,并且不时会突然体验到这一点。因此,帕菲特认为,如笛卡尔式纯粹自我一般的实体信念实际上是不可理解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予以拒斥。③
主要基于以上三点反驳,帕菲特认为,人格同一性的非还原论观点不可能得到证成。这是否反过来表明,还原论的人格同一性经典观点是正确的呢?帕菲特并没有给出简单的判定,而是通过考察此前对这种观点的诸多反驳,引出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其中有些反驳并不成立,因而帕菲特作了辩护。一是回应了巴特勒(Butler)对心理标准的如下反驳,即心理连续性预设了人格同一性。帕菲特通过引入类记忆(quasi-memory)的概念,并设计了一个复制表面记忆的虚构情形来说明,心理连续性并非必须预设人格同一性。二是帕菲特提出,心理连续性的载体不必是脱离个人大脑和身体而存在的某个实体。另一方面,有些反驳比如威廉斯对心理标准的反驳表明,还原论的经典观点确实存在问题。帕菲特对人格同一性还原论经典观点的反驳,正是从考察威廉斯的反驳开始而逐步拓展的。
威廉斯的反驳也借助了其所设计的一个虚构情形,帕菲特对此整理了一个简化版,以下则是基于该简化版整理的一个极简版:
[威廉斯的虚构情形]某个冷酷的神经外科医生意图通过扰乱我的大脑来打断我的心理连续性。我在他操作时是有意识的,并处于痛苦状态。
这个医生告诉我,他会在我处于痛苦时做几件事。首先,他将按下一个开关,触发一些会让我失忆的神经元。我将突然失去此前所有的人生记忆。这时我的痛苦不会突然停止,而是仍然占据我的心,乃至我注意不到自己的失忆。接下来他会按下另一个开关,给我关于拿破仑生活的表面记忆,从而导致我自认为是拿破仑。当然,我同样不能以为这将使我的痛苦停止。最后在我受折磨期间,他会接着按下第三个开关,这将改变我的性格乃至变得和拿破仑的性格一模一样。依然不变的是,按下这个开关并不会终止我的痛苦。①
威廉斯认为,在上述虚构情形中,我被告知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我有理由认为,我在受折磨期间将不再存在;我反而有理由认为,在心理上经历失忆、发疯,变得像拿破仑,自认为是拿破仑等种种变化的过程中,感受到痛苦的那个人仍然是我。但是,按下各个开关时我的记忆、性格等心理变化显然不具有连续性。因此,我的持存就不可能在于心理连续性。为了回应“痛苦是贯穿这一过程的连续性心理”的可能反驳,帕菲特还为该情形补充了一个特征,即我在按下开关的一瞬间是无意识的,从而排除了我的持存包含心理连续性的可能。
对于威廉斯的虚构情形,帕菲特提出了一个拓展版(他称之为心理谱系),以便更深入地考察心理标准。②帕菲特拓展版的主要思路是:将威廉斯包含三次不具有心理连续性变化的单一情形,展开为一个谱系或一系列情形,该系列中每一种情形都极其相似于其邻近情形,由此涵盖所有可能程度的心理关联性。具体说,这个心理谱系包括N多情形,每个情形有一个可供该医生使用的开关,这N个开关将控制我的记忆变化和性格变化。假定这个谱系中的这些情形和开关是从左至右让相关变化逐渐增强的:打开左边第一个开关,在此情形中我将失去一点记忆,同时获得一点拿破仑的表面记忆;然后打开第二个我又失去一点记忆同时获得拿破仑的一点表面记忆;依此类推,到了最右边的情形时所有的开关都被打开,我就失去了自己的所有记忆,同时拥有拿破仑的所有表面记忆。性格变化亦如此,最后我的性格也和拿破仑一样,并自认为就是拿破仑。
对于这个心理谱系,帕菲特要问的是,既然在这个自我心理关联不断弱化、与拿破仑的心理关联不断强化的谱系中,我经历哪个情形或者说过了哪个分界线之后才不再是我,而是变成拿破仑?这个问题针对的是人格同一性的心理标准。鉴于相邻情形极其相似,这可能就是一个类似“沙堆难题”的模糊性问题,因而要给出确定的答案,那就不得不以独断的方式来划出这个分界线。但与“沙堆难题”主要涉及命名这一形式认定不同的是,心理标准所要解释的人格同一性问题却被设定为一个事关个人身份认定的重要问题,采取这种独断的方式显然不当,也不可能有实质意义。可以说,帕菲特的拓展版虽然也是对心理标准的反驳,但其关注点以及认为心理标准成问题的部分显然不同于威廉斯。
心理标准的不成立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诉诸物理标准呢?帕菲特通过改造心理谱系,提出一个物理谱系,它是由大脑和身体细胞被复制取代程度不断加大的诸多情形组成的。在左边的第一个情形(打开第一个开关)中,我的大脑和身体被取代一点点,比如说1%,而在所有开关都打开的最右边情形中的复制体已经100%取代我的大脑和身体,从左至右则是大脑和身体与我的相似度不断减少的一系列情形。帕菲特依据对物理谱系的分析,认为诉诸物理标准将面临与心理标准类似的反驳。接下来,帕菲特又设计了一个物理谱系和心理谱系两者结合的联合谱系,以解释人格同一性的联合标准同样是成问题的。①
那么心理标准和物理标准成问题之处何在呢?按照帕菲特的情形设计及其论说,在这三个谱系中,如果要追究人格同一性,那么在这些谱系的各个情形之中,我就总要不停地问,我在这个情形中还活着吗?是否已经被取代或者说就要死了?而就其中任一谱系的整体来说,我总会问:作为我生死存亡分界线的情形会是哪一个?在帕菲特看来,这些提问只是一个不会有确定答案和实质意义的空洞问题,因为其要求是不合理的,要求一个“要么是,要么否”的绝对答案。因此,帕菲特这里的观点主要在于,人格同一性的提问方式可能是成问题的。
那么,人格同一性的提问方式的问题何在?帕菲特认为,其提问蕴含着为威廉斯所揭示的两个要求:“要求(1):某个未来的人是否将会是我,这必须仅依赖于我们之间关系的内在特征。它不可能依赖于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要求(2):既然人格同一性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同一性成立与否不可能依赖于某个微不足道的事实。”②按照帕菲特的解读,这两个要求简单地说就是:一是人格同一性必定是某种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要求(1)],二是这种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要求(2)]。但帕菲特认为,没有任何同一性标准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
三、对反驳所得结论的解读与清理
既然无论是关于人格同一性的非还原论还是还原论观点都不可行,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和处理人格同一性问题呢?帕菲特的回答是,人格同一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于恰当类型原因而产生的心理关联性和心理连续性,亦即关系R。可以结合帕菲特各部分的论说,对这个看上去令人费解的回答作一个概括性的解读,在此基础上对其中核心语词的蕴含作一些清理。
首先要解读的是帕菲特为什么认为人格同一性不重要,其要可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对于解释个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来说,人格同一性的提问方式并非必要的,我们只需要随时能够确定个人的身份(identity)就足够了。就确定个人的身份而言,我们只需要解释意识的统一性和人生统一性,而这一点可以诉诸关系R来解释。至于自我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否同一个自我、这个“同一”如何界定,其实是个额外的问题。
第二,人格同一性问题即使是必要的,也不可能有得到证成的答案。如前所述,按照帕菲特的观点,如果诉诸还原论观点,那么人格同一性就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和实质意义的空洞问题。而非还原论观点虽然说一旦成立就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但其本身得不到证成。因此,帕菲特在正式讨论之前就指出,人格同一性问题与原子论式的个人预设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WpaPYRXOZjF2ofnvdbL6Gg==两者要么都成立要么都得不到证成。③帕菲特的反驳蕴含着,非还原论观点诉诸抽象实体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任意的预设,缺乏讲得通的理由和站得住脚的证据。
第三,如果取消人格同一性问题或者说像第一点所述的那样改变人格同一性的提问方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改造还原论的某些观点(主要是心理标准)来提供重要且有实质意义的答案。
仅诉诸关系R而不诉诸人格同一性对于确定个人的身份是否足够呢?帕菲特对此的一个较清晰的解释,可见于它与休谟关于国家身份的解释的类比④。一个国家的身份在于其领土、公民、政府、制度、风俗等,我们可以根据与该国有关的这些因素来解释其身份,并且一个国家比如说中国的持存可能意味着,其中各种因素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但变化前后有可理解的关联性或连续性。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要追究国家的历时同一性,比如说宋朝的中国与明朝的中国是否同一,那么这同样也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和实质意义的空洞问题。而要解释中国在从宋朝向明朝的转变过程中仍然具有统一性的身份,我们只需了解那段历史中各种因素的变化及其关联性和连续性就足够了。同样地,对个人身份的认定也可以借助他由于人生经验而产生的各种关系R。
帕菲特认为,重要的是关系R。这个答案仍然是还原论的,因为它主要来自对心理标准的修正;但与人格同一性的还原论经典观点根本不同的是,它要回答的不是人格同一性问题,而是个人自我身份的确定问题。这种根本不同的关键在于,它取消了人格同一性蕴含的一个无法得到满足的要求,即历时同一性或一对一关系这一要求。也可以说,按照帕菲特的观点,人格同一性提问方式的不合理之处就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为此,帕菲特从大脑分离的医学进展出发引出一系列虚构情形,如“我的物理考试”“我的分离”“大脑分离产生的兄弟10年后的球赛”等,由此表明,个人历时同一性的问题是空洞的,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产生具有实质意义的内容。
帕菲特还对其观点作了两点补充解释,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一是其观点为何主要基于对心理标准的改造,而未纳入对物理标准的考虑。通过考察和反驳内格尔(Nagel)的相关观点,帕菲特给出了相应的解释。内格尔的观点是,心理连续性的原因是大脑,因而大脑才是确定个人身份之所在,个人本质上就是其大脑。①帕菲特的观点是倒过来的。他认为,“大脑是心理连续性或者关系R的载体……当大脑的连续性并非关系R的载体的时候,它就不再重要”②。也就是说,与个人身份的确认直接相关的是关系R,大脑反而是由于能够提供关系R才重要。
进一步说,物理标准的其他方面也可能③具有派生意义上的重要性。帕菲特举例说,对于某些特别漂亮或英俊的人来说,其身体外貌的历时相似性对其身份确认可能是重要的;但同样地,这种重要性也是通过这个人的心理关联性和/或心理连续性才发挥作用的。如果把这些派生的重要性也考虑进来,那么帕菲特所要辩护的还原论观点的完整表述就是,“在任一时期,个人的存在仅仅在于其大脑和身体的存在、其思想的想法、其行为的做法,以及许多其他物理事件和心理事件的发生”④。但他同时强调个人的这种存在的前提,“个人截然不同于他的大脑、身体和经验,但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⑤。这样看来,重要的是关系R这一观点,是被帕菲特视为其还原论观点的核心而提出的。
二是如何理解帕菲特还原论观点所支持的个人存在身份。对此帕菲特虽然没有作为一个特定的问题来讨论,但可以从他关于关系R的各部分论说尤其是在对内格尔“系列-个人(series-persons)”概念的讨论中梳理出来。⑥简单地说,个人存在的这种身份是一种统一但并非同一的身份,可供我们理解的身份内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但这些内容的变化由于关系R的成立而得以统一,并且这种统一性对于确认我们的意识统一性和人生统一性来说是足够的。这里可以举个简单的虚构情形,并按照帕菲特的思路作简要解释。
[我身份内容的变化]我本来是个四肢健全的人,但昨天遭遇一场车祸,不得不截去双腿。因此,今天我成了一个残疾人。
如果我们问,昨天未遭遇车祸之前的我与今天的我还是同一个我吗?那么这个人格同一性式的提问是一个不会有确定答案的空洞问题。按照帕菲特的提问应该是这样的:昨天的我和今天的我是否具有统一的身份?这场车祸是否中断了我的意识统一性和人生统一性?帕菲特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会是肯定的,对第二个会是否定的。可以这样来解释:其一,相对于昨天的我,今天我的身份内容发生了变化,即昨天的我是四肢健全的人,今天的我是残疾人;其二,这种身份内容的变化并没有中断我的意识统一性和人生统一性,从而未改变我身份的统一性。引起我身份内容变化的事实(车祸)是我知道并不得不接受的,因而从昨天到今天的心理变化(昨天我自认是四肢健全的,今天自认是残疾)由于恰当的或者说可理解的原因而具有心理关联性,我不会因此而认为成了另一个人,仍然具有统一的身份。
接下来仍然有一个有待解释的问题:既然人格同一性问题蕴含着无法满足的要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关注这个问题,并且近代以来引起持续讨论并形成这么多的经典观点呢?这一点似乎可以从帕菲特关于能否相信非还原论或还原论的讨论中找到答案。①
帕菲特认为,在人格同一性问题上,真相与我们倾向于相信的事情有很大的区别。我们有强烈的主观愿望去相信非还原论观点,而不怎么愿意接受还原论的观点。但我们如果诉诸理智层面,就会发现真相恰恰相反。帕菲特甚至指出,在自然而然的意义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大多数人都是非还原论者,因为我们对未来的关注在自然的意义上总是自我中心式的,而自我的延存无疑是其中最具吸引力也最强烈的愿望。但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无论有多强,都不能代替论证,在得不到证成的情况下都不能作为理论说明上的理由,或者说它只能作为私人信念而不能“僭越地”用作论说公共知识的理由。
帕菲特认为,其还原论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提供一个缓解乃至替代的方案,只要我们能够从那种原子式个人主义的抽象自我中解脱出来,转而从关系R的观点来看待以自我为中心展开的人生中的各种关系,由此不仅关注自己的未来,也关注那些与我们有各种关系的人们的未来,因为这些人由于关系R而在不同程度上也构成了自我的因素。用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所看重的就不是同一特定大脑和身体的持存。我们所看重的是自己与他人之间各种各样的关系:我们所爱的人和事、我们的抱负、成就、承诺、情感、记忆,以及其他好几种心理特征”②。
四、帕菲特之反驳的伦理意义
基于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说,帕菲特通过其反驳和论证基本完成了其预定的目标,亦即本文第一部分末尾给出的四点结论。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些反驳、论证和结论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其两部伦理学代表作的问题意识及其主要内容来分析。
作为一名伦理学家,帕菲特反驳的主旨显然不止于抽象的哲学层面,毋宁说更多地指向伦理理论和现实的伦理问题。在Reasons and Persons 中,帕菲特对基于原子式个人主义预设的自利论提出了大量的批评,而他对人格同一性经典观点的反驳,其最终针对的正是“个人是独立存在的抽象实体”这一原子式个人主义预设;并且在反驳之后,他基于关系R提出了一个他所认为的“反对自利论的更好论证”③。就此而论,他反驳人格同一性经典观点的主旨可能就在于,通过对原子式个人主义预设的解构和反驳,摧毁自利论的理论基础。这种个人主义预设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西方主流的伦理理论,表现为思考伦理问题的个人主义视角,只不过在自利论这里表现得更鲜明,也最为典型。因此,他接着依据反驳得出的结论,反思了若干理论问题,比如自主性问题、效用主义观点、分配正义问题、平等问题、生命目的问题等。在帕菲特看来,这种伦理理论基础方面的问题不仅仅体现在理论的意义上,而且表现在指导伦理实践方面的局限性,其突出表现是,我们运用个人主义的伦理视角难以为当代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有说服力的伦理解释和有效的规范指导。在Reasons and Persons 第四部分,他基于对人格同一性问题的反思,引出并深入探讨了一个关系到未来人生活质量的新理论问题,亦即他所称的“非同一性问题”。
不过,面对有深厚积累、已经体系化的个人主义伦理思想传统,帕菲特的反驳虽然很有力度,但他要树立的观点亦即关系R的观点显然还比较单薄,难以抗衡进而替代前者以形成新的伦理理论基础。这直接影响到其理论说服力,也难以较系统地处理现实的伦理问题。换个角度来说,帕菲特如果拿不出一套可行的替代方案,其反驳就没有真正完成,至少没有完成驳倒之后的重建工作。因此,他在三卷本的On What Matters 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方案,其中第一卷实际上已经较完整地呈现了这个方案,第二、三卷主要是批评与回应以及一些局部的补充和修正。有鉴于此,以下主要结合On What Matters 的内容,对其重建方案中与反驳人格同一性或个人主义伦理视角相关的部分作简要梳理。
首先,这一方案的核心在其元伦理部分,亦即On What Matters 第一部分的理由理论。帕菲特的理由主张是基于价值的客观主义,其主要对手则是理由的主观主义。按照帕菲特的解释,这种主观主义的理由理论认为,我们的行动理由是主体给予的(subject-given);也就是说,我们最有理由做出的行动,就是能够满足我们当前欲求或实现当前目标的行动。基于价值的客观理由理论则主张,我们的行动理由是对象给予的(object-given);也就是说,仅当或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试图获得的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或值得做的,我们才有理由那样去做。①主观主义理由的根据在于主体内部,也可称作内在理由;客观主义理由的根据则在于主体之外,也可称作外在理由。这两种理由理论要解释的是我们行为的规范性来源问题。
在相当程度上,主观主义的理由理论采取的是个人主义的伦理视角,②这种视角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的各种思想运动发展而得以强化,在康德那里得以综合和表达,并融汇于其系统性的理性主义伦理学方案之中。在康德看来,规范性的基础在于道德法则,而道德法则实际上是来自主体的自由意志的自身立法。其中的主体指的是有着双重存在者身份(作为理性存在者和感性存在者)的个人,而其所谓自由意志就笔者的理解就是个人对其作为理性存在者身份的自觉,由此指向能够实现个人自由的目的王国。这样看来,自由意志背后其实预设了某种抽象的理性个人的存在,其中不乏独断的形而上学因素。③可以说,在康德这里,行为的道德动机以及规范性的来源均在于理性主体的内在世界,并且通过其三大批判,形成了一套可以为理由的主观主义奠基的系统性方案。当代西方的主流伦理学不乏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但很少从根本上动摇这一方案的基础,或者退一步说,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比康德更有竞争力的系统性方案。
而帕菲特元伦理部分的主旨正是要通过分析和论证,反驳主体给予的理由方案,进而证成其理由的客观理论,并且On What Matters 第一、二卷包含大量检讨和批评康德伦理学的内容。如第一卷的自序就包含不少针对康德伦理学的思考和批评,第二、三部分有大量篇幅是对康德伦理学规范部分的讨论,第二卷6个附录中有4个都是对康德伦理学的批评。就元伦理方面来说,第二卷的附录“I 康德的动机论证”是尤为相关的。帕菲特通过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康德的论证是不融贯的,其立场则可称作一种道德内在论。①他还在别处指出,康德伦理学实际上建立在主观主义的基础上,沿着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路发展下去将导致道德虚无主义。当代元伦理学的主观主义虽然使用的术语不同于康德,但在很多方面是根本一致的。
这样看来,帕菲特的元伦理立场与康德伦理学的相关部分是正相反对的,在此可以借用当代持有类似观点的哲学家斯坎伦(Scanlon)的解释:
对于理由……康德提供的是一种从上至下的观念。在他看来,关于理由的主张根植于理性能动性的要求。我们如果拒绝这种论说,那么替代的选择看来就可能是一种“从下至上的(bottom up)”观念——根据这样的观念,实践推理始于有关特定的诸理由及其相对强度的主张——由此“往上”进行而达至的结论是关于全盘考虑所有的相关理由,亦即我们最有理由去做或思考什么。基于欲求的行为理由理论至少看上去属于这种形式。这样的观点认为,如果做X会增进某行为者对其所持的某欲求的满足,该行为者就拥有做X的至少达到初步的理由。经过通盘考虑,行为者最有理由做什么,取决于在这些可能相冲突的多种理由之间做出的权衡。②
这里所谓的“从上至下”,是指由理性能动性派生出行为理由。斯坎伦认为,这是一种原子式实在论(atomistic realism)的立场。③“由下至上”的观念则是由某欲求的相关事实产生初步的理由,然后通过与行为选择相关的这些初步理由之间的比较和权衡,最后产生决定性的理由,从而驱动行为。不过,帕菲特的元伦理观点虽然和斯坎伦一样是以客观理由为基础的,但似乎有更高的抱负:他认为,我们可以按照这种“由下至上”的方式逐步上升到最高的道德原则,指向客观的道德真理。他在第三卷中给出了一种关于如何指向客观道德真理的论说。④如果要与康德的方案形成对照,我们也可以说康德是从主观的道德真理规定出实践规则和行为理由,而这主观道德真理的哲学内核仍然是原子式的个人主义。
其次,帕菲特在第一卷其他部分对伦理学的规范部分作了清理,这一清理的核心正是通过以其基于价值的客观理由理论置换康德伦理学的元伦理根据、以集体式伦理视角取代康德的个人主义伦理视角,对在Reasons and Persons 中讨论过的问题和理论做出更为简明扼要的修正式论说。其中与人格同一性反驳最为相关的是关于群己困境(Each-We Dilemmas)的重新整理。
他认为,在博弈论中得到大量关注和讨论的囚徒困境其实是自利论的困境,只是属于群己困境一大类别。囚徒困境中的个人正是按照原子式个人主义预设的个人,而困境的产生恰恰体现了个人主义伦理视角的局限性。帕菲特指出,如果采取个人主义的伦理视角,群己困境在社会生活中是大量存在的,比如说贡献者困境、渔夫困境、气候伦理问题、环境伦理问题、搭便车问题,如此等等。群己困境的一个共性是涉及公共益品和公共负担的分配。而个人主义伦理视角是从考察个人行为及其影响入手,其局限性在于,不能对个人行为微不可察的负面影响给出相应的伦理解释,对其累积效应无法归责和提供规范指导,从而陷入了悖论式的理论困境。因此,理性自利的原则或理论在集体的层次是直接地自我挫败的。⑤要有效地处理这类问题,帕菲特的建议是代之以集体式(collective)的伦理视角,并且认为这是一种更恰当的伦理思考方式,因为“道德本质上是一套集体的守则”①。
进一步说,在On What Matters 中帕菲特对康德伦理学的处理,鲜明地体现了取代个人主义伦理视角的问题意识。在卷一的序言中他就多次提到康德,他不否认康德的思想极富原创性,但同时指出康德是大哲学家中最不清晰的。帕菲特的不满不仅是由于康德语言的晦涩和粗糙,而且更多的是认为康德提出了大量的主观臆断,并且不乏自相矛盾之处。他对康德伦理学的修正式解读同样贯穿着拒斥个人主义伦理视角的问题意识。
对于康德绝对命令的三大公式,他分别作了不同的处理。对于康德的人性公式,他分解为同意原则和手段原则,分别予以讨论。他认为,同意原则的蕴含通常是可行的,而手段原则并不能解释行为的不当性。对于康德的自主性公式,他在卷二的附录中作了考察并总体上持批评态度。对于康德的普遍法则公式,他作了大量的讨论和修正,将之改造为康德式契约论公式,并作为其“三重理论”的一个版本。可以说,帕菲特的批评和反驳都是针对康德伦理学中的个人主义伦理思路和主观主义的因素。而他对普遍法则公式的修正,可能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不一定符合康德的原意,但在正文中他认为符合康德的精神,只是以力图取得理论进步的方式达成康德原本想要寻求最高道德原则这一目标。但实际上,其康德式契约论公式的元伦理前提不再是康德的理性能动性或者说理由的主观主义基础,而是建立在帕菲特自己的元伦理观点之上,而该公式的内容更像是普遍法则公式与同意原则中蕴含的契约论观念的组合。
对康德普遍法则公式的修正进而“三重理论”的提出,很可能还蕴含着帕菲特更高的理论雄心,即提出能够达成最高的客观道德原则,寻求客观道德真理的新方案,以取代个人主义伦理或者说康德主观主义的道德方案。这一点在卷一最后的部分做出了较明确的表达。同时作为论证客观真理存在的一部分,主要道德理论的趋同以及“三重理论”的提出,也有回应麦凯(Mackie)“错误论”的用意。②
最后,对人格同一性的反驳还有面向当代重大现实问题的一面。他在规范部分不时会提及个人主义理论视角在处理当代重大现实问题的局限性。除此之外,其非同一性问题可以说是直接基于对人格同一性非还原论观点的反驳而提出的。在帕菲特看来,只要诉诸我们的理智和直觉就会发现,我们的行为对未来世代人们的影响都可能对应不同身份的不同人群。比如说,我可以选择行为A和B并且这两种行为会对未来人的生活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行为A的影响要优于B。但实际上,正是由于行为A和B的影响不同,两者造就的未来环境就是不同的,而如蝴蝶效应一般,环境因素的改变总是意味着未来活着的人的不同身份。如果采取人格同一性的思维或者说个人主义的伦理视角,那么无论我们怎么做,实际上都不会影响到未来人的生活质量,因为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作比较,就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的生活状况会由于我的选择而变得更差或更好,也就没有任何特定的个人有理由要求我负责,我想负责也找不到合理的负责对象,更不知道该如何负责。
我们如果放弃人格同一性蕴含的身份同一要求,转而采取容许身份变化的集体式伦理视角,那么这种问题就可以得到解释,进而提出相应的伦理解决方案。帕菲特的解释是,我们需要负责的对象不必是特定的个人,而是容许身份变化的笼统的个人(general person),而一些有可能存在但最终实际上没能存在的那些人构成的集合,可以成为衡量我们如何影响未来人生活质量的比较对象。
总之,对人格同一性观点的反驳及其蕴含的问题意识,贯穿于帕菲特整个伦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对这种反驳的伦理意义概括为如下几点:其一,它揭示出,人格同一性的提问方式蕴含着原子式个人这一预设,该预设不仅是自利论的哲学基础,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现当代西方主流伦理理论的前提,并表现为思考伦理问题的个人主义视角。其二,它表明人格同一性问题不可能有得到证成的答案,由此揭示出原子式个人预设存在深刻的理论困难。其三,它进而指出,人格同一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系R。不仅理论上如此,帕菲特还通过对当代若干重大现实伦理问题的分析,说明个人主义伦理视角解决现实问题的种种困难,相反采取关系R或集体式伦理视角,这些困难将得到解决,从而更有说服力。其四,该反驳在On What Matters 中有了后续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对康德伦理学元伦理层面的批判以及对其规范伦理的修正。当然,帕菲特是通过提出自己的元伦理理论来置换康德伦理学相应的部分而实现的,而其元伦理理论可以说是在其理由理论框架下对关系R观点的理论深化和系统化。在当代元伦理领域,帕菲特的元伦理理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面临不少质疑。其元伦理理论如果能够成为主流,那就必然给当代伦理理论带来巨大的变革;退一步说,即使它得不到普遍接受,其由此派生出的各种观点也已经对思考当代重大现实问题如环境与气候问题、平等问题、代际伦理问题等提供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并产生了重要的反响。①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