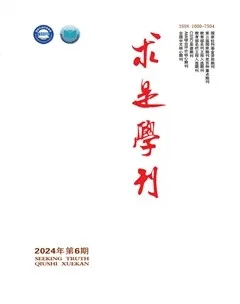当代俄罗斯文化危机与主体性突围
摘 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复杂历史境遇中经历着艰难的文化跋涉,失陷于文化身份的遗失、哲学形而上学的荒凉、末日论精神的复活等多重文化危机。制度解体与转型的解构性起源为俄罗斯社会关系打上“解体”的烙印;全球资本霸权和市场总体性导致俄罗斯文化基础发生市场化突变;文化主体性遭到功能性分解。面对俄罗斯文化的整体失落与全面异化,当代俄罗斯左翼思想家布拉夫卡-布兹加林娜在“苏联怀旧”的时代症候中重返苏联历史经验,以主体性原则作为化解21世纪俄罗斯文化危机的跳板;提出确立以创造性活动为基础的文化价值原则和社会主义文化空间。布拉夫卡对俄罗斯如何走出文化危机的探讨,同时切中了人类文化的普遍性问题。
关键词:当代俄罗斯;文化危机;文化异化;文化主体性
作者简介:杜宛玥,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专职博士后(成都 610207);郭丽双,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20&ZD011);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1世纪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2020BZX011)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6.002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在曲折的国家转型历程中遭遇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持激进立场的学者对此直言不讳:俄罗斯的现代化显然没有成功,人们牺牲了很多,但现代化却没有发生。可以说,当下俄罗斯的现代化困境更为深层地表现为一场文化危机。俄罗斯文化处在整体失落与全面异化之中,人文价值急剧消逝,精神信仰的神圣性不复昨日,国家-民族身份认同失衡愈加突出,艺术和灵感逐渐凋敝,文化的存在方式发生彻底变革。面对该困境,作为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批判派思想家,布拉夫卡-布兹加林娜(Л.А. Булавка-Бузгалина)认为,俄罗斯文化重建的必要性已经迫在眉睫,并在重返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发掘重启俄罗斯文化的关键要素。本文立足于布拉夫卡的文化哲学视界,从俄罗斯文化危机的现实境遇出发,探究俄罗斯在转型阶段遭遇文化危机的实质及出路。
一、整体失落:当代俄罗斯的文化危机
数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角力中进退失据,始终受困于文明发展方向上的不确定性。俄罗斯历史的主要转折点无不伴随着关于文化道路的讨论。俄罗斯文化在持续追寻的苦旅中表征出某种“未完成性”。20世纪末的国家转型和社会变革再度扰乱了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步伐,使俄罗斯文化发展遭遇重创。俄罗斯学界普遍认为,在苏联文化传统被自由主义改革全然摧毁之后,俄罗斯未能发展出更加进步、和谐、有潜力的文化以带领民族探索创造性的现代化道路。俄罗斯在复杂历史境遇中经历着又一轮艰难的文化跋涉,文化领域的危机与动荡不断,表现为文化身份的遗失、形而上学的荒凉、末日论精神的复活等多重形态。可以说,当前俄罗斯面临一场文化的整体失落,文化发展和演变趋向于冻结和停滞,悬浮在历史的时间和空间之中。
(一)文化身份的迷惘
在一般的文化研究范式中,文化身份可被理解为文化的基因编码,它指向的是集体所共有的历史经验和意义表达,用以确证该文化集体的特殊性和唯一性。对俄罗斯的文化身份进行自我辨识和定位,一直是俄罗斯思想家苦苦求索而不得解的理论谜题。从历史视角来看,俄罗斯文化的无根性源于其处于“东西方文明结合部”的地理空间,斯拉夫主义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牵制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文明道路的选择。然而在现实层面,苏联解体之后国家新旧发展路径的转换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历史连续性,使俄罗斯的文化身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对于俄罗斯民众而言,苏联既是不复存在的政治实体,也是扎根于集体意识之中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苏联时期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价值伴随着苏联解体在名义上走向消亡,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自我撤销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化归属的混乱。“20世纪的灾难已经改变或抹去了许多俄罗斯民族从前的品质。现代俄罗斯人性格里有许多与他们的既定原型——例如集体主义、无私、突出的宗教性——相矛盾的东西。”①随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在转型的洪流中相互激荡,进一步消解、淡化了固有的文化认同。在布拉夫卡看来,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化在雏形阶段就具有多重文化称谓,如“无产阶级文化”“苏维埃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文化”等,而俄罗斯文化“从未真正获得自己的名字,这里所指的与它所指向的人与世界的形象,以及它以这些形象和名义所代表的东西有关”②。这表明,“俄罗斯文化”这个名字本身并不能充分捕捉这一文化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无法体现和代表俄罗斯人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形象,而只能指向当今俄罗斯社会正在形成的混沌现实。此种状况反映出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不确定性和混乱,揭示了在国家快速变革和制度解体过程中,人们在价值观、文化认同和社会角色上的艰难探索。可以说,俄罗斯人已然丢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构业已解体的文化身份是俄罗斯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核心课题之一。
(二)形而上学的荒凉
与文化身份的遗失相伴而来的是形而上学的荒凉。在这里并不是说俄罗斯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或学术活动在数量上的减少,而是指俄罗斯哲学的终极旨趣和根本精神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面临存续危机。俄罗斯哲学的觉醒和发展从一开始就被纳入宗教世界观的框架,学界也往往将白银时代的宗教哲学作为俄罗斯哲学的代表。俄罗斯哲学家洛斯基曾说:“俄国哲学的全部发展都倾向于以东正教阐释的基督教精神来解释世界,在此基础上独立的哲学思想是与推翻德国式的哲学思维方式相联系的。”③因此,宗教精神构成了俄罗斯哲学相较于西方哲学的独特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哲学可以被简化为一种宗教理论或书斋里的学问,俄罗斯哲学的问题意识始终在于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对人类存在及其历史命运的关注。应该指出,宗教哲学是俄罗斯哲学家在东正教文化传统的背景下,从宗教体验和信仰出发,用宗教资源对一般哲学问题进行的直觉和反思,俄罗斯哲学在宗教形式之下所处理的仍然是生发于现实且与人的生存境遇紧密相关的问题。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哲学在处理与传统哲学、宗教哲学、苏联哲学、西方哲学之复杂关系的无序境况中走向沉默,丢失了自身的价值支点和根本信念。有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哲学失去了中心议题,不知何去何从。“白银时代俄罗斯哲学家以及他们的著作只是今天俄罗斯哲学家阐释的对象,他们思考的问题,即出于对人类的命运与道路、历史的意义与目的等问题的关注而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却很少有人问津。”①斯米尔诺夫在论及俄罗斯哲学的发展现状时也谈到了这一点,他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对立:“现在的一个极为尴尬的处境就是,一方面社会对哲学有需求,但另一方面哲学对社会需求没有回应。换个说法,俄罗斯现在发生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对立的问题。个体意识主要指哲学家们的个体意识,社会意识指整个国家对哲学的需求以及哲学对现实所做的回应,在它们之间发生了对立。”②可以说,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哲学未能在把握时代精神的前提下构建起新的理论论域,进而完成哲学理论的范式转型以回应时代问题。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哲学系学者弗拉基米尔·波鲁斯(VladimirN. Porus)认为,现代俄罗斯哲学缺乏在本土和全球文化背景下确定自身地位的勇气,已经从过去占据的中心位置沦落到俄罗斯文化的边缘:“哲学可以通过回归其最初的目的来重新获得其尊严和文化意义——即对人类(更准确地说是文化)存在的基础进行批判性分析,并有意识地将其综合项目的发展作为社会和个人发展的目标。这似乎是当今俄罗斯最重要的任务,但我们在处理这个任务时过于谨慎,导致我们无法应对时代的挑战。”③
(三)末日论精神的复活
别尔嘉耶夫说过,俄罗斯民族历史使命的终极特点是末世论的,这是俄罗斯思想的“世纪性选择”④。每当风云变幻的历史时刻,俄罗斯民族总会迎来末世论神话的复活,当前俄罗斯的文化危机也体现出这一特点。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的主要信仰,相较于天主教和新教,东正教更为典型地体现出保守主义、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三者的相互作用造就了俄罗斯民族温顺忍辱的性格特质和自我牺牲精神,而这种性格也是酝酿末世论情绪的沃土。牢固的末日论渴望使俄罗斯人倾向于在终结的意义上讨论现实的尘世生活,渴盼救世主的降临和完满的新世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全球秩序动荡的背景下经历着持续的动荡,导致社会上弥漫着末世论情绪,反映出人们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对某种特定事物的恐惧,而是更加普遍的对于混沌的、支离破碎的内外部世界的恐惧,映射出个体的生存状态和危机意识。
二、异化发生:文化基础的解构与市场化突变
当下俄罗斯所面临的文化失落固然与该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传统基因、更久远的历史沿革密不可分,也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为现代化模式必然导向的危机。对此本文不作进一步讨论,而是着眼于俄罗斯近三十年的社会文化实践进行反思。布拉夫卡-布兹加林娜沿着这一思路将研究视野回溯至20世纪末,将该问题与苏联-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初始时刻相关联,揭示了当代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范式不仅破坏了苏联的文化遗产及其人文潜力,还剥夺了作为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之衡量标准的“人”的意义,导致俄罗斯文化领域遭遇全面异化。“可以说,现代市场中人的聚居地是一个本体论死亡的时空体,在那里历史被剥夺了运动,文化被剥夺了活生生的关系。”①
(一)自由主义转型中的断裂和解构
20世纪末,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混沌现实中开启了全方位的自由主义改革。在布拉夫卡看来,正是这样一种在短期内以激进方式展开的制度转型扼杀了文化发展潜力,留下积重难返的结构性难题,M9sOLQhVmVySEfHPzXG3dQ==导致其后文化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总体低迷与力不从心。究其原因,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转型是在原本框架经历崩塌式解构的前提下展开的,对于整个国家发展而言都构成了一种断裂性的变动。自由主义改革未能解决苏联制度的矛盾,使得“解体”本身成为当代俄罗斯社会现实的普遍关系。从这个视角来看,俄罗斯文化领域的整体失落与全面异化正是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国家制度转型时期埋下的种子。
布拉夫卡区分了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存在的“过渡”和“否定”两种状态,并指出从苏联向俄罗斯自由主义模式的转型,实际上仅仅表达了对苏联制度的“否定”而未能真正实现“过渡”。首先,“过渡”这一概念是一种辩证的否定,应包含“否定之否定”的意蕴,即在解决前一阶段的矛盾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从苏联向俄罗斯的过渡因其并未解决苏联社会现实的矛盾,而恰恰是一种非辩证的“纯粹否定”。“从苏联制度向俄罗斯制度的过渡实际上是在历史发展的典型辩证法之外实现的,即不是基于积极批判(否定之否定),而是以纯粹否定的形式(‘赤裸’‘空洞’)对整个苏联制度的全面否定。”②其次,这样一种非辩证的“纯粹否定”意味着前后两个环节之间存在断裂。也就是说,俄罗斯社会诞生于与苏联制度相分裂的逻辑,这决定了俄罗斯社会现实及其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分裂的产物,所谓的“断裂”指的是在苏联和俄罗斯社会现实之间存在未被澄清的矛盾地带。正如布拉夫卡所说:“正是这种解构性的起源定义了整个俄罗斯系统(经济、社会关系、政治)的社会性质,它的普遍末日论精神。”③再次,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作为非辩证的否定,使系统内部的矛盾和解决矛盾所需的潜能变成一种虚无,其结果是系统本身的停滞。这是因为,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一方面没有解决苏联制度的关键矛盾,使这些矛盾在系统中得以保留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破坏了苏联制度的发展潜能,进而彻底抹掉了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在布拉夫卡看来,矛盾本身是系统发展的内在动力,但非辩证的“纯粹否定”抹杀了解决矛盾所需的潜能,使矛盾本身变得“无力”,无法再作为一种动力。“因为一旦发展潜能被破坏,这个潜能现在就变成了虚无,这意味着在辩证关系中的这个矛盾变得‘无力’。换句话说,系统的发展潜力被剥夺,使得它无法通过内部的辩证过程来解决自身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导致了停滞和衰退。”④因此,俄罗斯的制度转型不具备完成过渡的社会现实前提,破坏了苏联制度的基础并将系统的“活”矛盾发展为“死”矛盾,使得文化发展走向死胡同。
(二)文化基础的市场化突变
如果说从制度解体和转型的开端来看,俄罗斯社会的解构性起源为俄罗斯现实的普遍关系打上“解体”的烙印,导向文化领域的整体失落,那么,文化世界的全面异化则是在俄罗斯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达成的。资本主义批判历来是当代俄罗斯左翼思想家的重要研究主题,在当代俄罗斯学界,已经有一系列理论成果致力于从该视角出发探讨文化问题。布拉夫卡也强调,在21世纪的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发展和新一轮信息技术的影响下,市场总体性对社会生活的瓦解和压制导致了文化世界的全面异化。
近十年来,在各种新兴数字技术的共同作用下,全球资本循环和资本积累的新形式重塑了资本主义的运行模式,不断更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样态。马克思曾说过,现代社会中资本逻辑的强势驱动和全球扩张将“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①。今时今日的市场成长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全球资本霸权中,新自由主义模式导致的结果是:“市场关系不仅是经济的唯一和普遍形式,也是几乎所有社会进程——从教育到个人生活——的唯一和普遍形式。”②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扩张助推市场关系的全方位渗透,市场关系发展成为异化的总体性力量。在这种市场总体性下,社会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无从逃避市场关系的影响。布拉夫卡延承了法国后现代哲学的关键概念——拟像,用以阐释当代俄罗斯的文化景观。拟像意指对没有原本的东西的摹本,它无需真实原物即可把“不在”表现为“存在”,还会反过来吞噬现实事物的真实。在布拉夫卡看来,21世纪的现代市场正是所有领域的拟像的综合体。具体而言,在经济领域是作为品牌的商品,在政治领域是作为政治姿态的原则或立场,在文化领域是作为人工制品的艺术现象,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市场同构”进一步强化了全球资本霸权的力量。“拟像市场征服了信息空间和商业运作、人际关系和正式机构、创造力和艺术领域,获得了全面的权力。因此,文化、人和社会都被置于市场的极权力量之下,市场不仅决定了它们各自的社会存在形式,也决定了它们的内容。”③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成为拟像形式的产业,受到商品拟像拜物教的统治。从唯物史观视角来看,文化本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化,以其自身的普遍性意义从整体上观照与诠释现实。但是,市场极权主义的主导使得文化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转变,文化直接受制于市场和资本的通行法则,其结果是文化本身的深层基础发生质变。布拉夫卡从历史视角分析对比了文化与市场的关系:过去,市场对文化的影响主要是以间接的形式展开,需经由宫廷、教会、国家、政党等社会机构的中介;如今,市场总体性和全球资本霸权使得文化在内容上趋于市场化,在形式上趋于拟像化。“其结果是,曾构成文化作为普遍关系和文化主体间相互关系世界的本质和实质的一切,现在都被一种根本不同的范式取代了。”④
(三)个体的无主体存在与功能分解
众所周知,人是历史和文化的主体,人之于世界的定位历来是哲学和文化的核心问题,当代俄罗斯文化领域的异化更为深层地表现为文化主体的异化。从历史视角来看,这是现代文化发展的普遍性问题。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就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主导控制作用使得人的本质陷入单向度化的异化困境。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异化本质时,也用“主体之死”来宣告具有独特风格的个体性主体在后现代文化境况中已然丧失主体中心地位,走向分裂和终结。在布拉夫卡看来,文化主体的异化主要体现为人的无主体存在与功能分解,个体从文化主体降格为客体,作为一种功能而存在。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主体被分散、打碎,主体存在降格为抽象的私人存在。在当代俄罗斯,人的无主体存在并非文化领域的个别现象,而是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普遍问题。“俄罗斯现实面临的一个最复杂和最痛苦的问题是,今天个体在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都不需要作为主体,更不用说文化或历史了。”①这一点可以从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说起,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存在个性自由与集体意志互相缠绕的矛盾性。当代俄罗斯人往往将弥赛亚意识、强国主义、国家主义等既定观念奉为最高价值、视作绝对不可改变的超越性存在,这些精神上的落脚点使他们难以克服主体意识局限。此外,在语言学的研究视域中,语言体系作为一种文化表达,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对世界的理解框架和感知方式。具体而言,汉语和英语的表达通常注重主体思维,强调施动者,相比之下,俄语句子的词序可以有多种排列方式,在形式结构上存在主体和主语不对称的情况,这种差异也反映出不同文化表达中主体意识的不同。斯米尔诺夫将语言学视角纳入对俄qf0O0su1Zhg9u+NAoxu59pAQeG/i4PhjuShbKI1wu+w=罗斯本土文化特质的研究中,揭示了俄罗斯语和西方语言在语法结构上的差异。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连接主谓的能力,俄语的语言体系将主体打碎,主体性被投射、分布到主体周围世界的整体性之中,这种差异也导致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事实上,对于处在文化转型中的当代俄罗斯人来说,公众长久以来对于公共自我和私人自我的认知比较模糊,人们在经历了政治文化混乱的背景下,对主体存在的原则难免感到陌生和不安。“现代人摒弃了与个人主观存在相联系的过去——此种过去存在于苏维埃制度中,与墨守成规进行激烈对抗,同时又害怕需要进行社会创造性活动的未来,因此只能无助地面对自己的现在。然而,当下的个人被市场和官僚关系网络所吞没,注定成为一种自我异化的存在。”②
其次,市场极权主义和信息技术的支配将个体变成社会、市场和政治操纵的对象。文化、社会和个人对于商业法则的严格服从,客观上强化了社会的异化总体性,文化的创造主体受到社会异化的羁绊,其直接后果是人的完整性的丧失。这尤其表现在,消费从一种功能变成人的生活方式,人的完整个性被分解成若干消费功能。布拉夫卡指出:“如果一个人在生活的任何领域都不被要求具有特定的个性,那么他就注定只是一种形式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虚无。”③如果19世纪俄罗斯小说创作史中的“多余人”代表着贵族知识分子的经典形象,那么在今天,人在无处可逃的情况下只能被迫进入抽象(私人)存在的黑色方块,从“多余人”沦为“多余的附属品”。
三、文化重启:主体性的突围
文化危机是社会结构性困境的文化表达,折射出与之相关联的社会境况。可以说,当代俄罗斯社会在很多领域经受着一系列挑战,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蹒跚,面临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恶化、经济结构畸形、政治治理成效低下、决策系统僵化等严重的内外部问题。近年来的社会调查研究也反映出俄罗斯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不足,根据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和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在2017年夏季联合调查的数据,大约60%的俄罗斯人希望国家实行“坚决而全面的变革”④。俄罗斯左翼学界对此已形成共识:现代俄罗斯呈现为“倒退式资本主义”,现行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不具备相应的发展潜能或者说没有形成发展潜能的基础,而后者是制度进行良性演化革新的载体。这种倒退尤其体现为文化发展潜力的倒退。
进入21世纪以来,俄罗斯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断回温,掀起了一轮向苏联时期文化模式转向的潮流。这种怀旧情结已成为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一种时代症候。“今天,人们不仅从逝去的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待苏联这个主题,而且或许在更大程度上将其视为一种现实的某种先例,这种现实至少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范围内承载着一种发展前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主线。”①这种诉诸于苏联经验的做法关乎对俄罗斯当前境况的反思,其目的是为了跳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文化陷阱。
文化关系到人在世界中如何自处的问题。当代文化的主要挑战与人的主体性密切相关,没有主体性的形成,任何历史和文化的发展都无从谈起。布拉夫卡将主体性问题作为重启俄罗斯文化的支点。在她看来,主体性是对个人存在的有原则性的坚守,意味着个人的立场、行动和责任,如果没有主体性,人就不可能成为历史和文化的主体,而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人的主体性集中体现为社会创造性。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体范围内确立起社会主义新方向,开启了“后资本主义”性质的进程,试图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将社会现实从各种异化形式中解放出来,并辩证地解决产生这些异化形式的矛盾。布拉夫卡将苏联制度的本质界定为去异化的创造性社会关系,也就是根据新的价值观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和活动形式;而苏联之所以能回应所面对的各种矛盾,关键就在于主体发挥了其社会创造力。“正是对现实进行共同的和创造性的改造的实践,将主体性原则体从异化的力量中解放出来,决定了苏联历史的国际主义和苏联文化的世界性原则。这就是苏联制度和苏联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世界的问题能够作为自己的问题来解决,也使自己的问题作为世界的问题来解决。”②
布拉夫卡认为,社会创造性活动预设了人必须作为历史主体和文化主体的辩证统一,这带来了个体存在范式的历史性变革。一方面,社会创造性活动不仅旨在解决社会现实矛盾,也是个体主体性发展的载体。创造性活动的解放趋势决定了主体的存在原则发生了质的改变。正如布拉夫卡所说,“20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的特点是社会创造力的发展,不仅与解决最紧迫的问题(清除铁轨上的积雪、建立农村学校和俱乐部、卸载货物列车、组织前线剧院等)有关,而且还与个人创造融入各种文化创造的社会形式有关”③。也就是说,十月革命重新设定了主体存在的原则——对历史进程的积极干预。④社会创造性活动使群众赢得了参与、组织、安排社会现实的权利,群众成为了历史变革的主体。只要一个人在现实实践中克服了某些特定形式的异化,在这种去异化行为发生的当下,人就实现了自己的主体存在。另一方面,个体只有在创造性活动中才能实现其主体性存在,个体也必须不断发挥创造力以获得作为历史和文化主体的权利。“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主体性的完整性,他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确定自己作为人类的发展前途。”⑤
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涌现出数以万计的新型社会组织形式,遍及经济、教育、慈善、科研、艺术等众多领域。这一时期的社会创造性活动形成了大众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一方面揭示并克服了苏联初期在文化上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实现了文化主体的自我需求。特别是在社会公共生活和文化领域,普通民众的创造力被唤醒和激活,群众广泛参与各种文化艺术活动,其规模是过去无法想象的。然而,在当代俄罗斯,创造力从个人生活中被直接剥离出来。在全球资本霸权、市场极权主义和官僚机构的统治下,个人只能作为一种功能性存在,人的个性、观点、风格、品味均服从于市场规范的统一标准,其结果是人丧失了存在的主体性。“如果个人存在的形式甚至在文化中也被排除在外,那么今天的个人在哪里以及如何形成为社会主体?”①
布拉夫卡认为,以社会创造活动为基础的文化价值原则可以在揭示文化的现实性的基础上消解文化消费主义,重新生成个体对文化的真实需求。对于主体来说,文化不应仅仅表现为商品,而应首先成为创造新的社会生活的工具。与此同时,社会创造性活动基于真正属人的主体间合作关系,排除了商品买卖原则和官僚结构的等级从属关系,使得文化成为克服异化统治的一种新突破。“一个时代的文化更新的本质是在辩证对待过去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个人本体论的必要性。”②布拉夫卡认为,十月革命后,苏联完成了对文化模式的革命性重置,在创造性社会实践的地基上重建了新的主体性原则,为苏联社会提供了发展潜能。正是这种主体性原则被布拉夫卡等当代俄罗斯学者视为化解21世纪俄罗斯文化危机的跳板。
[责任编辑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