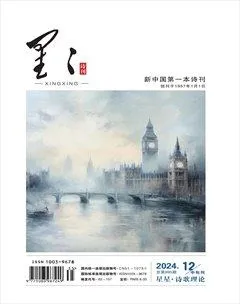马背和鹰翅上飞翔的诗人
阿古拉泰是中国当代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是中国著名的诗人,是从内蒙古走向全国的文艺界艺术家。提到阿古拉泰,我想说的话很多。作为一个诗人,我与阿古拉泰相识四十年,就从一个诗人朋友的角度谈一下我认识的诗人阿古拉泰。
1982年,我从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的《星星》诗刊工作。1984年,刚走出校门不久的阿古拉泰与另一位年轻人雁北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麾下正忙于创办《诗选刊》。也许阿古拉泰天生就是一个诗人,经过几年的努力,两位同龄人创办的《诗选刊》异军突起,命运让阿古拉泰一踏入社会就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诗歌引领文学潮头的时代。1984年我开始从退休的老主编白航手上接任《星星》诗刊的工作,虽然在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折腾”下,《星星》诗刊办得风生水起,发行量迅速上升,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主管的《诗选刊》却成为《星星》强有力的竞争者,甚至有诗人说:“北有《诗选刊》,南有《星星》。”
当时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在中国诗坛影响最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发行量曾达到六、七十万份,占据了全国的图书馆以及大中小学等主流发行渠道。《星星》诗刊当时只是一家省级刊物,主力订户靠中小城市的底层青年人和诗歌爱好者自掏腰包,因此邮亭、报摊是《星星》诗刊的发行主阵地。从1982年到1986年,靠着这种游击战术的不断开疆扩土,《星星》诗刊的月发行量从一万多份上升到五万份。到1984年,我发现情况有了变化,在各地的邮亭、报摊上,《星星》诗刊的旁边多了一本《诗选刊》。经过认真研究,我发现这本刊物装帧讲究,选稿面广,不仅许多地方小刊、小报上露面的新人因入选《诗选刊》得以进入诗坛,而且许多名家的大作也能在这里得到推广。两个年轻人,一家边疆出版社,一本横空出世的《诗选刊》,让我惊叹不已。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诗选刊》的月发行已近三万份,超过了当时许多诗刊、诗报的发行量,发行增长势头紧追《诗刊》和《星星》。这让我这个主持工作的人不能不感到赛道上多了个厉害的对手。
1986年夏,老诗人胡昭、芦萍牵头在北戴河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诗会。非常幸运的是,我在这个会上认识了阿古拉泰,一位蒙古族小伙子,文静儒雅,又激情跃动,说话笑眯眯,标准帅哥。交谈中,我知道他是个真心热爱诗歌的人。诗会期间,我记得阿古拉泰谈到办刊的不易,他在回忆文章《不老的艾青》中记录下了当年的一些办刊情况,“在寂寞偏远的西部草原,办一份‘选刊’,谈何容易!要有名师指点,要请名家来当顾问。名家首举艾青,他是诗坛泰斗,当之无愧。于是,连夜写信寄往北京。苦苦的企盼中迎来喜讯,高瑛老师信称艾老已允,并有题词一幅:‘新诗充满希望’,随信寄来。简直是一夜之间梦想成真……《诗选刊》异军突起,声誉日隆,社会影响、经济效益稳中有升……来稿、来函,乃至来人源源不断,隔三岔五,便有一两位风尘仆仆、衣着不整、面色憔悴、披散着长发的男诗人或削着短发的女诗人,背着行囊骤然降临,勇士一样自报家门:诗人××,徒步考察黄河……长城……造访‘驿站’《诗选刊》。像怀揣‘鸡毛信’的海娃,历经艰辛终于见到组织,纵情倾诉,半躺在破椅子上,望着天花板话语滔滔地颂扬《诗选刊》,讲述一路见闻,而后奄奄一息的样子……我和雁北责无旁贷地掏出散金碎银,精心打点这些踉踉跄跄、披头散发、同命相连的诗人们,自然也是苦中有乐。一个月刊两个人办,每每还要招架此等意料之中的‘意外’,我们一点也不比徒步考察轻松,甚至有些身心疲惫,却乐此不疲”。这篇文章让我想起当时的交谈,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因志趣相投而惺惺相惜。老话说作家是编辑部的“衣食父母”。要知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办刊物真是如此,办刊物的人要把作者当作亲人。当年我在《星星》诗刊做编辑时,因经费有点积累,来了有点名气的诗人,编辑部会全部人马出动作陪。请诗人吃饭时我常开玩笑:“这是罗汉请观音,好饭好菜还是自家人吃得多。”如果遇见了游走的、有困难的诗人,更是会设法资助。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诗歌让人们精神上富足;诗坛也相对淳朴,诗人与编辑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利益交换。
北戴河之行让我和阿古拉泰成了好朋友。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热情真诚,善解人意,体谅他人,没有某些作家身上的江湖气。这些人性中闪光的修养让我明白阿古拉泰为什么能把北疆边地的《诗选刊》办得风风火火。可惜在北戴河相见后的第三年,正在势头上的《诗选刊》突然停刊了。当时有传言刊物是由内蒙古地方出钱,刊发的作品多数是外地的,被当地批评办刊方向有问题。我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遗憾,根本没有因少了个竞争者而轻松,心底泛起的却是失去同行者的孤独感。回首这段往事,初登诗坛的阿古拉泰不是以诗人的作品名世,而是以开疆拓土的创刊勇士为中国诗坛创造了一个奇迹。两个年轻人创办的《诗选刊》,影响广泛,发行量高,声誉鹊起,成为八十年代中国诗坛现象级的文学事件。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在各民族诗人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阿古拉泰是草原的儿子,也许就像转场的牧人一样,从办刊物当编辑为他人作嫁衣裳,很快在诗坛转而成为一个诗人,自信而自在。阿古拉泰步入诗坛后,他的才华像骏马一样,在稿纸上驰骋,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和散文。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他立足中华,放眼世界文坛,其作品高雅深沉,在空前喧闹繁杂的文坛如一股清泉,独具风范。到目前为止,他先后出版了十九部诗文集。更令我敬佩的是,在此期间他让诗歌插上音乐的翅膀,由此成为一个著名的词作家。这对于诗人是一大胆的“破圈”之举,同时也是对当时中国诗坛流行“小众”“反抒情”“不迎合一般读者”“白领智性”等思潮的大胆逆行实践。我常听到歌手们唱阿古拉泰的《这是英雄上马的地方》。因创作了大量在中国各地传唱的歌词,阿古拉泰成为当代中国歌坛著名的词作家,先后结集出版了九张歌曲光碟;他担任交响音乐史诗《成吉思汗》以及舞台剧《马可·波罗传奇》的文学执笔,让舞台艺术更具文学性。当然,这一切与我们这个时代分不开,更与内蒙古各界对他的认可、重视与关爱分不开。他的努力得到社会的高度公认,现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等职务,内蒙古也授予他“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殊荣。但我认识的阿古拉泰却始终低调谦和,这让我想起一句“将军本色是诗人”。在荣誉和成就的光环中,阿古拉泰最清澈的底色仍然是一个诗人,是一个在马背和鹰翅上飞翔歌唱的骑手。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在2024年6月出版了阿古拉泰的文集《黎明拾穗》,这对于读者了解阿古拉泰非常重要。这部文集中的诗篇小辑部分取名“言志”,精选了《众鸟高飞》《像一棵草一样行走》《浅草上的蹄花》《孩子与鹰》《母亲站在蒙古包前》等近三十首短诗、组诗和长诗。阿古拉泰将小辑命名为“言志”,我认为既表达了诗人的心迹,也表达了对中华诗歌传统的敬意。我曾用诗言志、诗缘情、诗无邪表述过中国诗歌精神的核心。在进入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当下,很多诗人越来越难以找到自我的定位;在漂泊变化的人生历程中,许多诗人难以确定自我的精神谱系及艺术生命基因。当我读到阿古拉泰的这些诗歌,不仅再次看到了青年时代为了理想而打拼的阿古拉泰,也看到了他为读者呈现出的一条溯流觅源的诗歌写作方向。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些诗篇中,小草、骏马与鹰这三个意象反复地出现,也正是反复咏吟这些诗句时,我意识到作为一个诗人的阿古拉泰,就像草原上的一棵小草迎着春天的阳光;作为蒙古人的后代,他的胸腔中激荡的是奔马的蹄声;面对天地,他推开一扇心窗,心巢之鹰就向着碧空亮出翅膀。小草、骏马与鹰,三个极其重要的意象,是情之根系,是心之向往,也是诗之胸怀。这就是阿古拉泰的自画像,也是他的精神图谱、情感血脉和生命基因。
阿古拉泰是草原的儿子,只有了解他的成长经历,阅读他来自生活的散文小札,感受他为那些远行的前辈写下的缅怀之作,倾听他为婚姻的伴侣写下的真诚祝福,才会感受到他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熏陶下作为一位诗人、散文家、词作家和文化学者的风范。诗人是活在人群之中的仁者,识人间烟火,怀平凡亲情,真心敬师待友,值得信赖依靠。这一切,也让我看到一个“人诗互证”的范例,也为我有一位相伴一生的诗友而感到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