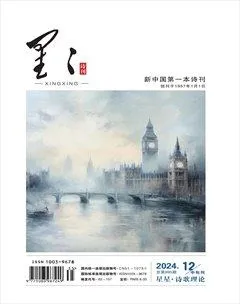“炼”:从“恋”到“链”的诗意传播何以可能
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的西塘镇紧邻上海,深受海派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既保有古典江南灵慧务实的传统底色,又敞开包容的现代胸襟。用紫藤睛儿的诗句来说,“西塘古镇是我们共同的部分”,像我们代代传承的肉身,活在一首诗的吟诵之中。
我曾经多次到过西塘。行走在古镇中,烟雨迷蒙,水榭长廊,曲水流觞,舟橹荡漾,像一首精致碧玉小诗的起承转合,现实和幻象互为倒影,既伏采潜发,又神韵悠长。如今在数字化光影的装饰和地方政府的治理下,西塘明眸皓齿,一如水城威尼斯前世走散的姐妹,在汉语之滨临水梳妆,楚楚动人。如王选在《流水辞》中写道的,“在西塘 烟火迷蒙/有人用刻刀重塑时光 用木屑煨亮内心的炉火/有人在巷弄用侧身 把一生的逼仄走完/有人临水而居 有人灯下相逢/有人把芡实糕捧于手心 看清了中药和大米握手言欢的喜悦/有人以墙为马 有人在一杯清茶里搅起江湖”。这是人性多姿书写的喻象迷宫,也是世情繁复撷取的人间样本,无论是东方读者还是非汉语阐释者,读这样的诗都是一种有幸、有缘、有福之事。
诗赛活动的打造与诗学的加持,赋予西塘古镇一副全新的翅膀,这是诗歌功能的全新拓展,也是生逢其时的诗人们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西塘借文化赋能走向四面八方,历经八年的成长,“恋恋西塘”已成为嘉善县的一张文化名片。其中,实现诗歌搭台、经济唱戏的双赢功能何以可能?正是紧扣一个“炼”字,推动地方之“恋”向传播之“链”的诗意转换,而“恋恋西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剖解研究的样本。
地域书写的真诚度,是从“恋”到“链”的东方拱桥。我曾提出一个观点,诗歌的首要敌人是假大空,次要敌人则非陈词滥调莫属。在假大空已成过街老鼠的语境中,诗界要与陈词滥调做持久不懈的斗争。而征文大赛、采风之作往往存在着一定模式化的陈词滥调的可能,如何克服这一瑕疵,“恋恋西塘”做了较好的探索。
本届大赛的获奖作品共有四十二首(组),不论是现代诗、古体诗,也不论是组诗、小长诗,还是等级奖或作者是否为著名诗人,其文本都不是拼凑的。如王选在《听雨》中写道,“于荒草中 割开一条路/秋雨 提着她的小灯笼”,诗人独辟幽径,像一个考古发掘者;在《流水辞》中写道,“而他却交出盘缠 放下衣襟 以流水和青瓦示人”,其感发是真切的,交出的“盘缠”也是实诚的。再如郭全华的《我,是西塘鲜活的散句》,鲜活如“一抹古韵墨香,落在西塘的宣纸上”,通过“豆花唤醒的味蕾”,他许下“我愿意成为你一部分”之愿,这个愿景是真诚的,承诺也是真挚的。
在全部作品中,李浔的组诗《西塘田歌》是真挚性的代表。诗人像一个当代的江南士大夫,在自然简洁的风格化叙述中,一派天真烂漫。如《回乡记》中,“梁上有牡丹,中堂有仙鹤/祖先坐过的凳上有着好客的气息/唐宋的老镇,明清的屋,西塘的水/八仙桌上的杯知道,茶泡半,酒要满,客随主/回乡的人,仍和老灶、风箱一样顺手/我知道,你在春天什么都说/尤其是喝了碧螺春之后/这个老男人,眼里有了水汽”。作为一个现实中疲惫的“老男人”,沿着《回乡记》的分行小径回乡,“我”的代入感特别强,眼中的“水汽”,既是情动于中的泪意,也是老眼昏花催生的生理结果,在亲切平和的语气中,“我”被还原成了内心唏嘘不已的沧桑之人,一缕“祖上”的“味道”和“气息”如祖传秘方带给读者满心欣悦。李浔数十年来一直主张“用吴方言写作”,沿着朴素劲健、柔韧绵远的江南河岸兴观群怨,步子越走越轻松,言志抒情的背影越走越丰盈。与李浔相近的还有宗小白,她在《瓦当轶事》中写道,“为雨水淋湿炊烟,也淋湿冬日细绳上/晾晒的萝卜白菜,以及福与喜的篆字/在脑海里回旋往复的纹样”。这是一首口语叙述的佳作,这样的风月抒写,需要才华,需要眼光,更需要真诚。
近年来各地的诗赛、征文活动此起彼伏,真正能避免模式化写作的不多,以至于产生了“获奖专业户”和“参赛体”这样的负面之说。而“恋恋西塘”诗歌大赛坚持个人化原创优先原则,拒绝平庸之作,走智性和感性融合书写之路;在地域文化符号和人性深度开掘方面独树一帜,走出了一条具有智性符号的深广之路,是从“恋”到“链”的观光大道。
浙江诗人陈墨在纷纭繁复的地方意象中独辟蹊径,用情爱命运的跌宕穿越来凸显个人的挚诚情怀。他在《江南胎记》中写道,“一曲渔歌:山突兀,月婵娟/有人牧月,有人迷失于万家灯火//吴镇兄你教我的,也将教会孤鹭/以它低飞的双桨临摹着你慢慢的暮归//水墨的幽暗留下了/谁内心汹涌的独白”。这首小长诗虽只节选了三节,但大块状的跳跃叙事、大幅度的意趣留白和痛快节制的事象抒情,加上句子简短有力,节奏激烈如鼓点,把五姑娘、吴镇和抒情主体的前世今生连接成一体。“仿佛火苗放进干柴”,哔剥声中推出的西塘之“恋”不只与地名相恋,也是白首盟约之“链”。如此诗意蕴藉的智性抒情,不仅满足了诗赛举办者的显性诉求,也充分必要地满足了诗歌审美自足的本质要求。
李遂的《西塘小语种》短小精悍,如绝句或小令,但绝非古人情绪的简单化拷贝,其诗在流丽清亮、睿智灵动的基调中,加入“进行曲”“不确定性”“生活手册”“墨镜片上的反光”等元素,既是对诗作文本的现代性标示,也是对诗中承载情感的异质性、悖论性的有效嵌入。胡云昌的《在西塘木雕馆,抚摸一件老家具》中,他以“智性瓦片”在司空见惯的水面激出一片涟漪,“我,一个简体的人/在西塘,闯入繁体的明清木雕馆/……/一件老家具,古旧/包浆着大沧桑”,打捞出“一声不吭的亲人”,这是诗人向包浆岁月的诗意撒网。罗燕廷的《断章:世外西塘》中,“西塘是另一种水。或者/是在镜子中取出来的一粒露珠/在晨光中浮动”,这是一颗敏锐多思的诗心的感光反映,属于向绒毛般细微处摄取的成果。
大赛诗写的技术性,是从“恋”到“链”的现代性转化。如何评价技术繁复之作,也是大赛活动的难题之一。“恋恋西塘”诗歌大赛的参赛作品表明,清新晓畅固然是一种真挚,往往受活动主办方偏爱,但技术繁复的先锋探索之作照样能跻身获奖作品之列。如惭江在《烟雨长廊》中写道,“这长廊,如一个女孩的伞下/仍然是不期而遇,于某处屋檐/一进,两进……再进/庭院缦回。互相看见彼此的心宇/互相走进对方的眼神/而没有尽头”。这首诗的传统意义大于先锋意义,其精彩之处在于借用东方建筑结构的形式特征,将人与西塘、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相遇相拥写得引人入胜。如果说这首诗仍有前人技巧痕迹,那么杨旭的组诗《西塘素描》则更像西方形式主义油画,意象繁复、语流堆叠、画面峻切,堪称现代学院式写作的一次实验探索,在大赛诗作中是比较罕见的。如杨旭的《石皮弄笔记》中,“时空逼仄,不经意的侧身/便错过被压缩的历史/高墙深巷,积淀太多的遗忘与古今/只身闯入如一粒贫瘠的火种/在史册的扉页找寻明清的古迹/亭台轩榭,戏子的戏腔与白墙共鸣/星辰被压得很紧,仰望的人得到/……/直面倾斜的坡度,借来身位/扬鞭,白驹过隙,细数雨滴潮湿青藓/浸润被洗刷的足印,回声在反复膨胀,清晰/……有时一个人/像一支没有划痕的铅笔,在石皮弄/这个巨大的凹槽里检阅,并摘抄/另一份身影,相互依偎”。这已不是现实的地域投影,而是经验、记忆、情绪、幻象、无意识和梦境经由现实催发,于内心深处发生的化合反应,是空间斑驳与光影膨胀中的凸凹嵌套,是一种穆旦式的变形与扭曲书写,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语象化、镜像化和不存在的心灵化的西塘。
总之,诗歌写作本身就是一场大竞赛,在海量诗歌作品经典化进程中,诗人、诗作、刊物、评奖、选本、文学史提纯等环节,无一不是时间与历史严格筛选下的马拉松式较量。尊重审美规律,鼓励百花齐放,致敬诗人“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锤炼诗意与诗情的同时,也应认识到,为人类提供鲜活的一手经验,不仅是每一位诗人的必修课,也是诗赛举办者必须正视的实践课题。
“恋恋西塘”是一个融合水韵、江南风情与文化底蕴的诗歌品牌,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传播的扁平化时代,如何借助资本将地方资源转换成消费者内心的向往,需要地方政府和文化工作者合力解答。诗歌的地方性和家乡感给人提供的是一种精神还乡之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次诗赛中的“石皮弄、五福桥、木雕馆、纽扣博物馆、智慧田、乌篷船”等物象,构成了诗化的“恋恋西塘”乌托邦,具有较高的家乡认同感和地方辨识度。如果能给阅读大赛获奖之作的读者带来更温暖、更贴心、更亲密的家乡认同感、地方感,那么,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恋恋西塘”的成功,也是诗的胜利,更是诗人的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