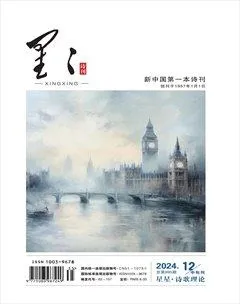引力在悲喜之间娴熟切换
北鱼的家乡在东海洞头,一个由三百零二座岛屿组成的“百岛之县”,现在是温州市的一个区。洞头西南有一座大瞿岛,说它大,是相对于中瞿岛和小瞿岛而言的,其实际面积仅略超过两平方千米,山下有两个渔业村,另一个自然村在山上,以林业和农业为主。北鱼出生于两个渔业村之一的蜡烛台门村。关于这个以蜡烛命名的出生地,北鱼写过《蜡烛台门缩写》一诗,“海上的门至今未得一见。但我确信/我经过了。一股几经折叠的愿力//将我传送出童年,又以荒芜的速度/关闭了回流的甬道//是月光?还是更遥远的马达声/将蜡烛台门擦亮,又隐藏”。故乡就像生身父母一样,是不可选择的,具有唯一性,它是“传送”也是“关闭”,是显在也是隐在。记忆只是部分的拯救,隐在的“失忆”总是更多,因为遗忘是人的本能。北鱼在《林场速忆》中写大瞿岛山顶的林场,“有日落的担忧,但不远处的岛/有更神奇的工具,将晚霞一一收留”,尽管有“神奇工具”的收留和慰藉,但“有一座老村正在失忆,好心劝我/不要去、不要去”。如此,北鱼的家乡记忆和海岛记忆就有了一种百感交集的复杂性,是离开与回望的徘徊、思恋与“不要去”的悖论,以记忆之名发愿的写作,成为对“失忆”的某种抗衡。
2023年12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北鱼的诗集《江海有信》,该诗集由“潮间信”“少年锦”“劝降书”“空城略”“云中寄”五辑组成,题材和手法多样,给人一种弥散性的、声东击西的阅读效果,其中也不乏差异性的表达和多向度的探索精神。这部诗集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写大海,二是写现代城市生活。阅读完诗集《江海有信》,我再次看到海岛对北鱼的“引力”。他在《蓝》中写道,“天空的古老姓氏,潜泳的/第一道痕。当我向自己靠近//空气稀薄,雨和血的颗粒/如星球浮动、撞击。始终有//更小的裂缝,令引力在悲喜之间/娴熟切换”。诗中“引力”的切换,不仅仅在“悲喜之间”、天蓝与海蓝之间,更体现于个人身份的变迁、经验的切身性以及变化中带来的写作热情。从“渔后代”到“都市移民”,从海岛的“逃离者”到陆地的“栖息者”,日常性之“小”与大海之“大”,自我与“边界”,沉溺与超然,隐藏的与显现的……都交织在一起,“我因此而多变,因此/喜欢所有蓝:在鸟背,在鱼腹//在汽车观后镜意外的反照”。由此形成了北鱼诗歌多样化的变奏,保有“蓝”之底色,“引力”化为内在的角力和张力,写作如同一次次的“自我博弈”。
北鱼对大海的表达是冷峻的、非狂想的。因为他一出生就是“面朝大海”的:平静的海,发怒的海,神秘的海,渊薮般的海……这“自由的元素”(普希金)和“死者永恒的摇床”(兰波),被希尼称之为“非宗教的神力”。2023年我与北鱼有过一次洞头之行,他给我说得最多的是大海给人带来的畏惧感。“小时候,大人们总在提醒孩子,离大海远一些,更远一些。同时,有一些神秘兮兮的小庙,也不让孩子们接近,因为里面供养着凶神恶煞。”大海是一个多重的、复合的存在,具有凶神恶煞的一面,吞噬的、溺亡的、再也不能归来的……“每一次浪击,都是大海在疼痛/接近于妇女难产,渔民善泳/却窒息在思亲的浪花中//他们已不能再收缩”(《台风,或忌日》)。这种普遍的“窒息”,是一种不可捉摸的生死拷问,也是一座动荡无垠的坟茔。“他很记得:/出航和归港,应该在同一天完成//假如回忆即是动身,大海欠男孩/一次解锁的呼吸。”(《归港》)因为缺少“解锁”的机会,北鱼甚至在《不要宣传大海》中写道,“最好不要问归港的渔民/不要在宣传大海的框架内/搭构你的沉思。更不要问我//一个在海边投寄童年的旅客/海浪起伏……这样一条/蓝色被单,盖着鱼群和溺亡者的鬼魂”。与继续生活在洞头的余退、谢健健、叶申仕等青年诗友不同,北鱼选择远离海洋去陆地上寻找“另一个海”,建设“另一个故乡”。值得庆幸的是,他的“逃离”中没有撕裂感,也没有刻意遮蔽自己的少年记忆。事实上,离开是另一种归来。因为离大海远了,乡愁和思念浓了,海岛记忆也越发清晰了。
北鱼对大海的记忆和表达,有色彩,有音响,有潮汐不倦的韵律。大海是“一条蓝色被单”,然而他写得最多的是大海的声音。“鱼声马达就安装在我背后/无形且没有触感,类似于潜水艇/沉入大海,和鱼就没有了区别/……当它哒哒作响/故人的信就从云中飘下来。”(《鱼声马达》)好像他依然是一位海岛上的倾听者,拥有一台“过去的探测器”。无疑,这是一种张执浩所说的“不在的在场”。有时,他把大海推得很远,推成一个背景、一种象征,潮汐就变成了一封故乡来信。如《潮汐来信》中,“来时速写的追忆片段,多年后/如假消息淤积在喉,沙滩卵石堆叠//未能寄出的信,又高一尺/快要超出我的强度了//而肌肉松垮,源于我咽下难以消化的数行/我说玻璃碎片,你要继续对瓶口隐瞒//像大海隐藏更深处的蓝/告诉世人的,唯吞吞吐吐的海岸”。这首诗写得出色,精炼、微妙、传神,个人化和准确性都具备,有内在张力,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痛感。再如《柳岸》中,“柳枝超出的部分/和我看到的大海相似//我熟悉大海,拍击或是抚摸/它反复试探的,不是海岸/而是自己的边”。诗人探索自我与探索世界其实是一个道理,诗歌能够不断拓展的“边界”,既是自我的,又是世界的。向内,向外,冥合而同归。
我注意到,“登陆”后的北鱼一直在重构与大海的关联。《与子说》《风筝》《吹蒲公英的少年》等作品是写给儿子的。年轻的诗人却像一位有点絮叨的老父,“有时真不知从何说起/说:大海没有边?/幸运的是/我有一座岛,你可以/用折纸船抵达它,也可以用蒲公英”(《与子说》)。北鱼希望通过自己的孩子去赓续大海记忆、故乡血脉,“仿佛与过去交谈的可能/正被吹远,我急于寻找那根织网的线/正系在儿子放飞的风筝上/这无伤的轻叹,很快编入了风中”(《风筝》)。风筝与纸船、蒲公英一样,也可以成为连接远方与大海的中介。当渔村一帧帧关掉虎皮色,诗人和大瞿岛的关系出现裂痕,风筝之线正是织网之线,织风、织苍茫、织天地,诚如北鱼所言,“为了更无所用,我需要更多无用之物/成为驱动身体的按钮”(《假期练习》)。大海表面上看是“无用之物”,但对于出生于海岛的诗人来说恰恰是“驱动身体的按钮”,更是他无法割裂的血脉和根深蒂固的基因所在。沃尔科特曾在《另一生》中说“大海是一部史书”,而“大洋翻过一个个空页/去寻找历史”,于是“我在这里开始,再次开始/直至这个海洋变成/一本合上的书”。在此意义上,大海无疑能够成为北鱼的启示之书、无垠之书。
“登陆”后的北鱼是城市生活的观察者、体验者和思考者。与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中的单一色调有所不同,北鱼书写的城市更为多元、多彩;与拟古、复古的“新古典主义”写作也有不同,他是城市生活的接纳者、包容者——一个开放的主体,一个“现代性”的接纳者,同时保有怀疑、批驳和警觉。如《洗碗的过程》一诗就写得具体、生动,把一次日常家务劳动无限拉长了。如果大海是一种“大”,生活与日常就是一种繁杂而琐碎的“小”,所以北鱼诗中充满了这种“大”与“小”、“快”与“慢”的变奏与辩证,而且常常是以小见大、见真情的。如《早春,与蜗牛散步》中,“我制造的暖风,是求教的试问/如果我降速登至山顶,它捕捉到//露水折射的光,请问,时间能否/将一生计算得更长”。因此,诗人愿意与蜗牛散步,“翻越软泥褶皱/在春草的嫩绿腰身,研习更慢”;与草木交谈,“向曾经辜负的山水致歉”。借由与“慢的信使”一起散步,山之高低、风之冷暖、光之明暗、一生之短长,在一首诗中汇合、交融,并告诉我们,从“小”和“慢”出发,可抵“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塔吊黄昏》《卡车驼》《高架求索》《绿植碎末》《地铁虫》等作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是“寓言体”,也是“成人童话”,令人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所具有的魔幻现实主义意味。在《高架求索》中,“一条蜈蚣无止境地传送自己/在人类出行的时刻,它要表演/水泥般的假死”。在《卡车驼》中,“卡车驼认为自己是食肉动物/至少从前是或以后是。三十年前/一只卡车驼吃掉了我最心爱的小堂妹/也吃掉了我对卡车驼饲养员的好感/他们是食肉的一部分”。在《塔吊黄昏》中,“那么瘦,如何拉起/钢与石的笨重?高楼不再为劳力担忧/那么瘦的父亲,双臂也曾一边一个升起//日与月两兄弟”。
北鱼的现实触角是敏锐的,表现出感官的开放以及对多样性和新事物的好奇,对经验的超越。他在城市生活中辨认时令节气,《早春,与蜗牛散步》《初夏,摘抄金华路》《立夏,过半山娘娘庙》《仲夏,访清风馆》《秋日,登山有悔》……他用一种“自然视角”重新打量、审视城市生活。北鱼发现城市中残余的“自然”不仅仅是一种教诲和提醒,更包含着超越经验的可能性,“它的开花/更像是一种偶然,在生活的经验之外/……/心疼比纸更薄的土层,心疼植物的根和虫卵”(《植物的可能》)。自然向他发出的不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召唤,而是一封落叶送来的“劝降书”。正如《秋日,登山有悔》中写道的,“但我也是递去橡皮擦的一个/可能还是斩茎、妄食、屠戮的一个//叛逃的,藏匿在登临者名单中。落叶/如钟声,自山的内部向我发放归降凭证”。
北鱼的诗集中有《潮汐来信》《江海来信》《云中来信》,但也有“独饮者撕碎云中来信,滂沱降生为尘世的/前缀词”(《雁江夜饮后序》)。“滂沱”一词用得好,不是“酒后,睡意接近悬空”的状态,而是体现出一种清醒和自觉。“滂沱”作为“尘世的前缀词”,是对现实的精准描述和对“现代性”的深刻洞察。
《引弓》是这部诗集中最短的一首,“众云列阵,从头顶飘过/哪一朵,才是蔚蓝的心脏/我抽骨引弓,射向成群空旷”。虽然只有三行,但内蕴饱满、元气充沛。它何尝不是关于写作的一首“元诗”、一个隐喻?诗歌又何尝不是“抽骨引弓,射向成群空旷”?而“空旷”中有大海和远景、大地与人,从大海到大陆、从逃离到栖息,他的变迁是“引力在悲喜之间娴熟切换”的变奏,也是小我与大我、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切换和变奏。立足此在和当下,并继续拥有大海这个启示录式的背景,这是我对北鱼生活与写作的期待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