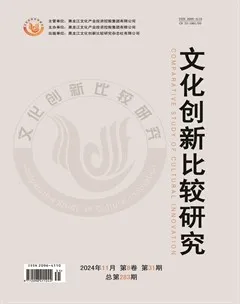《昭明文选》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摘要:和《白氏文集》齐名,《昭明文选》是对日本文学影响最为深远的两部中国文学典籍之一,早在飞鸟时代就已传日,其经典地位始终不可撼动。《昭明文选》在日本的传播是自上而下的。奈良时代《昭明文选》的主要受众为贵族阶层,平安时代扩展到中下级官员和知识人阶层,江户时代以后进一步普及到普通市民阶层。《昭明文选》对日本文学的影响是由外而内的。自文字用词的借用开始,到历史典故受到关注,直至思想文化的理解与吸收,即由最初的对《昭明文选》的追捧,到模仿学习,直至对其中蕴含哲学思想和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该研究真实、具体地勾勒出《昭明文选》在日本各时代的传播及接受情况,以及对日本政治、文学、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影响。
关键词:《昭明文选》;汉文学;传播;接受;影响;日本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1(a)-0165-05
Dissemination and Influence of Zhaoming Wenxuan in Japan
ZHANG Y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Jiangsu, 213159, China)
Abstract: Zhaoming Wenxuan, renowned alongside The Collection of Bai Juyi's Poems, is one of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literary classics on Japanese literature. It has been introduced to Japan as early as the Asuka period, and its classic status has never been shaken since then. Its dissemination in Japan was top-down. During the Nara period, its main audience was the aristocracy, which expanded to mid- and low-ranking officials and intellectuals in the Heian period and further reached the general public class after the Edo period. In addition,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literature followed the external-to-internal approach. It started from the borrowing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developed to the attention paid to historical allusions, and progressed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absorption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that is, from the initial fascination with its popularity, to imitation and learning, and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acceptance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and values it involves. This study truthfully and specifically outlin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Zhaoming Wenxuan in various eras in Japan,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Japanese politics, literature, culture, education, and other fields.
Key words: Zhaoming Wenxuan; Chinese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Acceptance; Influence; Japanese literature
《昭明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与《白氏文集》是对日本文学影响最为巨大的两部中国文学典籍,可谓是影响日本古代文学的中国典籍之“双壁”。《白氏文集》相关的先行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与其相比,学界对于《文选》的关注较少,尚有巨大的研究空间。目前相关先行研究主要聚焦于注释学及版本文献学领域。《文选》在日本各时代的传播及接受情况如何?对日本政治、文学、文化、教育等领域有哪些影响?本研究力求真实、具体地勾勒出《文选》在日本传播、接受及影响的原貌。
1 《昭明文选》在日本奈良时代以前的传播与影响
奈良时代,日本贵族已经开始接受汉文教育。在这一时期,通过与邻国百济等的交流往来,日本贵族已经接触到《文选》,并广为传颂。当时学习《文选》,采用汉字音读和训读的独特方式,后成为日本贵族早期学习汉文的一般方式,被称为“文选读(文選読)”,可见《文选》影响之深广。《文选》传入日本之初,主要在政治、教育以及文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文选》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指标,其部分内容还被纳入当时日本最高学术机构大学寮的进士考试范围[1]。养老律令《考课令》中规定,《文选》的讲读为进士考试的必考内容。因此,《文选》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必读书目,以及文人的汉文必备素养,由此确立了其典范地位。8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已出现受《文选》影响的痕迹,其中“深谋远虑”“聪明神武”等诸多词语和用法均是来自《文选》。不仅限于《文选》白文,《文选》李善注本中多处内容也出现在《日本书纪》之中,这也侧面印证了当时中日两国书籍交流的盛况,以及日本贵族学习《文选》的热情。此时文人诗文创作也多以《文选》作为范本。《万叶集》中的东歌、防人歌的语汇素材、风格,以及歌人大伴家持、山上忆良的创作思想深受《文选》之影响。
8世纪前半叶,日本相继编纂了《播磨国风土记》《肥前国风土记》《常陆国风土记》,以及《丰后国风土记》等用汉语书写的地方志。其中多处词语和用法都出自《文选》,如出自《高唐赋》的“险峻”“峻极”,以及出自《西都赋》的“峥嵘”“汤泉”等,说明这一时期《文选》已经开始对日语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由于宫廷贵族的学习需求,当时日本宫廷写经所的写经生除抄写佛经之外,还承担了抄写《文选》等中国典籍的任务。“正仓院文书中曾发现关于宫内用纸与抄写工作的记录……表明8世纪前半叶《文选》一书在奈良皇宫中已非常流行。”[2]抄写活动规范、有组织,参与人员众多,体现了当时日本贵族学习汉文的热情。与此同时,由于写经生在接触、抄写《文选》的过程中产生了学习兴趣,开始了自觉的私下学习活动,推动了《文选》向非宫廷贵族阶层的渗透。《文选》在日本奈良时代的传播充分展现了“东亚学人共读一书”的盛况,为促进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2 《昭明文选》在日本平安时代的传播与影响
平安时代,《文选》的受众扩大到一般贵族阶层。此时《文选》仍是贵族文士学习汉文学的重要教本。与《源氏物语》并称平安文学双璧的《枕草子》作者清少纳言非常推崇《文选》。她在文中说,“要论好的文章,当数《白氏文集》《文选》……”[3]。菅原清公、菅原道真、大江匡衡等担任天皇侍讲,世代相传,从而形成了以菅原家和大江家为首的《文选》研究学派。《文选集注》在这一时期成为贵族文人学习汉学的教材,“其主要作用是注释相关典籍,于平安中后期文人而言是一本相当于辞典性质的工具书”。最早成书于日本的汉诗集《怀风藻》,三大敕选汉诗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均受到《文选》的影响,《本朝文粹》等的编集也是以《文选》为标准。可见,平安时代《文选》在日本的影响地位进一步巩固扩大,离开《文选》而谈日本汉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不成立的。
这一时期,除了延续奈良时代的《文选》接受特征,日本的语言文字继续受到《文选》影响之外,日本贵族开始通过《文选》关注并了解中国历史及文化,并把历史故事应用在文学创作之中。其中《文选》卷四十六《豪士赋》中孟尝君听雍门抚琴而落泪的故事及卷二十七《怨歌行》中班婕妤失宠,以团扇自比的故事在文学作品中使用最为广泛。如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物语集《源氏物语》,就提及了《豪士赋》和《怨歌行》;《大和物语》中则提及了《怨歌行》。
虽然到了平安后期,《文选》的“霸主”地位逐渐被《白氏文集》所取代,但并不代表其影响力在衰退,而是由表层深入内在,对后世日本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一直持续。汉学家静永健指出,“当时的日本贵族文人认为,新传入的《白氏文集》已经继承了《文选》之基本功能。换句话说,他们将《白氏文集》看作一部更为实用的流行版《文选》”[4]。此外,《荣华物语》中还记载了日本贵族为实现政治目的,将《文选》内容绘制于屏风、帐幔等器物之上,来培养家族女性的汉文素养[5],说明《文选》已经成为当时贵族提高汉文素养的重要手段。
3 《昭明文选》在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的传播与影响
《文选》在日本镰仓、室町时代仍然是士人、僧侣、文人看重的典范读物,其注解、注释功能愈加受到重视,被广泛应用。《文选集注》成为平安后期到镰仓时期文人编撰佛经音义、注解诗文别集最重要的参考书。此外,还出现了《文选》的解释书《御注文选表解》,该书是以菅原和长为日本中世贵族子弟讲授《文选》的授课笔记为基础而辑成。
镰仓初期学者平基亲所著《往生要集外典抄》引用多部我国古代文学典籍,其中引用最多的为《文选》。除引用《文选》正文外,平基亲还引用李善注、五臣注及王逸注等注释本,对《文选》正文及注释内容相当了解,谙熟于心。从平基亲的经历来看,虽然其中年时代升迁至从三位,位列公卿,已从属于下层贵族行列,但其少年时代接受的教育并非贵族阶层教育。这说明在镰仓初期,《文选》的受众已经由贵族阶层扩展到了中下层官员及知识人阶层。当时在贵族阶层中《白氏文集》的流行潮尚未退去,而《文选》则为普通官员和知识人阶层所用。
日本中世知识人的《文选》素养深厚。藤原定家《明月记》等著述中多处引用《文选》,并多次进行《文选》讲释活动。汉诗人义堂周信的《御堂关白记》、瑞溪周凤的《卧云日件录拔尤》,以及这一时期流行的《异制庭训往来》《云州往来》等“往来物”中均频繁提及《文选》的讲释、学习及引用。
这一时期,《文选》《豪士赋》的故事仍然受到关注,如《十训抄》《中世日记纪行集》中都引用了其中典故。除此之外,《高唐赋》和《饮马长城窟行》等也反复出现在物语文学等作品之中。如《松浦宫物语》和《太平记》中就引用了《高唐赋》中楚怀王梦游高唐,幽会巫山神女的故事。历代武将的故事也受到这一时期日本军记物语文学的关注。
这一时期的《文选》接受,除延续前代对于历史典故的了解和运用之外,还体现在对于《文选》中哲学思想、价值观念的理解和认同。日本两大随笔之一的鸭长明《方丈记》,其开头的思想理念就出自《文选》陆机的《叹逝赋并序》。同时,《叹逝赋》的影响遍及《方丈记》序章全篇。与《方丈记》齐名的另一随笔名篇《徒然草》中一段是《文选》《古诗十九首》中第十四首《去者日以疏》的阐释,对《文选》的哲学思想、生命价值的感悟产生认同。
4 《昭明文选》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与影响
《文选》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影响力仍然持续,并未衰退,仍是文人学习汉文的必读书。这一时期,有“文选为天下之半才”之说[6]。著名汉学者服部南郭的《南郭先生文集》就深受《文选》影响。其学习《文选》主要通过李善注本,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元禄十六年(1703年)圆通所撰的《难华长渐心斋桥记》,其中很多地方以《文选》所收作品为典故。
这一时期汉文典籍的刊刻盛行。贞享四年(1687年),风月庄左卫门刊刻了明代王象乾编《文选音注》。其中有宇都宫遁庵注跋文写道:“文选白文梓行之也久矣……故就加是正……欲便于彼习句读者也。”指出刊刻目的是供学习之用。《文选音注》于天保二年(1831年)再次刊行。嘉永三年(1850年)刊行的片山兼山校点《文选正文》中有久保爱跋文“唯吾山子执中译之,有益学者”。以上均说明江户时代文人学者对于《文选》的学习仍有旺盛的需求,此需求推动了出版商对于《文选》的刊刻发行。嘉永五年(1852年)刊《新刻文选正文音训》中,平田丰爱在序言中写道:“文选行于我邦也久矣。游文之士。无不讽诵之者。是以五尺之童,必习读之。然为其书,颇不易学焉。”[7]点明了《文选》在当时还被作为少年学习汉文的启蒙读物,充分说明了《文选》受众的年龄层之广。
江户时期,日本对于世界文选学作出的重要贡献是发现了《文选集注》抄本残卷。《文选集注》自19世纪初发现以来,成为收藏家竞相收藏的珍贵藏品,不惜斥巨资购得一二残页的大有人在。这一时期《文选》六臣注的流行也值得关注。浮世草子《浮世亲仁形气》中,记载了书中人物求购《文选》六臣注的内容[8]。《看羊录》中还记载了朝鲜儒学者受汉学家藤原惺窝指引,在日本书写儒学经典,并著《文选纂注》的始末[9],说明《文选》不仅对日本,乃至对整个东亚文化圈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5 《昭明文选》在日本近代的传播与影响
时至近代,《文选》的影响并未因时间流逝而削弱,依然被视为写作文章所依据的经典。这一时期,《文选》作为学习汉文必读书的地位得到了继承。《明治启蒙思想集》中指出,“《文选》为学习汉文的必读书,尤其应读李善注《文选》”[10]。对《文选》文体的摹写,以及《文选》思想的内化也愈加成熟。
据明治十五年(1882年)近藤元粹《音释训点文选正文》自序,“文选,难读之书也,而故事成语,满卷溢册,不亦文林之良材哉……故欲作奇文妙篇。非腹富于文字之材料,则安能有破天荒之技哉。而致其富。无如读《文选》矣”。说明《文选》虽内容难懂,但是汉文写作的绝好素材,如要提高汉文写作技能,阅读《文选》是极好的途径。学者北村透谷的《于松岛读芭蕉翁》就是受到《文选》第七卷贾谊《鵩鸟赋并序》的影响;写于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的《一种攘夷思想》,明显是模仿了《文选》第六卷郭璞的《江赋》;而《思富域诗神》一篇则是依据陆机的《叹逝赋并序》而写成。可见北村透谷对《文选》内容颇为熟悉,并将《文选》思想内化为自身的文学思想。
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年5月19日,夏目漱石在给友人正冈子规的书信中有其所作汉诗《古别离》一首。在信的末尾夏目漱石讲述了自己从旧书店中偶然购得《文选》一部,归家读后受其影响,而作《古别离》一首的始末。虽然其在信中说明自己只是“通读两三页”,但诗中从题目到立意、词句却可见模仿和引用张衡《四愁诗》、江淹《杂体诗三十首 张司空华离情》、谢灵运《七月七日夜咏牛女》以及《古诗十九首》等多首诗的痕迹,领会深刻,绝非夏目漱石自己谦虚所说的仅通读几页而已[11]。岛崎藤村《落梅集》中名为《響りんりん音りんりん》的诗,描写在异乡流浪漂泊20年的游子再次踏上乡土的情景,也是出自《文选》。该诗在明治时期被选入中等学校教科书,受到大众的喜爱[12]。
6 《昭明文选》在当今日本的传播趋势及展望
在当今日本,由于一众名家学者对《文选》持续的关注研究,《文选》研究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可,文选学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尤为引起关注的是仅存于日本的《文选集注》及九条本相关研究,以及清水凯夫的“新文选学”研究。
日本正式将《文选》作为一门独立学问加以研究,大约始于大正末年。其契机为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斯波六郎和吉川幸次郎二人在京都大学聆听铃木虎雄先生的《文选》讲座。斯波六郎博士毕业后在广岛大学任教,期间写成对后世文选学具有重要影响的《文选诸本的研究》一书,确定了其在日本文选学的奠基者地位;又著有《文选索引》以及《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奠定了文选学的学科基础。其研究对海内外《文选》研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13]。在其影响下,广岛大学由此形成了文选学研究传统,成为日本文选学研究重阵。如今,有佐藤利行、陈翀的《文选》版本研究,并在中国文学专业开设《文选》研究课程,具有优良的师承体系,培养了众多从事《文选》研究的学者。笔者有幸在广岛大学攻读博士课程,师从佐藤利行教授,并受陈翀教授指导,因此认为通过《文选》研究建立起中日交流与理解的桥梁,为自己应尽之责。
此外,日本学者对于《文选》的翻译与阐释也不断有优秀成果涌现。如岩波文库《文选诗篇》、明治书院新释汉文大系《文选》全卷译注等。今后,《文选》的现代日语译本应是其传播、普及的重要途径。日本翻译家们也正在致力于产出更加简明易懂、大众乐于接受的译本,进一步扩大《文选》的受众群体。
7 结束语
《文选》是影响日本古代文学作品时间最长的汉诗文集。可以说,抛开《文选》则无法谈及日本汉文学的起源及发展。自奈良时代以前传至日本时至今日,《文选》的经典地位始终不可撼动。《文选》的影响涉及日本政治、文化、文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从传播特征和受众层面来看,《文选》在日本的传播是自上而下的,影响是由外而内的。奈良时代的主要受众为贵族阶层;平安时代扩展到中下级官员和知识人阶层;镰仓室町时代,普通官吏和知识人阶层接受的《文选》熏陶内化为其汉学素养,奠定了其文学创作的基础;江户时代以后,受众扩大到普通市民阶层。日本文人对于《文选》的接受自语言文字开始,到历史典故的关注,直至思想文化的理解,由刚开始的追捧和对潮流的趋之若鹜,到模仿学习直至对其蕴含哲学思想和价值观的认同。
从古至今,日本知识人对于学习《文选》具有很高的热情,但鉴于《文选》原文内容难懂,多借助注释本进行学习。《文选》李善注本多援引《庄子》《史记》等汉籍,因此通过李善注《文选》来转引其他汉籍内容也是日本人学习并活用《文选》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有力证明。《文选》对于整个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发展以及稳固具有重要的作用,《文选》研究是东亚汉籍研究不可逾越的高峰。我国每年定期举办文选学国际研讨会,各国学者积极参与,争相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域外文选学研究也必将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
参考文献
[1] 赵季玉.《文选》在古代日本的流传与影响[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5):140-147.
[2] 高薇.日本正仓院藏《文选》李善注拔萃发覆:兼论《文选》在日本早期的抄写活动[J].中国典籍与文化,2023(2):59-68,122.
[3] 清少纳言.枕草子[M].东京:小学馆,1997:336.
[4] 静永健.《文选》与《白氏文集》:对东亚古代汉籍流变史的一个考察[J].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21(1):170-178.
[5] 山中裕,秋山虔,等,译注.荣华物语[M].东京:小学馆,2008:245.
[6] 井沢长秀.本朝俚谚[M].东京:静嘉堂,1715.
[7] 芳村弘道,金程宇,张淘.关于和刻本《文选》:从版本看江户、明治时期的《文选》接受[J].古典文献研究,2011(00):214-247.
[8] 长谷川强,译注.浮世草子集[M].东京:小学馆,2000:493.
[9] 朴钟鸣,译注.看羊录[M].东京:平凡社,1996:156-157.
[10]西周.明治启蒙思想集[M].东京:筑摩书房,1967:315.
[11]屋敷信晴.夏目漱石《古别离》与《文选》[J].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023(76):223-243.
[12] 丹羽纯一郎.明治翻译文学集[M].东京:筑摩书房,1972:376.
[13] 富永一登.日本《文选》研究之现状与展望[J].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2018(2):1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