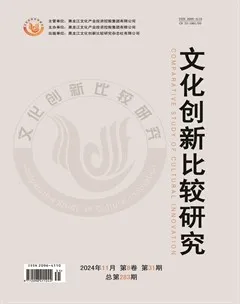试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主要探索对象
摘要:在探寻中华早期文明的过程中,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所开创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治理和运行模式,为后续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特征显示了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发展高度,显示了夏王朝时期的文明样态,也奠定了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基调和发展高度。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具有重要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它是夏文化的主要探索对象。该文旨在通过梳理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特征、社会组织、经济形态,以及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探讨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代历史;早期文明;核心地位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1(a)-0064-06
The Erlitou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the Xia Dynasty
WANG Jianhua
(He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Zhengzhou Henan, 451464,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Erlitou culture, represented by the Erlitou site,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The governance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wide area royal state it pioneere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futu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litou culture demonstrate the high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bronze civilization, show the civilization form during the Xia Dynasty, and als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tone and heigh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future. As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China's early bronze civilization, the Erlitou culture has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value, and is the main exploration object of the Xia culture.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unique position and role of Erlitou cult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by examining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social organization, economic form,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n surrounding areas.
Key words: Erlitou Site; Erlitou culture; Xia culture; History of the Xia Dynasty; Early civilization; Core position
二里头文化是夏商时期主要分布于中原地区的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代表性文化,其最典型的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发掘和研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夏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盆地的周边地区,也发现有较多的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址。经过学者的研究,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南境内,与河南毗邻的陕西、湖北、山西境内也有少量分布。依据目前考古调查的情况,洛阳盆地的伊河、洛河,郑州一带的索须河,漯河、平顶山地区的淮河支流是二里头文化重要的分布区域[1]。学术界对于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广域王权国家——“最早的中国”的象征与代表已经达成共识。不管对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如何限定,其为夏代文化的核心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
1 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了夏文化的发展高度
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首个广域王权国家——“最早的中国”的核心表征文化,其文化的主要特征显示了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发展高度,显示了夏王朝时期的文明样态,也奠定了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基调和发展高度。这些特征主要体现在考古发现的城市布局与宫殿建筑、青铜器和礼器、陶器和玉器、社会等级和礼仪制度等方面。
1.1 城市布局与宫殿建筑
二里头遗址作为二里头文化中规模最大、文化特征最典型的大型都邑性遗址,其城市布局与宫殿建筑代表了二里头文化发展的高峰。目前,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多处宫殿建筑。
一号宫殿遗址是二里头遗址中最为著名且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之一。它坐落于一座大型夯土台基上,整体略作正方形,东北部向内凹进一角。该宫殿由主体殿堂、宽阔庭院、正门门塾、四周围墙和廊庑等部分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布局严谨。主体殿堂位于台基中部偏北,东西长约36 m,南北宽约25 m,建在基座之上后,其尺寸变为东西长30.4 m,南北宽11.4 m。根据柱洞和残留遗迹判断,这是一座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大型木构建筑[2]。一号宫殿可能是当时统治者发布政令和举行祭祀活动的礼仪性建筑。除了上述宫殿外,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二号、三号、四号、六号、七号等宫殿建筑基址。这些宫殿基址虽然规模和布局各异,但共同构成了二里头遗址庞大的宫殿建筑群[3]。
总的来说,二里头遗址中的宫殿建筑群是中国最早的大型都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展示了夏朝时期高超的建筑技艺和规划水平,还为我们了解古代王朝的政治、文化和生活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二里头遗址展示了早期中国城市化的特征。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域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具有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显示了早期城市规划的高超水平。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与规模宏大的夯土宫殿基址相配套的礼仪建筑,这些建筑显示出早期国家权力的集中。
1.2 青铜器和礼器
青铜器的出现是二里头文化的显著特征,标志着早期中国文明进入了青铜时代。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各种青铜器,特别是青铜礼器如爵、鼎等,这些器物不仅具备实用功能,还具有重要的礼仪象征意义。此外,铸造工艺的进步为后来鼎盛期的商周青铜文明奠定了技术基础。
青铜器方面,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种类众多,包括工具、兵器、礼器、乐器和装饰品等。据统计,青铜器总数达到250多件,这些青铜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工艺复杂,制作精美。主要器型有容器,如鼎、爵、鬲、斝、盉、觚、角等。其中,爵的数量较多,束腰、平底、椎足,较早的素面无柱,具有浓重的陶爵特征;较晚的陶器特征显著减退,有小柱,有的施简单花纹或镂空。斝为素面敞口,口沿上有两个三棱锥状矮柱,单把,束腰平底,三条腿下呈三棱锥状,上部微显四棱。鼎则是烹饪食物的炊器,而后逐渐演变为祭祀神灵的礼器。兵器,如戈、戚、钺、镞等。戈上装有约1.2 m长的短柄,是可以砍击和钩杀的兵器;钺则是古代帝王权力的象征。工具,如刀、锛、凿、锥、锯、镢、钻、纺轮、鱼钩等。这些工具多仿自同时期的石质工具,但采用了青铜材质,更加坚固耐用。
二里头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精湛,多使用陶范浑铸而成。这些铜器的铸造技术有一个从双范铸造到多范合铸的发展过程。生产工具和兵器多采用双面范浇铸而成,而礼器如爵和斝等则用陶质块范铸造,工艺比较复杂。据测定,一件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于典型的锡青铜[4]。
礼器方面,二里头文化的礼器主要包括青铜器中的爵、斝、鼎等容器,以及玉器、绿松石器等。这些礼器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着古代社会的礼仪制度和宗教信仰。二里头文化的礼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例如,青铜爵和斝等容器在形态上经历了从陶爵特征显著到青铜器特征明显的演变过程。同时,这些礼器在数量和种类上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和丰富[5]。二里头文化的礼器在古代社会中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们不仅是贵族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862739ea7cc70fc34c7739461df4840f2fe83da46d8e569efd13832f5557b8c3,也是古代社会礼仪制度和宗教信仰的重要载体。通过这些礼器的使用,古代社会得以维持其秩序和稳定。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和礼器是古代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技艺,也为人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3 陶器和玉器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陶器多以灰陶为主,具有规整的造型和纹饰,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成熟。同时,玉器也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的玉琮、玉璧等器物显示了当时工匠的高超技艺和玉器在礼仪活动中的重要性。
陶器方面,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数量巨大,种类繁多。这些陶器主要分布在河南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制作工艺精湛,器物成形多轮制,也有一些是模制和手制。陶器装饰运用了磨光、滚压、拍印、刻画、堆塑等手法,纹饰多样,包括绳纹、附加堆纹、弦纹、回纹、旋涡纹、云雷纹、圆圈纹、花瓣纹、篮纹和方格纹等。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器型丰富,包括酒器、食器、炊器、盛贮器、汲水器、食品加工器和杂器等。其中,酒器和食器的制作最为精致,它们往往被随葬于贵族墓中,成为显示身份与地位的礼器群的组成部分[6]。
玉器方面,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这些玉器包括玉钺、玉戚、玉刀、玉璋、玉圭、玉戈等大型有刃器,以及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等。玉器制作工艺精湛,器形对称与平衡,器身尖锐化,器体薄片化,制作意念复杂化。玉器表面往往经过精细的打磨和抛光,呈现出温润的光泽。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器型多样,功能各异。其中,玉钺、玉戚等可能是古代社会中的权力象征,用于祭祀、礼仪或战争等场合。而玉璋、玉圭等则可能用于祭祀和礼仪活动中,作为沟通天地、祈求神灵保佑的媒介。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玉器如柄形玉器等,可能用于佩戴或装饰。典型玉器如牙璋:一种长条形的玉器,两端呈斜刃状,有的还带有锯齿状的扉牙。牙璋在二里头文化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可能用于祭祀、礼仪或军事等场合。七孔玉刀,一种长条形的玉器,刀身上开有7个圆孔。这种玉刀可能用于祭祀或礼仪活动中,作为象征性的武器或法器。玉戈,一种类似于戈的玉器,但并非实战武器,而是用于祭祀、礼仪或舞蹈等场合的礼器[7]。
二里头文化的陶器和玉器是古代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展示了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技艺,也为人们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1.4 社会等级和礼仪制度
通过考古发掘,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和宫殿建筑表明,该时期已经形成了明显的社会等级制度。上层贵族阶层通过礼仪活动和器物的使用,巩固了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二里头文化的礼仪制度对后来的商周礼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1.4.1 社会等级方面
(1)墓葬等级差异体现社会等级
有学者对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做了详细研究[8],依据研究资料,大致可以把二里头文化墓葬分为4个等级。一级墓葬,为随葬有铜、玉礼器的墓。随葬青铜酒器如爵、盉、斝等,大型玉器像璋、刀、圭、钺、戈以及柄形器等,一般还伴出漆、陶礼器(含白陶器)等随葬品。这类墓有木棺、铺朱砂,墓坑面积在2 m2左右,仅发现10余座,宫殿区内随葬绿松石龙形器等罕见的贵族墓规格更高。二级墓葬,随葬有陶礼器的墓。随葬陶酒器如爵、盉、鬶、觚等,其中不乏白陶器,一般还伴出陶质的食器和盛贮器,以及漆器、小件玉器和铜铃等。有的有木棺或铺朱砂,墓坑面积在1 m2左右,这类墓数量占墓葬总数的一小半。三级墓葬,随葬少量日用陶器或没有随葬品的墓。一般不见棺木,无朱砂,墓坑面积在0.8 m2以下,这类墓数量占墓葬总数的一半以上。四级墓葬,是被用作人牲埋葬的祭祀场所,他们或被随意掩埋,抛弃在灰坑、灰层中,有的尸骨不全,有的手脚被捆绑,做挣扎状。
(2)礼器使用反映阶层分化
从二里头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已形成文化礼器制度,陪葬礼器群组普遍出现在墓葬遗址中。夏朝处于青铜文明早期阶段,青铜礼器使用不普遍,以陶器、漆器居多,或青铜器与陶器、漆器相配伍。墓葬中礼器材质可判断墓主人等级高低,反映出君王、贵族、平民的阶层分化。
1.4.2 礼仪制度方面
(1)都城布局体现礼仪制度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有“井”字形主干道路网络,将都城规划成以宫殿区为中心的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官营作坊区、祭祀区分居宫殿区南北两侧,共同形成都城的中轴区域,中轴区域东西两侧是贵族居住和埋葬区。这种严整有序的布局规划显示出严格的社会等级,体现出一定的礼仪规划思想。宏大的宫城和复杂的大型夯土宫殿建筑显示出清晰的宫城宫室制度,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加工作坊设置在宫殿区以南,有围墙防护,体现出对奢侈品生产使用权力的垄断,而在宫殿区北部设置专门区域进行祭祀,表明对祭祀活动的特别重视,这些都是礼仪制度在都城规划布局上的体现[9]。
(2)礼器使用反映礼仪制度
二里头文化中有青铜、玉质礼器及绿松石龙等重器,这些珍贵复杂的礼器体现等级礼仪。例如,陶盉这种专门用来调酒的器具及陶爵等礼器的出土,说明当时形成了文化礼器制度,并且从这些礼器在墓葬中的情况可以看出不同等级的人在礼器使用上的差别,从而反映出当时的礼仪制度。
2 二里头文化反映夏代的社会组织与经济形态
目前,夏代尚未明确发现文字,而传世文献对夏代历史的记载多神话传说之事,故考古学发掘与研究成果对夏史的研究起到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前文笔者已经对相关考古发现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进行了简要梳理。在此基础上,将对二里头文化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夏代的社会组织与经济形态进行分析,以说明研究二里头文化内涵对于揭示夏代历史的重要作用。
2.1 社会组织
二里头文化相关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该时期的社会组织已经高度复杂化。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及墓葬的差异,显示出严格的社会分层。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政权可能已经形成,君主通过掌控宗教和礼仪,强化对国家的控制。
二里头文化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以氏族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非常普遍,并表现出明显的等级制度和分工制度。在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中,贵族是最为显赫的阶层,他们拥有大量的财富和权力,掌握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命脉。贵族之下是普通百姓,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这种等级制度的存在,使得社会分工开始形成,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二里头文化的村落通常规模较大,有时甚至可以达到几公里。村落的布局十分有序,街道宽敞,房屋排列整齐。这种规模和布局的村落,反映了二里头文化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组织和管理能力。同时,村落内部可能有家族与宗族等社会组织的存在,但具体的社会组织结构由于资料限制,还无法作进一步的分析。
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分工。小型家族墓地的“居葬合一”特征表明,不同氏族可能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墓葬随葬品组合也反映出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了新的礼制和价值观。这些特征进一步证明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里头都城建制规划严整,具有九宫格式的功能布局和完备的城市道路系统。这种都城规划建设的特点均可追溯到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甚至仰韶文化晚期。在二里头都城内部,世俗王权的形成是早期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世俗权力以社会管理为基础,在兴修水利、工程营建、战争军事等方面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是地缘政治发展和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
二里头都城内的居民在文化背景、生活习俗、饮食传统及遗传基因方面均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这种多元文化融合的现象不仅体现在都城内部,也体现在二里头文化对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和扩张上。例如,在盘龙城周围及临近的湖北东北部,已发现十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可能是夏王朝控制主要交通路线上的据点[10]。
综上所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社会组织具有氏族基础与等级制度、村落规模与布局有序、职业分工与家族墓地特征明显、都城建制与世俗王权形成及多元文化融合等特点。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2.2 手工业与贸易
青铜器、玉器、陶器和骨器等手工业的发展是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经济支柱。二里头遗址的青铜铸造作坊表明了该地区手工业的规模化生产能力。手工业产品不仅在本地使用,还通过贸易网络传播到周边地区,促进了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2.2.1 手工业方面
二里头文化形成了丰富的手工业种类。二里头遗址发掘出大量铜器、骨器、玉器、绿松石器、石器等手工业考古遗存。这表明当时的手工业涵盖了多种材质的加工制作,品类十分丰富。例如,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青铜制作技术在当时达到了一定水平,人们开始使用青铜制作各种器皿、武器等。在制陶方面,二里头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陶器制作技术的进步。人们开始采用窑烧陶器的方法,使得陶器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极大提高,还出现了彩绘陶器和黑陶器等不同种类的陶器。制陶时通过加入藻类、红土等材料制成的釉层,在陶器表面形成美丽的色彩。
考古发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发达的官营作坊区。二里头遗址发现了最早的官营作坊区。例如,在遗址的围垣作坊区发现有较大范围的青铜器浇铸工场、陶范烧烘工房和陶窑,以及熔炼铜料的坩埚、陶范、铜矿石、木炭、铜渣等,证明此处存在一处铸铜作坊。近年的考古发现还确定了绿松石器加工作坊,总体面积不小于1 000 m2,其内发现有加工工具、原料,以及加工嵌片、毛坯、成品、残次品等大量与绿松石器加工过程相关的遗物。此外,基本确定二里头遗址的两处制骨作坊,一处位于宫城内4号建筑基址的南侧,一处位于V区墓葬集中分布区的东北角[11]。
二里头文化手工业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社会分工的细化。在青铜器制作、彩陶制作等领域里,出现了专业分工,手艺精湛的匠人逐渐站到了社会的顶端,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等级制度。这也表明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在手工业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演变,为从原始部落向国家的转化提供了经济和社会基础方面的支持。
2.2.2 贸易方面
二里头文化手工业的发达为贸易提供了物质基础。丰富多样的手工业产品,如精美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等,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可能有部分用于对外交换。这些制作精美的物品可能因其工艺价值和实用性而成为贸易中的重要商品。
二里头文化遗址所分布的地域范围不仅局限于洛阳盆地,还包括周围的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份,形成了“二里头文化圈”。这种文化的扩张和影响范围的扩大,可能伴随着物品的交换和贸易活动。例如,在湖北盘龙城周围及临近的湖北东北部,已发现十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可能是夏王朝控制主要交通路线上的据点,据点的存在可能与贸易的控制或者开展有着某种联系。虽然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当时贸易的具体形式和规模,但从手工业产品的分布和文化影响力来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区域间贸易往来。
2.3 农业经济
农业是二里头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遗址出土的农具和炭化的粟、稻谷等植物遗存显示了以粟和稻为主的种植业。家畜饲养业,如猪、牛、羊等,也在该时期广泛存在。这种农业与畜牧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为早期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物质保障。
二里头文化时期,农作物种植已经相当发达,主要农作物包括粟、稻、黍、大豆、小麦等。这些农作物不仅满足了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还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粟是二里头文化时期最主要的农作物,广泛种植于各个遗址中,数量比例最高。在二里头都城遗址内,稻谷的出土比例也相当高,尤其在贵族居住区更为显著,说明稻米在当时受到统治阶层的喜爱与控制。黍、大豆、小麦这些农作物也有种植,但数量相对较少。不过,它们的存在丰富了当时的农作物种类,提高了农业生产的多样性。
家畜饲养也是二里头文化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牛、羊、猪等家畜的饲养技术,这些家畜不仅提供了丰富的肉食来源,还成为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劳动力。牛被广泛饲养,尤其在二里头文化后期,黄牛的数量和饲养方式都有了显著提高和改进,可能已经被用于农业生产中的耕作和运输。羊也是重要的家畜之一,提供了羊毛、羊肉等生活必需品。猪在当时也被广泛饲养,是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人们使用各种农具进行耕作和收割,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还形成了科学的农业管理方式,能够根据天象合理安排农业生产,防灾避损,提高农作物产量。
二里头文化的农业经济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还对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产生了深远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形成了手工业、商业等不同的经济部门。同时,农业经济的繁荣也为国家的形成和统一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里头文化的农业经济以其丰富的农作物种类、发达的家畜饲养业、成熟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对社会的重要影响而著称。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二里头文化农业经济的基本面貌,也为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结束语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具有重要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它是夏文化的主要探索对象。学术界对于二里头遗址作为中国早期广域王权国家——“最早的中国”的象征与代表,已经达成共识。不管对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范围如何限定,其为夏代文化的核心地位则是毋庸置疑的。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深入研究,不仅能够了解夏商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形态,还能够进一步探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尽管关于二里头文化是否代表夏文化的争论尚未完全解决,但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多跨学科的合作,结合文字、考古学和科技手段,以揭开这一古代文明的更多谜团。
参考文献
[1]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2] 杜金鹏.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基址初步研究[J].考古学集刊,2006(00):178-236.
[3] 杜金鹏.偃师二里头遗址4号宫殿基址研究[J].文物,2005(6):62-71,1.
[4] 许宏,袁靖.二里头考古六十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351-352.
[5] 段玉琬.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研究[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16):57-59.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陶器集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7] 许宏,赵海涛,邓聪.玉器与王权的诞生:二里头时代玉器研究[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21.
[8] 郑若葵.论二里头文化类型墓葬[J].华夏考古,1994(4):63-72,36,73-81.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10]孙卓.试论二里头晚期中原文化对江汉地区的扩张[J].华夏考古,2021(5):52-59.
[11]赵海涛,陈国梁,许宏.二里头遗址发现大型围垣作坊区[N].中国文物报,2006-07-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