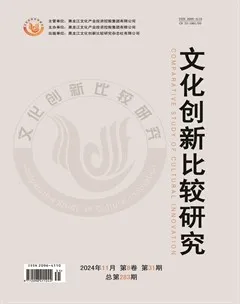《红字》译本中翻译“文学性”效果研究
摘要:《红字》是美国浪漫主义时期著名小说家霍桑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新英格兰背景下,小说中人物在清教信仰中或沉沦或挣扎。作者对《红字》倾注了真挚的情感,与他自己的成长背景密不可分。霍桑在塑造人物时,充分体现出语言的文学性,把人物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故事大幕的拉开,复杂剧情也一一揭露出来。由于小说的文学性很强,翻译的过程文学性的再现至关重要。文学作品是可以为读者带来艺术享受的著作,以文字的形式展现语言的工具性,将作者对生活、自然、人性与社会的思考表达出来。文学翻译中的语言问题理应成为我们的主要关注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关于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我们当下的研究对语言层面的关注越来越少。该文通过分析王元媛和梦伊洛两位译者《红字》中词汇和句子的翻译,看到文学性再现与缺失,并进一步探讨两个译本的文学性效果。
关键词:《红字》;翻译文学性;文学性缺失;文学性保留;文学翻译;译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1(a)-0020-04
A Study on Literariness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carlet Lett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Wang Yuanyuan and Meng Yiluo
QIN Yanlin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Guangxi, 537000, China)
Abstract: The Scarlet Letter is a novel masterpiece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American Romantic period written by Nathaniel Hawthorne, which tells the story in a New England with Puritan beliefs. The Scarlet Letter allows a variety of interpretations on its character and attracted many Chinese readers. In this novel, there ar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in its language and the theme. It is crucial for the translator to keep the literariness of the novel in translating.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Scarlet Letter by two translators, Wang Yuanyuan and Meng Yiluo, especially the vocabulary and sentences in The Scarlet Letter, thereby revealing the loss and reservation of literariness, and further exploring the literary effects of the two translations.
Key words: The Scarlet Letter; Literariness; Loss of literariness; Reservation of literariness; Literary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analasis
《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霍桑悲观地嘲讽传统而封建的宗教思想,小说的人物深受其害。小说的女主人公海丝特正是清教徒狂热分子讨伐的对象,而她身上烙上的红字“A”以及她产下的女儿珠儿就是“惩罚”与“罪果”,而她的丈夫“死而复生”隐姓埋名回来复仇;她的情夫——“被人尊敬的”丁梅斯代尔代表清教徒的伪善与陈腐,尽管内心十分煎熬,却不敢说出其实他就是人们苦苦逼问找寻的“奸夫”。小说主题深刻,语言使用巧妙,故事内涵含糊不清,译者在翻译时理解不同,译文也有所区别。因此,现当下也有学者对《红字》的中译进行研究,主要从翻译标准,以及译者行为批评等角度做翻译研究。基于这些研究,本文主要从翻译文学性来分析王元媛和梦伊洛两位译者《红字》中词汇和句子的翻译,从而研究翻译文学性效果。
1 翻译文学性概述
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性是指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原作的艺术风格、表达方式和情感效果。这是一个复杂且常有争议的过程,因为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有着不同的表达习惯和欣赏标准。“文学性”(literariness)是当下文学翻译里备受关注的研究。雅各布逊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也就是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形式特征[1-4]。文学性语言的再现是文学翻译的灵魂。文学语言是主观的,是带有作者个人情感的,所塑造的人物也情感不一,而其他的文本类型语言是相对客观的。文学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还要与目标读者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相对接,与读者建立共鸣。在翻译文学性语言,即文学翻译时,文学性再现,对于译者而言首先要做到在理解和吸收原文语言、修辞、作者意图等文学信息之后,再对其进行目标语言的重组,进一步去正确领悟并阐释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故而,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文学性的保留至关重要,体现了文学审美并体现原文语言的内涵,有助于目标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还原作者创作时的意图和文学美。因此,翻译文学性效果的呈现能有效地避免读者理解上的错误,并增加了目标读者的接受程度。翻译文学性是指在翻译过程中保持或传达原文的艺术性和美感,以便读者能够在目标语言中欣赏到相似的效果和情感。
2 《红字》的文学特色
《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是纳桑尼尔·霍桑的代表作品。作品描述了在清教传统下相互纠缠、相爱相恨的4个主要角色:红字A烙印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海丝特的女儿珠儿、海丝特的丈夫齐灵渥斯和她的情人丁梅斯代尔;小说的人物剧情线索繁杂纷乱;小说语言使用得巧妙、凝练,意象丰富,具有很强的艺术力量。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形容词描述人物的性格,体现了故事的含糊性及人物的性格,并让读者通过对人物的描述去了解作者对于人物的态度,从而体现了文学作品中的含糊以及黑色浪漫。作者为了体现人物的画面感,不仅使用了形容词,还运用了大量的长句,来描述人物。例如,小说的开篇第一句便是描述人物,使用了合成词sad-colored和steeple-crowned,还有一些具有颜色或质感的词语来增加画面的色彩美与现实感,如gray,wooden,iron等。除此之外,在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关押女主人公海丝特的监狱时,也使用了大量的颜色和氛围感的词语来说明作者对于监狱的界定,是black、grim、grisly。对于看守海丝特的狱卒,也是使用了一些长句来详细描述,让读者在阅读时,脑海中已经浮现出来了一个冷酷无情、恐怖至极的狱卒形象。尤其是对女主人公海丝特的描述,就更加表明了作者对于严酷的清教教条下犯了所谓“通奸罪”的海丝特持有非常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他既夸赞她具有“perfect elegance”,走出监狱那一刻,甚至是比任何时候都要“lady-like”,全身都是“make ahole”。除此之外,作者为了读者不被繁杂的剧情所困扰,使用了“we”的叙述角度,更加拉进了作者和读者的距离。
3 《红字》译本文学性的缺失与保留
本文通过分析王元媛和梦伊洛两位译者《红字》译本的文学性,研究两位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文学性的缺失与保留。在翻译《红字》的过程中,两位译者都努力再现原文意义,保留文学性,但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原文部分文学性在译文中有所缺失。文学性的缺失通常指译文中丧失了原文的艺术性、情感表达和语言风格。在此译者要注意其自身并不是原文文学性的接受者,而是中转者,因此其要充分考虑到目标语言,也就是汉语言读者的文学性阅读需要[5]。通常在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对译著的思想、价值、意识等有精确的把握,然后根据目标语言读者的审美需求、审美能力、审美水平等,按照目标语言文化的审美习惯予以重构[6]。
3.1 词汇文学性的缺失与保留
《红字》原文在开篇使用了大量的修饰性词语,整本小说也运用了大量的长句来进行人物和人物状态的描写,部分词汇保留了文学性,但有些词汇翻译时选择了不恰当或平淡的词汇,没有体现原文的丰富内涵,导致了文学性的缺失。
例1:A throng of bearded men, in sad-colored garments and gray steeple-crowned hats, intermixed with women, some wearing hoods, and others bareheaded, was assembled in front of a wooden edifice, the door of which was heavily timbered with oak, and studded with iron spikes.
梦伊洛译本:一群蓄着胡须的男人,身着颜色黯淡的衣服,头戴灰色尖顶高帽,混杂着一些女人,有的兜着头巾,有的什么也没戴,聚集在一所木建的大厦前面。大厦的门是用厚实的橡木做的,上面钉满了粗大的铁钉子[7]。
王元媛译本:一幢木制的大房子前聚集了大群的男男女女。男人们蓄着胡须,身着颜色灰暗的衣衫,头戴尖塔形的灰帽子;女人们有的裹着头巾,有的巾帽全无。这幢房子的大门由厚重的橡木制成,门上满是尖尖的铁钉[8]。
由例1可见,词汇方面,在处理一些形容词时,梦伊洛直接将bearded翻译为形容词“蓄着胡须的”,采取了直译法,没有和后面“身着”形成词性对应,目标语言不够流畅。sad-colored是由连字符构成的复合词,sad指的是伤心的、难过的,与colored构成复合词时,形容衣服颜色比较暗,衬托出这个人不修边幅、低调的状态。原文这一句出自第一章,情节发生在牢狱的门口,按照当时的时代背景,句子里面聚集牢狱门口的男人和女人应该是平民,因此,梦伊洛将它译为“颜色黯淡”,将原文所要突出的含义弱化了。王元媛翻译时,不仅在处理bearded时将其变成动词,整个描写的部分使用了动词,sad-colored也翻译为“颜色灰暗”,既保留了原文的内涵,也符合目标读者的语言习惯,保留了原来语言的文学性。
例2:A writhing horror twisted itself across his features, like a snake gliding swiftly over them, and making one little pause, with all its wreathed intervolutions in open sight. His face darkened with some powerful emotion, which, nevertheless, he so instantaneously controlled by an effort of his will, that, save at a single moment, its expression might have passed for calmness.
梦伊洛译本:他的面容蹙起一种辗转不安的怒怖,像是一条蛇正从那面容上急剧地缠了过去,而后稍一停留,蜷曲成一团,暴露在众人面前。
王元媛译本:他的五官因突然袭来的恐怖而扭曲变形,仿佛有一条蛇在脸上蠕动爬行,稍一停留,就蜷成一团,凸现得清清楚楚。
这一句话来自第三章“相认”,海丝特的丈夫“死而复生”,回到新英格兰,看着刑台上的海丝特。这一句话是描述海丝特丈夫在看到刑台上的海丝特时的面部表情。按照作者的描述和剧情的发展,海丝特的丈夫应该是带着恨意,并且还用了snake来形容,因此在处理writhing horror时,梦伊洛译者选择了“辗转不安的怒怖”,强化了不安,但是作者在设计时,强化的是恐怖,译者弱化了恐怖,因此文学性的效果没有达到原文的效果。而王元媛译者保留原文的文学性,让我们看到了海丝特丈夫的表情是恐怖至极的。在翻译文学词汇时,选用能够传达原文情感和语气的词语,能够让读者准确把握人物。
除以上例子外,小说中出现了很多为作者创造的复合词,比如half-hushed(半抑止的,略微压抑的),picture-gallary(长廊,画廊),heaven-defying(滔天罪恶的,藐视上帝的)等,两位译者在处理时,理解不同,翻译时选择的词汇也有所不同。梦伊洛译文略微偏向欧式白话文,阅读性不强;王元媛文学性稍有保留,相对而言更有可读性,文学性效果更好一些。
3.2 句子文学性的缺失与保留
不同的作家有其独特的写作风格,翻译时应尽量保留这种风格,比如,句子的长短、用词的选择、节奏的把握,不仅要翻译文字的表层意思,还要传达原文中的情感、氛围和美感。理解和传达与原文相关的文化背景,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深层含义。霍桑的句子往往较长且结构复杂,常使用从句和插入语,这种风格使得语句更具层次感,需要译者体现出来,才能让目标读者细心体会。
例3:It may seem marvellous that with the world before her—kept by no restrictive clause of her condemnat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Puritan settlement, so remote and so obscure—free to return to her birthplace, or to any other European land, and there hide her character and identity under a new exterior, as completely as if emerging into another state of being—and having also the passes of the dark, inscrutable forest open to her, where the wildness of her nature might assimilate itself with a people whose customs and life were alien from the law that had condemned her—it may seem marvellous that this woman should still call that place her home, where,and where only,she must needs be the type of shame.
梦伊洛译本:这事也会令人觉得惊异的:她面前既然开放着一片世界——而她的判决又没有严格规定要限制她留在清教徒聚居的那么遥远、那么荒僻的殖民地里——她可以自由地转回她的诞生地,或是到欧洲任何别的国土去,在一种新的环境下,隐姓埋名,适应环境,彻底重新做人。再说,那黑暗得深不可测的森林的路径也在对她展开,那里人民的生活习惯,都是与制裁她的法律全然不同,她的奔放的性格很可以跟他们同化——看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女人却把这个地方视为自己的家园,而在这里,只有在这里,她才必须充当耻辱的典型。
王元媛译本:有一点颇令人费解:她的判决中并无限制性的条款,强迫她留在这偏远荒凉的清教徒聚居地;整个世界都对她开放。她可以返回她的出生地,或者在欧洲的其他任何地方,隐姓埋名,开始全新的生活。那幽暗莫测的丛林也在向她招手;那里的生活习俗与制裁她的法律截然不同,与生俱来的野性能使她被那一民族同化。但是,这女人却仍然留在唯一逼迫她成为耻辱典型的地方,还把这里视为家园。
例3来自小说第5章,此段描绘的是女主角海丝特的复杂心理状态和处境,凸显出个体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冲突。这一句的结构复杂,通过多个修饰语和从句呈现了女主角的内心挣扎及其处境。句子开始便展示了“我们”的不解“marvellous”,为后面的矛盾做好铺垫,句子最后又出现了一次。两位译者翻译时,针对最后的“it may seem marvellous that”,梦伊洛基本保留了原来的意思,体现了“我们”对于女主人公挣扎后做出的决定感到诧异;而王元媛则直接省略了,选择了“但是”,弱化了“我们”的态度。在处理长句时,两位译者都适当进行了拆分,有考虑到目标读者的阅读感受。梦伊洛从第三个破折号处就进行拆分,把后面意义相关的内容放在一起,王元媛译者选择了从最后破折号后面的句子拆分,可读性更强一些。
例4:The eloquent voice, on which the souls of the listening as he swelling waves of the sea, at length came to a pause.
梦伊洛译本:犹如汹涌澎湃的海涛擎托着听众的灵魂高高升起,牧师雄辩的话音终于停往。
王元媛译本:牧师那恢宏雄辩的演说如同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听众的灵魂高高托起,送往天际。可这声音终于停住了。
例5:There was a momentary silence, profound as what should follow the utterance of oracles.
梦伊洛译本:这一刹那的沉默显得那样的深沉,仿佛刚宣告了神谕一样。
王元媛译本:那瞬间的沉寂犹如宣示神谕之后的寂静,令人倍觉肃穆庄严。
例4、例5是来自23章的开头连着的三个句子。霍桑作品以充满想象的反讽与象征手法著称,“隐喻”在其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9]。句子中使用了隐喻、比喻、拟人象征等修辞手法,使得文字富有表现力。《红字》中,作者大量地使用“as”,这两个句子也都用了“as”来描述情景环境,将其与人物内心情感相结合。例4中,作者使用“as”,将声音与海浪对比,使用了拟人手法,将灵魂赋予动作,体现主动性,也具有意象感。两位译者都能够将这两个句子里面的隐喻体现出来,但梦伊洛译者在处理灵魂时,弱化了其动作;王元媛译者使用了“托起”更能令读者感受到其中动态感。同时,为了体现原句当中声音“eloquent”和“pause”强烈的对比,王元媛进行了拆译,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原句中的情感张力。对句子例5,梦伊洛的译文句子结构上没有改变,王元媛选择了换序,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思维,文学性更强一些[10]。
4 结束语
《红字》塑造的人物饱满,情感色彩鲜明,译者在译文中尽量保留原文的情感色彩,以引起读者的共鸣;原文的语言丰富,译者保持内容的一致性,同时追求形式上的美感,符合目标语言习惯,使得整体作品和谐统一。本文所研究的两部译著,文学性都存在缺失和保留。梦伊洛译者更加偏向直译,部分语言偏向欧化白话文;王元媛译者偏向于意译,语言比较流畅易读。翻译文学性效果会导致中西文学史上对人物形象的评价有所不同。文学翻译能够让读者在不同语言中体验到相似的美感与深度,从而实现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对于译作来说,读者的体验至关重要,应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习惯和阅读习惯,使译文适合他们的期待。
参考文献
[1] 谭敏冬.胡允桓《红字》译本误译错译评析[J].青年文学家,2010(20):147,149.
[2] 牛锦华,刘宣仪.从女性主义视角看霍桑《红字》中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的自我救赎[J].散文百家(理论),2020(8):35.
[3] 许钧.关于文学翻译的语言问题[J].外国语,2021,44(1):91-98.
[4] JAKOBSON R. Modern Russian poetry: Velimir Khlebnikov [C]//BROWN E. Major Soviet Writers: Essays in Criticism.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62.
[5] 孙伟.接受美学视角下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与文学性的辩证关系:以《简·爱》的两个汉译本为例[J].黑河学院学报,2022,13(8):107-109,176.
[6] 梦伊洛.红字[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
[7] 王元媛.红字[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8] 陈一琦.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红字》汉译复杂定语研究[J].文教资料,2024(5):11-14,18.
[9] 刘燕.基于语言学视角分析英美文学作品语言特点:以《红字》为例[J].名作欣赏,2023(30):50-52.
[10]周领顺.散文翻译的“美”与“真”[J].中国翻译,2015(2):117-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