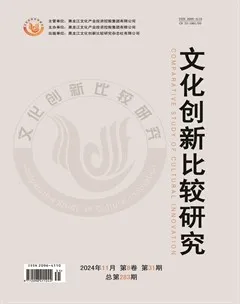莫言《生死疲劳》中的“善”与“美”形象及其英译研究
摘要:该文基于形象学理论框架,将形象放在观察首位,对比分析莫言《生死疲劳》中文化形象和艺术想象的塑造及其在英译本中的再现。该文主要基于文本内部分析,以主人公西门闹及转世的动物形象为主要基点,从道德情节和审美情节层面分析《生死疲劳》中“善”与“美”形象在英译版本中的再现与重构。形象学主要观察形象对于翻译活动的影响,该文基于这一角度,结合葛浩文翻译特点,对比分析其英译本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中“善”与“美”形象的再现与重构,分析发现,多重身份赋予译者理解原文文化内涵的能力,译者常采用增译和具体化策略弥补文化障碍,并以地道的英文传达给目标读者。
关键词:形象学视角;人物形象;动物形象;《生死疲劳》;英译;增译
中图分类号:I046;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11(a)-0011-05
Study on "Kindness" and "Beauty" Image and Its translation in Mo Yan's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LI Ruo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7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magology, this paper takes image as the primary observation factor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shap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image and artistic imagination in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and its translation. This pape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extual analysis. Taking the hero Ximen Nao and his reincarnation of animal images as the main basis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age building of "kindness" and "beauty" in this book from the level of moral plot and aesthetic plot. Imagology mainly observes the influence of images o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prod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kindness" and "beauty" images in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multiple identities give the translator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 translator often adopts the strategies of addition and explicitation to make up for the cultural barriers, and convey them to the target readers in authentic English.
Key words: Imagology; Human image; Animal image;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 English translation; Addition
莫言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新世纪文学是在文化焦虑的中国语境下自然而然产生的,主要特征是回溯中国传统古典文学,以确立中国小说的独特意义[1]。中国叙事传统中的叙述体式主要包括志人志怪、笔记体、章回演义等[2]。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就采用章回体,书写主人公西门闹转世的经历,用轮回的方式将动物世界、人的世界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人畜混杂的特殊艺术画面。《生死疲劳》中包含大量中国传统中的古典文化形象和艺术想象。因此,本文从形象学视角出发,对比分析《生死疲劳》中文化形象和艺术想象在原文与英译本中的形象塑造。
1 形象学与翻译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开始聚焦于文化,形象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翻译文本中的形象塑造和形象投射开始被广泛讨论,但是在前期的研究中,形象仅作为一个观察因子和解释工具,多用于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翻译研究。随着形象学逐步进入翻译研究领域,形象学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形象成为核心因素,聚焦翻译过程中他者形象与自我形象的构建过程[3]。
翻译与形象之间有很强的互动关系,翻译可以建构出关于源文本的特定形象,而这种形象可能与源文本中的形象相去甚远,但又对形象在文学中的传播影响颇深[4]。在形象学视角下,形象介入翻译过程,影响翻译选择,翻译是形象塑造与重塑的辅助手段[5]。
形象学路径在翻译研究中有很广阔的空间,该路径以翻译与形象的互动关系为核心,从形象学视角对相关翻译现象进行解释和描述,从而探究翻译本质,形象学主要关注形象对翻译活动的影响[6]。
2 《生死疲劳》中“善”与“美”的形象构建
现代文学中,主人公形象往往代表着作者的审美和思想,采用一系列抒情话语,表现主人公的内心感受,让所有的场景对话充满主观色彩,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也是现实中某类人群的真实映照,通常具有时代意义,以文学来描绘时代,引发读者对这类人物形象的思考,以及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和反思。《生死疲劳》中,主人公西门闹作为时代的牺牲品含冤而死,面对酷刑绝不屈服,始终保持愤怒,求一个公道,原文中曾用“硬汉子”来描述西门闹的坚强品格,还以第一人称视角着重刻画了西门闹和阎王等之间的对话,西门闹的据理力争以及懂礼节等美好品格都在第一视角对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死疲劳》中,主人公西门闹勤劳且富有道义,却不幸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走向悲剧的宿命,发人深省,引发读者对当时社会的反思与批判。
此外,“美育立人”也是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思想,美育突出感悟和体验,突出自然美、艺术美对人的感化[7],通常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主人公的人物形象之“美”,表现手法多为外貌描写。原文中对西门闹的直接外貌描写并不是很多,《生死疲劳》这本书讲的就是西门闹转世投胎的经历和在其中体现的美好品质,西门闹转世后,无论寄居于何种动物身上,都仍然保有鲜明的人性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外貌之美。《生死疲劳》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情节就是对西门闹寄居动物外貌的惊叹,文中也花费大量笔墨塑造寄居动物外貌之“美”,从侧面烘托西门闹的正面形象。
总而言之,莫言在《生死疲劳》中刻画了一位兼具“善”与“美”的正向人物形象——西门闹,给予读者正确的道德启示,是文章的灵魂,因此,其形象在译文中的构建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尤为重要。下文将从道德层面和审美层面两方面去分析《生死疲劳》中主人公西门闹这一形象的“善”与“美”构建,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原文与译文中的典型案例,对比分析“善”与“美”形象的构建。
3 《生死疲劳》中“善”与“美”形象构建的英译
《生死疲劳》在2006年首次出版,两年后,葛浩文英译本出版,直到现在,《生死疲劳》仍只有一个译本,葛浩文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曾翻译多部莫言的文学作品。《生死疲劳》英译本一经出版,就在西方世界引起广泛讨论,葛浩文使用尊重原文内涵和思想的翻译策略,用地道的英文表达将原文内容传达给西方读者。《生死疲劳》英译本在西方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因此,对其中西门闹“善”与“美”形象的构建进行鉴赏,可以从中窥见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冰山一角。
3.1 从道德层面鉴赏西门闹之“善”的形象构建
人物形象是现代文学的灵魂,尤其是正向人物形象,即文学作品中体现积极、正向的价值观,具有善良、勇敢等道德品质的人物形象[8]。这些正向人物很有可能在文中扮演着主角或其他重要角色,他们的道德决策和行为反映作者的价值观念,对读者进行道德启示和引导[9]。译文中,葛浩文使用 “iron man” “appropriately”等词来形容主人公善良的品格。在《生死疲劳》中,主角西门闹被枪毙后,也仍然保持着生前美好的品格,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正向人物形象。
例1: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一个硬汉子的名声。(莫言,2012:3)
译文:Not a word of repentance escaped my lips though I was tortured cruelly, for which I gained the reputation of an iron man.(Goldblatt, 2012: 3)
例1中原文塑造了西门闹的硬汉形象,译文将“硬汉子”译为“an iron man”,这一词在西方世界里有独特的含义,并不能和原文完全对应,“Iron Man”是美国漫威电影中的重要角色,是美国个人英雄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用“an iron man”来塑造西门闹的形象,在文化内涵上显然偏离原文很多,但和原文一样塑造出西门闹勇敢坚毅、不畏强权的英雄形象。葛浩文追溯自己的本土文化,以“自我”形象描述“他者”形象,更方便译文读者理解。
例2:豁出去了,我想,宁愿在他们的石墨里被研成粉末,宁愿在他们的铁臼里被捣成肉酱,我也要喊叫:
“冤枉!”(莫言,2012:3)
译文:To hell with them! I thought appropriately; let them grind me to powder under a millstone or turn me to paste in a mortar if they must, but I'll not back down.
"I am innocent!" I screamed.(Goldblatt, 2012: 4)
例2是西门闹在地府经受很多磋磨后,仍然坚定不移地喊冤叫屈,这一段原文是对西门闹的心理描写,译文中也是有一段心理描写,即“I thought appropriately”,译者补充“appropriately”更明显地点出这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视角在讲述故事,译文中的“appropriately”也是在呼应前文的“have suffered their earlier brutalities in vain”,更符合英语行文注重逻辑关系的特点,西门闹不想让之前的磋磨白白承受,所以豁出去的想法非常“appropriate”。最后,西门闹大喊“冤枉”,在译文中被处理为西方法庭惯用的“I am innocent!”,更便于西方读者理解,达到相同的效果。总的来说,译文刻画了西门闹坚强不屈的形象,“I will not back down.”,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葛浩文的英语母语者身份使得他的译文能够更好地贴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
例3:我家的大门虚掩着,从门缝里能看到院子里人影绰绰,难道他们知道我要回来吗?我对鬼差说:
“二位兄弟,一路辛苦!”(莫言,2012:8)
译文:Through the unlatched gate at my house I saw many people in the yard. How did they know I would be coming home? I turned to my escort.
“Thank you, brothers, for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seeing me home,” I said.(Goldblatt, 2012: 9)
例3原文中西门闹虽然在阴曹地府饱受折磨,但仍然保持良好的品性,对两位押送他的鬼差礼貌答谢告别:“二位兄弟,一路辛苦!”译文中将其译为“Thank you, brothers, for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seeing me home”,表达更加具体,译文塑造出西门闹礼貌善良、能够体谅他人辛苦的绅士形象。
除了主人公的“善”,作者在描述凶残的鬼卒时,也使其偶尔流露出人性的“善”。例如阎王对西门闹宣判之时讲到以下内容。
例4:“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这是本殿也无法改变的现实。现在本殿法外开恩,放
你生还。”(莫言,2012:4)
译文:"All right, Ximen Nao, we accept your claim of innocence. Many people in that world who deserve to die somehow live on while those who deserve to live die off. Those are facts about which this throne can do nothing. So I will be merciful and send you back." (Goldblatt, 2012: 5)
例4原文中展现出阎王也受到一些制约,也有无法改变的现实,译文中将其译为“this throne can do nothing”,很好地展现了阎王和鬼界的“无能为力”,这说明,阎王和鬼界与人间官府一样也受到很多制约。
这从侧面体现了阎王的“善”,《生死疲劳》中,阎王具有人性,对应人间官府中的官员,这个形象塑造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阎王前期明知西门闹是冤死的,仍然对其使用酷刑,而后又巧言令色哄骗西门闹,但在此段中,阎王传达出自己的无可奈何,给这个反面角色增添了一丝善良底色和人性,与此同时,也向读者传达出个人命运在历史洪流中的无可奈何,揭露残酷的现实,引人深思。
3.2 从审美层面鉴赏西门闹之“美”的形象构建
小说中的外貌描写也是形象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貌描写对形象性格、内涵的刻画也有很大影响。《生死疲劳》中,对于主人公西门闹的直接外貌描写不是很多,但作者巧妙的侧面书写生动勾画了一位勇猛强壮、英俊果敢的绅士形象。比如蓝脸、黄瞳对西门闹的感叹、面对自己妻子时的男性自卑。除此之外,西门闹被枪毙后进入轮回,精魂寄居于各种动物身上,对这些寄居动物的外貌描写其实也是对西门闹之“美”的形象构建。译文中采用 “wonderful”“intelligence”等词修饰动物之“美”,衬托西门闹“美”的形象。
西门闹转世成为驴时,陈区长一见到西门驴就惊叹:
例5:“真是一头好驴,四蹄踏雪!”(莫言,2012:31)
译文:“That's a wonderful donkey. His hooves look like they're stepping in snow." (Goldblatt, 2012: 37)
例5原文刻画的是一头英俊无比的小毛驴,健壮英勇,译文中用“wonderful”“fine”表现出了周围人对西门驴外貌形象的赞赏,美中不足的是,中文简短有力的四字短语没有能够在译文中体现,最后也以句号结尾而不是原文中的感叹号,对西门驴外貌的惊叹没有完全表达出来。葛浩文在此段译例中更为注重原文内容的传达,忽视中文特殊语体的审美作用,虽能传达西门驴的外貌之美,但审美效果不可避免地大打折扣。
第二次西门闹转世成为牛,原文中对西门牛的外貌描写有:
例6:这头小犍,约摸有一岁年龄,毛色如栗,皮滑如缎,双眼明亮,透着机灵与顽皮,四蹄矫健,显示着速度和力量。(莫言,2012:93)
译文:Looking to be about a year old, it had a chestnut-colored coat, a satiny hide, and big, bright eyes that signaled both intelligence and a mischievous nature. We could tell he was fast and powerful by looking at his strong legs. (Goldblatt, 2012: 111)
例6原文是蓝脸去牛市第一次见到西门牛的描写,通过外貌描写可以看出西门牛是一头品质上乘的牛,完美具备主人公西门闹的英雄气质,译文中也选用“big、bright eyes、intelligence、mischievous、fast、powerful”等褒义词再现原文中西门牛身材矫健而又聪明的形象。葛浩文有意识地运用简短词汇尽量还原原文中四字词语的韵律之美,虽不能完全等同,但体现出葛浩文对原文审美的感知和理解,译文也成功塑造了一头健美聪明的牛的形象,达到对西门闹之“美”的形象进行塑造的效果。
第三次西门闹转世成为猪,原文中对西门猪的刻画如下。
例7:这头猪智力非凡,蹄腿矫健,但个性倔强,一般情况下都是我行我素,不喜欢听人摆布。(莫言,2012:241)
译文:He's smarter than other pigs, and has powerful legs. But he can be stubborn and he likes to do things his own way. He doesn't take orders well. (Goldblatt, 2012: 267)
例7对西门猪的刻画也是智力、体力双强,译文巧妙运用“smarter than other pigs”阐释西门猪的聪明机智,“powerful legs”则展现西门猪的强壮,为之后西门猪成为猪王做铺垫。葛浩文用地道的英文表达传达原文的情感内涵,增强文章可读性。
接着西门闹转世成为狗,原文中描述为:
例8:在我儿子身后,是那犹如牛犊一样的威武大狗。(莫言,2012:419)
译文:Behind him came that brute of a dog. (Goldblatt, 2012: 423)
例8这段话原文着重描写西门狗的体型,“犹如牛犊一样”“威武大狗”,展现西门狗的勇武健壮,译文用“brute of a dog”来表述,“brute”一词虽然展现出西门狗的魁梧,但其强调粗野、野兽,包含贬义,感情色彩有失偏颇,并且省略原文中的比喻,没有将原文“美”的形象真正阐释出来。
最后西门闹转世成为猴:
例9:这只猴子自然是雄性。它不是我们习常所见的那种乖巧的小猴,而是一只身材巨大的马猴。(莫言,2012:523)[10]
译文:Naturally, it was a male monkey, and not one of those cute little things we're so used to seeing. It was a large rhesus monkey. (Goldblatt, 2012: 521)[11]
例9是对西门闹动物转世最后一世西门猴的外貌描写,原文描述为“身材巨大的马猴”,译文中为“a large rhesus monkey”,阐释了西门猴的高大威猛。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西门闹转世成为的动物形象都是身材高大、勇猛健壮而又很有智慧的正面男性形象,译文也基本传达出西门闹寄居动物的正面形象。西门闹的魂魄寄于这些动物身上,其实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西门闹精魂的勇猛与智慧,借动物塑造西门闹的“英雄”形象,更鲜明地表达出对他悲惨遭遇的反讽和悲叹。
《生死疲劳》中对西门闹精魂之“美”的塑造除了正面描写,还有对鬼卒、阎王等形象塑造的反面衬托,“阎王和判官们脸上油滑的笑容”“不怀好意的笑容”“狡猾的笑容”,译文中的描述对应为“oleaginous”“no trace of kindness”“sinister”等,为非常明显的负面形容,阴险狡诈、面目丑陋的鬼卒以及阎王的形象被鲜明地表现出来,更好地反衬出西门闹精魂之“美”。
4 结束语
/cl8ejOgXEk5jfgJfIJSuw==莫言的《生死疲劳》是一部杰出的当代小说,本文通过对其中文化形象和艺术想象的分析及其在英译本中的再现,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文化间的沟通交流。《生死疲劳》中,西门闹的精魂体现了“善”与“美”的品格。在道德层面上,西门闹面对强权从不屈服,坚毅勇敢,是一个硬汉子,同时也反映出西门闹有高尚的品格,是一位懂礼貌,能够体察别人辛苦的绅士。在审美层面上,以动物为载体,其外貌被刻画得勇武英俊。主人公西门闹是时代造就的悲剧,作者赋予其“善”与“美”的品格,促使人们对当时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此外,译文在刻画西门闹的“善”与“美”时,由于原文中包含许多的文化元素,可能无法使得西方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完全对等的反应,但葛浩文英语母语者和汉学家的双重身份,促使他为弥补文化障碍做了很多努力,最常见的翻译策略就是增译,辅以地道的英语表达,增强文章可读性。葛浩文根据自己对原文形象的理解,采用增译、具体化等策略对原文的情感和内涵做出阐释,方便译文读者理解,实现文化沟通和交流,虽然略有不足,但仍是一篇较为成功的译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有非常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牛佳欣.新世纪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以贾平凹、莫言为中心[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23,23(4):15-19,86.
[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2.
[3] 王运鸿.形象学视角下沙博理英译《水浒传》研究[J].外国语,2019,42(3):83-93.
[4] LEFERVERE A.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M]. London:Routledge,1992.
[5] 张欣.政治化的言说与先锋性的重塑:“十七年”《麦田里的守望者》译介的形象学阐述[J].东方翻译,2020(1):15-23.
[6] 石欣玉,黄立波.翻译研究的形象学路径探索[J].外国语,2024,47(1):90-97.
[7] 冯能锋,唐善林.现代文学中的“美育立人”思想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22,42(9):80-86.
[8] 王小燕.中国现代文学中“零余者”形象的价值探讨:基于郁达夫作品为例[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23,21(2):124-127.
[9] 刘茜.现代文学中正向人物形象与道德启示研究[J].极目,2024(2):18-22.
[10]莫言.生死疲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1]GOLDBLATT H. Life and Death Are Wearing Me Out[M]. 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 New York,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