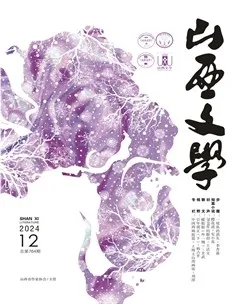中国西画摇篮:上海土山湾画馆
在西画传入中土的漫长过程中,传教士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回顾相关历史,在4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先后三次出现过与传教士相关的西画东渐现象。第一次是在明末万历年间,第二次是在清代中期,时间跨越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第三次是在晚清的同治年间。如果说,前两次是在罗马耶稣会派遣传教的背景下,使西洋画在中土产生一定影响,那么,第三次就是在鸦片战争的背景下,传教士由禁教所迫转为大规模地卷土重来,从而开辟了一种师徒形式的西画传授。创办于同治年间的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画馆,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事例。这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修士共同担当的结果。西班牙传教士范廷佐、意大利传教士马义谷、法国传教士范世熙以及中国修士陆伯都、刘德斋等,这些原本陌生的名字,在西画东渐中获得了历史的尊重。
一
清道光22年,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由此构成五口通商,形成外国人在中国租地通商的特殊时代并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1843年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实施。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条约规定,教会可以到通商口岸及内地游历传教。此后,西方各国教会势力大量涌入上海,而上海作为首批开放口岸和中国沿海较为繁荣的城市,必然成为列强的首要目标,于是,西方各国的教会势力纷至沓来。有关资料统计,从1842年到1911年,来华的欧洲传教士多达130余人。随着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张,天主教堂如雨后春笋在江南地区出现。因此,造成大批宗教饰品的短缺,包括圣像画、雕刻品和祭台等。尤其是大批量的宗教人物画的需求量猛增。因此,搜罗绘制宗教画的艺术人才,就成为一件头等大事。于是,天主教在上海大兴土木,建造教堂,使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流与融合,并且出现了新的格局。土山湾画馆应运而生。
土山湾地处上海徐家汇。早在1832年到1837年间,思想家、民族英雄林则徐出任江苏巡抚,府衙设在苏州,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同时,他率领官员民众,全力治理太湖水系,疏浚河道,促进漕运与经济繁荣。在疏浚漕溪、肇嘉浜、蒲汇塘的同时,用淤泥堆积出一片高地,当地人称其为土山湾。1864年,孤儿院迁移至此,而土山湾画馆仅仅是孤儿院诸多下属部门中非常特殊和规模最小的一个。但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成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之地,造就了一代艺坛宗师。
当年,在徐家汇肇家浜和蒲汇堂两河交汇处,有一片名为“徐家汇”的土地,在当时仅仅是江南的一片农村景象。举目望去,阡陌纵横,遍地坟茔,夜晚磷火跳跃。冬季早晨,薄雾弥漫在河流之上,穿行在树木之间。土山湾占地面积80余亩,曾经是上海的一个重要地标。当年,上海天主教会孤儿院从横塘搬迁到这里时,曾经是一望无际的芦苇荡,当时易名为“土山湾孤儿院”。三年后,土山湾孤儿院在这里建造了教堂和多排房屋,成为孤儿住宿、学习和职业训练的场所。随着江南地区天主教堂的不断增多,教堂内的绘画、版画和雕塑供不应求,于是,土山湾孤儿院决定开设拥有木板雕刻、印刷、金工和美术工场,后来,土山湾画馆就成为那些孤儿学习西洋画的重要场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美术教育机构。
尽管那些为数不多的历史照片早已泛黄,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土山湾画馆当年的面貌。高高的围墙,青砖黑瓦的建筑,以及教堂上镶嵌的十字架。“正门前有码头靠岸的石砌台阶,驶入肇家浜的小船可以在这里上岸。粉墙上有毛笔书写的大字——土山湾,围墙上有一块书有TOU—SE—WE—土山湾的木牌。进入正门,迎面尽头是一座雅致的圣母亭,左右两边是对称的两排建筑,右面是大修院,左面是一排两层楼的房子,画馆就在其中。就是在这里,土山湾的孤儿们拿起了油画笔,开始了迥然有别于他们祖先的绘画训练,并成为第一批系统掌握油画技艺的中国人。” (《中国油画500年》 第1卷,赵力、余丁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第643页)
谁也没有想到,土山湾画馆的开办,给无缘涉足西方艺术的中国人提供了一扇观察、了解和学习西方艺术的窗口。
土山湾孤儿院中的美术工场,被称为土山湾画馆,画馆于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正式设立,当时招收的学生屈指可数,而中国修士陆伯都(1836—1880)在这个时候成为绘画雕塑工场的第一任中国主持。直到三年之后,孤儿院扩建,还增加了一座小型教堂,孤儿院的人数多达342人。由于陆伯都长期生病,从1869年开始,绘画雕塑工场的主持工作就由刘德斋(1843—1912)代理。这是目前美术史研究所知中国最早以学徒方式培养中国西洋画专业人才的场所。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大约有300多名孤儿在那里接受过严格训练,他们学习的科目有素描、水彩、版画、雕塑和油画等,经过六年的学习之后,大多数人留在画馆工作,为日益增多的教堂提供圣像以及其他宗教用品。与此同时,他们也为上海之外的教堂绘制作品,可以说,他们的作品遍布全国各地的天主教堂。
画馆内有安静的教室,坡顶结构的天花板上画满了圣经故事,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油画绘制的圣像,那些外国传教士教师在教室里走来走去,巡视着每一位学徒者专心致志地临摹的作品——那些中国学生,头戴瓜皮帽,后背拖着长长的辫子。他们在自己的座位上聚精会神地用教师传授的方法,再用素描或油画的方法去描绘圣像。但是,那些孩童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所作所为,超越了自己的祖先而成为第一代系统掌握油画技法的中国人。在教师的耐心指导下,那些圣像被他们描绘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从土山湾画馆走出的徐咏青,最后成为中国的水彩画之父,漫画大家丁悚,月份牌的先驱者杭穉英,雕塑家张充仁等,都曾在土山湾画馆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海派大家任伯年,曾通过土山湾画馆的朋友学习西洋素描。雕塑家张充仁在谈到任伯年时说道:
一个有趣的回忆,余十七岁时卅八年前与上海土山湾图画馆前主任刘德斋之门人安守约谈天,安偶然谈起刘德斋与任伯年之往来曰:“一日,余与刘修士访任伯年,讨论绘事,任曰:‘西法画与国画较之,国画为快。’随后手取一纸,画玉蜀黍二,很快完成。”
这个事实说明任与萌芽状态之西画界,不但有接触,而且有一定观察认识,乃至有过研究,对此我们更有其他材料足以证明。(《中国油画500年》 第1卷,赵力、余丁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第641页)
多少年之后,当他们走出土山湾画馆时,在社会上开设工作室,向学生们传授西洋画技法和理论,传授在土山湾画馆所学到的知识,曾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画馆将西洋画的多种技术因素贯穿于教学之中,构成了继北方清宫油画、广州“外销画”之后近代中国西画东渐又一处重要的典型样板。与中国人聪明、勤奋、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数千年的传统艺术相融合,出现了一批享誉海内外的艺术家。正如曾经受过土山湾绘画影响的徐悲鸿先生所言:“土山湾亦有可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1943年,由土山湾画馆印刷出版的《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对画馆有这样的描绘。“图画馆,分水彩,铅笔,油画等。其出品曾获得南洋劝业会历次褒奖。又制造彩绘玻璃,供给各交通及建筑界之应用,为中国彩绘玻璃之第一出品处。”
从1864年到1934年的70年间,土山湾孤儿院先后收养孤儿2500余人。如何解决这么多孤儿的生计,确实是一个需要面临的问题。实际上,1864年开办的土山湾画馆,就是为孤儿院的孩子们长大之后的就业考虑的。画馆以孤儿院的孤儿为招收就业的主要对象,最初开设国文、算数、习字、天主教义等4年文化基础教育课,到13岁时,再根据学童的具体情况授以不同的工艺技能。满19岁时卒业。“或留堂工作,或外出谋生,悉听自便。”有关文献记载,留堂工作的学生居多,当工艺学校和孤儿院合并之后,收养的孤儿可以一边在画馆学习各种美术知识,也能够在工场中进行具体实践操作。就这样,他们成为最早接受西方美术教育的中国学子。实际上,土山湾画馆也是中国最早的正规美术教育机构,它的出现,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全新方式和内容,开创了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之先河。
土山湾画馆最初设有图画与雕刻两个部门,图画间从欧洲直接引进西洋绘画艺术,有铅笔画、水彩画、木炭画、油画等。雕塑间有塑像、木雕、木刻等西洋雕塑艺术。尽管西洋美术早在明末的万历年间由传教士利玛窦带入中土,但毕竟是作为从艺术的欣赏和观看开始的,将西洋美术纳入正规的教育,是从土山湾画馆开始的。
二
徐家汇位于上海西南部,当时一片荒芜,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因为徐光启的后代在此居住,及其徐的墓地也在此安葬,耶稣会便在此设立中心会院,但还没有一座正规的教堂。1851年,耶稣会筹集8000银两作为建筑费用,由辅理修士范廷佐((Joannes Ferrer,1817—1856)亲自设计,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按照欧洲建筑风格建造的希腊式教堂——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上海的第一座天主教堂。这座教堂是以耶稣会的创始人、去世后被罗马教皇封为“圣徒”的依纳爵(Ignacio de Loyola)命名,被称为“圣·依纳爵堂”(《雄狮美术》1994年第2期)。圣·依纳爵教堂的设计者范廷佐,西班牙人,他的父亲是西班牙一位著名的雕塑家,他希望儿子未来继承自己的事业,于是他将范廷佐送到意大利罗马进行深造。可是,范廷佐来到罗马之后却积极参与了天主教的活动,在修道院做修士。数年之后,在他的反复请求下,耶稣会派遣他到遥远的中国传教。范廷佐于1847年经过数月的海上旅行之后到达上海,由于他在建筑、雕塑和绘画等方面的专长,被派遣主持董家渡天主教堂的设计。
范廷佐亲自绘制并雕塑圣像,并且认真指导木工制作祭台等宗教用品。史料记载,该天主教堂祭坛下部的浮雕《基督的葬礼》就是范廷佐所作。1851年,范廷佐看到在建设中的教堂内部需要大量的绘画与雕塑,但是,上海又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于是,他建议将工作室扩大并兼做艺术课堂,教徒即为学生,向他们传授绘画、雕塑和版画的技法和专业知识。范廷佐的建议很快得到郎怀仁(Admianus Languilat,1808—1878)神父的大力支持。1852年底,德高望重的郎怀仁神父亲自从张家楼修道院里选中中国修士陆伯都作为范廷佐的第一个学生;那时,陆伯都刚满16岁,在跟随范廷佐学习数年之后,成为土山湾画馆中雕塑、绘画、版画工场的第一任主持,为西洋艺术传入中国作出了杰出而重要的贡献。
土山湾画馆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洋美术的传授机构,缘于上海及周边教堂数量的不断剧增,以及教堂内宗教用品的需求。
艺术史家张弘星在《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摇篮——上海土山湾孤儿院的艺术事业》一文中这样写道:
1847年以后,徐家汇是中国耶稣会总部所在地,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些教会机构,比如天文台、藏书楼、圣母院、教堂、大小修院以及徐汇公学。土山湾位于徐家汇南端,占地大约八十余亩,一条河从他的东南两面流过,许多年前当疏通河道时淤泥积在湾处,而形成土山湾。孤儿院的大门正对着河,河上有一慈云桥把孤儿院与对岸连接起来。孤儿院北面是大修院和主教公署,西面则是大片农田。(《东海文化》1991年第5期)
可以说,土山湾画馆是土山湾孤儿院工场里最特殊的一部分,画馆的学徒不过20多人,年龄都在十五六岁左右,对土山湾更多的孩子来说,绘画是一种不知所云的偏门课程,所以很少有人关心,而其他修士对绘画同样是外行,甚至根本不懂识别绘画的人才。在教学的内容上,画馆采用了西方美术的技法,范廷佐曾在意大利罗马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深受文艺复兴之后罗马艺术思想的影响。在画馆早期的教学中,他曾担任素描与雕塑的教学工作,同时也开设油画课程——这是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中前所未有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上,范廷佐极其注重工艺美术的传授,在绘画方面,主要以宗教人物、花卉和壁画为主要内容,同时让学生临摹欧洲名画并出售。也让学生创作油画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幅油画《利玛窦与徐光启像》,作品采用的是西方油彩和中国传统工笔相融合的方法,描绘了身穿中国传统儒士服装的利玛窦与徐光启,成为兴趣与事业的同道者。在雕塑的教学上,以泥塑圣像为主,那些中国学生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专业能力迅速提高,很快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重要的是,这种科学的美术教育方法,揭开了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全新的一幕。
孤儿院的大部分学生进入画馆之后,便开始了为期六年的基础学习和工场实践。画馆实行全封闭管理,不允许随便外出,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在美术教学方面,以临摹和写生为主,还有石膏像等物体让学生进行造型训练,同时加强学生擦笔画、木炭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和油画等基本技法的训练,等到学生初步掌握一定的技艺之后,画馆面向社会接纳订单,让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去独立完成,学生们恰恰在这样的学习与实践中,迅速成长壮大。
在土山湾画馆从事美术教学工作的教师,最初是以欧洲传教士为主,再往后,一批中国学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之后,被留在画馆任教,既补充了师资力量,又成为画馆在圣像制作上的骨干力量。画馆初期的教师有范廷佐、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马义谷(Nicolas Massa,1815—1876)、修士画家陆伯都、法国传教士范世熙(Adolphe Vasseur,1828—1899)、中国画家刘德斋等,这些中外画家一起,共同培养了徐咏清(1880—1953)、周湘(1871—1934)、张聿光(1885—1966)、丁悚(1891—1972)、杭穉英(1900—1947)、张充仁(1907—1998)等一批日后成长起来的中国美术大家。尽管当时土山湾画馆的条件极其有限,在教学上还处在对西洋画的临摹阶段,但是为满足教会的需求,“唯所画,皆为宗教性质之题材”。土山湾画馆的诞生,意味着中国最早的西洋美术传授机构已经在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而那些被称为“土山湾堂囝”的孤儿,成为第一批系统掌握西洋画技法和手艺的中国人。
1851年,当范廷佐在徐家汇的工作室开始招收中国学徒并传艺时,曾请马义谷传授油画。当时,他们除了从欧洲带来少量的绘画作品之外,颜色与画布都要在当地制作。所以,中国学徒在马义谷的带领下,开始学习研磨调制颜料和制作画布,土山湾画馆的学生,不仅能够创作油画,还掌握了自己动手制作颜料和画布的本领。随着各地天主教堂的建立,圣像的需求数量日益增多,而工作室复制圣像作品达到供不应求的程度。画馆的那些中国学生,通过临摹复制圣像的过程,在马义谷身边学到了许多油画的技法和专门知识。范廷佐去世之后,马义谷成为土山湾画馆的主持,在他的学生当中,除了陆伯都之外,还有刘德斋等人,遗憾的是,其中一些人的姓名,被时间和岁月所冲洗,逐渐不为人知。
刘德斋是江苏常熟人,早年从家乡到上海徐家汇,就是为了学习绘画和雕塑。1856年范廷佐去世之后,他跟随马义谷和陆伯都学习,1867年跟随陆伯都进入土山湾孤儿院之后,曾经绘制过大量的圣像和圣经插图。1869年,因为陆伯都疾病缠身,刘德斋开始主持画馆工作,同时处理日常事务。19世纪70—80年代,是刘德斋创作上的一个高峰时期,他为董家渡教堂绘制许多油画,尽管这些作品多为仿制品,但是完全可以和马义谷在油画的教学内容取得某种联系,体现出一种西方模式下的传承关系,也是西画东渐过程中——作为一个重要阶段——的开始。实际上,刘德斋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在西方化的关系中注入了浓厚的中国色彩。这一点在他的《中华圣母子像》的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上圣母端坐在中国式椅子上,耶稣立在她的左腿之上,有趣的是画面上两个人都是身着清人服饰。“此画是中国中华圣母像的代表作品。”
三
如果从近代美术教育的意义上说,范廷佐和马义谷这两位欧洲传教士,是西洋美术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而且,他们的传教方式远比广州“外销画”时期钱纳利对林呱等人的传播具体而生动,也不逊色于郎世宁和王致诚等人。重要的是,范廷佐和马义谷所教过的学生,后来成为画馆的主持或教师,有的甚至成为影响深远的艺术大家。
受教于土山湾画馆的周湘,是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开拓性人物,20世纪初曾在上海开办“布景画研习所”,乌始光、丁悚、张聿光、汪亚尘、陈抱一、刘海粟等一些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闪闪发光的名字,当年都是“布景画研习所”的学生。出自画馆的另外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徐咏清,曾经在上海四马路开设过水彩画馆,在接受商业订单的同时,也曾吸引了大批上海青年前来学习。同样出身于画馆的艺术家张充仁,擅长油画与雕塑,他于1936年在上海合肥路开设了“充仁画室”,很快就有一批青年艺术家围拢过来,这些年轻人在张充仁的指导下迅速成长,他的画室所培养的学生人数达300之多。随着时间的流逝,土山湾画馆的西洋画技法为更多的人所学习并掌握。事实上,正是这一批西洋美术教育的先行者,以及发挥的启蒙作用,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相关的历史文献表明,土山湾画馆的美术作品,从主题上说属于宗教作品,完全供应宗教事业的发展和需求,是为宗教服务的。在1860年代之前,随着各地天主教的兴建,圣像的需求量急速上升,艺术家们的主要工作是绘制油画、水彩以及雕塑,终日埋头苦干,依然无法满足诸多教区的需求。仅上海而言,当时的天主教活动极其频繁,周边所建造的天主教堂日益增多,教堂内所需要的圣像画、雕刻、祭台、圣爵和圣盘的数量大幅度上升。尽管教会旨在为宗教宣传服务,但客观上促成了美术工场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并且系统地传授西洋美术知识与工艺技术,培养所需的专门人才。1914年出版的《徐汇记略》曾有这样的记载:“图画馆非水彩铅笔油彩等,其所绘花草人物,摹真写影等件,前经南洋劝业会颁奖凭,十九件之多。近日新添彩绘玻璃,将人物鸟兽彩画于玻璃上,后置炉中煨炙,彩色深入玻璃内,永久不退,中国彩绘玻璃,此为第一出品处。”尤其是西洋画与雕塑,在当时的上海实属罕见。有些作品还销往海外,其中一些欧洲古典名作的临摹作品,价格非常昂贵。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发展的基础,正是铅笔画、水彩画、水粉画、油画和雕塑的西洋美术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铅笔画(素描)到油画的认识与实践,构成了西画东渐的一个重要过程。尤其是在传习上,新的教学方法贯穿于土山湾画馆从开办之初到最后的整个过程,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传习模式,由此建立起画馆最明显的教学方式和专业特色。如潘天寿所说:
上海徐家汇土山湾教会内,亦有若干人练习油画,且自制油画颜料。唯所画,皆唯宗教性质的题材,指导者为法国教士,学习者则为中土信徒。(《中国绘画史》,潘天寿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土山湾画馆的现象,作为传教士文化的余脉,为西画东渐的历史提供了可以深入研究的文本,尤其是它的艺术价值,远远超过了传教自身的意义。而土山湾画馆,构成了“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作为西画东渐的一个重要现象,随着历史不断被揭开,它的“摇篮”效应在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与挖掘中不断被展现出来,无论是它的艺术实践和被称为“中国早期的现代美术教育”,成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
上海土山湾画馆从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到20世纪40年代末,前后历时80余年,几经社会动荡与变革,成为历史的记忆,永远保留在历史的深处。画家丁悚在他的《上海早期的西洋画美术教育》一文中记载道:
上海西洋画美术教育,最早是徐家汇土山湾天主教堂所办的图画馆。该馆创立于清同治年间,教授科目分水彩、铅笔、擦笔、木炭、油画等,以临摹写影、人物花卉居多,主要都是以有关天主教的宗教画为题材,用以传播教义。(《上海地方史料》第五期,丁悚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 第208页)
梁锡鸿在他的《中国洋画运动》一文中写道:
上海西洋画输入的机会较多,在徐家汇有一所天主教所立的学校,内设图画一科,专授西洋画法,不过所有作品,均带有极其浓厚的宗教气氛。(广州《大公报》1948年6月26日)
早年曾经参观过土山湾画馆并一度受其影响的徐悲鸿,对其作出了准确的历史评价:
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其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中国油画500年》第1卷,赵力、余丁编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第645页)
当晚清传教士美术在北方宫廷逐渐走向它的衰退时,面临的是百年夭折的窘境。也许就在这时,土山湾画馆在上海出现,意味着历史选择了上海,使“西画东渐”在传统文化深厚的中国发生历史性的转机,由此奠定了上海油画最初的格局,体现出它所具有的划时代的美术史意义。
土山湾画馆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影响不仅仅是兴办美术学校,重要的是对近代美术教育的内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当时,很多教材都成为“我国西画教育最早的教科书”,不仅使学生的眼界得以开阔,思想得以解放,也掌握了西洋画的方式方法,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珍贵文本。尽管它自身还有许多局限性,但是,在当时对学生所起到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而那些学生,有些人走出国门,到东洋或西洋学习继续深造,对西方美术继续深入地研究与实践,回国后在现代美术教育或西洋美术的实践上,成为开拓性人物。
土山湾画馆是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画家在中国活动的一个侧影。从范廷佐到马义谷再到刘德斋等人,完全可以梳理出画馆的油画在实践与发展上的一条脉络。而马义谷和刘德斋,构成了西洋画在传习中的两个重点——在师徒关系和两位画家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情结,还潜藏着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在相互渗透中获得一种中西融合的全新画风,由此体现出清末“西画东渐”进程中的某种变化与超越。而这种超越的真正意义,构成清末民初西洋画在中土的全新面貌。由此使土山湾画馆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土山湾画馆作为在西方教会的直接影响与需求下创办的美术教育机构和美术工场,它既是西画东渐过程中西方文化“中国化”的产物,同时也使学习西洋画在方法上建立起一个基本的框架。尤其是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明确了培养对象和学习方向,并且逐渐确立了教学内容和学习方向,特别是其独特的教学方式和运营机制,对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的启蒙和推进,不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上海是中国油画起步最早的城市,而土山湾画馆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特别是在教学的方法上,已经具备了较为完整的形态,使欧洲油画以完整的技术在上海出现。上海在油画上所拥有的一切,完全得益于土山湾画馆。可以说,一部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在那个时代就是以上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油画史。正如陈抱一所说的那样:“上海方面洋画运动的发端,也可以说是中国洋画运动的开始。”(《民国美术思潮论集》,素颐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第509页)
当年由土山湾画馆绘制的油画原作真迹现已消失,不复存在。出现于同时期画馆以及教会场所的作品,如今可以从残存而早已发黄的历史照片中辨别。其绘画风格与特点,依然可在后人的评论中,获得佐证。可以这样说,土山湾画馆的出现,在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1940年代徐悲鸿先生在《新艺术运动的回顾与前瞻》的文章中对土山湾画馆第一次赋予它应有的历史评价和定位,并将其称之为中国西画的“摇篮之地”。尤其是为中国油画的兴盛,起到极为重要的铺垫作用。
另外,土山湾画馆是自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所中国的美术学校——尽管它的组织与建制与现代美术学校还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更多地带有中世纪欧洲作坊的痕迹,但毕竟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首次开始有规模、有系统、有方向地向欧洲学习的具体操作与实践。重要的是,培养了很多精通西洋美术的专业人才,由此成为上海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艺术的前沿阵地,对20世纪的中国现代艺术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土山湾画馆走出去的周湘,成为现代中国最早创办美术学校的开拓者。
土山湾画馆的美术教育,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启示——如果没有西方传教士入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教育,现代美术教育更不知从何谈起。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向李鸿章(1823—1901)建议,清政府应该每年拨出100万两银子投资教育。李鸿章回答说:“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李提摩太说:“这是种子钱,将来会有百倍的回报。”李鸿章问道:“多长时间能看到回报?”李提摩太说:“大概需要20年。”李鸿章连连摇头说道:“我们可等不了那么久。”其实,李鸿章和李提摩太都没有想到,义和团事件导致清政府大赔款,大赔款用于中国教育的大发展,这等于强迫政府拿出一大笔钱投资教育。
如今,土山湾画馆的旧址早已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遗址之上每天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而河流中静静流淌着的却是默默无语的千年之水,构成一种水脉相通、文脉相连、人脉相亲的全新景象。在从农耕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江南文化得以传播、弘扬。
尽管当年土山湾画馆的油画早已无影无踪,但是,它由宗教走向世俗,从画馆走向民间,最终,走出土山湾,为西方油画在中国的传播,为现代美术教育开辟了一片新的天空。
【作者简介】刘淳,1957年出生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成长于山西太原。毕业于山西大学艺术系油画专业。主要著作有《中国前卫艺术》《艺术·人生·新潮――与41位中国当代艺术家对话》《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文库:刘淳自选集》《中国油画名作100讲》《薛松访谈录》《邱光平访谈录》 《中国前卫艺术》 《中国油画史》《艺术的态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