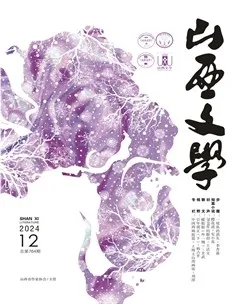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
时常会想起在童年,我很喜欢待在外公家里,在二楼的平房当中,放置许多书和旧报纸。千禧年代初,可供娱乐的消遣本就少得可怜,外公家甚至都没有安装电视,这些书籍成为我想象世界的一个窗口。其实这里面的大多数书是正在读小学的我看不懂的,它有我舅舅的初高中教科书、港台娱乐八卦,还有我当时最讨厌且觉得无聊而外公最爱看的报纸。二楼干燥,这些书少说放置了十五六年,早已经发黄起麻点。夏天炎热,所有的东西都在高温下炙烤,木板楼、木窗、木柜、木桌等等,这些死去多年没有生机的东西,散发出木质独特的味道,有点像木匠刨木花,少了带水汽的生味,多了些时间在里面。
就在这样干燥郁热的夏天,我记得拿到过一本名叫《科学》的教材书,印刷着伦敦烟雾、日本水俣病后死去人的惨状,在黑白印刷、黄色纸页上显得极为恐怖扭曲。外公家本就处村落一隅,安静,一旦起风,从没有护栏的二楼阳台,可以探到梨树哗啦啦的枝叶,小时候不懂,并不畏惧走到阳台边缘去,年龄大了反而对边缘充满了恐惧。傍晚无聊的时候,就在门口的池塘看鱼,天气好的时候,波光粼粼的水面和鱼鳞反射的光相映成趣。外公外婆给我讲那些奇幻的民间故事,有会算命行乞者、游走的气功大师,还有后面住着阴郁时常发疯的女人。这些故事满足我的好奇,也成为恐惧,就一直在记忆那里。后来搬家,往后还回去过几次,外公阳台边那棵梨树被砍掉了。
很久后的某天,我坐大巴返乡时候在车上假寐,在半醒半睡之间做了一个梦,主人公A潜心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提出来一个震惊众人的发现,但是又无法证明,为此他受到了诸多谴责,人身安全也失去保障。他冥思苦想最终找出方法,隐藏一个观点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置身于众多观点之中,因此他在网络上发布许多观点消息,真真假假,顺利引发讨论与猜测,而他的发现在这次讨论中也变得平平无奇起来,成功从这次风波中脱身。
于是我想着把这个突如其来的灵感变成小说,在我的脑海中很多次总会不经意间产生一些有趣的点子,触发的因素也很偶然,它们成为我创作的开始。很显然这个灵感是我创作《一尾鱼的消失》的原型,小说最后的成型与之相去甚远,相似点大概是“消失”的主题没有变化。在大脑放空的时候,抑或每个失眠的夜晚,很容易就会想起要写的故事,我会在脑海中演示,不断设定情节又推翻,直到它基本成型。而我在创作上,确实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如果没有一些写作的契机,它可能就仅仅停留在我的大脑中。
2021年的夏天,友人约我一起去上海图书馆自习,我终于开始把这个故事写下来,等到把大脑中的故事诉诸笔端的时候,其实又与之前有很大不同,却出乎意料写得非常顺畅。甚至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想起幼时翻过泛黄的书页,事实上再去的时候,它们早已积满灰尘,我曾经渴望却没能见到游走在乡村的气功大师,在小说中为他添上一笔。八月的上海,每个周日,我和友人一起坐地铁到上图,结束后,我们从淮海中路的梧桐树下,窜入各个小街道寻访美食,往往经过一天的输出,早已经饥肠辘辘,我会和他讲我的小说进展,他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但是有意思的是,在写完这篇小说后,我并没有把这篇小说发给他看。
当然它也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帮助,我热衷于薅羊毛,向朋友们请教,从事金融行业的小均为我提供职场上的经验,朋友孙宁建议我改成现在的题目,还有王文、小鹿等人,建议我对结尾的修改,小说一直待在电脑桌面的文件夹,等我准备再投时候,也像拂去那没有的灰尘。
前些天看到一个读者评论:“作者太爱写夏天了,许多的夏天在不同人物、不同城市间交织。”我毫不掩饰对夏天的偏爱,过于热烈的氛围,稠密郁热密密匝匝的热潮从四周涌来,所有生命热烈膨胀,写作无意识的时候也把对季节的偏爱化成了小说里面的时间选择,惊觉这又是一篇发生在夏天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