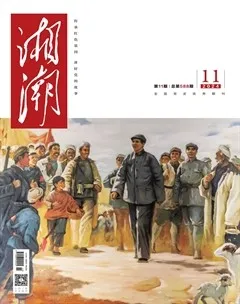原文选读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专家推荐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的文风既明白如话,又跌宕起伏。几乎每个章节都用鲜活的案例引入,可谓先声夺人、引人入胜。毫不夸张地说,只需稍加修改,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作为纪录片的解说词——既大气磅礴,又具体而微;既能让人获得文字构筑的画面感,又能让人感受辞章带来的韵律美。贯穿在这些画面和韵律中的,则是作者胸中那股子生生之气,从笔尖注入纸面。这里面凝聚着两位学人多年来研习传统文化的学养积淀、修身工夫和生命体验。那植根内心的家国情怀,历经伟大时代的淬炼激荡,终化作《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基因》一书的万千气象、无限生机。
(作者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国传统文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李勇刚)
1932年11月,上海《东方杂志》发布了一则征稿启事:“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启事一出,反响热烈。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以83页的篇幅刊出了142位社会各界人士的244个“梦想”。有人希望“未来的中国是大众的中国”,有人梦想“共老共享的平等社会”,有人相信“未来之中国,将是新锐青年的中国,不是昏庸老朽的中国,将是勤劳大众的中国,不是剥削阶级的中国”,还有人认为“理想中的中国是能实现孔子‘仁’的理想、罗素科学的理想与列宁共产主义的理想的”……这一场征文,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做梦”。而这些梦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型——“大同”。
《礼记·礼运》记载,孔子以贵宾身份参加鲁国年终蜡祭。礼毕,孔子出来在鲁宫大门楼上游览,喟然叹息,说出了一段震古烁今的话: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是一个天下和平、政治清明、经济富足、生活幸福、社会和谐的美好社会,在这里,资源公有,官员贤能,矜寡孤独无不得到悉心照顾,人人各得其所。如果分析“大同”的内涵,至少有如下三层含义。
(一)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是大同梦想最核心的标识。首先是公有。什么是“公”?《说文解字》:“公,平分也。”东汉经学家郑玄将“公”注释为“共”。《韩非子》则形象地解释:“自环者谓之ム,背ム谓之公。”ム就是私,形状像人将手臂弯曲,回护自己独有的利益。而公则是私的对立面,是大众所有,而非私有。无论上述哪种解释,“公”首先意味着全民共同拥有,正如《吕氏春秋》所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根据《礼记·礼运》,孔子向往回到的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尧舜时代。“选贤与能”一词揭示了孔子对“公”的理解——天下属于所有人,故而应当选择最贤能的人来治理,而不是像后世家天下般世代相传。本质上,这是一种民本政治、贤能政治,强调的是民众而非君主对天下的所有权。
其次是公利。在天下为天下人所有的基础上,大同社会还强调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最大限度地照顾所有人的利益,“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周易·系辞》中说得明白:“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什么是真正的事业?能让天下民众受益的,才能称为事业。中国共产党则用最通俗的语言来描述——为人民服务。
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十多年间,中国14亿多人的温饱问题得到有效解决,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超过4亿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翻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反观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较早实现了“丰裕社会”,但这种物资的丰裕主要是服务于少数资本家,而并非为社会大众服务。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发表了《丰裕社会》一书,他敏锐地观察到,当时美国的私人产品和服务十分丰裕,但公共产品与服务实际上相当贫乏。1998年,加尔布雷斯为《丰裕社会》40年纪念版写序,他再次感慨:“我的批评仍然有效。虽然我们的私人消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裕,但我们的学校、图书馆、公共娱乐场所、医疗保险甚至执法力量都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与过去相比,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差距可以说是越拉越大。”“‘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变成了‘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标语所示,我们是99%的民众,但被1%的人所控制。”
再次是公心。公有与公利,其出发点是公心——从天下人的角度出发,为天下人着想。“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这个“独”正是与公心相对。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之所以传唱千古,正是由于这一份以天下为己任的关怀。明末官员周汝登曾说:“盖人之好,即己之好,而何得独无?己之好,即人之好,而何尝独有?此谓之大同。呜呼,至矣。”
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菲科问道,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习近平主席回答,这么大一个国家,责任非常重、工作非常艰巨。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这正是对“公心”的最好诠释。
(二)博爱兼济。
“公”意味着整体,但整体中一定有差异,不同族群、区域、个人,天生禀赋不同,差异必然存在。但在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中,物无弃物,人无弃人,一个也不能少。这正是孟子“达则兼善天下”的胸怀。
聂荣臻在一封致父母的家书中写道:“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四万万同胞的衣食安乐,一个也不能少,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博爱情怀。无论是疫情中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一视同仁,还是小康路上“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不能丢了农村这一头”“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的公平普惠,都是这种博爱兼济的鲜明体现。
(三)人尽其材。
大同是完全相同吗?非也。正如没有完全平等的公平,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大同。大同,不是千篇一律,不是千人一面,而是和而不同,是人人在社会的共同体中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在这里,个体的价值从未被泯灭,每个人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进而参天地之化育,实现人之为人的最大潜能。这正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诠释中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由此可见,天下为公正是为每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完全的“人”,创造更好的平台和条件。
天下为公、博爱兼济、人尽其材的大同梦想,始于两千年前的中华元典《礼记》,之后又经由无数文人学者的阐释发扬、历代政府和民间的孜孜实践,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断重复、从未熄灭、日益浓烈的“中国梦”。
早在先秦时期,《尚书》记载大禹治水后“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国家得到了治理,老百姓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九州”是中国最早的行政版图。《道德经》则描绘了一幅“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陶然景象。庄子以“四海之内,共利之之谓说,共给之之为安”为其社会理想。墨子渴望“兼爱”而“尚同”的社会,人们不分等级,相亲相爱,自食其力,各尽其能,机会均等,对普通大众“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孟子倡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王道政治,他追慕周文王的仁政,称“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这与大同的“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何其相似!《诗经·国风·硕鼠》中对“适彼乐土”“适彼乐国”“适彼乐郊”的一唱三叹,则表达了对剥削者的讽刺与憎恶,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到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道》进一步发挥了对“大同”社会的想象:
民家给人足,无怨望忿怒之患,强弱之难,无谗贼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发衔哺而游,不慕富贵,耻恶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虫不螫,猛兽不搏,抵虫不触。故天为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凤凰麒麟游于郊。囹圄空虚,画衣裳而民不犯,四夷传译而朝,民情至朴而不文。
《淮南子》也描绘了类似的景象:
……强不掩弱,众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限,道不拾遗,市不豫贾,城郭不关,邑无盗贼,鄙旅之人相让以财,狗彘吐菽粟于路,而无忿争之心。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熟,虎狼不妄噬,鸷鸟不妄搏,凤皇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黄伏皂,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
更著名的是魏晋时期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那一片“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世外桃源,若有若无,似曾相识,处处有《礼记·礼运》中大同社会的影子,却又寄托了乱世之人对太平的深切渴望。
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之际,神州陆沉,九原板荡,康有为著二十万字《大同书》,详尽设计了一个“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这个社会破除了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等“九界”,使人类享有极致的平等、公平、自由与民主,是大同理想社会的升级版、具体版和时代版。书名原为《人类公理》,后改为《大同书》,无疑,这是康有为对两千多年前先人“大同”梦想的一次致敬与回望。
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他曾说:“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据说,“天下为公”是孙中山最常题写的词句,而他撰写的《中华民国国歌》中也有这样的句子:“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由上可见,大同社会的美好理想,穿越无数苦难与辉煌,始终历久弥新,引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丰裕、和谐、幸福的美好生活奋斗不息。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人并未将大同理想停留在纸面上,而是努力将其落实在社会治理的不同层面。
比如,建立粮食储备制度。民以食为天,衣食无忧是大同社会的基础条件。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古人养成了防患于未然的长期主义,特别重视对粮食的积蓄,相信“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贾谊《新书》指出,国家至少需要储备九年的粮食,方可称为充足,可以防备不时发生的水旱灾害。汉代开始设置常平仓,既可调节粮价,避免贫富悬殊,也可储备粮食,救济民众。之后,历代皆有政府主导的粮食储备体系。唐宋以后,民间的力量得到充分调动。隋朝度支尚书长孙平不忍民众因灾荒而困乏,建立“义仓”。不同于属于政府的常平仓,义仓属于民间,由民众自发捐赠粮食储藏,以备凶年之用。明朝强调义仓的“民捐、民管、民用”,使得义仓在乡村广泛普及。在义仓基础上,南宋大儒朱熹创立“社仓”,在青黄不接之时以平价将粮食借贷给百姓,也收到了“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的良好效果。
实施灾荒赈济。《周礼·地官》记载了不少救济灾荒的政策,如借贷种子和粮食给灾民、减轻赋税、减缓刑罚、免除力役、放松山泽禁令、免除关市之税等。灾荒救济也被列入政府财政支出,包括公共设施建设、灾荒补贴、政府公职人员的抚恤赡养等项目。秦汉起建立了一整套包括蠲免、赈济等在内的灾害救助和保障体系,包括雨雪、收成、粮价等的奏报制度,报灾检灾制度,等等。明清时,政府广泛鼓励地方富商和士绅赈济灾民,以补官府之不足。同时广泛收集民间救灾经验,编写救荒民书,比如明初藩王朱橚编纂《救荒本草》,清代顾景星著《野菜赞》,张能麟著《荒政考略》等,让千万饥民得以果腹。
保障弱势群体。根据《礼记·王制》记载,西周时期,聋、哑、瘸、废、残、躯体矮小者,都在政府抚恤的范围内。养老方面,实施“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的分级养老制;对于鳏寡孤独困穷之人,提供谷物粮食;残疾之人不列入征兵力役之列。《管子·入国》则记载了齐国的“九惠之教”,国家设有“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等机构和官职,照顾老幼病孤等弱势群体,并相应减免徭役。比如,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有官家的馈肉;八十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有酒肉供养。汉魏南北朝开始设立专门救助机构,如孤独园、六疾馆等。唐朝实施侍丁养老制度,由国家雇请专业养老人员;此外,各州县设有医学博士及医学生,常为贫民免费义诊,属于中国较早的医疗福利制度。宋代广泛设立各种救助机构,如接济老疾孤穷丐者的福田院、依寺庙而立的医院兼疗养院安济坊、安葬无主尸骨及家贫无葬地之人的漏泽园等。宋朝在各州郡设置广惠仓,用于贮藏公地所产的租谷,作为对鳏寡孤独幼等人群的福利救济粮,等等。
正是上述绵延不绝、广泛实施的赈灾、仓储、救助等政府政策和民间实践,令“大同”理想并非完全遥不可及,在中国大地上的某些区域、某些时间段,曾有限地实现了“太平盛世”的善治。《韩非子》记载郑国子产为相,“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最著名的是唐太宗贞观之治,《资治通鉴》称“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
历史学家许倬云曾介绍旧日无锡的民间社会,宗族邻里守望相助,结成紧密的共同体,一起开设作坊,合办社区福利,照顾贫寒老弱,发展学堂教育,俨然一个小小的“大同世界”。这样的景象在传统社会的村落里其实并不少见,学者李华东这样描述:
选贤与能,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者告老还乡的官商,带领村民修桥铺路、编族谱盖祠堂;人不独亲其亲,设法筹置公田、义庄,所得用来赡养矜寡、赈济穷困、抚养孤儿,使得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教。……小的时候生活在村里,连锁都没见过。门扣上别根竹枝关上门,防的不是他人,而是乱跑的鸡犬。
然而,由于生产力的局限和私有制的本质,大同理想终究无法在传统社会中真正实现。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的仁人志士赫然发现,流传千年的大同理想竟然与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不谋而合,他们纷纷用大同的语汇来描述这一外来思想。比如孙中山说:“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李大钊号召劳工阶级联合起来,“一步一步的向前奋斗,直到世界大同”。瞿秋白在《赤潮曲》中歌颂十月革命,词中曰:“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1926年,郭沫若写了一篇《马克思进文庙》,设想了马克思与孔子相逢的奇妙场景,双方惊异地发现,其思想的出发点几乎完全相同,马克思不禁对孔子感叹,“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这里所称“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就包括流传千年的大同理想。
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真正通往大同的可行之路。新中国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收归国有,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改革开放后,在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原则的基础上,逐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策略。到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成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且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渐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愿景化为实景。
小康已立,大同在望。当新时代的实践让大同梦想持续照进现实,我们不能忘记历代先贤的努力,也不能忽略其中一以贯之的中国价值、中国气质和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