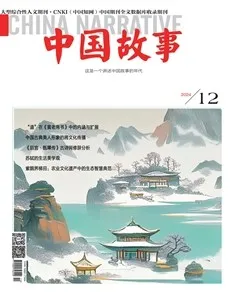“道”在《黄老帛书》中的内涵与扩展
【导读】“道”是老庄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在道家的思想体系中属于最高范畴,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近代,随着《黄老帛书》的出土,学界对“道”在老庄之后的发展与变化有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本文由此为切入点,对黄老之学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作进一步探讨。
一、“道”的原始意义
20世纪70年代,位于长沙的马王堆汉代古墓经过考古挖掘,出土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其中《老子》乙本卷中的四篇——《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被称为《黄老帛书》。帛书出土后,学界对道家思想的相关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黄老帛书》是黄老之学的代表性著作,它继承了老子思想的“道”论,认为“道”是万物的起始,也是宇宙最高概念。同时,它也蕴含着法家的思想观点。但《黄老帛书》与道、法两家的观点又不完全相同,如《庄子》消极无为的出世主义与帛书完全相反,帛书主张积极的入世主义,投身政治实践。
学界对帛书中的政治观点有许多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黄老之学的政治主张,是道、法两家观点的融合,比如钟肇鹏的《黄老帛书的哲学思想》;也有学者如吴光先生,认为黄老之学是在道学的基础上融合了多家主张,是秦汉时期的道家学者以黄帝、老子的理论为基础,集先秦百家之长,创造出来的一种学术体系。
“道”是黄老之学的最高概念,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虽为老子首创,但在帛书中也是一个起始性的概念。《黄老帛书》对“道”的重点阐述,主要见于《道原》一篇,在其他各篇中也都有零散的论述。
老子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理念上,反映在社会领域就成了“小国寡民”的政治愿景。黄老之学虽也有无为而治的思想,但帛书追求的政治思想是“天下可一”,这与老子“小国寡民”的观点截然相反,因此二者对于“道”的论述也不尽相同。
所谓“洞同天地,混沌为朴,未造而成物,谓之太一”,帛书中的“道”在“恒无之初”是一个混沌的存在。“虚同为一,恒一而止”认为“道”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帛书中常用“虚”“一”等词去代指“道”,“太虚”在《黄帝四经》中意为天空,但也有学者认为是“宇宙”“天地”之意,在时间的刚开始,宇宙还处于混沌状态。张岂之先生认为:“气在原始状态时无形无名,迥同太虚,与太虚为一。”这个“一”便等同于“道”,也就是说“道”等同于“气”,但“气”是物理意义上的真实存在,而“道”在物理意义上却不存在。学者吴光认为,黄老之学提出的“道”是一种没有任何客观实体支撑的“虚无”,但世间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却都是由这个“虚无”的存在所产生的。
“道”是万事万物的起始,也在万物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最终万物复归于“道”。这样看来,所谓的“鸟得而飞,鱼得而流(游),兽得而走”,便是说世间的各种事物都有各自的规律。虽然“道”只是抽象的、并无客体的存在,但是万事万物都由其而生,并且可以和谐并存,其中的规律也能够被我们认识。
二、“道”存在于人事中的“理”
帛书中谈论的“道”具有规律性,当它表现于具象化的物体时,便会被称为“理”。因此有言:“理之所在,谓之道。”“道”不仅在自然规律下起作用,在人类社会的法则下也同样起作用。因此,学者丁原明认为帛书中的内容虽将“道”框于固定的架构内,但并非意在对其本身进行论述,而是重点强调“道”在老子思想中的规律意义,将其定义为“世界的总规律”。帛书中将“道”多层次地放在人类社会中,就自然而然地生出了逻辑性的、条理化的政治观点。
综上,“道”体现在自然社会和人类社会中便形成了“世界的总规律”,而在帛书中则主要集中于“天道”“地道”“人道”的论述中。“因天时,伐天毁,谓之武”,有学者注释为“顺应天时,诛灭本就会灭亡的国家”,其中所谓的“天”便是天道规律体现出的必然性。由此来看,“天道”的变化似乎只是一个并不具备意志的自然现象。《黄帝四经》中对“天”的描述大多都是如此,如“天地无私,四时不息”。但“过极失当,天将降殃”表述中的“天”,似乎又是有意志的。近代有学者提出这些观点或许是矛盾的。帛书中认为的“天道”刚正不阿,从未停止过运转,此时“天道”明显是不以任何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但帛书中又提出若是人类活动在某处与“天道”相违背,那将会受到“天道”处罚.如此一来,“天道”就不再单单只是某种自然规律,而是像人类一样拥有了主观意志。
帛书中对社会地位等级进行了说明,如“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意即人类社会中的一切活动和规则应以“天道”为根本准则。但这种“贵贱恒定”思想必定是不公的。帛书中提出“人主者”应自“天道”取法,制定各项律法和政策,以此让百姓安身立命。如果以此为前提,若是“天道”与“人主”相矛盾,又该如何选择?从帛书中的论述来看,“天道”是最高准则,但忠于君主也是“天道”之下的必然要求,帛书中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天下可一”,将这几种论述都考虑到的话,就必须对君主的无上权力进行限制。那么“天将降殃”无疑是限制权力最好的理论武器,警告君主不可任凭私心行事,即帛书中所言的“功成而不废,后不逢殃”“犯禁绝理,天诛必至”。书中甚至提出了“五毋”“五逆”等用以规范君主言行。这也能看出帛书思想的时代局限性,它将“天殃”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威胁,本质上还是期望君主注重自身修养和言行。
“天道”,作为客观存在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中具体体现为诸如“度”(适度、平衡)与“稽”(考察、验证)等原则,这些原则是人类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如学者陈丽桂提出“人事上的建功立名、祸福生死是和天道、天常息息相关,且相应分配,分毫不爽的”。学者萧萐父认为,“守度”是把握好事物发展节点和变化状况不可缺失的一步,如同唯物辩证法中量变引起质变的概念,要注意掌握事物数量的增减情况,使事物的发展始终保持于“适度”以内,这就是“处于度之内”,若是处事过度会导致天降灾祸,也就是“适者,天度也”。帛书中有言:“天建八正以行七法。”学者陈丽桂认为“八正”是指君主在进行统治和颁布政策时能够顺应天地和四时,以应对各种变化;“七法”就是“天道”所具备的恒定规律与性质。“度”意为人们行事必须遵循“天道”,与“天道”相符合为适度,相反即为失当。
帛书中有言:“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是指遵循农业耕作的天时,“静作得时”即君主应让民众在农忙时节去进行农作,这与“天道”是相符的,如果民众不进行农作生产,就无法满足基本的吃穿需求,这就与“天道”相悖;“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用),因时秉[宜],[兵]必有成功”是指战争的时宜,自古战争皆要考虑天时、地利、人和。综合看来,在遵循“天道”的前提下,帛书也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考察“时”的条件,具有积极意义。
学者丁原明提出,在“道”的概念之外,帛书中对于事物运行的规律又提出了“理”“数”“纪”的概念,他认为这是对老子“道”的思想的一次突破性发展。学者刘世宇曾探讨“理”的意义,他认为“理”首先就是“道”的规律思想的代替;其次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如上文论述的适度;最后是义理之意。而学者金春峰认为“理指事理或者秩序”。帛书中谈及“理”一般都会牵扯到人类社会中的顺逆之事,如“理之所在,谓之顺。物有不合于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这里指的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即人事之理。
三、“道”与“法”的秩序
帛书中不仅谈论人事之理,还有言:“四时有度,天地之理也……四时而定,不爽不忒,常有法式,天地之理也。一立一废,一生一杀,四时代正,终而复始,人事之理也。”意为天地运行有恒定的规律,终而复始是有“度”的,符合“天道”就不会有意外差错。但人事之理则不同,它有着具体的生、杀、立、废,是由具体的人决定的。天地之理与人事之理相互贯通,只是人事之理有人的主观因素,所以“循理”时要考虑到规则秩序,要与“天道”相符。学者钟肇鹏提出,在“道”这个总原理之外的“理”,是各种具体事物的规律,“理”分属于“道”而不违背“道”。万物皆出于“道”,那“顺逆”便只是针对人事。
帛书中有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人类社会中的“法”是由“执道者”制定,但却是由“道”而生,并非由个人的心意决定,制法者也要受“道”的约束。
“‘道生法’就是国家最高权力拥有者根据‘道’的法则制定出具体的法律规范”,“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只有君主才是执道者,才能执道生法”。这些说法基本符合历史现实,但君主的言行并非总是符合“道”,因此“执道者”不能与圣人等同。于是,帛书中提出了“圣王”,期望在“道”的约束下去规范统治者的言行。学者胡家聪认为,这样的论述意为君主的权力来源已不再是君权神授,而是变成了道家思想,即君主被披上了一件“道”的外衣,成为“执道者”,也就是“有道明君”。
综上所述,帛书中所蕴含的“道”“天道”“道生法”等思想,通过与人事社会的多种联系,衍生出政治愿景,即在“明君”修身及“尊君”的条件下,塑造一个秩序井然的“天下可一”的封建社会。虽没有跳脱“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框架,但依然是进步的,可供今人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汉墓帛书[壹][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3]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
[5]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6]吴光.黄老之学通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7]陈丽桂.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8]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中国古代哲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吴光.关于黄老哲学的性质问题——对《黄老帛书》和《淮南子》道、气理论的剖析[J].学术月刊,1984(8).
[11]刘世宇.“无为自然”向“法”治转变的可能性与正当性[J].现代哲学,2014(1).
[12]钟肇鹏.黄老帛书的哲学思想[J].文物,1978(2).
[13]金春峰.论《黄老帛书》的主要思想[J].求索,1986(2).
[14]张增田.《黄老帛书》法治思想的初探[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2(3).
[15]关志国.论黄老学的“一”与“法”[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16]知水.关于“黄帝之言”的两个问题[J].管子学刊,2000(1).
[17]萧萐父.《黄老帛书》哲学浅议[A].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8]祁涛.《黄老帛书》的政治思想研究[D].西安:西北大学,2015.
[19]万政铄.《黄帝四经》“道”的思想研究[D].西宁:青海师范大学,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