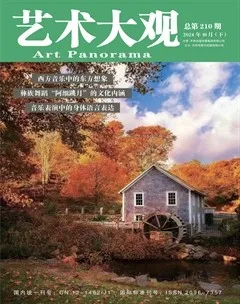“书画同源”新解——以画入书
摘要:“书画同源”是中国画写意体系理论话语之一,纵观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其源流、技法、历史发展等方面的讨论,很少有学者从“审美观”的角度深入讨论书画背后所蕴含的共同审美逻辑。特别是大多数研究只是笼统认为“书画同源”是传统书画“计白当黑”等创作原理的体现,基本没有涉及“书法”对“画”的审美借鉴,也没有细致地分析产生此结果的底层逻辑、美学原理等。因此,本文试图从“以画入书”式品评方式的角度对“书画同源”这一命题做一阐释,并联系当今社会现状深度挖掘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在当代人精神家园建设中的意义。
关键词:书画同源;审美观;以画入书
一、“以画入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水墨”作为中国书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一直备受青睐,艺术家对它的讨论也不绝于耳。比如,现当代有不少艺术家尝试运用控制变量法解构书画要素,呈现了探索书画本质的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但当艺术表达的载体不再是汉字或者水墨时,观者却常常会对它是否还属于中国书画的范畴生出疑惑,同时也很难对这个作品产生独属于中国书画的情感共鸣,这时反而更倾向于将它看作另一个独立的艺术类型。在中国书画传统理论方面,虽然“书画同源”的品评理论由来已久,但我们在评论具体的作品时通常还是将“书”“画”当作两个不同的领域,即使在评论写意画时会提及用笔有“篆籀气”,但从来不会以看画的方式品论书法。以上现象揭示了“书”“画”割裂的现状,也说明了再次讨论“书画同源”的必要性是势不可挡的。但在此,笔者将不再赘述“以书入画”的必要性,而是论证“以画入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将绘画的评论方式运用到书法中似乎会有损书法的独立性,被质疑将书法作品“图像化”以及忽略了书法最重要的载体——汉字的作用。但笔者在此想讨论的并非“画学书法”一类的特定风格类型,而是想深入探索“以画入书”的可能性并且论证其合理性。
二、“以画入书”和“画学书法”的区别
张亚圣在《碑学与帖学之外的视觉革命:画学书法研究》中提出了“画学书法”的定义,“所谓‘画学书’,即将绘画中的笔墨观念和造型技巧等渗透到书法的创作中,有别于传统‘书家书’的概念,又与学者熟知的‘画家书’在源流上和‘以画入书’的深入程度上迥然有别。同时,‘画学书’并不颠覆传统书法的守则,甚至对艺术家的绘画水平也有着不同一般的要求。[1]”换句话说,就是将汉字视为纯粹的图像,由此以“造型意趣”为导向进行汉字创作变形,文中主要论述了“画学书”的法度问题,详细地说即笔法、字法、章法和墨法,但对“画学书法”的精神内核和实操性的探讨仍然不够深入,私以为张亚圣对“以画入书”技法的讨论过于浮于表面。因为从“书法同法”的角度来说,在这几个方面书画的关联性只是自然发展中书画技法符合逻辑的应用,所以,笔者认为据此将“画学书法”作为独立于“帖学书法”和“碑学书法”以外的书法体系是不够严谨的。但这也确实为笔者讨论“以书入画”的可能性提供了一条可参考的路径。不过,笔者提出的“以画入书”不仅包括了适当融入绘画的造型意趣,更重要的是厘清绘画与书法更为本质的审美观的相同之处,尤其是写意画和书法的审美逻辑关联。据此,也可以为“以画入书”的合理性提供论据。
葛兆光提出,“语言文字是把面前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看的一套话语系统,每一种语言和文字都以一种既定的方式来描述和划分宇宙,使生活在这套话语中的人们在学会语言文字时就自然地接受了它所呈现的世界[2]”。又由于中国古代书画家身份的高度重合,所以我们可以预想到中国书画的“审美观”是同样源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思维模式的产生的必然成果。
三、“以画入书”的实际运用
在书法中,“线”的表达总难免受到字形的局限,“以画入书”往往只能止步于基于同种书画工具的技法经验影响。可是,相对技法,画的“意境”之美才是它艺术气质的核心,因此,讨论“以画入书”的可行性必将解决如何将“画境”转化为“书境”这一重难点。
一方面,把控书画中的象形因素比例。值得注意的是,象形因素的比例判断并不是指计算字形的保留程度,而是考量在改变字形的同时对“势”的保留程度。“以画入书”最忌将书法中的汉字视为纯粹图像,即完全摒弃字形结构,丢弃笔顺承接顺序,只注重“字”的外观形状。只注意外观形状会造成脱离“势”的结果,而“势”却是构成书法节奏韵律的主要手段,没有“势”的存在,书法就丧失了整体的逻辑性和表现“气韵”的必要条件,最后彻底沦为“图画”。比如,“少字数派”①就陷入了过度取“象”而毫无“书势”的误区。北宋郑樵亦提出:“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然书穷能变,故画虽取多而得算常少,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六书也者,皆象形之变也。[3]”可见,“物象”的增加不是“以书入画”的进取之道,过度滥用反而会降低书法的艺术表现力。
另一方面,探索书画中“符号”承载情感的可行性。首先,我们需要确定“符号”的具体含义。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曾经提出将语言符号视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4]。“能指”即语言符号的称谓,“所指”即符号表达的含义。但笔者这里的“符号”并非此意,而是指书画家情感载体,这个载体没有具体形象,而是抽象意识的具象化。
四、“以书入画”中“符号”的运用逻辑
我们需要通过探讨书画家运用“符号”的底层逻辑来证明“书画同源”在“以画入书”中的理论可行性。
(一)“符号”在书画中的表现形式不同
“符号”表现在书法中就是用高度提炼简化后的抽象点画符号为载体,以笔势映带为逻辑进行艺术表现;而在山水画中就是依托画家心意、审美去构建山石结构及组合。
(二)书画艺术理论来源具有高度统一性
书法作品的“章法”与中国画的布局逻辑往往高度重叠,如“计白当黑”“密不透风,疏可走马”“阴阳相生”等,理论来源基本不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范畴。在古代书论中也有直接提到书画审美相同之处的例子,如刘熙载曾提出“书宜平正,不宜欹侧。古人或偏以欹侧胜者,暗中必有拨转机关者也。画诀有‘树木正,山石倒;山石正,树木倒’,岂可执一石一木论之?[5]”而造成这种现象的还有一大原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对“八雅”的推崇,这
也直接导致了古代书画家和文人身份的高度重合性,同时
也为书画艺术审美的统一性奠定了现实基础。
从第二点提出的现象似乎就可以断定“书画同源”的根本原因,可是这个逻辑成立的前提是创作者个人性情是艺术作品表现的逻辑起点而非社会思潮。但这个前提成立与否是存疑的,还需要再进行仔细推敲。而要想确定书画家创作思维的底层逻辑就要尝试找到此逻辑的起点,所以我们首先要厘清社会思潮和人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究竟是人决定了社会思潮从而诞生了符合“人”的审美的艺术作品,还是社会思潮孕育了相似的人从而通过“人”这个客观载体创作出了相符的艺术作品?这听起来似乎是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荒谬争论,但其实对厘清书画诞生的本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从书画品评标准来说似乎是第一种,自魏晋人物品评说兴起时,书画作品的优劣评比标准既包括了作品所用技巧的生疏、取法格调的高低,还包括作者的人品性情,甚至宋朝时期人们还将书画家的个人修养纳入考核标准。但从艺术的起源的角度分析又似乎是第二种。在远古时期,人类社会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统治阶层,先民们对器物的装饰行为动机更多是审美本能等,发展至封建社会,“礼乐文化”的诞生让艺术作品染上了“阶级色彩”,艺术作品的作用自此便不仅是表现对美的追求,更是阶级区分的象征,除了纯粹的礼器,平时使用的功能性器具也多带有象征身份的作用。从这种变化来看,似乎是社会的发展推动了艺术作品诞生动因的改变。可是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从远古到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先民也始终与我们一样主观地将那些器物归为“艺术作品”。但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在远古时期,先民眼中的大部分东西,无论是器物还是书画,往往是实用性远大于审美作用的。并且,因为社会制度变革的节点要早于书画独立的时间点,而在书画独立之前也确实有许多虽然并非以审美为目的去主观生产但又确实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所以会导致我们产生似乎应该由社会制度变革的时间点来界定书画审美观发展的转变点的错觉。但其实不然,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艺术制度的演变并非严格的同步转变,故笔者大胆猜测,书画在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类别之前的创作动因是“人”对美的本能追求,当社会生产力发达到社会经济基础足以支撑特地创造只具有纯粹审美作用的艺术品后,艺术作品的发展和变革更多是由于社会思潮的推动。
(三)“符号”具有表达完整情感的承载力
从艺术表现力来说,书法和文人山水画的整体视觉效果呈现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对“点、线、面”的审美布局。所以,当我们在欣赏书法和文人山水画时不会首先注重文本的可识性或者山石的写实程度,反而将“气韵”“意境”的表现当作评判的首要标准。比如,徐渭在《草书诗卷》中完全打破字体结构,不强调行气和上下字的笔势连贯,而是将白纸当作整体安排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面貌。即使作品文本的可识性不高,但不可否认它是一件优秀的书法作品。事实上,我们在观赏草书作品时,往往还需要联系上下文来确定某个字具体的写法,但绝不会将狂草与图画画上等号。这不仅是因为线条的质量、章法的安排、书家的情感会赋予“符号”独一无二的表达,也是因为书法中所有线条的走向都是符合“书势”这一底层逻辑的。同理,我们也不会将文人山水画和真实景色去亦步亦趋地一一对应。
以上问题既是“以画入书”的实施思路,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以画入书”的合理性。总的来说,“线”同时作为书法和写意山水画的重要表现元素,是奠定书画审美观具有相通性的基础。同时,利用“符号”表情达意的相同的艺术形式和书画家同样的思想文化内核又再次推动形成了具有相近品评标准的中国书画审美观。据此,采用“以画入书”式评论视角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五、结束语
“书画同源”作为经典的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价值不仅是“书画同体”和“书画同法”两个方面的,更是在探究中国式艺术审美观方面的。中国式审美观的研究意义既体现在剖析中国书画审美的底层逻辑,找到中国书画的本质特征和核心艺术魅力,打破“书”“画”两个领域的创作壁垒,从而构建更为完整中国书画创作理论体系,也在谋求中国书画审美观与现代艺术思想的最大公约数,在保持中国书画核心精神的前提下,推动它进行新的演变,同时找到中国书画在现代化背景下的有效传承路径。毕竟,被束之高阁的“阳春白雪”永远不能拥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书法和山水画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艺术必须根植在日常生活中才能焕发出它真正的生命力,而只有做到契合人民的精神需求才能真正地融入民族的骨血,成为永不衰竭且能代代相传的艺术种类。
参考文献:
[1]张亚圣.帖学与碑学之外的视觉革命:画学书法研究[D].上海大学,2016.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3]郑樵.通志二十略(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5.
[4]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刘熙载.艺概[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基金项目: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画写意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2ZD15)子课题“中国画写意的理论范畴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梦月(2000-),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从事国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