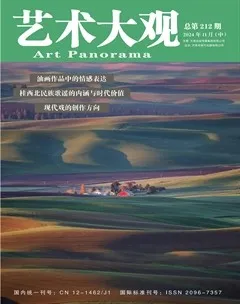绘画中的时间与空间观念释义
摘要:弗朗西斯·培根是20世纪英国的著名艺术家,他的绘画根植于战后文明反思的土壤中,以其自身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绘画,抗争泛滥俗套图像的“围攻”,开创了绘画的“第三条道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和智能手机的普及,资讯最大化地实现了共享,然而,绘画却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并出现了“照片化”的倾向,绘画作品中的艺术性逐渐减弱,似乎离艺术越来越远。“照片化”的倾向所呈现的是在当今的绘画创作仍普遍停留在对客观世界“再现”的认知理解的既定的传统观念上。一种“再现”是为追求逼真效果的照搬照片,绘画的意义仅剩对技法的追求与对情怀的迷恋;另一种“再现”是主张利用写生来完成对自然的机械模仿再现,这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照片化”。人仿佛被抽空了思想,变成了机器工具。艺术家在创作中如何有效地避免模仿再现客观世界即“照片化”,真正实现视觉思想的创造表达,便成为当今艺术家在绘画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为研究线索,梳理出培根是如何在二维平面上通过实现直接时间与断裂空间的结构装置与创造的独特的理解与实践来完成实现思想、感受的自由表达,以求从中得到对当代艺术及艺术创作的形而上观念上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在架上绘画的对直接时间、断裂空间连接的可能性的试验、装置和结构中重新获得创造的体验及实现。这里其主要的目的还是强调一直被我们忽视的理论观念的研究与认识,通过改变观念来解决实践即画面的生成与创造的问题。
关键词:弗朗西斯·培根;绘画;直接时间;断裂空间;形象
一、“照片化”绘画的时间与空间
绘画由图像(实际上是形象)构成,即画面上各种点线、图形、色块、体积、空间等组合体,当然也可以从内容对象上说即人物、植物、器具、场景等。这时,我们就可以以此使用时间和空间概念来讨论画面了。当然,我们也知道时间概念是人为给定的,并又把时间对应到了具体的存在物上,来理解谈论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存在及相互关系,一旦出现了形象,形象本身就自然占有了空间,同时也拥有了时间[1]。
“照片化”绘画中的时间是现实世界标准物理时间或流逝时间的截面,因此“照片化”绘画中所有物象也就必须符合客观存在的完整连续的时间与空间的存在关系,所以,“照片化”的绘画就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与模仿,因此艺术家的思想就无法参与到画面结构的组织与安排中,也就是再现模仿现实的图像根本无法实现思想的表达,最终只能停留在对客观现实进行简单机械的模仿复制上。当下“照片化”绘画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都是因为艺术家思想观念和认识的陈旧刻板、保守僵化,误将现实的时间、空间当作艺术时间与空间。为避免“照片化”,仅让艺术家停留局限在画面上作出修修补补的调整,也就是用传统的“学画”方式,教或学一套既定的程式化方法是无法真正避免“照片化”的,而是要让艺术家彻底从认识上、思维及观念上进行提升、改变,理解什么是艺术,理解图像与形象、理解媒介符号与意义,理解艺术史的发展与谱系,理解绘画中断裂空间与直接时间……当理解与认识发生彻底转变,也就是重视并加强理论研究的能力,强化并提升思想的生成能力,画面才会随之而转变,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照片化”。
(一)时间
时间是物质的永恒运动、变化的持续性、顺序性的表现,包含时刻和时段两个概念。时间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学科和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理解。时间是人类用以描述物质运动过程或事件发生过程的一个参数,确定时间,是靠不受外界影响的物质周期变化的规律。也就是说时间是人为给定的,也是借助宇宙万物、大千世界斗转星移,客观存在的千变万化、荣枯生死的事实来感知和理解的。因此,就产生了过去、现在和未来,黑天白昼,上午下午以及几点几分的概念。因此,时间是流逝的,且不可逆的即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是绵延连续的;时间是永恒的。而时间往往又依附于具体的存在来谈论,因此,图像上的具体物象则相应就有了时间的所属性,这正是艺术作品中物象即时间所要利用的。创造时间即生成了世界。
(二)空间
空间是与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客观存在形式,物与物的位置差异度量称为“空间”,位置的变化则由“时间”度量。空间由长度、宽度、高度、深度、大小表现出来,通常只四方(方向)上下。空间既有实存的实体空间也存在虚拟空间,如有宇宙空间、网络空间、思想空间等,都属空间的范畴。实体空间来源于现实存在的感知与体验,虚拟空间则生成于形而上的意识思维。而艺术作品中涉及的是非人虚构的组合生成的可能空间(包括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
(三)传统绘画中的时间与空间
传统的古典绘画中的时间与空间观念是文学性的,画面再现的是文学故事。画面往往选取某个戏剧性的高潮,将画面定格在戏剧性冲突最剧烈的瞬间。如法国画家泰奥多尔·籍里柯以真实的海难事件为题材,于1819年创作的《梅杜萨之筏》;1824年法国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以1822年土耳其侵略军在希奥岛对希腊平民进行的大规模屠杀为主题而创作的《希奥岛的屠杀》,还有其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自由引导人民》,这些作品都相对使用的是线性时间,截取事件中的某个瞬间进行创作。
然而,纵观艺术史我们会得到惊人的发现,人类一直在自由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中世纪绘画、中国古代壁画上看到大量的自由巧妙地连接、组合各种不同时空内容并用的例子。古代洞窟壁画中可能受承载画面的崖壁面积的局限而导致的画面时间是“直接时间”,他们随机、自由甚或是癫狂地描绘每一只动物及人物的组合场景,自然地形成了或创造了其人为的新型的结构关系,在作为线性时间的单独个体在与其他个体的结构关系中又呈现出脱离并违背了线性时间的复杂的“直接时间”的连接。无意中,重组、再造了新的时间与空间,改变了画面的维度,使画面中的时间、空间变成了直接时间和断裂空间,总之是多种复杂凝固时间的并存。我们看敦煌254窟《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图》,故事发生的整个过程被凝固分解在部分时刻中又被完美地重组定格在一个画面中,创造了直接时间和断裂空间的奇妙结合的绘画效果并生成了巨大的震撼力量。当然,我们还是不能下结论说中世纪绘画及中国古代壁画的创作者他们对时间及空间有了明确的超前认识与理解。因为,创作者面对的是一整个墙面,所以在同一画面中绘制了不同时间发生的好几个故事,致使画面中天然或自然地就会出现所谓的直接时间和断裂空间,但,事实上他们也一定会感觉到:超越真实存在之外的自由连接会对表达“画他们知道的”更自由,更有效,更有力量。
当然,古代绘画也不全使用直接时间,也有部分作品是流逝时间的体现和对故事的描绘。总之,是可能的,自由的,任意的,共存的,高效的。
或许那是本能或内容的特殊需求所致,或者说,这原本就是古人视觉行为的自然的正常的反映。比如,在一面墙上要画上多个不同内容的故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时间和空间复杂存在的关系,因为每一个不同的故事内容都是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里,它们被自然地连接配置在一个平面内,造成一种似乎是一个视角下或者是同时发生在你眼前的既真实又虚假并存的景观;当然,我们的观看就是诸多视点的不同移动、反复审视的整合的结果。但这种任意、自由的表达语言形态随着时代文化诉求的变化而变化。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关注与重视自然导致了视点由“神”转向了人世间,世俗的现实存在开始出现在绘画的结构中。特别是17、18、19世纪反映世俗生活记录生活的重大活动场面的绘画,大部分倾向于现实时间、空间的使用。但人类最初的率性任意自由的书写表达的遗产仍没有被割断,如米开朗基罗、格列柯、塞尚再到培根等艺术家的作品,在今天仍在发挥作用。
(四)“照片化”绘画的时间与空间
“照片化”绘画对时间空间的使用就是:流逝时间和现实空间。绘画“照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是在图像时代的不同发展时期存在的一个具体现象。写实绘画也不是指对照片的完全直接的模仿与再现,其中仍是复杂的二维平面与三维空间的交叉与纠缠,线性时间与直接时间的共存与共生。
所以,“照片化”时间的特点就是时间是由无数个代表“现在”的点连续构成,“现在”的点不断形成又不断逝去,逝去的时间就变成了过去的时间,流逝时间只是人工化的产物,并不是时间本身,是我们对时间的形象化的理解,而该理解使我们将每一个点对应于存在的每一个凝固的时刻的具体物象上。如此看来,这样的每一个具体的时刻只能是现实存在的具体时刻的记录或再现。相机就是这个记录“点状时间”——记录再现的产物。在相机的快门声中,一个时间点以一张图像的形式生产出来,这使得真实生活场景在连续、流畅的时间中被机械切割成无数个图像并被记录下来,绘画所谓再现瞬间的场景,仅仅是把时间压缩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也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视位上看到的现实整体存在的一个瞬间点。
绘画再现瞬间的场景一般以这两种情况比较多见:一种“再现”是为追求逼真效果的照搬照片,绘画的意义仅剩对技法的追求与对情怀的迷恋;另一种“再现”是主张利用写生来完成对自然的机械模仿再现,这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照片化”。如此的再现,人仿佛被抽空了思想,变成了机器工具。
但绘画是一种主观性极强的、认识和思考表达世界的媒介语言方式,今天仅满足于记录再现的认知功能的绘画已无法满足当下人们表达思想与观念的需要,而应该是笔,是书写,是表达,是我们必须担负起的我们的责任即我们必须重新来回答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新型关系。
假如说在没有相机、手机的时代,发生的事件仅仅用语言文字记录,那么利用绘画来再现某一个时间点上的发生的具体活动场景是有意义的,但那一定是人类早期的认知年代。然而在读图时代、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任何利用时间点的绘画再现都无法承载或担负起现代人表达复杂思想的要求。即使“照片化”的绘画在今天还是会频繁地出现在各大展览中,虽然仍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和欢迎,但这也是或只能是文化保守和绘画一味迎合民众的结果,原本作为引领提升民众的先锋文化却变成迎合讨好民众的媚俗产物。绘画在无视其艺术存在的现代性时失去了其发展的指向性和创新性,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失去了创新和创造能力。
当然,也存在主动利用照片进行艺术创作的行为。如照相写实主义绘画,它几乎完全以照片作为参照,在画布上客观清晰地加以再现。正如克洛斯所说:“我的主要目的是把摄影的信息翻译成绘画的信息。”它所达到的惊人的逼真程度,比起照相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不是机械照抄复制照片,其性质属于观念绘画的范畴。
二、弗朗西斯·培根绘画中的直接时间与断裂空间
从现代主义开始,绘画跟图像之间的关系就已经比较明确了,绘画的功能不再是对图像进行瞬间的抓取与再现,而是努力创造生成一个自足自主、独立的未知世界——艺术世界。塞尚凭借一己之力打开了自足图像世界的窗口,培根更是通过多重时空的绘画突破了图像的局限。培根既拒绝绘画描述故事,又反对抽象绘画。培根在绘画中通过直接时间与断裂空间的使用将绘画从图像再现中解放出来,创造了绘画的第三条道路。那什么是直接时间和断裂空间呢?
(一)直接时间和断裂空间
直接时间即生成的时间,创造的虚构时间,不是客观现实中某一段或某一瞬单一的时间;断裂空间即重组空间,不是客观现实中某一处的单一空间。直接时间与断裂空间的使用可使艺术家在创作中获得极大的自由,不受现实时空的限制。
绘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画出时间,一个视点下的场景主要是指常态物理空间即三维空间,也就是照相机的视角,这个视角体现的是现实时间的瞬间切片;但出现两个或多个视角时,这时就必须考虑时间问题了。培根绘画中的时间是直接时间,所以培根的画面是自由的,人可以存在于过去、未来和现在,也可以存在于已知、未知中,可以自由组合,也可以共时存在。
我们观看世界就是诸多视点的不同移动、反复审视的整合结果,相机只是还原了其中一个视点而已。而进入现代艺术之后,则更是充分地展示这种自由: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形状有机地进行结构重组、连接,就能在平面中生成或形成不确定的新的复杂轮廓及形状——形象。直接时间与断裂空间的使用使培根的作品达到了更大的自由,使创造成为真正的可能。
(二)不会游泳的游泳冠军
德勒兹在《什么是哲学》中谈到了“不会游泳的游泳冠军”,“不会游泳的游泳冠军”游泳时所用的动作不是我们所熟悉的体育竞技竞赛的标准形态动作,而是一种“错误”的动作,是一种只注重对象形体、形态并发生变形所生成的新的动作。它的肢体形态“错误”,但能像竞技比赛冠军一样拥有非凡、强大的视觉冲击力与情感爆发力。而这种扭曲变形的形态看似“错误”却具有很强的一种美学价值,比原来标准的动作具有强大得多的造型能量、精神能量和生命力,它开启了新的可能。当然,前提是他们是存在于艺术世界中,消灭对象,切断正常,悬置知识和经验系统,制造陌生,引发沉思,呈现巨大可能性。因其艺术形象的生成,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在作品中都是充分饱和的艺术形象,同样都极其有表现力。形象异化扭曲所带来的灵感与光亮或许就是艺术图像的价值和作用,如中世纪的形象,米开朗基罗的形象,格列柯、塞尚、培根的形象,戈达尔将其称为避免被真理所毁灭的“视觉符号”。
(三)绘画与形象
古代绘画同具象绘画和图解的关系与现代绘画不同主要是因为:照片已经担当起了图解性的、资料性的功能,以至于现代绘画不需要完成这一原本属于古代绘画的功能。培根提出绘画必将走向形象化。
形象是指创造出来的感觉的聚块,形象不是对象的复制再现,而是创造出来的一个新的品种,具有独一无二的非人的存在的生成性性质的形象。
培根选择“画形象”,是为了避免复制与再现,也就是“叙述性”“图解性”,又是为了避免抽象绘画形式。形象不同于对象,形象是人创造出来的,对象是客观现实本身。形象虽然新创造出来新事物,但它一定要携带原物象的信息。形象同时又要与其他的图像配置构成新的抽象关系,在这种新的抽象关系中,原有知识经验派不上用场,“图解性”“叙述性”可以被有效避免,在阻断确定的、正常的秩序后,画面只能生成新的意义和可能。
(四)事情与事件
“事情”通常指广义上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社会现象,包括已经发生和未发生的情况,使用范围广泛,适用于各种大小和性质的活动。而“事件”则特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已经发生的不寻常、有影响的大事情,通常带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不是现实中发生的,而是人的思想中发生的。吉尔·德勒兹说:“事件并非发生之事。[2]”他认为,事件没法实体化,事件是观念,是思想,事件不是发生之事,而是对某人发生之事。两者有重大区别,如大雨是某件发生的事情,但不足以构成一个事件,因此如果要有一个事件,我就必须感到雨水的落下,是某件为我而发生的事情。“事情”是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地发生;“事件”是针对并且为了某人在某一地方发生[3]。卡洛·迪亚诺认为,“事件”总是此时此地,只有在我所在的一个确切的地方和我察觉到他的瞬间,才有事件。
事情是客观现实,但绘画是“事件”而不是“事情”,绘画不能再现现实,绘画不能照抄对象,而应是艺术家脑中生成的新的图像,可表达艺术家的思想与理念。
(五)无器官的身体
德勒兹最早于《意义的逻辑》一书中提出“无器官身体”的概念。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提到,无器官的身体是卵、是欲望和生成强度。德勒兹在《弗朗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一书中用“无器官身体”来解释弗朗西斯·培根的绘画,培根的绘画抛离了古典绘画具象、优美的特征,它是后现代的、抽象的,甚至展示了疯狂、扭曲的视觉维度——这正是身体的本质。
无器官的身体不是没有器官,正如同卵在孵化之前的混沌状态,卵可以生成任何器官,但卵在此刻并未孵化,因此具有很多重组、装置、重新连接的可能性,摧毁了确定性。在绘画创作中“无器官的身体”指创作时我们要重新安排画面,而不是如实地画出客观对象,在画时受到客观存在的制约。无器官的身体是去组织化,去真理化,重新安排画面的图像与形状,不受客观对象影响,自由地重组、装置画面。
三、“感觉”与绘画的第三条路
“感觉”最初由塞尚提出,德勒兹对培根的绘画解读以“感觉”为逻辑主线,故而“感觉”是研究培根绘画无法逾越的重要因素,是理解培根绘画的关键核心。那么,什么是感觉?“感觉”在字典中解释为:客观事物的个别特性在人脑中引起的反应——感觉是最简单的心理过程,是形成各种复杂心理过程的基础。德勒兹认为,“感觉”不是知觉,不是情感,不能是任何模仿、再现物,“感觉”是独立拥有自身价值的生存物,而且超越任何体验,是非人的存在[4]。
培根提出,对现实的再现因为摄影技术的发展已经变得不再必要,而完全主观化的抽象绘画所采取的编码化呈现,使绘画陷入象征的危险境地,这两种绘画方式都是对绘画之外事物的表达。那么绘画如何才能通过自身而起作用呢?培根认为是“感觉”。德勒兹认为,培根的绘画以纯粹的形象取代了具象绘画,形象赋予绘画以情感负荷,倍增感官刺激[5],在“感觉”的范畴里,并没有任何已经被完整描绘的物体可再现,也没有任何可被表达的概念要表现[6]。培根的伟大之处就是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找到了绘画的第三条道路,拯救了形象在20世纪的命运,这是图像生成形象的智慧所在。
四、结束语
如何有效地避免绘画创作“照片化”,是各位艺术家在绘画创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艺术家仅在画面中进行调整并不能避免“照片化”,而应改变艺术创作学习模式,在重视实践的同时也要重视理论学习,彻底从观念上、认识上、思维上全面提升,理解艺术的本源,理解图像与形象、理解媒介符号,理解艺术史的发展与演变过程,理解绘画中断裂空间与直接时间……当理解与认识发生彻底转变,画面也会随之而转变,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照片化”。
参考文献:
[1]吉尔·德勒兹.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M].董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吉尔·德勒兹.意义的逻辑[M].董树宝,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
[3]罗兰·巴尔特.明室:摄影札记/罗兰·巴尔特文集[M].赵克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吉尔·德勒兹.什么是哲学?[M].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
[5]吉尔·德勒兹.时间·影像[M].谢强,蔡若明,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6]大卫·希尔维斯特.培根访谈录[M].陈美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赵俊(1991-),女,吉林梅河口人,硕士,三级美术师,从事油画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