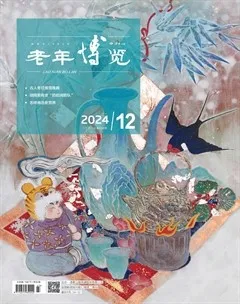古人冬日堆雪雅趣
宋代开始全民参与堆雪狮
“在宋代以前的文献里,找不到人们冬天堆雪游戏的记载。到了北宋,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人们的生活意识越来越自觉和强烈,普通人也有了享受生活的追求,在冬天,堆雪狮就成为一项全民参与的趣味活动。”侯印国说,“之所以选择狮子,是因为这是一种具有王者之气的瑞兽,往往来自异域进贡,非常珍稀,人们赋予其威武神秘的想象和吉祥辟邪的寓意。”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富贵人家在冬天第一场大雪后,就要堆雪狮、做雪灯,同时安排宴席,邀请亲朋故旧前来欣赏。南宋的豪门贵族同样如此,《梦粱录》中说南宋杭州的“豪贵之家,如天降瑞雪,则开筵饮宴。塑雪狮,装雪山,以会亲朋”。他们在宴会中浅斟低唱,倚玉偎香,宴会结束后还会到西湖边欣赏湖山雪景,正所谓“瑶林琼树,翠峰似玉,画亦不如”。而诗人才子在雪后除了堆雪狮,更会以雪煎茶,吟诗咏曲。
侯印国介绍,在宋代皇宫中,雪狮由专业的工匠制作,并且装饰有金铃和彩色丝帛,大气端庄。《武林旧事》中记载,南宋时期“禁中赏雪,多御明远楼,后苑进大小雪狮儿,并以金铃彩缕为饰,且作雪花、雪灯、雪山之类,及滴酥为花及诸事件,并以金盆盛进,以供赏玩”。清代诗人史梦兰创作《全史宫词》,在南宋部分特别提到当时皇宫中的雪狮,写道:“明远楼前驻辇时,彤云低绕万年枝。炉中添爇胡桃炭,共倚雕栏看雪狮。”
雪狮融化有专门记载
堆雪狮在古人心目中如此重要,以至雪狮融化时,都有人专门记载。
雪狮塑成后显得威武霸气,明代有诗人骑马遇到雪狮,马居然被雪狮吓到,因而写诗云:“积雪为狮巧藉形,紫骝何事浪为惊。需知日出消融尽,鼓鬣春风自在行。”他安慰自己的马儿不要害怕,等太阳出来“狮子”就会融化。
有趣的是,在雪狮融化的过程中,“狮子”会变得挤眉弄眼、千奇百怪,宋代有人专门写诗描述这个有趣的细节。张耒的《戏提雪狮》云:“六出装来百兽王,日头出后便郎当。争眉霍眼人谁怕,想你应无熟肺肠。”说的是太阳一出来,这号称百兽之王的“狮子”就再也没有平日的威严气象了。明代诗人李濂则巧妙地把雪狮在阳光下的融化和相思使人消瘦联系起来:“自君之出矣,沮痕渍罗袖。思君如雪狮,时时渐消瘦。”读来别有情致。

侯印国还讲述了明代一个和雪狮融化有关的故事。据《坚瓠集》记载,明成化年间,嘉善县一位林姓知县杀死一家十三口,当时的御史似钟决定追查到底。林知县重金贿赂太监李文,请他把似钟请来吃饭,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似钟知道这场饭局的背景,便故意准备了一场相声。吃饭的时候,这场相声表演也开始了,台上有艺人打扮成官员赏雪,还堆了一头雪狮子。官员让下属把雪狮子藏在阴凉冰冷之处,不要让它融化,方便过些天再拿出来欣赏。官员问下属藏在哪里好,下属说:“山阴县如何?名字里有个阴字,应该比较阴凉。”官员说不行。下属又说:“那江阴县可以吗?”官员又表示不可以,然后忽然抬高声音说:“但是可以藏在嘉善县。”下属忙问:“这个地方和阴没有关系,为什么要藏在这里呢?”官员说:“你难道不知道嘉善县令杀死一家十三口人都没有偿命吗?这地方岂非有天无日?”台上表演完,台下人全都为之震惊,太监李文再也没有办法开口求情。
清代中后期开始堆雪人
堆雪狮的习俗一直延续到清代,并且堆的种类多了雪象和雪马。
清代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中写道:“乾隆壬申、乙酉,以雪狮、雪象联句。嘉庆戊寅,又堆为卧马二,东西分列,有与内廷翰林联句诗。”这在《清实录》等文献中也有记载。比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正月初十,乾隆帝就专门以雪狮为题,和15名心腹大臣联句作诗,乾隆帝诗中说雪狮“精莹玉质状昂藏,似虎如何不正黄”。嘉庆十五年(1810年)瑞雪连降,皇宫中除了在养心殿两侧堆雪象,还堆了雪马,嘉庆帝也和大臣们来了一次以雪马为主题的联句赋诗。
“堆雪狮最积极的往往是儿童,皇宫中的皇子们也会积极堆雪狮。”侯印国说。在郎世宁绘制的《弘历雪景行乐图》和《乾隆帝岁朝行乐图轴》等作品中,都有皇子们堆雪狮的画面。在乾隆与大臣的联句中也有皇子们嬉戏打闹堆雪狮的场景:“崇牙并列猛趪趪。茸蹄却逊隃腾迅,耏尾犹蕤闪灼光。砌塑争听儿女闹……”
清代开始,民间除了堆雪狮,还开始堆雪罗汉。清代华喦绘有一幅《婴戏图》,描绘的正是儿童堆雪罗汉的情景,画上题诗云“儿童亦爱西天佛,破却工夫雪作成”。鲁迅先生也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提到自己小时候堆雪罗汉的情景。
侯印国表示,人们如今熟悉的“堆雪人”这个词,是从清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的。例如在道光年间花月痴人的《红楼梦》续书《红楼幻梦》中,贾母便跟几位专门做雪人的工匠说:“诸位手艺巧妙极了,灯戏里扎的故事好得了不得,今儿堆的雪人儿自然更好了。”到了民国时期,堆雪人越来越普遍,慢慢取代了堆雪狮和堆雪罗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