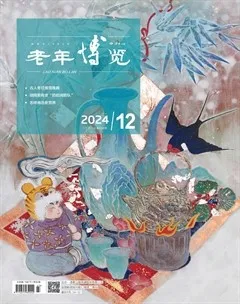古琴声起,忘却年龄
在大清谷,我拾级而上,路过一排排茶垄,见茶山顶上有一屋,如黑鹰张开羽翼,停留在崖顶之上。当地朋友说,那是养老社区在山顶上开设的一间茶室,里面陈列着养老社区老人的插花与书画作品。
忽然,我听见在云雀高一声低一声的鸣唱中,隐约有古琴声传来,弹奏的是《渔樵问答》。这首曲子很妙,采用渔者和樵者对话的方式,以上升的曲调表示略带惊讶的提问,以下降的曲调表示从容不迫的回答。曲调在飘逸潇洒、悠然自得之中,饱含劳动者自得其乐的情趣,同时又暗含哲理。
越往上走,琴声越是清晰,如山间活泼明亮的流水一般。进入茶室,见一位满头华发、穿一袭赭石色苎麻中装的阿姨正在抚琴。
一曲毕,有听者问:“琴好,曲好,气质好。只是,阿姨,您为什么不染头发?”
众人皆诧异,怕此人莽撞的提问会破坏此间和谐安详的气氛。然而阿姨并不以为意,笑着说:“古琴上的丝弦也从来不染色,我为什么一定要染发?”
所有人都因这奇妙的回答笑了起来。正好有上山遛弯的老伯带了好茶来,邀请抚琴的阿姨同饮,同时向我们介绍说:“这位是泌水老师,是我们社区义务教古琴的老姐姐,今年80岁了。”
泌水阿姨简单地讲了她的故事:她与老伴是大学的同届同学,结婚后,家中大小事宜都是老伴料理。她一直活得很文艺范儿,喜好古琴、茶道,还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一双儿女早已成家立业,都在国外的大公司工作,无须泌水阿姨烦神。谁承想,她刚过完77岁生日,老伴突发心梗去世。泌水阿姨的生活坍塌了,她仿佛被抽走了魂魄,很长时间回不过神来。
回家料理父亲丧事的儿子请泌水阿姨同去国外定居。泌水阿姨谢绝了,因为她担心老伴的墓无人祭扫,也担心远离故土,将来无法叶落归根。
很快,泌水阿姨决定卖掉房子,来养老社区住。让她下定决心的,是参观养老社区时,一位刚打完八段锦的老太太猜出了她名字的由来:“当年,你爹爹一定很喜欢《诗经》。‘泌之洋洋,可以乐饥。’你的名字,来自《诗经·陈风》里的句子呀。”
这让泌水阿姨觉得,入住养老社区,不仅饮食、起居、就医有人帮助料理,更重要的是,这里有的是聊得来的同龄人。
当然,做这样的选择,是需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的。泌水阿姨将大部分家具与收藏赠予了子侄辈,衣服与图书也淘汰了一大半。她犹豫着要不要把古琴送掉—老伴离去后,她已经许久没有把琴从琴囊中取出来过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告别,她仿佛对之前所有自己爱做的事都失去了兴致。
但养老社区的管家说服她带上了古琴,理由是:“很多老人家到了我们那里,才跟着音乐学院退休的老师学会了弹钢琴、拉二胡,还有美声唱法。很多叔叔阿姨的新本领—书法、绘画、游泳、太极拳,都是跟着我们的义工学的,有的义工比学生还大十来岁呢。说不定哪一天您来了兴致,会收几个古琴学生呢。”
泌水阿姨的眼神像黑暗中的萤火一样亮了一下,但又迅速暗淡下来。她觉得自己的琴艺大不如巅峰时期,《平沙落雁》《获麟操》《山居》《醉渔唱晚》等这样比较难的曲子,她经常弹到一半就“坐忘”,中等难度的曲子她如今也越弹越慢了,岂能当老师?
管家是1998年出生的小伙子,个子很高,长得很像她最小的侄子。他鼓励她说:“我们养老社区有个游泳队,游泳队的陈队长有一句话:‘大江大海里的鱼,再年迈,也在游。’只要一直游,活力就在,雄心壮志就没有丢光。弹琴也是一样的道理。”
到养老社区才几天,泌水阿姨就发现了一处弹古琴的好地方—像鹰一样盘踞在茶山顶上的茶室,四面有窗,写有行草的米白色挂帘在茶山的清风中飘荡。一开始,管家帮她背琴上山,她在后面跟着,要歇息两三次,才爬得上那128级石阶;后来走得多了,她也可以一口气走上去了。当然,爬上茶山后,要歇息片刻,她才有余力坐在窗前抚琴。只要琴声一响,这个世界的烦忧,生命烛火渐渐微弱带来的忧伤,还有活得仿佛一朵孤云的暗叹,都仿佛不存在了。
泌水阿姨收了四位老太太与两位老爷爷当学生,先让他们听熟乐曲,了解乐曲的创作背景和意境,明确乐曲的分句、气口以及各段落之间的关系,再讲右手弹拨的强弱、缓急与音色处理。然后,教他们想方设法背谱,同时调整左右手的指法,这样,练琴时眼睛可以脱离琴谱,把注意力放在左手如何按准音位上。六七十岁的学生难免手忙脚乱,感叹他们这个年纪学琴太晚了。此时泌水阿姨脱口而出的,竟是游泳队陈队长的观点:一条鱼,只要在游,它就称不上年迈。想了想,她又补充了一句:“弹古琴要左右手配合,还要记谱,一心三用。老顽童周伯通的武功,当年差不多也是这样练成的。”
秋高气爽,经历了一个酷暑的茶山,暗绿的茶垄之上新的茶芽又在萌动,犹如一片嫩绿的火焰。泌水阿姨教完课,又独奏一曲,仍意犹未尽。她把琴案挪到茶室外面的观景平台上,对着绵延无尽的茶山开始抚琴。
此刻,泌水阿姨仿佛进入了一条隐秘的通道,与历史长河中许多高洁的灵魂对话。她早忘了年龄的负荷,只专注于这清凌凌的七根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