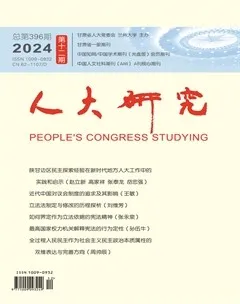近代中国对议会制度的追求及其影响
内容摘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后中国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及其预备立宪,是清王朝的自救之举,客观上也为其后的革命与共和作了思想准备。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新纪元,革命党和立宪派合力仿效美国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一脉相承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南京参议院、北京参议院,是近代中国“立宪法、开国会”理想的即将实现,也是近代中国人心所向的求变之举。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对国会制度进行了美妙的构想和设计,但宋教仁的被刺及其后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实证了议会道路在中国的失败。袁世凯等封建势力的破坏、多党制和“不党主义”的乱象以及国会议员的弄权纳贿造成了议会制度在中国的彻底消亡。
关键词:议会制度;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宋教仁
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为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探索。
一、议会思想的传入与清末君主立宪的失败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坠入了亡种亡国的边缘。这迫使中国开始对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进行反思。如何选择一个良好的G5RgtXQ2XXHtl3FWN+iiJj4Jpojkc3lV+A6ooDv+Als=国家制度,以避免亡国亡种,使中华民族走向国富民强,成为一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最高理想。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标志的宪法和国会,开始登上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历史舞台。
议会政治思想是在1840年前后开始进入中国的。林则徐是最早注意到西方议会制度的中国官员,被后人称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40年,林则徐组织人员编写《四洲志》,首次向中国介绍了英、美、法等西方国家议会,包括议会的组织、权力关系和选举等。
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推行的第一场改革自救运动。这场运动试图通过练兵、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来“求强”“求富”。洋务运动坚持在不触动封建统治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是一场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前提的改良运动。然而在甲午战争中,洋务运动的标志性成果——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有为者,也日益认识到制度问题对国家强弱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发动了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效法俄国和日本进行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学习西方的各种制度,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试图通过对国体政体的变革,使中国走向富强。但它触动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的根基,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统治集团血腥镇压。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是中华民族又一次的“创钜痛深”,又一次的生死存亡考验。1901年1月,清政府痛定思痛,诏令变法,开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史称清末新政。在十年时间里,清朝几乎同时进行了教育制度、军事制度、经济体制、财政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直至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政治领域,晚清政府于1906年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随后宣布实行预备立宪,议定在中央实行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1907年,清廷下谕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作为立法院的“预备”,在各省设立咨议局,作为省议会的过渡。这些政治变革,基本打破了沿袭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初步建立了一个已显三权分立雏型的立宪政体。此外,还制定了宪法大纲、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近代法律,建立律师制度,中国政治开始向法制化、民主化迈进。
但清王朝统治者主持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是被形势所迫的无奈之举,其目的是维护和加强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权力,他们是根本不愿意、也根本不可能承认国家权力是来源于人民并且属于人民的。他们反而借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走上了一条自我灭亡之路。
一是在宣布预备立宪时没有规定立宪时间,而是“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竭力拖延时间。二是在改革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过程中,保留了军机处,满族亲贵专权倾向非常明显,满汉矛盾未能得到调和。三是压制民间国会请愿运动,拒绝提前召开国会,坚持先制宪后开国会,变相剥夺立宪派在制定宪法过程中的话语权,把制宪主导权牢牢控制在手中。四是推出“皇族内阁”,13位国务大臣中满族占了9位,其中皇族又占7人,赤裸裸地反映出了清廷皇族集权的真正用意,打破了立宪派对预备立宪的幻想,成为辛亥革命的催化剂。
但在清末新政及其预备立宪活动中,立宪思想的传播,资政院、咨议局的成立和运转,国会大请愿运动的广泛开展,却为其后的革命与共和作了思想、舆论、人才、组织和制度的准备。
二、彪炳史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中华民国国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结束了二百多年的清朝封建统治和中国历史上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开启了中国民主共和新纪元。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是辛亥革命期间,独立的南方14省为尽早确立共和政体、筹组临时中央政府,仿效美国大陆会议成立的一个过渡性议政权力机构。1911年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首先在上海宣告成立,其后又移迁汉口、南京开会,几经波折,终于议决临时中央政府的基本组织模式和建国程序,并就争执最激烈的首都设置地点和元首人选达成共识,从而迅捷迎来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该机构起初由各省独立后成立的都督府派出的代表组成,后来一些未独立的省(直隶、奉天、河南)立宪派把持的咨议局也派出代表参加,具有临时国会的性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仍代行参议院的职权,成为民国第一个议政机关。直到1912年1月28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开幕,才圆满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成立和履职,是辛亥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国会成立的重要开端。辛亥革命从无序变为有序、从分散趋向统一,共和民主从理想变为现实、从愿望变为实践,中华民国从提出到成立,如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临时大总统、成立临时政府、组织参议院,以及南北双方从停战议和到和平统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都功不可没,彪炳史册。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的关于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纲领性文件。虽然是一部政府组织法,但因为它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认了中华民国的民主共和政体,确定中华民国仿效美国实行民选总统制,宣告了君主专制世袭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并据此产生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可以说是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共4章21条,对临时政府建制作了粗线条勾勒。内容主要有:1.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选举产生。2.参议院以各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员组成。3.行政机关设外交、内务、财政、军务、交通五部等。
南北议和是武昌起义胜利、南方各省独立后,南方革命政权与北方袁世凯政府就停战实现和平、建立未来统一政权的谈判活动。它酝酿于湖北军政府与清朝军队的停战协议,后成为南方政权与北方政府的全面谈判。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全程指导了南北议和活动。具体表现为:一是授权湖北军政府派出议和代表;二是制定临时停战规约5则;三是公布长期停战条件,全面议和;四是确定4点议和原则(推倒满洲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待满人);五是两次通过以“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为将来统一全国、建立全国性的共和政体作法理准备。
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在帝国主义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以前,大清国是没有国旗的。直到1888年10月,清朝才在《北洋海军章程》中,规定大清国的国旗为黄龙旗。
用什么样的国旗,实际上代表着什么样的建国理想和政治理念。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在海外讨论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时,就曾在国旗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为国旗;黄兴主张用旗帜左上角带“井”字的井田旗为国旗;辛亥革命的发动者、武昌起义的组织实施者——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则设计了“十八星旗”,以表示汉族为主体的关内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
武昌起义成功后,“十八星旗” 高高飘扬在蛇山黄鹤楼上,成为革命的象征。但“十八星旗”仅代表清帝国的十八个行省,黑龙江、吉林、奉天、新疆四个行省以及内外蒙古和西藏等广大区域被排除在外。使用这一旗帜的建国思路是借鉴美国的独立模式:十三个英国殖民地的北美革命者们竖起了“十三星条旗”,把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的版图上分裂出去,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
“五色旗”最早由李鸿章北洋陆师、水师所使用,后来的北洋新军也沿用为海军军旗。1911年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后,立宪派召集已移会武汉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的留守代表召开各省代表会,决定赋予五色旗以“五族共和”的意义,采用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经舆论媒体的广为宣传报道,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正是由于“五族共和”,加上南北议和之后清皇帝逊位诏书的合法性,使得中华民国大致完整地继承了大清王朝的主权、版图与人口,包括完整的疆域、整合的政制体系、多元融合的民族、自由发展的宗教,以及其他所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从而避免了边疆和民族地区因为大清帝国的解体崩盘而落入列强之手,避免了国家分裂,维护了民族团结。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由于五色旗曾作为北洋军旗,孙中山一直反对将五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曾两次利用临时大总统的法律发布权把五色旗作为国旗的决议案搁置了。但“五族共和”的思想早已被全体国民所认同。五色旗事实上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在使用。南北和谈统一后,1912年5月10日,北京参议院第三次通过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由袁世凯正式颁布。其后的中华民国,有十多年都是使用五色旗作为国旗的,直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国民政府后,才又以青天白日旗作为中华民国的新国旗。
三、临时政府时期南北两个参议院的历史功绩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宣告代行参议院职权。1月28日,南京参议院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宣告结束。由于同盟会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取得政权后,迅速分化为对立的两股政治势力,南京参议院也迅速形成了以同盟会为代表和以立宪派为代表的两派。在此期间同盟会会员人数一直稳定占据参议院议员半数以上。这使得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中央政权基本上由同盟会所控制。
南京参议院的主要成就:一是用法律形式确认清朝皇帝逊位,接收清王朝主权、领土和人口,通过谈判和平统一全国。二是制定和颁布《临时约法》,粗线条地勾勒了中华民国过渡时期政治体制的基本轮廓,通过临时宪法的形式确立了民主共和的立国原则。三是制定了一批法律,奠定了中华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崭新的法律基础。如参议院于1912年4月1日制定的《参议院法》,对参议院的组织和运转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为北京参议院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北京参议院是在南京参议院基础上改选而成的。与南京参议院比较,北京参议院明显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议员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南京参议院议员由各省都督指派;北京参议院议员由各省民意机构——临时省议会或咨议局选举。二是议员人数多、代表区域广。南京参议院由17省代表、最多时49人组成;北京参议院则除西藏外,其他25个省区都有代表出席,议员达120多人。三是参议院两党对峙局面初步形成。同盟会成功改组为国民党后,国民党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重组后的共和党在参议院中人数也达40余人,成为与国民党抗衡的一支政治力量。四是北京参议院议员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些议员议政能力不强,一些议员道德素质低下。社会舆论开始对北京参议院进行抨击。
北京参议院的根本任务是制定法律,产生国会。其主要功绩:一是通过《国会组织法》,明确中国国会采取两院制;二是公布国会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及施行细则;三是发布正式国会召集令,成立第一届中国国会。此外,北京参议院还在内阁组成问题上,与袁世凯进行了几次的斗争,甚至弹劾了陆征祥内阁。
一脉相承而来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南京参议院、北京参议院,是近代中国“立宪法、开国会”理想的即将实现,也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求变的人心所向。特别是南京、北京参议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开会,综220次,议决之案,凡230有余”,创造了制定临时约法、国会组织法、国会两院议员选举法、省议会选举法、国务院及各部官制以及有关国籍法、印花税法等55部法律的非凡业绩,“制定各项法律之成绩,似较正式国会为优”[1]。可以这么说,“自清末中国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大凡从宪法、国会、政党、内阁着手,其中内阁向国会负责,政党以国会为活动中心,国会又为制定宪法的机构,议会明显居于民主政治之枢纽”[2]。
四、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民国国会及宋教仁遇刺案件
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对国会制度进行了美妙的构想和设计。根据《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等法律规定:中华民国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组成,实行两院制。国会职权在宪法没有制定以前,延用《临时约法》中所规定的参议院职权。两院职权基本相同,凡《临时约法》所规定的临时政府时期的参议院职权,均为国会两院的共同职权。
这种照搬西方国家议会两院制模式的做法,给其后的民国国会行使职权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民初国会议事效率低下,与国会的两院制设计不当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因为为了体现两院的平等,保障两院共同行使职权,设计者们不厌其烦地设计了一套两院议事的程序规定,却不知正是这套繁琐复杂的程序规定,影响到国会的议事效率,致使国会运转不顺畅,给世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损害了国会的尊严。
国会两院议员的任期是不同的。参议员任期六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任期三年,到期全体同时改选。国会两院议员的产生方法是不同的。参议员采取地域代表制,由地方议会选出,代表地方政治势力;众议员按“人口比例主义”选举,由各地方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之意。
选举众议员,有性别、财产、文化程度等方面的限制。如:(1)男子;(2)年满21岁;(3)在选举区内住满2年以上,以及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或有价值500元以上的不动产或有小学以上毕业或相当之资格。选举参议员没有对选举人的文化、财产等作出限制,但参议员由地方议会选出,只有地方议会议员才有选举权。而地方议会议员也是有类似于上述资格规定的。广大妇女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1912年12月举行众议员选举时,全国人口总数估计为40680余万人,参加投票的仅4293.3992万人,占总人口的10.5%。
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颁布施行后,中国进入了国会选举阶段。各党派秣马厉兵,积极参加竞选。此时同盟会已由宋教仁实际领导改组为国民党。国会选举期间,宋教仁在各地演讲,不遗余力宣扬其议会组阁的政见。宋教仁明确表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本来就是为了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3]。
选举结果表明,国民党在两院中的席位遥领其他党派之上。“国民党对于国会之前途遂抱以无穷之希望”。兴奋之中,黄兴、宋教仁等在上海讨论未来政治方针时,一致议决“组织政府采议院政府制,即国务总理由众议院自行选定,由大总统任命。各部总长由国务总理推定,由大总统任命”[4]。然而,正当宋教仁满怀希望准备登车北上组织责任内阁时,他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给尚未召开的第一届国会、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带来不祥征兆。
在清末民初,宋教仁是最为积极主动推行政党议会制度的革命家、政治家。1911年武昌起义后,宋教仁曾奔赴武昌主持起草《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州约法》。它以“天赋人权”为理论基础,仿照西方“三权分立”原则,把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政纲和《革命方略》所勾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蓝图,第一次以约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为以后其他独立各省组建政府和制定约法提供了样板,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和雏形。
及至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召开后,宋教仁作为湖南代表,更是竭力主张临时中央政府实行英法式的内阁制。在孙中山回国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开会讨论组建临时政府时,宋教仁即与孙中山在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黄兴劝宋教仁取消提议,宋教仁没有答应。于是,政体问题被提交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讨论。结果各省代表一致反对宋教仁的提议,选择了孙中山期盼的总统制。
此后,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担任法制局局长、在北京临时政府担任农林部总长。1912年宋教仁随唐绍仪内阁辞职后,袁世凯曾派人做他的工作,邀请他担任混合内阁总理。但宋教仁醉心于组织纯粹的“政党内阁”,因此袁世凯的提议被他断然拒绝。
宋教仁精通法律,对宪政制度情有独钟,一直寄希望于中国实行议会制度,通过议会和政党斗争,和平夺取政权。1912年春,他作为南京临时政府派出北上迎接袁世凯到南京任职的特派专员之一,在经历了北京兵变之后,改变初衷,赞成政府定都北京,回南京后被同盟会元老指责为“袁世凯的说客”并遭到殴打。他赞成“革命功成革命党消”的主张,在缺乏同盟会高层有力支持的情况下,联合统一共和党等小党,将具有帮会性质的同盟会改造成现代政党——国民党,并使国民党成为中国第一大政党。他还在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拒不就职的情况下,代理理事长,负起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国民党取得了国会选举的胜利。他在国会选举后踌躇满志,欲行政党内阁之时,却招来杀身之祸。
宋教仁之死,一般史学上定论为袁世凯所指使。“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势力遭受重大挫折,致使宋案真相陷入历史迷雾中。宋去世后紧接召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会,以实例证明了议会道路在中国的失败。
五、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及其党争内斗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袁世凯特派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登台代读致贺词:“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实四千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兆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谋幸福”,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5]
由于第一届国会是在宋教仁被刺后不久召开的,社会上传言纷纷、人心浮动,对国家前途、国会命运和共和政制存亡的担忧始终如一片巨大的阴影,笼罩着第一届国会。当月25日,宋教仁被害案件证据公布,表明为袁世凯授意指使。7月,国会两院向袁世凯提出了四项弹劾案。国民党同时发动“二次革命”。但很快,“二次革命”被袁世凯以武力镇压了。
袁世凯一面用武力镇压“二次革命”,一面加紧向孙中山称之为“民国之命脉”的国会和《临时约法》进攻。当时第一届国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宪法。国会两院所组织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天坛祈年殿为会场,在60名宪法起草委员中,国民党人占多数。袁世凯采取公开迫害手段,逮捕、拘留和杀害多名国民党籍委员。宪法起草委员会预见到袁世凯的全面迫害即将来临,于是加快起草速度,于10月31日“三读”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案。这个宪法案后称《天坛宪草》。
《天坛宪草》所设计的政体主要参照了法国的责任内阁制度,在议会的召集、对总统的弹劾、对国务总理的任命和对国务员的不信任、对财政的紧急处分以及众议院的解散、政府官制官规的制定等重大问题上,都作出了有利于国会的严格规定。这是国民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法律条款上对袁世凯作的最后限制。
袁世凯得知宪法草案将大大不利于自己后,两次发表通电组织各省军阀反对宪草,随后又宣布国民党为“乱党”,两次下令取消国民党人的国会议员资格,致使国会两院人数不足法定的半数,不能举行会议。11月13日,国会两院议长宣布次日起停止议事,袁世凯破坏国会的目的得逞。次年元月,袁世凯正式下令将滞留在京的非国民党籍议员遣散回籍。至此,第一届国会连第一期常会也没完成,即告解散。
在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期间,中国实行多党制。自民国成立后,政党纷起,各党成立、分化、合并及党员跨党现象层出不穷。国会议员选举揭晓后,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议席相加不及国民党。要想抗衡国民党,三党除了合并别无选择。在袁世凯的支持以及梁启超、黎元洪等少数党重要人物的积极努力下,1913年5月27日三党正式组建进步党,标志着民国政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此时进步党已为原立宪派所控制。袁世凯军事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政治对抗国民党,遂指使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于1913年9月成立了御用的公民党,为袁世凯顺利当选正式大总统服务,以实现其个人目的。它的成立,标志着民初政党发展走向了私利化和工具化。
各党派在国会内部的分化、合并以及斗争,构成了中国第一届国会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景象:各党派以本党利益为最高利益,以打击对抗其他党派为唯一目的,在国会内激烈争吵,影响了国会的正常运转和职权行使。如国会召开伊始不久,议长选举竞争激烈,参众两院都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勉强选出议长、副议长。国会两院的全院委员会和各审查委员会,则一直争执到10月才终告选出。但不及半月,国会就被迫宣告解散了。又如国会议员们在争执过程中,动辄采取非正常的议事手段阻碍会议,往往使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议;有时甚至大打出手,在社会上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国会讨论大借款案时,就有议员以墨盒抛击议长,此后这种场面屡见不鲜,逼得国会两院秘书厅不得不用铁链把砚台、墨盒、毛笔等固定在座位上。
六、第一届国会的两次恢复及议会制的终结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死去了。在全国舆论压力下,黎元洪下令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第一届国会,恢复《临时约法》。
第一届国会恢复后,自行行使它在解散之前所具有的权力,并继续进行被中断的制宪活动。由于经历了之前多党制下非正常的党争之后,各政党都对此深恶痛绝,认为党争是影响国会议事效率、让袁世凯坐收渔利、最终损毁国会、损害共和政治的主要根源之一。为此,国会再次召开会议的第一时间里,进步党党魁梁启超、汤化龙等即高唱“不党主义”,反对国会议员组织政党,要求国会议员超越政党,一致协商,共济国事。
然而,国会奉行“不党主义”以后,800名议员立即失去了组织,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了。时人对国会这种状态戏称为“八百罗汉八百党”。“不党主义”的实质,是抛弃了议会政党制度。在“不党主义”的国会里,由于没有有效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国会议员们对一项议案,或赞成,或反对,或修正,众说纷纭,难以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且议员们不受政党纪律的约束,往往各行其是,在议场动辄起哄闹事。很快,国会又完全无法正常议事了。
于是,国会议员们故态复萌,在议事活动中发生各种争执,甚至变本加厉,以至互相斗殴并分别诉讼法院,演绎了一出出比之前党争更为火爆和吸人眼球的闹剧。最终,国会在“不党主义”的幻象中四分五裂,以第二次被解散的命运,为政党政治的失败作了一次很好的注解。
第一届国会第二次解散后,中华民国再次分裂为南北两个政权。南北双方为宣示各自政府的正当性和法统,各自成立了国会,南方为“非常国会”(国会非常会议)、“护法国会”,北方为“第二届国会”,形成了“一国两政府”“一国两国会”的混乱局面。经过多年军阀混战,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取胜,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通电提出“恢复法统”,主张恢复第一届国会。8月1日,第一届国会第二次恢复。此时,距第一届国会召开,已经过去近十年了。
国会第二次恢复后,更是乱象纷生,比第一次恢复时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一年多的内部争权斗殴和外部武力倾轧,1923年又由直系军阀驱逐总统黎元洪下台。10月,在直系军阀曹锟以每张选票五千元的高额贿诱下,国会选举曹锟为继任大总统。曹锟贿选总统丑闻一经揭出,全国各地同声反对,国会被斥为“猪仔国会”。为了遮掩贿选总统的卖身行为,国会选完总统后,发奋工作,“于是把争持十余年以来,制不成功的宪法,在两三天工夫以内通过二读三读”,火线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遮一遮羞”[6]。
1923年10月10日,曹锟在北京宣誓就职。同日,国会公布《中华民国宪法》。由于曹锟等直系军阀对一纸宪法根本不放在眼里,对宪法条文不加干预,于是该宪法规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实行联邦制度,其他方面则仍是以《临时约法》和《天坛宪草》为基础,实行“三权分立”。曹锟贿选总统,使国会及议员声名狼藉。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也随着后来曹锟的下台无疾而终。
1924年秋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锟被囚。奉系军阀推举段祺瑞重新上台,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11月,段祺瑞下令搜捕贿选议员,随后宣布废弃曹锟制定之宪法,废弃法统,取消约法。自此,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辛亥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十三年后,在中国彻底消亡。
七、四度担任国会议长的吴景濂及其炮制的“罗文干案”
吴景濂(1873—1944),辽宁宁远人。自幼聪慧好学,21岁中举人,1897年考取副贡,成为天子门生。甲午战争后,吴景濂开始探讨时务,支持维新派图强救国主张,在家乡开馆布学,研授新学。1900年后,在官府和士绅支持下,操办团练,维持地方治安。1902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师范馆。后留学日本考察教育和新政,归国后任奉天两级师范学堂监督。1909年,当选为奉天省咨议局议员、议长。
辛亥革命爆发后,吴景濂曾与革命党人蓝天蔚密议奉天独立,事泄逃亡,南下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参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及临时大总统选举。中华民国成立后,为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同时受蔡锷支持组建统一共和党。临时参议院迁移北京后,为议员、议长,主持起草并通过国会组织法、选举法等系列法律,“颇能尽职”。后率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成立国民党,为国民党创始人之一。
1913年,吴景濂当选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竞选议长,落选。1916年国会第一次恢复后重为众议院议员,汤化龙辞职后接任众议院议长职务。1917年国会第二次被解散后,响应孙中山号召南下“护法”,组建国会非常会议(后宣布召开正式国会),任众议院议长。1922年,国会第二次恢复后,回北京出任众议院议长。同年,在直系争权内耗中配合曹锟等打击吴佩孚势力,以议长身份制造“罗文干案”,推倒王宠惠内阁。
9ec056734a746fbe2aab88f517e80ea81923年3月,吴景濂引发“议长大闹东方饭店”事件,一时轰动全国。事件缘于吴景濂在东方饭店打麻将时,要求饭店垫付50大洋作为陪同打牌小姐赏钱,遭婉拒后指使手下怒打茶房,砸毁房间陈设,留下查封饭店的扬言后拂袖而去。因吴议长身份,当时虽有巡警在场,也熟视无睹。饭店经理在股东会的支持下通过媒体大造舆论,坚决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各大报和上海报纸连篇累牍发表文章,一时舆论大哗,导致60多名议员联名提出惩戒。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道歉赔偿。
1923年10月,吴景濂为谋求国务总理职位,以满足曹锟当总统的愿望为交换,组织实施了贿选总统。但曹锟当选后未履行承诺,双方矛盾激化。不久后,直系高凌尉摄政内阁指令京师警察厅强制撤换国会众议院警卫和吴景濂住宅警卫,迫使吴景濂连夜逃离北京到天津寓居。后几次活动复出,意图东山再起,均未成功。九一八事变后,多次拒绝日本人请他回东北主持政务的要求,拒不复出。1944年在天津病逝。
罗文干是王宠惠内阁财政总长,上任后坚持财政公开,得罪了直系军阀中的天津派和保定派。王宠惠内阁是以直系重要将领、洛派首领吴佩孚的意见成立的,时称“洛派内阁”或“英美派内阁”。直系天津派、保定派对洛派包办王宠惠内阁、把控北京政权十分不满。加上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也对吴佩孚主张限制国会职权不满,故直系天津派、保定派与吴景濂联手,意图推倒王内阁,打击吴佩孚。
1922年11月15日,吴景濂与王宠惠在外交总长顾维钧的晚宴上,因立宪与政党政治问题发生争辩。王宠惠是留美法学博士、著名法学家,对吴挟国会以自重不以为然,借题发挥语有讥讽之意。吴景濂争辩不过,与王宠惠发生口角。宴会后,睚眦必报的吴景濂决心弹劾内阁,于是借财政总长罗文干可能受贿的密报材料,等不及众议院召开会议弹劾罗文干,即以国会议长、副议长名义起草致大总统的公函,亲自到总统府检举罗文干违背约法、僭越职权、收受巨额贿赂,要求立即逮捕罗文干。傀儡总统黎元洪同意了。
王宠惠获知罗文干被捕后,立即率全体内阁成员到总统府质问黎元洪:国会不开会,议长私自请大总统逮捕内阁成员是否违法?总统不把此事交内阁议决,不与内务总长、司法总长商量而直接动用军警逮捕罗文干是否违法?黎元洪理屈,于是答应王宠惠发布命令说明事件经过,并议定由法庭传唤举报人吴景濂、张伯烈到法庭对质。吴景濂、张伯烈见法警上门传唤自己,大为愤怒,认为议员、议长有司法豁免权,何况检举别人受贿并不是犯罪,于是也率议员20来人赶赴总统府质问黎元洪。黎元洪又把责任推到内阁。
为抓住机会一鼓作气推翻王宠惠内阁,吴景濂全力发动国会,一连通过《查办派署财政总长罗文干丧权祸国纳贿渎职案》《咨请政府前财政总长罗文干所订之华义银行借款合同宣告无效建议案》,将两案通告全国。同时还率国会议员30余人到黎元洪总统府值守,要求黎下令免职王宠惠、罗文干。
吴景濂制造“罗文干案”,目的在于倒阁,最终是要尽快把曹锟扶上总统宝座。眼见国会与内阁在“罗文干案”问题上纠缠不休没有结果,后台老板曹锟只好亲自出台,通电痛斥罗文干丧权辱国,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彻底根究。吴佩孚在曹锟表明立场后也立即改变态度,舍王宠惠内阁而去。国会乘胜追击,又于11月27日一连通过了4个查办案。29日,黎元洪发布命令,免去王宠惠内阁全体阁员职务。
1923年1月11日,经过两个多月的关押,京师地方检察厅对“罗文干案”作出裁决,公布了《罗文干案不起诉处分书》,认定罗文干受贿不成立、伪造文书不成立、损害国产不成立。罗文干得以释放。但吴景濂等再次利用国会通过内阁名单的权力作要挟,迫使新内阁通过重办“罗文干案”的决定,使罗文干第二次被捕。后京师地方检察厅再次裁定罗文干无罪释放。
中国国会,以其三起三落的悲剧命运和招致国人一片臭骂的意外结果,为议会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和实施,树立了一座历史的墓碑。国会先后被独裁者、北洋军阀、革命党、立宪派和广大民众所抛弃,以国会为重要载体和产生形式的中国“宪政”“法统”,也一并垮台。议会制度,在中国彻底失败。
“经过民初短暂的民主宪政之不成功尝试后,革命的呼声再度在中国掀起”,“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与青年党的‘全民革命’几乎同时并起”“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导发展为多党竞举的局面”[7]。
此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力量,彻底放弃了所谓“立宪法、开国会”的民主共和幻想,两党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开始走上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国民运动、组织新型政党、建立国民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的崭新政治道路,开启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历史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参考文献
[1]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M].南京:正中书局,1937(民国二十六年):73.
[2]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第二册·志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135.
[3]刘景泉.宋教仁[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177.
[4][5]李守孔.民初之国会[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4:84-85,87.
[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601.
[7]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1920年代中国三大政党的党际互动[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1920年代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