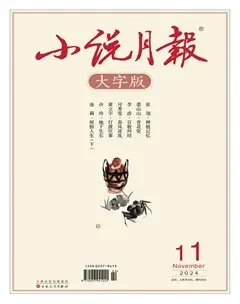灯渡往事
渔村是因追逐鱼群而“不断流动的社区”,它们的命运跌宕起伏,就像其赖以生存的猎物一样行踪不定。
——约翰·吉利斯《人类的海岸:一部历史》
一九九〇年盛夏,编辑部组织一批青年作者去灯渡岛开笔会。去之前,刘川林主编收到一组来自灯渡岛的诗作,作者小真在她的诗作后面,附了一封信:
刘老师,我很苦恼,彷徨得使自己不能自解,我是一位性格内向的女性,只因这种性格,给我造成了爱情中的不幸和痛苦。我有一个追求者,死皮赖脸,我一点也不喜欢他,在这样一个小岛上,我要摆脱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谁都觉得我是他的女朋友,他到处跟人说我跟他睡过了,连我父母也慢慢接受了,催着我订婚。可我心里有一个真正喜欢的人,而他却因此对我产生了深深的误会,我该怎么办?
此信离我们去灯渡的日子尚有月余,刘主编大概觉得马上就会见面,没有给她回信。不过,临走前,他往他的马桶包里塞了一本弗洛姆的《爱的艺术》。
去那天风浪很大,船颠簸得很厉害,两位省里来的老师都吐得不行。
到了灯渡岛,第一次见到这么清澈的海水,大家兴奋得哇哇大叫。一群赤条条的渔家孩子尖叫着从高高的船头跃入海中,浪花飞溅。海湾里挨挨拶拶的渔船,渔民们来回张罗着他们的生计,有人正在杀鱼,大群的海鸥围着他翻飞,等着吃他手中即将丢弃的内脏。这里天风浩荡,充满自由与野性的意味,目光所及,无不激荡着我们这些外来客的内心。岸上,石屋绝壁而立的那些肃穆而幽深的石窗,都面朝大海。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倚窗女人的忧伤。我拾级而上,一直在石屋里七弯八绕,沿途都是一些与渔业生产密切相关的小店铺,还有台球房,许多年轻人围在那里,里面传来阵阵击球声,一派混乱。
刚下船的时候,碰上一个黑瘦的女人,跟渔嫂打扮并无二致,但看得出来,她是邮递员,我们的船还没有停稳,她便一脚跨过来,干练地踏在颠簸不停的船帮上,把甲板上的几大袋印着“中国邮政”字样的邮包拎到岸上,放进她要挑回去的篓筐里。
刘主编跟她打招呼,称她丘姨。原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丘姨的家。她家是一幢两层楼的砖瓦房,邮所就设在一楼的厢房里,涂着绿色油漆,柜台边还挂着一个投币电话。丘姨是全国邮政系统的劳动模范,邮所的墙上贴着她的奖状,旁边还有一张有关她常年奔波在这个崎岖小岛上的先进事迹的报道版面。
我们一行十人,就此安顿下来后,大家在院子里七零八落地坐下。刘主编很严肃,他的意思是:上午看稿改稿,或请省里来的老师给我们上课,其余时间灵活安排,还要跟这里的文化站互动一下;灯渡岛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他鼓励大家多多走访这里的老渔民,听听他们的故事;灯渡风景很美,晚上出行要两个人以上,注意安全,等等。
院子里,丘姨的小女儿正在帮忙剥豆角,很文静的模样。她在沈家门读高中,正好放假,应该是和我们同船回来的。过了会儿,来了一个小伙子,斯文得不像是渔家子弟,红着脸,害羞得不成样子。他拎过一把椅子坐下,看得出,他对女孩深情款款,但是女孩嘟着嘴,并不理会他。倒是她家的那条叫阿黄的土狗对小伙子无限缠绵。他姓温,跟我同龄,是灯渡电影院的放映员。刘主编过来,向他打听文化站站长,哎,你们的张老师呢?小温说,棒冰厂的机器漏水了,没有人会修,让张老师去看看。刘主编说,他是狗皮膏药啊,哪里都能贴。小温笑。刘主编又问起小真,让小温给她带个口信,小温点了点头。
等我们吃饭的时候,丘姨还没有回来。她先生说,不用等她了,她今天要送信到岛那头最后一户人家,很晚才能回来。丘姨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吃好了。她是挑着担子进来的(岛上没有自行车),她的篓筐里还有沿路人家托她寄出的几件包裹和邮件。我叫了她一声丘姨,她没有理我,她迫切地要跟她先生叙说沿途见闻,东家长西家短的,我听了一耳朵,并不是太明白。
海边景色很美,风也很大,吹得省里来的青年诗人衣衫乱飘。他姓徐,徐诗人有风格,头发长得像拖把一样,肢体语言也很丰富,他的两个手臂像翅膀一样,走到哪里都要展开来,啊呀呀地感叹一番,当地人不免要对我们侧目,指指点点。走在海边的山路上,四周都是闪烁的渔火,正是墨鱼繁盛的季节,成群结队的墨鱼到此洄游,各地的捕捞船队也随之而来,附近的岛礁上都是他们临时搭的棚屋,星星点点,恰似星河入梦来的感觉。
我们在海岬边遇到一个老渔民,他手里有一顶很大的板罾,凭空伸出海面。他在一盏马灯下沉默抽烟,过会儿,提网看看,有没有一群墨鱼走进他的网里来。他跟我们说,以前只有渔汛时节才会到这里来,渔汛一过,他们就像候鸟一样飞往大陆。有一年冬天,他母亲在灯渡生下了双胞胎,小得跟猫仔似的,他们的父亲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
从海边绕回来,又经过灯渡电影院,其实就在我们的住处附近,它有点像过去公社大礼堂的模样,大门旁边有一个小小的售票窗,旁边挂着黑板,用粉笔写着影片名、放映时间和票价。每天只有一场。我们去探了个究竟,电影刚好结束,场内并没有随之响起一片噼里啪啦的声音,原来座位并不是常见的椅子,只是简陋的水泥长凳。看的人也不多,可能跟渔汛季节有关系,人们都忙着跟墨鱼打交道去了。
我们上楼去找小温聊天。小温正好结束他的工作,坐在他的放映室,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小温有些害羞,看着我们光是笑。我们透过墙上的几个放映孔看,电影院内已空无一人。小温说,如果你们冬天来的话,男人们都出海捕带鱼去了,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全是清一色的女人。我说,男人出海了,女人还有心思看电影吗?小温说,有时候难得上来一部大片,比如《日本沉没》,谁都不想落下。这个场景令我想象出,女人们一边看着罹难者的挣扎,一边牵挂着海上丈夫的安危,该是多么纠结复杂的心态啊。
夜深了,我们坐在电影院的后阳台,丘姨家和电影院都在岛的南坡上,从那里可以看到丘姨家的院子。小温说,以前我常在这里看她在水槽边洗衣服,那时她天天来电影院找我,有月亮的晚上,我弹吉他,她唱歌,她唱得很轻,怕被她妈听到。我说,她妈反对你们交往吗?小温说,她妈看不起我,总以为她女儿以后要远走高飞,我一个小小的放映员哪里入得了她的法眼。小温突然说,这个女人很坏,她把我写给她女儿的信全都扔了,她一个邮递员怎么可以销毁别人的信件?我要去告她,让上面撤销她的劳模资格!我听得笑死。
我对灯渡岛的印象,全部来自刘川林的叙述。虽然他比我年长一轮,但我们关系还不赖。他调文联之前,曾经是灯渡中心学校的校长,人长得像长脚鹭鸶似的,但能量惊人,不仅是个诗人,也会乐器,在岛上组织起了“孤岛”诗社和“黑礁”乐队,一时风生水起。他跟我说,在这个一点四平方公里的悬水小岛上,有四五千人,在这样一个人口如此密集的弹丸之地,所有的隐私都是敞开的,无一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当年,他就像脚下的这座岛屿一样,被大片喧哗的海水所围困,内心的孤独无处诉说。他本来发过誓,不再踏上这个小岛半步,但是,当我们讨论笔会去哪里开的时候,答案显然只有一个,我们说灯渡岛,他就笑了。我知道,他的心里非常热爱这座岛屿。
我的那篇小说,故事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据说是很久以前发生在灯渡岛的一件真实事件,一条庞大的蓝鲸被海浪推上礁滩,搁浅在那里,不断甩动的鱼尾巴,让这里下了几天几夜的雨。灯渡人奔走相告,甚至有人走进了鱼的肚子,在里面看个究竟。说实话,渔民第一次拿鱼没有办法,任它在那里折腾、腐烂。鱼之大,其中的一根骨头,需要七个孩子才扛得动。这篇小说,我想表现的是渔民和大海之间喜忧参半的情感关系。省里来的那位年迈的小说家对这篇小说非常肯定,他说,几乎不用做大的修改。这让我自信满满。
大家都在用功,我拿着相机一个人遛街去了。灯渡街上人来人往,不时有提桶担水的渔民急促地从我身边过去。夏天的时候,岛上的用水总是成问题,因此这里民居的房顶都做成收集雨水的容器。台球店里永远围着一群人,还有录像厅传来的不绝于耳的枪战声。一些闲散的老渔民聚坐在门口,一边聊天,一边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异类。
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这里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大海。海边有一个钓海鸥的小孩,有个提着塑料桶的女孩跟他搭话,问他钓到了海鸥没有。渔家女孩都长得漂亮,海洋鱼类提供的优质蛋白让她们发育得很好,但是相比邻家小妹式的乖巧可人,我眼前的这位可谓是天生的尤物。那感觉就像是一束没有来处的光,打在她的脸上,也投射到我的心里,我简直看呆了,直至她消失在前面的村庄里,我跑过去看,她已不见了踪影。
当年我二十三岁,虽然年纪不小,也有过一些懵懂的经历,但内心仍然苍白。我怀着一个巨大而虚无的心事,茫然地走着,一个看上去比我年长得多的渔民打扰了我,他是一个跛子,所以站在我面前很自然地做着稍息的姿势。他虽有腿疾,但身板结实,皮肤黝黑,双眼被海水渍得通红。他的脸上挂着害羞,他看上了我的相机,问能不能给他拍张照,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拍过照。我说,好,没问题。
他说,那你跟我来。我跟着他,他在前面一瘸一拐地走,他的船在很远的地方停着。他跟我说,我要跟我的船拍一张照片。从摄影的角度,我想从船头拍过去,他说不行,他要把这条船全须全尾地呈现出来。他的船是渔村常见的鳖壳船,不大,但取景框里照顾了船,人又显得太小。我让他离我近一点。他说,我得跟我的船在一起。我说这样人有点小。他说,人小没关系,主要是拍我的船,这条船跟了我很多年。
他叫顾洋,做了很多年的“水乌龟”。当地人把采集野生贻贝(淡菜)的人和行当,都称为水乌龟。他问我是否有兴趣跟他一块去采贻贝。我当然有兴趣,改天吧,我说,我出来还没有请假呢。他告诉我,他最早做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器的,不借助氧气泵和潜水服,一头扎下去,贻贝都吸附在峭壁上,他是用铁钩子钩的。他说,你别看我有残疾,可水性好,在灯渡是数一数二的。我说,我相信,不过我是一个旱鸭子。他笑了。
他告诉我,有一次他碰到了鲨鱼,他们村里有人整条腿都让鲨鱼咬掉了。当时,他在水里死命护着自己的裆部,他说,人这东西在海里发亮的,鲨鱼就盯着你这个地方,你让他咬上一口,你就完蛋了。说罢,他自己先哈哈笑起来。他说这东西长在他身上也没有什么鸟用。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好看的姑娘都飞走了,难看的也轮不上他。
我觉得他不必跟我说这些,他比我年长,而且我们素昧平生,但是他还在不停地说。他说,他最大的愿望是打一条大一点的船,铁壳船。他说,我要在船上放一张床,以后就睡在船里,我打了这条船,就可以到城里去看你。他反反复复地说着这些,让我听得特别难受。分手时,我特意要了他的地址,我说照片洗好了,我会寄过来。
那天下午,文化站张老师过来了,他跟刘川林是老交情,他带来的几个文艺骨干,以前也是刘的麾下。他们看到刘主编都很亲切。后来大家转移到电影院的舞台上,在污迹斑斑的垂幕之间。其实我们都没什么才艺,也就唱歌、诗朗诵什么的,还有我一直揣在裤兜里的一把口琴。他们一个个都是活跃分子,吉他、提琴,还有爵士鼓。那个鼓手跟我说,这个乐队就是刘川林在的时候搞起来的,那时候条件差,甚至没有鼓,他拿来几个木桩子让我们敲,我们到沈家门才见到真鼓,就这样,我们也在文艺汇演中居然还拿到了名次。
后来又来一个笛子手。他跟大家寒暄几句后,一个人站在边角,神色落寞地看着幕后。他为大家演奏了一曲《友谊天长地久》。这本来是我的口琴曲,我只好改吹《啊,朋友再见》。我也不太懂,但是他,准确地说是他手中的笛子,让我想起小真的诗。小真在她的诗中写道:你说忘记吧/黑黑的窗口下/亮闪闪的笛/你说忘记吧/冷飕飕的雨中/湿漉漉的你……我不知道,他是否就是小真内心喜欢的那个人,我很想跟他去聊点什么,但是在高贵的笛子面前,一支破口琴实在无法表达我内心的那份没来由的、要了命的优越感。
那天下午,我们拼命唱歌,从东北的松花江一直唱到海南的五指山。大家都在用年轻人的热情,维持一个因为彼此的陌生而难以烘托起来的欢乐场面。我呢,满脑子都是那个女孩。最后,张老师拿出他那裹着红绸的唢呐,给我们吹了曲《一枝花》,压轴。
后来,小真来了。小真是和她哥哥一块儿来的,她哥哥居然就是顾洋。顾洋给我们带了下午刚采来的贻贝。他有些不好意思,仍然是他特有的稍息的姿势,努力让他的腿疾看上去不是那么突兀。他看到我很意外,也很惊喜,久别又重逢的样子。再看小真,她柔软、轻巧而明澈,略带羞涩的浅笑里郁结着一缕不散的忧伤,我不禁把目光扫向那个吹笛子的年轻人,他已经躲到垂幕的另一边,时不时地扫过来一眼。
刘主编跟小真说,你的信我收到了,你也是我们的作者,这几天你就跟我们住在一起,正好有一张床铺空着。大家都觉得挺好。但小真有顾虑,大概是某人不想看到她跟几个城里人在一起吧。她说她只是想来看望一下大家。刘川林果然是个诗人,他说,你不是不爱他吗?这句话我听到了,他说话的声音很大,简直是吼,你怎么可以受制于你所不爱的人?他算什么,他怎么可以限制你的自由?我告诉你小真,你只属于你自己。
小真被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我们还在台上,像是在等待一场戏剧的开始。
顾洋跟我说,本来他也没觉得那个男的有什么不好,各方面条件还不错。他知道妹妹不喜欢他,但他又觉得“喜欢”这件事是一件多么不靠谱的事情。刘主编刚才的一声吼,似乎正在慢慢动摇顾洋的想法,他跟我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讲话都跟我们不一样。
看得出来,顾洋跟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因为他带来的贻贝,晚餐丰富了不少。他在饭桌上给我们讲了许多海上船上的故事。他正说着,外面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某人。某人瘦长斯文,在他沉郁的脸上,我看到了很不喜欢的一些东西。他并不声张,黑着脸站在那里。再看小真,似乎要哭出声来。此时,顾洋腾地站起来,他忘掉了自己是个跛子,一瘸一拐地走过去,动作幅度很大。顾洋说,你回去。他不回去。顾洋又说了一句,你回去。那个人不动。我没想到,顾洋竟转身向厨房腾跳而去,等刘川林把他截住,他手里已经多了一把明晃晃的白刀。他拿着这把刀,指向某人,你回去!
某人这时开了腔,他说了一句,你这个疯子!
他走了。他走了以后,现场似乎留下来一个巨大的空洞,顾洋还在气头上,情绪的风暴席卷着他的脸部,而我们都陷入了沉默。
那个女孩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闪烁,我无法打听,又不知道人家叫什么,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心里平白无故地怀着一个巨大的害羞。
那天也是巧了,我看到台球房和录像厅之间有一间小小的借阅室,估计也是文化站的地盘,就拐进去了。原来她就在那里上班。看到她,我的脸刹那就红了,真是害羞得莫名其妙,仿佛暴露了一个巨大的秘密。后来有人进来借书,她忙她的。我不知道咋办,找不到缝隙,无处下手。我从一张贴在墙上的值日表上看到了两个女性的名字,我不知道她是哪一个,又不好意思问她,只好凭空估计,分析她应该是那个看起来年轻一点的名字:冯婷婷。我默念着“冯婷婷”三个字,感觉像贻糖含在口中,奇妙无比。
她终于开口问我是否借书。我七挑八挑,挑了一本看上去最有学问的书。登记的时候,她让我签字,我签字。我的手不停地在颤抖。她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抬头看我,你也是诗人吗,跟刘老师一块来的是吧?我笑了,看来这个岛上的人对我们的存在了如指掌。我夹着书离开了那里,回去以后,满脑子全是冯婷婷的影子,每个细节都在一遍遍回顾,浑身火烧火燎的,仿佛已经燃成了炭。
小温下来跟我聊了会儿天,他很开心,他说他给普陀广播电台的晚间节目打了电话,给丘姨的小女儿点了一首歌。他还说,晚上他要把电影院的大喇叭接出来,这样全岛的人都会听到他的表白。我真是羡慕他,对一个女孩子的喜欢,可以这样大胆地说出来,我说不出来,也不能告诉他,一切都腌在自己的肚子里。我问他从哪里打的电话——我猜他还没有勇气去打丘姨家的投币电话。他告诉我,他是在乡政府打的。
当生活存在另外一种选择和可能的时候,你真得感谢上苍——这个乡政府在我们离开之后的半年里就宣告撤销——它连个招待所都没有,但是它有一部通向外部世界的电话,因为它的存在,靠近电话机的玻璃窗没有一块是完好的。正值渔汛,乡干部都很忙,他们看起来就像渔民,没有丝毫国家干部的光芒,他们因为一件亟待解决的事争吵不已,然后又因为什么事,像被一阵风刮跑了似的,全都出去了。
留下我一个人,无比庄严地向那个红色电话机靠近。
我给电台打完电话,回去时又见到了那个笛子手,他在丘姨家后面的山坡上踌躇不前。他问我小真在否,我说在的吧。他低头踢着土疙瘩,不肯再多说半句。其实这个人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好的印象,我想小真的摇摆不定,也只是源于内心的彷徨罢了。
我去找小真。小真在房间里,省里来的徐诗人正在跟她交流。徐诗人一边说话,一边小幅移动,像是慢三步的舞蹈节奏,他们在谈一首诗为什么可以是美的。徐诗人很健谈,我已经领教过他的风采。他俩对我的到来视若无睹。我看到小真的床头放着那本翘着封皮的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我跟小真说,外面有人找你。小真转过身来,她似乎知道是谁,表情已经开始为难,我说不是他。她便明白了,跟我点了点头,飞一般地出去了。
故事就只好凭我自己的想象。我的想象总是那么的美好,因为我也给普陀电台的晚间节目打了电话,给冯婷婷点了一首《粉红色的回忆》,晚上八点半就会播出来,它此刻就像一只蝴蝶,扑扇着马上就要从我的嘴里飞出来。
下午三点半,乡政府安排了一条船,带我们从海面上围着灯渡岛绕一圈。
我们到指定的小码头去等船,结果还没有出发,乡政府的人就过来跟刘主编说,那条船螺旋桨的叶子被海里的网线缠住了,动不了。那个人看到小真,很意外,问,你哥现在在哪里?小真说她不知道。顾洋作为灯渡岛最具潜水资质的渔民,正是解叶子的行家里手。乡政府的人走了,不久,山上的大喇叭就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呼喊顾洋,如果我们不知道顾洋,根本听不明白那个人的方言夹杂在普通话里讲的是什么。
本来挺好,在海上绕一圈,回来差不多就该吃晚饭了。现在离晚上还遥遥无期。我期待天快点黑下来,把无关的时间都省略掉,让电台快点播出我献给冯婷婷的《粉红色的回忆》。由于对时间的焦虑,我发现刘主编戴了一款国产钟山牌手表,但他从来不去看它一眼。我不掌握时间,时间在我未知的地方机密地行走。我后来发现,楼下小邮政所的墙壁上挂着的一只圆钟——我认为它已经坏掉了,在我两次回头看它的间隙,它居然没有移动的迹象。我也实在是闲得发慌。丘姨不明白,我为何老是在她跟前闲晃,她可能以为我想跟她攀谈什么,她的目光里第一次有了友善与期许,这很难得。
此时,恰好有一个姑娘拐进来寄信。她和丘姨之间有一段简洁的对白,充满了邻里之间的信任,然后她就走掉了。我估计她要寄的是一封情书,因为她在信封上羞于写上自己的地址,只写了“内详”二字。这是惯常的做法。每封信的命运都是不一样的。这封充满甜蜜的信交到丘姨手上后,丘姨端详了半天,她捏了捏,然后像鉴定一张假钞似的对着阳光照了又照。我觉得她有把信件拆开的企图,当然还不至于,往日的荣誉阻止她这么做。她在抽屉里找了一支圆珠笔,习惯性地朝笔尖哈了一口气。她太专注了,以致遗忘了我的存在。我看到,她拿笔把“内详”两个字涂掉了——她不允许内详,灯渡岛上没有她不知道的人或事,这种想瞒天过海的做法是她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她又在涂掉的“内详”二字的后面,替人家注明:灯渡乡南田村第四渔业小组某某寄。她对此非常满意,开心地笑了。
餐桌在院子里支了起来,夕阳的余晖透过啤酒瓶在桌子上留下异常明亮的一抹,这是一个节点,是另一个开端,神圣的夜晚由此降临。夕阳一点点沉下去,但是天色并未完全暗下来,它还处于蛋清似的晦滞状态,仍有一些微弱的影子,像是被遗忘的外套未及收走。我从来没有如此期待过夜晚的降临,我满腹心事,怀着甜蜜与不安。我不知道冯婷婷住在哪里,怕她家不在喇叭声的有效范围内,又怕她早早就睡了。
吃了晚饭,他们都到海边去了。我看时间尚早,来到台球房,看人家打球,那个持杆人抽着烟,斜眼盯着其中一只球,等他击球的时候,便把他的烟狠狠地扔掉了。我的心思在隔壁的借阅室,借阅室里亮着灯,意外的是,里面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陌生女人。我不知道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似乎我有什么东西遗留在里面的感觉,令我牵挂。我进去了,问她,冯婷婷在吗?那个老女人从她的座椅上站了起来,她说,我就是。我直接蒙掉了,感觉脚下的水泥地正在崩塌,我悬浮在空中,慢慢地缩小,极端地不真实。我嘴巴里嘟囔了一句,立刻逃了回来。经过电影院的时候,我望了一眼楼上放映室的窗口,知道等电影结束,小温就会把喇叭拿出来。这个想象中的美好夜晚,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无处逃遁,径自回到住处,我连灯也没有开,就趴在床上睡下了,像进入冬眠的昆虫慢慢缩成一团。
我还没有起床,丘姨就已经在院子炸开了,她极其亢奋地向她先生传递着什么,好像是谁家老婆被她老公揍了一顿,接着我听到了一句“粉红色的回忆”。我的感觉好像是一脚踏空,又或者是谁把我重新从高处甩到那张床上,床架一阵痉挛。我知道发生了什么。
借来的那本书我根本就没翻,我想必须马上迅速地去把它还掉,对我来说,故事已经结束了。借阅室的门关着,我不知道它的开放时间,也许管理员只是临时外出。我在对街看到一家理发店,决定先剃个头——或许我只是想暂时躲避一下。老板一个人躺在转椅上,店里的玻璃上贴着许多各式发型的摩登女郎,我张望了一下,他看到的应该是这些摩登女郎之间的一个因为贴着玻璃而变形的脸。他立刻从转椅上坐了起来。老板一看就知道我是哪支“部队”的。他说,你们来了好几天了吧?我说,来了三天。我这么一说,把自己吓了一跳,真的那么短暂吗?在我的感觉里,我好像在灯渡岛度过了一生那么漫长。
这时,有个少妇透过玻璃橱窗向里面张望,老板招手让她进来,她可能看到了我这个外人,扭脸就走了。老板说,其实他最有心得的还是女人的发式,但女人好像都有点忌讳他。我说,肯定是你勾搭人家良家妇女,名声不好。他好像被我猜中什么似的,嘻嘻哈哈地打着马虎眼。我听刘川林说过,在灯渡岛,理发店跟厕所是一样的,女人到男理发师店里去的也有,但这无疑是一桩有风险的事情,特别是这个理发师名声不好的话。
那么,在这个岛上,谁比谁的名声更好一些呢?
这样说着,话就说开了。理发师说,表面上这里的人对男女之事看得很圣洁,其实底下一塌糊涂,就拿那个文化站的冯婷婷来说吧,她勾引了多少男人,全灯渡的人都知道,只有她老公蒙在鼓里。昨天不晓得哪个龟儿子给她点了歌,《粉红色的回忆》,哈哈,这下有关她的所有传闻都坐实了,昨天半夜里冯婷婷被她老公揍得嗷嗷乱叫。我说,是不是跟你也有一腿?理发师笑坏了,露着他的龅牙,抱着我的头乱笑。
从理发店出来,我去还书,我要还掉的不只是一本书。借阅室的门开着,我进去,见到是她,我第一次没有脸红,没有任何害羞的感觉,我被这件事弄得心如死灰,虽然她还在,一切如常,但我心里已没有了期待,我只是来还一本书而已。她本来坐在柜台内,看着自己的手指,看到是我,便站了起来,脸上有些泛红,这是以前没有的,她还冲我盈盈一笑。我说我来还书。本来我想好的,我会在这本书里夹上一张小纸条,上面写上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我还没有想好,故事就结束了。谁会想到她不是冯婷婷。她说,你这么快就看好啦?我低头嗯了一声。她把书收了,问我还借什么书,我说不了,也许我们明天就回去了。其实我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或许明天,或许后天,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但我这样说出来,表达了我内心的毅然决然。你们明天就走啦?我说是的,她看着我,目光里似乎有些不舍,她想跟我说什么,又欲言又止。但是我已经被这件事弄得心情全无,转身便离开了那里。
在我的感觉里,这天的夜晚来得格外早。
我在阳台上看着远处渐渐被乌云吞噬的火烧云,灯渡岛转眼便陷入了黑暗,然后它像一张泡在显影液里的底片似的,在黑暗里慢慢显现它的细节。我远远地看到丘姨房前的路灯旁站着一个女人,好像就是她。我下去了,我想,她在那里等我,她是否在等我呢?我心里并没有把握,我佯装本来就要外出的样子,和她只是意外邂逅。我这样想着,直接从她身边走过去了,然后再回头道,呀,是你。她没动。她不动,我就很为难,我到底是马上离开好,还是再跟她说两句?她换了一件白色连衣裙,连衣裙有些小,把她的身材衬托得非常紧致,我都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和胸口的起伏。
她说,你的书里有一样东西你忘了拿。
我很纳闷,这本书我翻也没有翻过,它只是我的道具而已。或许它原本就夹着什么,恰好这时候跳出来,给了她来找我的理由。她把东西塞给我,我接过来,是一张纸片,上面好像写着一首短诗,我看不太清,黑暗中,那张纸片像一片充满涟漪的水面。她却轻轻将它念了出来:也许/你的目光/飞越城市与海峡/与我的目光相遇,也许/你的吻/落在我美丽的黑发/与我的吻在你的胸中叹息……我有些吃惊,我根本不相信这是书中之物,这是她写的诗,她在诗中向我示爱,她又是怎么知道我是喜欢她的呢?从我借书时羞红的脸?还是那双颤抖的手?抑或是来自两颗心的神秘感应?我说,这是你写的诗?
她没有否认,害羞地笑着。我纳她入怀,她像小动物一般在我怀里挣扎,然后慢慢地平静了。我们在黑暗中抱得紧紧的,一动也不动。她说,走吧。我说,走吧。我拉着她就往海边跑,她一路都在笑,我们穿过村庄,穿过灌木丛,踉踉跄跄地奔到海边,爬到一块火山岩上,我们牵着手,并排躺在那里,她的手像寄居蟹一样老是在动。
夜幕下,星辰低垂,似乎比刚才清亮了许多。我听着轻缓的海潮的节奏,还有它翻动卵石的细微的声响,一阵轻雾从海面上散开来,海风拂过她光洁的脸庞,她仰望着辽阔的天穹,眼神遥远而空茫。她跟我说起了她的父亲。
她说,我家五姐妹,我爸很想要一个儿子,轮到我出生的时候,我爸都没瞧我一眼就出海了。他每次出海,我都在睡梦中,第二天醒来,问我妈,爸呢?我妈不吭声,我爸一出海,她就沉默得像个哑巴。她最关心气象,遇到坏天气就想把我爸拦下来,可拦又拦不住。每次出海,我妈都会把身份证和钱用一个布兜缠在他的腰上。我知道我妈的心思。后来我爸他们在海上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再也没有回来。
据我所知,海难之后,家里人会去海边招魂。是时,海滩上会燃起篝火,好让死者辨别回家的方向。一根毛竹插入瓮中,上面挂着替代死者的稻草人,潮水涨起,钟磬铙钹之声齐发,竹竿摇动,亲人手执火把沿着潮水线边走边喊,伴随着一声莫名的巨响,算是把灵魂招入了稻草人中。我曾亲聆来自海边的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极其凄凉,况味无法细述。
但她给我讲的,却是另外一个怪力乱神的故事。当年同乡的一艘渔船开到一个地方开不动了,原地打转。轮机长查不到原因,船长说,好像有东西。然后船员下海打捞,打捞上来一具尸体,从他身上绑着的布兜里,找到了她父亲的身份证。
mwwe4DV1aCbTVD9P7SRMTA==她讲这些时,语气平静得似乎在讲别人的故事。我把她搂过来,摸到的却是满脸的泪水。我吻她,用舌头舐去她的泪水,拨弄她的眼睫毛,缠绕着她的小鼻子。她滚烫而丰盈的身体被我紧紧地包裹着,我感觉我的身体正在发生变化。她说,带我离开这里,永远不再回来。她说这些的时候,她的手蛇行而至,捏着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有些吃惊,但要命的是,我没有吭声,我突然从单纯的荷尔蒙的冲动中清醒过来,我无耻地沉默着,只是把她抱得更紧,她似乎从我有力的臂膀里找到了她要的答案。
下雨了,她说,我们走吧。我们逃离。回到村里的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她说,到我家坐坐吧。我很意外,好在她家离我们躲雨的地方不远。当时灯渡岛上多数人家已经造起了楼房,而她家还是简陋的石坯房,房间的某个角落好像还有点坍塌,我听到风穿过石缝发出的萧一样的声音。我进去,触目便是五张床排在那里,五个绝色美女,她母亲不在。她的床在最里边,她说,这就是我的床,没地方坐,你坐床上吧。她四个姐姐的眼睛都看过来,各种意思都有,她也没想起来介绍一下我,之前也没有任何的铺垫,凭空而来。而我是一个木讷的人,我大概坐了两分钟,便实在坐不下去了。这种情景,这种气氛,我坐不下去,她似乎也没什么话好讲。我站起来,说,我还是回去吧。我就回去了。她递给我一把雨伞,让我放在旅馆就好了,第二天她会去拿。
当晚,小真在雨夜里失踪了。
我回到旅馆的时候,还有几个人没有回来,刘川林问我,你们没在一起吗?我说,没有啊。是时,还不到九点半,这个时间刻度似乎还在安全值内。
此时,没有人知道那位省里来的徐诗人也同样不在。他和那位年迈的小说家一个房间,不过,年迈的小说家有早睡的习惯,此时他已进入梦乡。
过了会儿,其他人也都回来了,唯独不见小真,没有谁能够回想起来她的去向,外面风雨交加,她会不会在海边出了什么意外。我倒觉得没事,这里是她的家,是她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能出什么事呢?当时小温也在,他陪几个人出去兜了一圈,也跟着过来了。小温说,小真不会回家了吧?刘川林说,不会的,她要回家会跟我说的。刘主编有点着急了,他说,有雨伞雨衣的大家拼一下,我们分头去找吧,两人一组,记得不要走散了。
我们分头去找,各个村庄以及海滩、码头,冰厂都是检查的重点,到处响彻着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声音被风雨吞没的同时,也在黑夜里迅速地传播着,岛上的灯光因我们的呼唤而被点亮,被惊扰的居民纷纷出来打听,而我们语焉不详。我们并不想告诉他们一点什么,尤其不能惊动小真的家人。而此时,年迈的小说家一个呼噜把自己惊醒,他发现徐诗人的床是空着的,去敲刘主编房间的门,刘主编也不在,倒是把丘姨惊动了。于是,小真跟着省里来的诗人跑了这个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了整个灯渡岛,本来只是单纯的找人,现在差不多就是捉奸了。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我试着叫了她一声丘姨,她立刻像神灵似的原地消失了。显然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我和小温来到海边,在海边巨浪的轰鸣声中,我们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呼喊。然而,在一条覆置在岸上的舢板上,我们意外地看到一个人,他就是那个忧伤的笛子手,他像死人一样躺在上面,任凭雨水在他身上冲刷。
等我们回去,小真和徐诗人没事人似的待在各自的房间里。他们说在外面躲雨,这听起来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个理由,显然无法支撑我们的兴师动众,以及各种不乏肮脏的猜想。此事也怪刘川林,他是诗人,诗人做事总是沉不住气。小真他们回来的时候也才十一点多,我们完全没必要如此张扬。当我们觉得事情差不多就这样过去的时候,整个灯渡岛已经闹得鸡犬不宁。小真的家人很快赶到了。顾洋气势汹汹,他扬言要杀掉那个徐诗人。徐诗人吓得躲在房间里不出来,而顾洋拿着刀在丘姨家楼上楼下奔袭。小真站出来,哥,如果你觉得你妹真是个烂货,你就把我劈了吧。顾洋倒是没动,她母亲上去就给了她两个巴掌。
很多年过去,我都记得那天上午离开灯渡岛的情景。正好有一支抬着棺木的丧葬队伍也挤在码头,他们要搭专船到对面的小岛上安葬。文化站的张老师一边吹着唢呐,一边跟我们挥手道别,如此怪异的情景,似乎与我们落寞的内心也很搭。小温来送我,站在岸边跟我说话,丘姨叫他滚开,她拉着脸把几大袋印着“中国邮政”的邮包扔到甲板上。我一直等着那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没有出现。我也搞不清自己的心思,昨晚上她跟我说过的,明天码头上人多眼杂,我就不来送你了,但是她真的不来送,我内心好像也挺失望。
此时,山顶上的喇叭响了。先是敲击话筒的声音,随后传出一个年轻女人呼喊她丈夫的声音。她说,沈家门姑妈已经替我们买好了小天鹅洗衣机,你去拿一下,还有你女儿的复读机你别忘了买,你答应过她的。还有,还有,另外再给我买两个发夹,我要红的,蓝的也行。在场的人,包括那支并不伤感的丧葬队伍里的人,都笑了。
我在想,此刻,如果是她,站在话筒后面,朗诵那首她自己写的情诗,那会是怎样动人心弦的场面啊,我又会如何感愧交集呢?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和她有过十几封书信来往,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城乡之间还横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她在最后一封信中深情地写道: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我咂味再三,终于没有再回复。后来我听说,她被人强奸,又和强奸她的人结婚,总之红颜薄命空流水。我再见到她,已是多年以后,面容枯蒿的她领着女儿来见我,让我解决她女儿在城里的上学问题。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求过别人,这是一次例外,以弥补我内心的愧疚。
电影放映员小温,最终没有和丘姨的小女儿结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决绝要离开灯渡的原因。他在定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街头广告,接着去了南方,他后来的职业和以前的放映员身份有一种戏剧性的关系——他在一家影视公司供职。有一年,他回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走了我一部中篇小说的电影改编版权,虽然一直没有拍出来。
小真的近况,我无从得知。几年后,我在舟山渔民画的一次进京汇展中,看到一幅作品,作者是小真。她画的是一个裸体的女孩躺在海岸边,画风非常像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的那幅《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画面大部分也是一片空旷的长着枯黄色荒草的山坡,不过远处是海,一个裸体的女孩无助而又苍白地匍匐在草地上,绝望地看向远处的海。
三年前,莺飞草长的三月,跟随舟山电视台摄制组,我又一次踏上了灯渡岛。由于渔业资源的衰退和迅猛的城市化进程,这里日渐萧条,几乎成为一座空岛。它的荒凉程度,让我无法面对。我不敢相信,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曾经如此拥挤而繁华的灯渡岛。电影院早已倒塌,我站在高处的石梁上,企图在狼藉一片的废墟里寻找什么。我想起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充满歌声的下午,一阵风起,将我的帽子吹落到那个水泥舞台上。舞台还在,两边的台阶也隐约可见,但是,那些歌声呢,它们飘落何处?
原刊责编 杨晓澜
【作者简介】黄立宇,写作经年,文字散见于《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大家》《钟山》等刊,著有短篇小说集《一枪毙了你》和散文集《布景集》,作品入选2021年“收获文学榜”以及各类选刊选本。曾获浙江省优秀文学奖、首届“三毛散文奖”等。现居浙江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