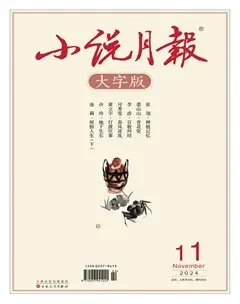春风凌乱
回芳村的路上,燕乔发来微信:哪天回啊?
燕乔跟我是发小,从小玩到大的那种。如今,她在县中学教书,我在北京瞎混。我们难得见面,平时联系也不多。但只要我回老家,她总要赶回芳村来,陪我说说话。私心里,我挺迷恋这样一种关系,确定的人,确定的地方,确定的友谊——生活中的不确定太多了,这点小小的确定,显得尤其难得,并且珍贵,不是吗?
照例是一干人等着,哥哥嫂子、妹妹妹夫,还有我八十岁的老母亲。早有孩子们通风报信,“来了,来了”地喊着。大家都跑出来迎接。我心里惭愧,恨不能像个魔术师,立时三刻变出一车子礼物来。打发走出租车,他们过来跟我寒暄,仿佛我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嫂子哎呀一声,问我怎么又瘦了,太瘦可不好。“女孩子到了这个年纪……”话说半截,被我哥打断了,叫她去厨房看看,炖着肉呢。老母亲在人群里悄悄打量我,一眼一眼地。大半年不见,她似乎显得比先前瘦了,人也矮了,佝偻着腰,被高大结实的孩子们遮挡着,碰撞着,又欢喜,又有点慌乱。我走过去,揽住她的肩膀,跟她贴一贴脸,她费力地挣脱开,有点不好意思:“嫑,嫑,这么大个人了……”
午饭颇丰盛,七个碟子八个碗,嫂子她们还在川流不息地端菜端汤,看架势,显然是待客的饭。老实说,我就怕这个,跟他们说过多少回了,甭费事,就家常饭最好——我在外头还吃不上呢。他们哪里肯听。看得出来,老母亲显得更为不安,甚至有点焦虑。她坐在饭桌的一角,不大说话,只是拿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带着一种近乎讨好和歉疚混杂的笑容,还有暮年之人常有的茫然无助的软弱。母亲老了,说话做事开始看儿女们的脸色了。当年那个风风火火、性格强硬的辣椒嫂呢?屋子里弥漫着饭菜的香味,立式空调吹着暖风,电视柜旁边的那盆水仙开得挺好,白花黄蕊,散发出幽幽的香气。男人们另开一桌,喝酒划拳,吹牛斗嘴,关心着买卖和时局。女眷和孩子们就安生多了,吃菜,说笑,扯各种八卦。我从兜里掏出几个红包,给孩子们发压岁钱。一阵欢腾和喧闹声中,老母亲悄悄扯了扯我衣角,嘴角嚅动,似乎想要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口。我拍了拍她的手背,叫她放心的意思。她的手干枯瘦削,秋天的棉花秸秆一样。我夹了一个肉丸子,放在她碗里。
阳光挺不错,明亮和煦,给人一种模糊的混乱的错觉,仿佛春天已然来临了。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今年春节晚一些,马上就要六九了。树木倒还看不出丝毫绿意,只是乡下的风里,似乎多了一些柔软湿润的气息。树枝微微摇动,也流露着温柔舒缓的表情,不似寒冬里那么冷硬倔强了。村庄静谧,偶尔传来一两声狗吠。
我们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一句没一句地说话。燕乔是午饭后赶来的。她穿一条今年很流行的米白色阔腿裤、咖啡色羊毛大衣,头发微微烫过,很随意地扎在脑后。她也说我瘦了,早先是圆脸,现在下巴颏儿变尖了。“你看你这儿,就这儿。”她摸着自己的脸,跟我比画着。我只是笑,不承认也不否认。在北京讨生活,好比在荆棘堆里打滚儿,胖了或者瘦了,都是小事一桩,皮外伤而已,倒是内心里那些个沟沟坎坎、大窟窿小眼儿,旁人看不见的那种,才最是要命。不过,这话我没有说出口。不是不想说,问题是,即便说了,有什么意义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罢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并没有人逼我这样。当初,我也完全可以留在家乡的县城里,结婚生子,过一种衣食无忧的安定生活,像燕乔这样。我怎么就一根筋似的,一心只想着离开,只想到大城市去呢?是我自作自受,怪不得旁人。燕乔说:“我倒是胖了,你看我这腰……”看上去,她确实比上次见面的时候胖了一些。从小到大,她一直是一个清瘦的姑娘,长胳膊长腿,单薄到叫人担心。而今,人到中年,她倒出落得比年轻时候更好看了,丰腴、饱满,称得上珠圆玉润,有一种到了这个年纪才有的成熟韵味。看起来,她的生活颇不错,至少,比我混得强多了。
嫂子收拾好碗筷,过来打招呼,端过来瓜子花生,又倒了两杯水递给我们。水太烫,一时喝不到嘴里,我抱着杯子,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燕乔呢,干脆把杯子放在地上。热水冒出袅袅白汽,在新春的风里迅速消逝。嫂子问起县城实验中学的事,好不好考、怎么报名、要哪些条件。侄子马上小学毕业了,嫂子想让他去城里读中学。燕乔耐心地给她讲解起来。可能是多年教书生涯的磨炼,她已经拥有一副很好的口才。我记得,小时候的燕乔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性格内向,一说话就脸红,甚至,有一阵子,还有那么一点轻微的口吃。尤其是当她着急的时候,或者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她的口吃会更加明显。什么时候,她口吃的毛病消失了?正月的阳光洒落下来,院子里仿佛铺上一层薄薄的金沙。天空是那种极浅的蓝,浅到发白,有几块云彩,一会儿变作一条狗,一会儿变作一匹马,变幻莫测。燕乔说的不是芳村话,也不是普通话,介于芳村话和普通话之间吧,夹杂着正式的书面用语,还有简洁有力的手势。她在讲台上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嫂子很认真地倾听着,不时点头、发问,眼神里满是信服和尊敬。“嫂子,有啥事你就说话,咱都不是外人——我跟萍这么多年——小时候,我白天黑夜长在这院里……”
我跟燕乔同岁,论生日,她还要比我小两个月。她性子温柔,安静懂事,不像我,出了名的疯丫头,顽劣淘气,什么坏事都干。在我母亲这里,燕乔是最受欢迎的。她的一句口头禅就是“看看人家燕乔”。我是在多年以后,才恍然悟出了生活的一些秘密,或者叫作命运的细微暗示。而今,几十年过去了,母亲也已经步入她的晚年,藏在她心底深处的那一句,恐怕还是这个吧——“看看人家燕乔”。当然,我怎么不知道,这是一个母亲的担忧。她那远在天边的闺女,漂泊在外,老大无成,并且,一个人,孤苦伶仃,并没有过上她想象中的理想生活。我该怎么安慰她呢?
哥的鼾声从东屋传出来,打雷一般,他又喝醉了。他总是这样,酒量不大,还挺敢端杯,耳根子又软,听不得人家一句劝。心眼儿又实,人家给一点好处,恨不能立时三刻掏心掏肺,割头换脑袋。难怪嫂子老骂他。我早就看出来了,在我哥和我嫂子的关系中,我嫂子属于强势的一方,处处压我哥一头。怎么说呢,嫂子是个好嫂子,芳村出了名的好媳妇,贤惠、能干、孝顺——这后头一条最是难得。不说别的,就凭人家给老刘家生下两个欢蹦乱跳的大孙子,坐定江山,绝不在话下。芳村有句老话,媳妇越做越大,闺女越做越小。早些年倒不觉得,这几年回来,嗯,确实不一样了。
午饭过后,人们都散去了,打牌的打牌,串门的串门。孩子们也呼啦一下子不见了,院子里的喧嚣热闹,仿佛也被他们统统带走了。地下零乱扔着橘子皮、花生壳、烟蒂,一只红气球被丢弃在那里,落寞地飘来飘去。老母亲颤巍巍走过来,端着一杯水,往东屋去。“又喝多了,一喝就多。”老母亲絮絮叨叨的。我想过去帮忙,到底忍住了。对于一个年过八十的老母亲来说,给喝醉的儿子送杯水,该是一种无人能够剥夺的权利吧。
我们都停下说话,齐齐屏住呼吸,看着母亲小心翼翼地上台阶,一磴,两磴,三磴。等她终于稳稳当当站在东屋门口的时候,才都轻轻吁出一口气来。“都老了。”燕乔说,语气里是感伤、悲凉和无奈交织的复杂情绪。不知道是感叹母亲她们这一代老了,还是感叹我们这一代也老了。“你还好,一点都不显老。”我说的是实话。当然,我的实话里也有那么一点修饰的成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在燕乔面前,我是不需要任何修饰的。是不是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对诸如真实啊,诚恳啊,这些所谓的人类美德,变得越来越麻木了?我有点讨厌自己。我讨厌自己这种熟极而流的话术,脱口而出,几乎没有经过大脑,更谈不上发自内心。问题是,我怎么以前从来没有觉察到呢?燕乔看了我一眼,笑起来。这一笑,她眼角的细纹被骤然聚拢在一起,变得明显。饱满的两颊微微凹下去,被散落下来的两缕碎发巧妙地遮住。她的头发还是那么好,蓬勃而茂盛,在阳光下闪耀着健康的光泽。“别看了……染的。”她再一次笑起来,仿佛这是一件令人好笑的事情。我记得,燕乔天生头发好,发量惊人,她常常为此苦恼,梳辫子要分四股,橡皮筋最容易弄断,洗头发呢,更是麻烦——要用一个很大的脸盆,头发满满铺进去,黑压压一把抓不透。伏天里,须高高盘起来,免得捂痱子。她母亲常常不无担心地叹息,贵人不顶重发——在燕乔的头发这件事上,她母亲一直怀有很深的偏见。是啊,燕乔的头发确实过于茂盛了。她母亲把她的瘦弱单薄统统归罪于她过于茂盛的头发,吃点东西,都让头发抢去了。这是她母亲的理论。还有一点,过于茂盛的毛发,总是让人产生过于丰富的联想,比方说,身体的某些部位。对一个姑娘家而言,这简直是一种羞耻。总之,少女时代的燕乔,为了自己一头过于茂盛的头发吃尽了苦头。“真的……我骗你干吗?”燕乔说。燕乔的头发烫成细碎的小卷,一大蓬松松扎在脑后,令她看上去有一种慵懒的松弛的腔调,小城生活滋养出来的烟火气,家常而温润,叫人觉得和煦宜人。不像我,这么多年了,在外头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浑身上下成天紧绷着,连睡梦里似乎都攥紧了拳头,仿佛随时随地就能身上长出刺、头上长出犄角来。我成天穿戴着厚厚的盔甲,化着浓妆——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厮杀和抵挡、进攻和防御。然而,我最终得到了什么呢?
我发现自己的第一根白发,是在去年,好像是个周末吧,早晨起来梳头的时候,看见鬓角有一根头发,半截已经白了。我心里一惊,知道岁月这东西厉害,岂肯轻易饶过谁。后来,我又发现了第二根、第三根。我先前还细心拔去,后来,白的多了,就渐渐失去了兴致。我不是不想跟时间对抗,我是不敢。时间这东西,谁能奈何得了呢?“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自古以来,这样的感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何况我等碌碌之辈。这么多年了,我离开故乡,在别人的城市瞎混,幻想着有一天能够混出一点名堂来。有时候意气风发,有时候心绪低沉,有时候彷徨歧路,有时候又觉得人生有味、人间值得。总以为一生漫长,足够我挥霍。在故乡和他乡之间往返奔波,万千滋味,说不得。
然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回芳村了?奇怪得很。在外面倒不觉得,一回到芳村,我就深切地感到,我老了。我们正走在一条越来越短的路上,当然,你说越来越漫长也行。街上走着的年轻人,不认识的越来越多了。那些跑来跑去的孩子,竟然没有一个能叫出名字来了。熟悉的老人,一个一个相继离开。每一回,当我提及某个人,母亲淡淡一句,“他呀,早走了”。我都会心下一惊,久久说不出话来。
“你——还是找一个吧……”燕乔说这话的时候,是小心翼翼的口气,还有一点不易觉察的迟疑,“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吧,一个人,总归还是孤单。”燕乔她为什么要解释呢?作为发小,作为一起见证过彼此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伙伴,她不需要任何解释。尽管,在这件事上,我不愿意接受所有人的善意,或者叫作美意也好。没错,我年过不惑,还是单身。在芳村人眼里,我简直就是一个妖魔鬼怪,要么就是有什么问题。总之,我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在芳村,跟我一般大的发小们,都早已经成家立业,儿女成行了,有的甚至还有了第三代,当上了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我不愿意猜测,在这件事上,我的亲人们,尤其是我的母亲,到底承受了什么,承受了多少。“慢慢来吧。”我说,“这种事,没办法。”燕乔没有说话。她把手上的戒指摘下来,戴上去,再摘下来,戴上去,反反复复,仿佛这枚黄金戒指是一个魔咒,戴上它,就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么多年来,这是她第一次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她算是早婚,二十三岁结的吧。当然,在我们这一带也属于正常。结婚,生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当老师,是我们这地方能够想象到的最适合女孩子的职业了。她住在县城,跟村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娘家在芳村,婆家在田庄——跟芳村相邻的一个村子。她在这个熟悉的人情世界里往返奔忙,如大雁在天上,鱼在水中。我从来没有问过她是不是快乐,也不知道她对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满意。我是觉得,我自己混成这样,有什么资格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呢。阳光从燕乔背后照过来,可以看见她脸颊上细细的绒毛,被镀上一层薄薄的金色。她的耳垂圆润可爱,近乎透明,还有下巴颏儿上那颗美人痣,在光影交错中显得俏皮生动。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恍惚了,仿佛眼前还是那个一头浓密头发的小姑娘,被大人的梳子弄疼了,噘着嘴,眼睛里含着泪花,不知为了什么,却又笑起来,笑得弯了腰,笑声清脆,在时间的深处激起迷人的回响。阳光静静地照下来,我们坐着,吃花生,喝水。花生是自家种的,拿细沙炒过。水是白开水。我们这地方,大多没有喝茶的习惯。老实说,我挺享受这种感觉。两个人,安静坐着,即便是不说话,也不觉得尴尬。风悠悠吹过,一点凉意也没有。暖阳之下,我有一种时间静止、地老天荒的错觉。我这是怎么了,一回到芳村,怎么就变得软弱了?
我哥的鼾声忽然停止了。东屋里传来砰的一声。母亲受到惊吓,瑟缩地看了我一眼,又小心翼翼看一眼东屋。东屋挂着丝绒门帘,大红底子,上头绣着莲和鱼,是连年有余的意思。我朝着母亲笑笑,叫她放心。她坐在廊檐下,离我们不远不近,安静地鼓捣她的那些干菜。燕乔也看着我,眼神里滑过一丝紧张。“没事。”我笑着说。我知道,这是每次回来必须上演的一出。没有这一出,我的回乡就算不得完整。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东屋里隐约传来争执声,极力压低了声音,却依然能够穿过门窗,穿过那张寄托着连年有余美好心愿的大红门帘,传到院子里。母亲显然变得惊慌,她已经顾不上她的干菜,坐直了身子,警觉地盯着东屋的门帘。我用目光安慰她,不让她过去看。“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我怎么不知道,这是一场无须劝说的战争,不见硝烟,莫名其妙地开始,莫名其妙地结束,每次回来,必定上演。我想,很可能,我就是那个唯一指定的观众,或者,叫作裁判,叫作事件终结者也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通力合作,演了这出好戏,给我这个远方归来的不孝女看。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对我的困境知情。也许,他们,尤其是嫂子,根本不相信,我在外头混了这么多年,真的是两手空空。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钱,甚至,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那我还瞎混什么呢,这么多年?很可能,我的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做派、打肿脸充胖子的臭毛病,容易给他们造成某种错觉。燕乔渐渐变得松弛下来。从她的表情看,她似乎也明白了一些其中的奥妙。以她的聪敏明慧、人情通达,还有什么是她不知道的呢?她在城乡之间往返,事实上,她自己就身陷在世俗人情的大网之中。她比我懂得太多了。小时候,玩过家家,她总是扮演那个当家的女人,做饭铺床、抱孩子做家务,内政外交,她都能搞得定。在那些童年游戏中,她就已经显露出某种过人的禀赋。这么说吧,燕乔是世俗生活的胜利者。不像我,我是在经受了这么多年生活的捶打之后,才慢慢悟出了一些道理。比如,东屋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及东屋门帘上的莲和鱼,它们之间某种不可言说的关联,千丝万缕,只能一点一点细细拆解。
燕乔的电话响起来,是任素汐唱的《大梦》。正月的阳光下,在芳村的老院子里听这首歌,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身边是迟暮之年的母亲,还有一生下来就认识的发小。东屋的鸡零狗碎,此刻也显得那么甜蜜。甜蜜而悲伤。这平凡而琐碎的人生,叫人爱不得恨不得,爱恨交织。燕乔接电话,不知是不是出于习惯,把身子略略向外倾斜了一下。日光下,她的影子落在连接院子和屋子的台阶上,被一段一段截开,歪歪扭扭,却富有某种韵律。她微笑的时候,下巴颏儿有点双,可是奇怪得很,她的双下巴挺好看,有一种中年妇人才相配的雍容。阳光从她的背后穿过,她的头发蓬松柔软,每一根都被勾勒了灿烂的金边,星星点点,金丝银线,有点雾鬓云鬟的意思了。她的咖啡色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米黄色毛衣,胸脯饱满,微微显出一点小肚子。她饱满的胸脯、微微凸出的小腹、双下巴、眼角的鱼尾纹,还有右手无名指上那枚金戒指,让人觉得亲切有味,甚至,让人隐隐生出一丝羡慕,我不想说出“嫉妒”这个词。没错,我一直在微笑,我为我的发小,我的多年老友而喜悦,可是,我得承认,内心深处,我是感到有那么一点点嫉妒了。岁月偷走了她很多,然而,生活到底还是给予了她更多的馈赠,或者叫作补偿也好。我这是怎么了?我为什么总是想起当年那个清瘦单薄的小姑娘呢?那时的她有点口吃,说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阳光照在我的背上,暖暖的,熨帖温柔,包容万物,给人一种巨大的抚慰感。强光下,我轻轻闭上眼睛。无边的黑暗包围了我,还有一种骤然降临的微微的眩晕,世界仿佛在安静地旋转,旋转……耳边似乎有轻轻的鸣叫,夹杂着燕乔说话的声音,嘈嘈切切,然而也安宁妥帖。就这样大睡一觉多好,大睡一觉,醒来发现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大梦。电话那头应该是燕乔的丈夫,他们在说孩子上补习班的事情。燕乔叮嘱丈夫去接一下,别让他老玩手机。燕乔说:“我在萍家……跟你说过的……”我睁开眼,燕乔冲我挤挤眼,小女孩一般,仿佛我是她的同谋,我们共同拥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没事吧?”我说,“耽误你接孩子了。”燕乔说:“让他接去,正好让他干点活——老打麻将。”关于燕乔的丈夫,我知道的并不多,就像燕乔对我的生活也不见得有多少了解。我只知道,燕乔的丈夫当过兵,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县城里工作。他们有一个儿子,正在读中学。这样的家庭,在县城里,算得上不错的人家,稳定、富足、体面,脱离了农村,又跟乡下血肉相连。燕乔是她父母的骄傲,这种骄傲看得见,摸得着,骗不了人的。不像我,说起来在北京,可是,天知道在北京干什么,混来混去,到现在还没有混上一辆车——当然,房子也没有混上,只不过人们看不见罢了——更要命的是,连个家也没有。这个你还不能跟他们辩解,婚都没结,怎么能算有家?我常常乱想,在母亲眼里,尤其是在哥嫂眼里,这么多年来,我是不是越来越成了一个不便提及的话题?这个让我日思夜想的家,我还能轻易回来吗?
正月里,白天到底还是短的。阳光一点一点收敛起它的金色光芒,淡淡的雾霭悄悄升腾起来,村庄沉浸在薄薄的暮色中。院子里有点冷了,杯子里的水也早已经变凉。我请燕乔到屋里坐,燕乔说不坐了,她还要回家去看看她母亲。我没有挽留,我已经占用了她一个下午。她的儿子、她的丈夫、她的母亲,正月里,她肯定还有很多家务琐事要应对。燕乔说,她母亲不知道她回芳村来,她们原来约定的是明天回来。东屋的门帘一动,嫂子笑眯眯出来,热情地留客,说:“晚上包饺子,现成的肉馅儿。你们难得见面,好好说会子话。”燕乔说:“今天就不麻烦了,下回再来吃嫂子包的饺子。”她还夸嫂子的羽绒服好看,气色真好,还是那么年轻,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萍的妹妹呢。嫂子欢喜得不行,脸上红扑扑的。两个人加了微信。嫂子说:“孩子上学的事,少不得麻烦你。”燕乔说“不麻烦,不麻烦”,笑眯眯的。
燕乔家早先跟我家不过隔着一户人家,后来搬了。她弟弟盖了新房,住在村子西头。她母亲跟她弟弟一家住。我眼看着她开着车飞快地向村庄深处驶去,汽车扬起淡淡的尘土,又慢慢落下来。天边的晚霞已经消失了。夜风吹过树梢,发出细碎的声响。门口的大红灯笼亮起来,暖融融的灯光,照着大门上的春联。“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桃花红”。门上贴着门神,怒目金刚,威风凛凛。母亲咳嗽一声,喉咙里发出一声类似于叹息的无意义的声音,蹒跚着往回走。此时,太阳早已经落山了,暮霭淡淡,笼罩着田野和大地。远处的树木变得模糊,只能看出大概轮廓。而夜晚的村庄越发幽深,幽深而安静。我正要抬头看有没有月亮,燕乔的微信来了:萍,好好的,都好好的。一个拥抱的表情。
嫂子包的饺子不错,猪肉白菜馅儿,是我们芳村最家常的吃法。我得承认,这么多年了,吃过千奇百怪各种馅儿的饺子,我还是最好老家这一口。你说怪不怪?
晚饭后,我出来,站在院子里,抬头看见天边的月亮,月牙朝上,细细弯弯的,金色镰刀一般,在蓝黑色的天上静静悬挂着。繁星点点,稠密极了,在头顶闪烁,那么远,那么近。而夜风浩荡,新的春天已经降临人间。
原刊责编 王梦迪
【作者简介】付秀莹,1976年出生,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野望》《陌上》《他乡》,小说集《爱情到处流传》《朱颜记》《花好月圆》《锦绣》《无衣令》《夜妆》《有时候岁月徒有虚名》《六月半》等多部。曾获首届《小说选刊》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首届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五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第四届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奖项。作品被收入多种选刊、选本、年鉴及排行榜,部分作品被译介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