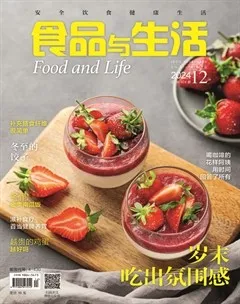五凤楼里的水乡风味
沈嘉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坛好吃分子。
慎余里
糟骨奉芋红膏蟹
今年的早春二月,我去慎余里赴一个朋友的饭局,向晚时分,游人稀少,复刻的石库门弄堂里,青砖砌成的墙壁火气十足,有水泥栏杆的阳台上也不见个人影。在我拍了几张照片之后,房间里倒是渐次亮起了灯光。这里已有数家餐饮企业入驻,“甬涌阁”就是其中一家。慎余里所在的天潼路,在清嘉庆年间已是“人家栉比,居然墟集”,这里也是浙商在上海抱团取暖、砥砺奋进的场域,20世纪30年代,租界工部局以浙江宁波天童(潼)为名,把原先浙商所建的“东唐家弄”改为“天潼路”。
后来改天换地,这里的人烟越来越稠密,妈祖庙被用作学校,还有一些房间则塞进了十几户居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坍墙,那里搭建,旧模样总被雨打风吹去。20世纪90年代,我误打误撞进去看过一眼,那里已破败得不成样子。再后来居民全部动迁,梁架窗棂及旧砖碎瓦被收拢来,堆在仓库里。现在经过修复和平移,这座没有妈祖像的妈祖庙就成了一个历史符号和文化地标,偶尔也会来一场时尚品牌发布会。
“甬涌阁”占了一幢石库门房子,装潢上努力还原上海滩黄金时代的调性,从旧房子里拆下来的彩色地砖铺得“天衣无缝”,走在上面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令人不免想起旧上海的种种奇闻轶事,比如商界同仁的宴饮,比如宁波商帮与租界工部局的争斗。
这一餐吃出了浓浓的乡味,比如一款自制糟骨加奉芋加红膏蟹。浙江菜系中有许多食物必须通过发酵来转换谷氨酸和蛋白酶,以呈现最鲜美的风味,这是长期形成的食俗,也是鱼米之乡民众的生存智慧。芋艿在红膏蟹的加持下,糯滑的本性被赋予了鳞甲一族的鲜甜。糟骨头又是“象山三宝”之一,厨师将猪软骨剁碎后加入酒糟发酵,酒香浓郁,咸中带甜,用来与海蟹同蒸。加上奉化芋头的尽力衬托,馥郁酒香与膏蟹的鲜甜呈现出令人愉悦的满足感。
蒲瓜家烧东海小白鲳、山葵叶烟熏鲳鱼饭、苔菜粢饭糕配小方烤、香酥雪花牛肉等等,也在老宁波风味基础上进行了改良,盐分减轻,使之成为适应现代人的风味饮食。
宁绍美食中苋菜梗和臭豆腐怎么可以缺席呢,它们可是完美定义了“臭鲜”的概念。在餐桌上,江南稻作文明就凭借着这一味安抚了无数游子漂泊的心。宁波三臭,清蒸是常规做法,而他家厨师以鲜汤为基底,将苋菜梗和臭豆腐及米鱼饼,烩制成一道浓郁的汤,鱼饼的鲜味似乎更加鲜活了。
曹家渡
老卤猪头肉
进入夏季后又在曹家渡一家新淮扬风味餐厅里体验。他家老板将江苏溧阳、淮安、盐城及其下辖县射阳一带的食材引进大上海,比如萝卜、蒜薹、韭菜、莼菜、蒌蒿、白茄、蒲菜、白蛤、银鱼、老鸭、甲鱼、花鲢等等,携来了一股股清新的乡土气息。
射阳老卤猪头肉,彻头彻尾的下里巴人的美食,据店家宣称,他家的那锅老卤已经有40年啦,爷爷传下来的。肥嘟嘟的猪头肉是上海老男人的童年记忆,但此物不登大雅之堂,所以虽然时起想念,却少有机会大快朵颐。而今,但凡得知饭店老板自射阳采购食材返沪后,我都要去这家店大吃一顿:“老卤猪头肉就是我的充电宝。”
渔姑巧手蟹豆腐,与上海的蟹粉烧豆腐不是一回事。据老板说,这是他从小在家乡吃惯的土菜,将射阳海滩上满地爬的蟛蜞抓来,放在石臼里捣烂,滤渣取汁,与黄豆浆、鸡蛋液一起制成有许多微小的气孔的非标豆腐,然后将豆腐切成骰子块,在蟹壳熬成的高汤里煨煮,最后加青椒碎提味。吃一块豆腐,豆腐里有满满的蟹香鲜味,再喝一口汤,汤里更有青椒的清新,令人感慨土菜亦不凡。
印象深刻的还有菊花脑猪干汤和野葱蒲菜,食材来自淮安。蒲菜,是蒲草插入河底泥中的一段嫩茎,出水后呈象牙白色,是当地人的口福,在上海几乎看不到,所以许多号称“吃货”的上海人不知天下有此物。其实蒲菜入宴已有2000多年历史,《周礼》上即有“蒲菹”的记载。明朝顾达有诗曰:“一箸脆思蒲菜嫩,满盘鲜忆鲤鱼香。”不过此物极其娇嫩,必须当天采、当天卖、当天吃,吃到便是福气。30年前我在淮安第一次吃到蒲菜,惊为天厨仙味。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至今还被多家媒体、多种图书转载,也算我对蒲菜的小小报答吧。如今冷链物流发达了,所以他家的蒲菜能够当天从苏北运来,还带着晶莹欲滴的露水呢。蒲菜一般是奶汤煨或开洋烧,他家是用野葱和法国朗德鹅油堂的,那股香气谁也挡不住。
还有一道土菜是麻虾酱蒿子杆。麻虾酱也是我家里常备的,平时用来炒通心菜、炖蛋羹,而他家的厨师用它来炒蒿子杆,有一种洋溢着野性的香气和鲜味,我头也不抬就吃光了自己的那一份。
朱家角
老建筑里的一场秋宴
上周去青浦朱家角安麓酒店参加“秋食记”分享会,这个活动已经办了5年,也是对朱家角旅游资源的挖掘和宣传,助力长三角深度融合。今年,主办方青浦文旅局特地取了个名字:吾爱青浦人情味——我爱青浦人、青浦物、青浦景、青浦味、青浦游。
我对青浦的风物是不陌生的,早在半个世纪前,姐姐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浦造船厂工作,其实是专造为内河航运服务的水泥船,规模也不会太大。但姐姐每月要回家休假,经常带来活蹦乱跳的鲫鱼和河虾,秋后则有刚刚轧出的青浦薄稻。逢年过节我还要奉老爸之命,早早地去车站接“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姐姐。吃了青浦的鱼虾,又得知“三泾不如一角”的说法,对青浦的好感自然形成。有一次还去青浦玩了两天,当时的城厢镇与故乡柯桥十分相似,河畔桥堍自发形成了喧嚣的集市,各种农副产品看得我眼花缭乱。去朱家角要到20世纪90年代初了,由姐夫陪着去,亲眼见了放生桥、北大街,还有衰败的城隍庙,感觉寂寥得很。我在一家古董店捡漏一只明晚期的青花盆,石榴、桃子、佛手构成了三多图,稍有冲线,无伤大雅。
最近20年里,朱家角的旅游开发得相当成功,景区不收门票的亲民举措,吸引了巨大的流量。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一两次,对朱家角的美食多有着意,阿婆大肉粽、稻草扎肉、熏青豆、云片糕、鳑鲏鱼、红烧羊肉等总是吃不厌。
课植园附近的这座国际范的精品酒店,大堂是一幢移建于此的明代“江南第一官厅”的五凤楼,保留了旧时宗祠仪门的制式,五对翼角如凤凰展翅,气势恢宏。前五后七开间,三进两天井,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门宽近4.5米,廊高约10米,由某大学士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题写的匾额保存得相当完好。修复时用苏造金砖铺地,严丝合缝,油光锃亮。楠木柱包浆厚重,冬瓜梁之粗壮,在江南一带也极罕见。难得的是没有过多雕刻,装饰花纹素简,可见主人品位不俗。如果临时改作雅聚场所,可容纳上百人。
流连于此,让我久久痴迷,不知今夕何夕。“秋食记”就在这里举行。
秋高气爽的时节,室外泳池的一泓碧水倒映着周边的嘉树,茶桌上有一壶清茶和一碟熏青豆,飘落树叶两三片。庭院两厢有长廊,廊有柱,立柱下半截是花岗岩,上半截是楠木,这种式样我是第一次看到。廊下,朱家角丝竹乐队在演奏,乐师都是当地的小姐姐小帅哥。朱家角的大叔大妈则在展示非遗手作,稻草扎得巧,就成了饭窠、草龙、草鞋和九层宝塔;麦芽塌饼是豆沙馅的,现做现吃,味道超好。
淀山湖
腐乳汁稻草扎肉配田螺塞肉
当晚菜品是典型的朱家角风味,因为活动请来了法国米其林星级厨师,所以头盘就让法国人走个秀吧,食材由娇嫩的樱花色虾肉、十年卡露伽鱼子酱、酱汁烤鳄梨组成,然后用虾黄打成的细腻泡沫提味。法国人喜欢泡沫,似乎所有食物都能以泡沫的形式呈现。
接下来切入主题。水乡三友:练塘茭白、淀山湖莲藕、淀山湖菱角三者合一,练塘茭白是上海的骄傲,不比无锡茭白差。这三种食材无须过度烹调,以素直形象出镜,茭白肥嫩、莲藕生脆、菱角粉糯,食材的本味呈现出秋的丰盈。接下来是水八仙石榴包,蛋清摊成的薄皮将江南人看重的“水八仙”一网打尽,扎成小巧玲珑的石榴包,看看也养眼。
主菜是淀山湖鳜鱼狮子头,这是对江苏菜的借鉴,鳜鱼与河虾仁及肥膘三者合一,经过一番细切粗斩的操作,抟成玉白色的狮子头,又经鸡汤的加持,晶莹剔透,十分入味。接下来是朱家角北大街江南第一茶楼里的臭豆腐,油炸结皮,再入汤煮,微辣更提味。据说第一茶楼每天要卖出数百块,老板娘从云南建水来,所以油炸臭豆腐干加了辣椒蘸水,入口相当刺激。从狮子头到臭豆腐干,这个转换有点猛,但确实提气。
时值蟹季,秋食季里当然要有一只淀山湖的大闸蟹。青浦朋友介绍,作为弱感潮湖泊,淀山湖生态环境得天独厚,一级水源地所养育的大闸蟹够得上“清水”二字。所以淀山湖大闸蟹虽然产量小,却也是蟹肉鲜甜,膏肥脂满,敢于跟江南其他水域的大闸蟹“比拼”一下。在兹念兹,吃相也要文雅,在安麓五凤楼的场景里,厨师就用淀山湖大闸蟹做成蟹酿橙。这道从南宋穿越千年而来的经典名肴,香气还是那么诱人,掀起橙盖,挤一下酸甜的汁水,与蟹粉拌匀,味道鲜甜酸爽。
还有每人一只的朱家角风味的大闸蟹,也是第一茶楼的手艺呈现,用古方松针酒来加持淀山湖大闸蟹,还配了河虾和蚬子增鲜,汤汁艳如滴金,酒液至纯至阳,仿佛喝醉了酒的大闸蟹别有一番风味。
还有一道腐乳汁稻草扎肉配田螺塞肉,扎肉与田螺塞肉都是朱家角饭店里的招牌,扎肉一定要用新割的稻草来扎,煮时才能散发谷物的香气。厨师将田螺汆一下后挑出螺肉,与猪肉一起切碎,经过去腥处理,馅心里还要加泡软后撕碎的油面筋,这样吃起来才不腻不柴而有层次感。馅心拌匀后塞回螺壳内,封口过油,再小火红烧,浓油赤酱的本帮味道,最能收服人心。
田螺塞肉这道土菜是有故事的。话说在旧时,有个念佛茹素的老太太,因病卧床已有多年,某日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突然起念要吃田螺塞肉。这叫榻前伺候的媳妇很是为难,不给婆婆吃,于心不忍,但要是给婆婆吃了,等于破了戒,使婆婆功亏一篑。踌躇半日,终于想出一个妙法,她将香菇泡发后切成末子,又将无锡清水面筋泡软切条,用这两种净素食材拌成馅心,塞进洗净的田螺空壳内,加酱油、白糖,小火慢煮,起锅后多浇麻油。不是荤腥,胜似肉味,婆婆吃了甚感欣慰。这个故事赞美了有变通能力的贤惠媳妇,老太太一身的修持也得以保全,结局堪称完美。
在分享会上我讲了这个故事,也想看看大家的反应。果然,在座的小姐姐们与老年朋友的观点不一样:人生道路接近终点,满足一下卑微的心愿有何不可?那个媳妇似乎在行孝道,其实是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卫道士。
主食是新米咸肉菜饭,厨师当场在庭院里烧煮,大家都吃得喜笑颜开,最爱这一味的宏非兄毫不客气地将锅巴铲起打包,第二天还能吃一顿。收尾甜品还是交给法国帅哥厨师雨果,他用青浦金泽老谷仓农场的新米做成米布丁,用梨子酒炖青浦当地所产的秋月梨,切成薄片后刻模,再以巴厘岛香草荚新鲜湿润的香草籽增添异域风味,最后盖在米布丁之上。用中国食材展现法国风情,太有想法了。
在当下百花齐放的餐饮场景,味觉返乡成为广泛认可的审美追求。来自乡间的土菜,得到城市文明的滋润,又融入了时代的审美,让我们进一步理解了食物与风土的关系,也让我们再次感受到民间土所蕴含的浓浓亲情和纯朴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