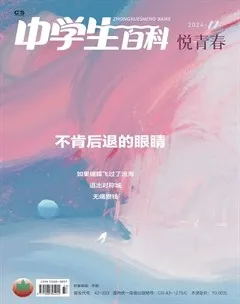谁懂新闻实习记者的心
在断断续续写稿、成为新闻实习记者的600多个日夜里,我不止一次从前辈口中听过这样的话:新闻记者可不好当,你可要慎重。听闻我从小语种转战新闻赛道,前辈们无不露出担心的神情。
新闻记者这个职业真的这么难吗?我想未必如此吧。在当实习记者的这些日子里,我体验了它的好与坏,喜与忧。这段经历让我对它仍然充满期待。
我自认为是半路出家的野生记者,并非新闻专业出身,没有专业的训练,关于记者的一切经验都来自实践。从一开始的慌乱无措到逐渐适应,最后竟也成了编辑口中还算不错的实习生。
《钱江晚报》是我和记者这份职业最初的联结,十来岁时家中常年订阅《钱江晚报》《都市快报》一类的报纸。那是十年前,每天厚厚的一沓报纸,记录着纸媒的黄金年代。在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新闻的年纪,每天定时翻阅报纸已然成为习惯。那时候我想,要是有一天我也能为报纸撰写文章,做个记者该多好。做记者的梦就此在我心里萌芽。
大学选专业时,我并未选择新闻专业,误打误撞进了小语种复合专业,但心里似乎一直放不下对新闻传播的执念。大二那年的暑假,《钱江晚报》发布了一则招募高校通讯员的消息。尽管缺少相关的学习和实践,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朝报社的邮箱发送了自己的简历,并附上了几个希望操作的新闻选题。
很快,我就收到了回复,是晚报深度部的副主任回复的。她告诉我,她很看好我的选题,希望我能尽快操作出稿件。彼时的我并未自己独立撰写过稿件,也未曾有过采访的经历,但机会来了,总舍不得放弃。我接受了老师的邀请,从此开始了实习记者打怪之路。
那是一个关于毕业季的温暖选题,2022年毕业的女生因学校无法举办毕业典礼,于是为自己策划了一场专属仪式——她在校园一角留下移动摊位,希望能用一颗糖果换来路过的同学的一句祝福。故事的结尾,她用400颗糖果换到了400句不一样的祝福语。那一次的采访出奇地顺利,从找人、采访到写稿,一气呵成。一周后稿件发布,我忐忑不安地等待编辑老师的评价。她言语里是温柔的鼓励,我开始觉得,我也许是可以把采访、写稿这些事做好的。
当然回头看,这算不上一篇多好的稿子,也无法被称为深度稿,它只是一则暖新闻,但不可否认,它给予我继续走下去的信心。在晚报实习的半年里,我过得很幸福。我实习的这个部门,多是女记者,与她们合作交流总让人如沐春风。老师们也不吝啬于教会我一些采访实践技巧。在写了十几篇稿子后,我有了关于记者职业的初步认知,我发现自己很喜欢采访时和陌生人建立的短暂关系,也对这样的联结充满好奇。
对记者职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是来源于《北京青年报》的深度部。在那里我度过了一段艰辛却也飞速成长的时光。我每天面临想不出像样选题的尴尬境地。在这里的六个月,我泡在各个软件的热搜榜里,想在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寻找独一份的选题。选题的挖掘与呈现也是需要煞费苦心的。在不断地报选题、采访、写稿中,我也算慢慢摸出了怎么发掘深度报道选题的方法与呈现方式以及操作路径。
参与突发事件的报道与采写的日子,是忙碌的,是煎熬的,也是充实的。在这样的日子里,记者熬,编辑也陪着一起熬。我们一起探讨事件的呈现角度,陈述真相,引发读者的深度思考,让我们发出的稿件能引起关注。也许我们的稿件很快会被其他新闻所覆盖,但我写过,记录过,就不算白干。这微小的声音曾被发出,就不算没有效用。
结束实习的那天,一位关系不错的老师送了我一句话:作为新闻人,要正义凛然,声音再弱,也要倾听,声音再强,也要敢质疑。为何报道,报道何事,必须时刻自省。这句话一直落在我的心里。
离开报社、退出编辑部群的那一天,我走在马路上,旁若无人地哭了。我哭是因为害怕自己再也做不了报道,再也写不了新闻了。也是在离开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我是真的喜欢上记者这个职业了。如果未来有一天,我无法成为记者,我会有多难过。那一刻,我的感叹是:以后无论去哪,只要继续写下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