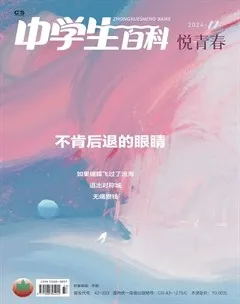唐诗里为啥没西瓜
在入冬的时节想吃西瓜,是不是跟唐诗里为啥没有西瓜这样的问题一样奇怪呢?这应该是个有趣的话题。
唐诗,被誉为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据统计,现存的唐诗作品数量有五万多首,对应的诗人数量也达到三千多人。无论是从创作者还是作品的数量来说,都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但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一个诗人或一首诗,有提到“西瓜”的。是他们不喜欢西瓜,还是他们不知道西瓜为何物?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楚西瓜的“身世”。
西瓜又叫寒瓜、水瓜、冰瓜,有“瓜中之王”的美称,据说它原产于非洲的热带沙漠地区,属于野生的葫芦科植物。在今天北非的某些地区,还能找到最原生态的野生西瓜。西瓜因瓤甘甜多汁,且能充饥解渴而颇得人们的青睐。
早在4000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开始在尼罗河畔种植西瓜,这也是人工栽培、改良西瓜品种的开端。之后,西瓜的瓜籽及种植技术,伴随着人类的经济、文化交流及迁徙活动,沿着地中海沿岸先传至北欧地区,而后又南下进入中东、印度等地,在公元五六世纪的时候,传播至西域的回纥(今新疆)等地。至公元9世纪,随着契丹破击回纥的战争,西瓜籽被带到了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今东北、内蒙古等地),而后机缘巧合,瓜籽又被一个叫作胡峤的汉人,千里迢迢从辽地带回中原地区。

说到胡峤,此人的经历颇有几分传奇。他原为同州郃阳(现属陕西渭南市)县令,公元947年,他作为宣武军节度使的副手,随萧翰进入契丹。没过几年,萧翰因故被杀,胡峤也被辽国给囚禁了起来。在关了六七年、饱受折磨之后,他终于趁看守松懈的机会逃了出来,一路风餐露宿,靠乞讨南归中原。回到故乡后,他根据自己在辽国(契丹)的经历和遭遇写成了《陷虏记》一书。其中有这样的记载:“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以牛粪覆棚而种,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首先是叙述了他刚入契丹时,在草原某地吃瓜的情形,说这种大如冬瓜的“西瓜”口感非常的甘甜爽口,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于多年之后还是念念不忘。同时他从当地人的口中获知了西瓜的来历是“契丹破回纥得此种”,也就是说,在契丹攻打回纥(新疆)时得到的瓜籽 ;他甚至还学到了西瓜的种植诀窍是“以牛粪覆棚而种”。
这段传奇的经历也让他斩获了好多个中国第一:他的自传《陷虏记》成为国内有史以来最早出现“西瓜”一词的书籍;胡峤本人也成了国人中(那时的契丹不在中国的管辖范围之内)有记录的最早吃到西瓜的人,可谓是最早的“吃瓜群众”;他也是最早将西瓜籽及其栽培技术引进到中原的人。胡峤也算是个有心人,尽管历经苦难、九死一生,还不忘在逃亡的途中,将吃剩下的西瓜籽缝到破棉袄的夹层里带回中原。他知道,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这是个好东西,既能抗饥解渴,还能卖钱糊口,做过父母官的他敏锐而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胡峤回归中原的第二年,即他将试种成功的西瓜的瓜籽分发给百姓,并指导他们用“牛粪覆棚法”培育西瓜的那段时间,中国历史正处于大分裂、大动荡的“五代”时期的最后一个王朝——后周。那一年是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4年),离唐朝“毕业”的公元907年已将近半个世纪。
胡峤的故事回答了唐代诗人的笔下为啥没有西瓜这个问题。不是他们不爱,而是在他们生活的年代,西瓜还没有传入中国。至少在诗人们的“触角”所能达到的中原、南方等地区还没有。见都没见过,又从何谈起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