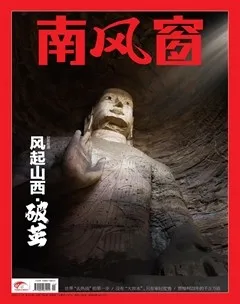没有“大放水”,只有审时度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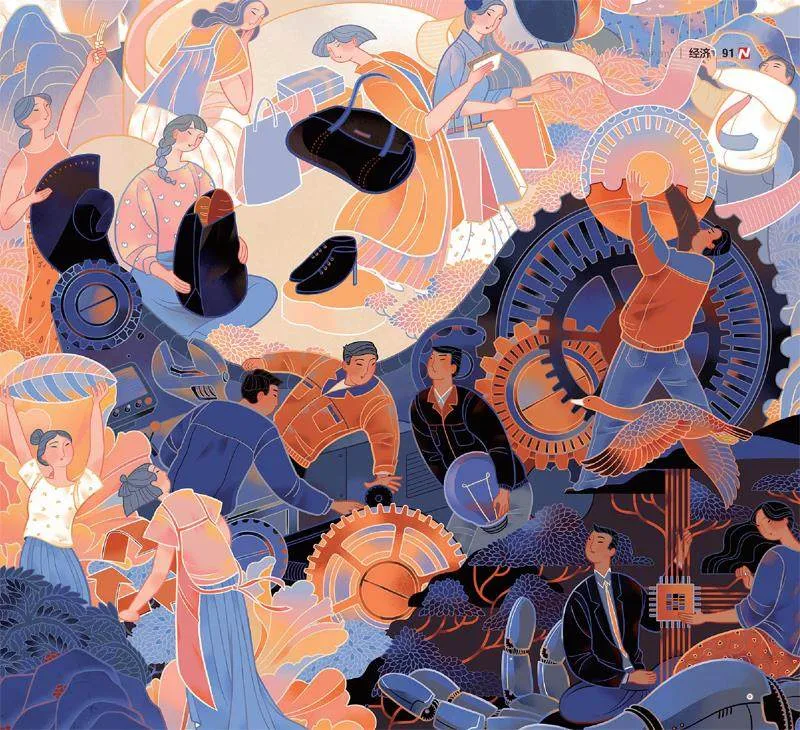
从9月底开始,伴随着A股的行情变动,关于提振经济的“万亿级计划”就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
11月8日,市场迎来了重磅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宣布,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
根据该议案,在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建议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为地方政府腾出空间更好发展经济、保障民生。
从数字上看,这的确是一次“万亿级计划”。但和一些市场观点所预期的不同,本次计划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债务,市场一度讨论的特别国债发行问题,并没有被重点涉及。此外,有关措施也主要指向了化债这一具体领域,问题导向明确,可操作性强。
实际上,某一轮政策和预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早已不是关键。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宏观政策的“工具箱”依然十分充实。随着外部形势的不断变化,比如特朗普的再次当选,留给未来更多的政策空间,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更显必要。
化债的意义
本轮措施涉及三个关键的数字。除了“6万亿”之外,还有“10万亿”和“12万亿”的说法。
从2024年开始,我国将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那么,加上这一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6万亿,就等于总计增加地方化债资源10万亿。这是“10万亿”说法的由来。
另外,2029年及以后年度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因此,市场上又有了“12万亿”的说法。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市场观点所谓的“大放水”并没有发生。“放水”主要指向了货币政策的加码,特别是银行信贷的宽松。虽然化债措施必然涉及银行,但它主要是通过财政手段来实现的,货币政策只是一种辅助。那么,什么是债务置换?要真正理解新一轮的经济提振措施的影响,就必须懂得这个概念。
顾名思义,“置换”更侧重于对债务存量的性质改变,而不是直接指向了债务增量。因此,地方债务的债务置换,相对于地方债务的新增发行来说,自然也显得更加克制。置换的意义是什么?最直接的意义,首先是疏导和化解可能的区域性、地方性金融风险。
本轮措施明确指出,将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所谓隐性地方债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些“半市场”的负债主体向银行借款,将资金用于地方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一些城投性质的地方国企。这些主体有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向银行借款也相对容易,过去很多时期的地方债务狂飙,都有它们的“功劳”。当然,它们也对城市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不可否认。
地方政府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大量公共服务的供应者,基于这个逻辑,本轮化债意义非凡。
但通过这一类“半市场”负债主体从银行借款,存在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增大了各级财政部门对地方债务的管理难度。负债主体虽然有地方政府的隐性担保,但担保到底到什么程度,无法界定。到底有多少算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也没有明确的比例划分。因此,将这些“隐性化”的债务进行调查梳理和重新界定,将其“显性化”,对地方财政管理的规范化很重要。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债务是非标的。比如,它们的负债主体可能股权结构复杂,不同级别的政府或者国企持有其股权。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一般来说,上级政府的信用会好于下级政府,政府部门的信用会好于国企,那么对一些股权结构复杂的负债主体,由于其股东结构混乱,那么自然很难确定其信用资质,不利于市场对信贷资金的定价。
此外,隐性债务的具体负债形式可能是多样化的,有不同期限的贷款,资金的融出者主要是银行。另外,也有相对标准化的债券,资金的融出者,不但包括了银行,也可能包括了保险公司、房地产信托基金等其他金融机构。不同类型融资工具的并存,也给对债务的管理增加了难度。
因此,按照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些通例,所谓的债务置换,一般会将融资工具尽可能地进行标准化,比如将非标的银行贷款置换为相对标准化的债券。过去几年,我国的债务置换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实情,进行了行之有效的创新,但主要指向依然是将隐性债务尽可能显性化,同时也将融资工具尽可能地标准化。
将隐性债务显性化和标准化的第一层意义,显然是方便管理,但另一种意义或许更加重要,即降低地方的融资成本。对金融市场而言,有更明确的负债主体,更标准化的融资工具,自然会降低债务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那么融资成本自然走低。当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银行对有关债务进行展期的动力,也会更大,这就降低了地方的还本付息压力。
对当下的地方政府来说,这一点非常重要。财政部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了23287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4.6%。显然,基于房地产市场的现状,一些地方的财力必然承受不小的压力。
一边是收入下降,另一边是债务存量依然可观,即使是隐性债务,也绝非小数。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年末,全国隐性债务余额为14.3万亿元。这一数字相对于过去几年,已经大幅降低,但基数依然不小。如此巨大的基数,每年需要支付的利息成本也自然十分可观。
如果通过债务置换,一定程度上降低利息支出,对地方政府的财力自然会带来积极影响。在压力降低之后,地方政府将更多的空间和能力,用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地方政府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更是大量公共服务的供应者,基于这个逻辑,本轮化债意义非凡。
充实的“工具箱”
稳健的化债正在推进,但市场对所谓“大放水”的预期,并没有在本轮措施中得到明显体现。此前,按照一些市场分析人士的预计,财政部门将可能发行特别国债,用来补充大型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以提升银行的放贷能力和信贷效能。
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具有严肃性和审慎性,市场预期很大程度只是代表了部分投资者或者分析师基于当下经济形势的一种期待,并不能直接影响有关政策。但是,预期也有一些线索。比如,10月12日,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就曾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资本。
在11月8日公布的本轮措施中,特别国债发行问题显然让位给了债务置换问题。但对市场来说,对发行特别国债的预期依然存在。毕竟,入股发行类似的特别国债,的确具有强烈的信号意义。
发行特别国债补充银行资本金,和“放水”的关系更加直接和明确。《巴塞尔协议》是全球银行业监管的基石性规范,对银行资本和风险界定有严格的监管要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巴塞尔协议》不断地进行完善和改革,但对资本金的监管一直都很严格。中国银行业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直都紧跟并遵循着该协议的有关规则。
《巴塞尔协议》曾一度把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定为8%,那么也就意味着,资本金比银行风险资产的数值,不能低于8%。简而言之,资本金充足率的严格限制是对银行安全性的要求,同时也限制了银行的放贷能力——银行风险资产主要通过银行放贷来创造。因此,如果银行信贷要不断扩张,要保证其达到监管要求,就必须补充资本金。
银行通过货币乘数创造资金,约束主要是资本金,但那是一种相对柔性的约束,而财政涉及很多深层次问题,约束往往更为刚性。这也是市场之所以对特别国债发行如此关注的重要原因。
1990年代末期,我国的银行业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当时,我国为提高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让其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便发行过一次特别国债,金额为2700亿元。资金注入大型国有银行,有效地提高了其资本充足率,让中国的银行业在这一标准上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
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期的增长,离不开银行体系的信贷。而银行作用的发挥,又离不开包括发行特别国债注资国有大行的这一轮改革。发行特别国债注资大型国有银行这一举措,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因此,有关措施何时出台,出台力度如何,也必然会慎之又慎。
特别国债的发行,可能是信号意义不亚于万亿级别化债的措施。对经济增长来说,银行体系提供资金的能力显然会超过财政措施。银行通过货币乘数创造资金,约束主要是资本金,但那是一种相对柔性的约束,而财政涉及很多深层次问题,约束往往更为刚性。这也是市场之所以对特别国债发行如此关注的重要原因。
中国经济的韧性十足,拥有强大的本币,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必然是独立自主的。但不容否认,中国经济已深入融入全球化进程,外部形势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会成为内部政策制定时的参考变量。
11月初,特朗普从美国大选中胜出,将于2025年1月担任新一任美国总统。作为一位行事风格和其他政治人物截然不同的总统,新一届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必然会有变化,而且力度无法预测。
如果美国关税政策进行大幅度的调整,那么必然会对出口有影响。出口一直都是包括我国在内很多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而且,出口不但影响经济增长本身,它的创汇所得还牵动着本币汇率和金融稳定。此外,爆发在东欧的战争和中东的冲突,也会有所变化。当国际上的“连横合纵”出现新趋势后,近几年的国际贸易新增长点,必然出现转换。
因此,对经济高度融入世界的大国来说,分轮次推出有关措施,让政策工具箱中保留足够的“弹药”,在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掌握宏观政策的主动权,引领和管理市场预期,无疑是一种理性而富有前瞻性的策略。
没有“大放水”,只有审时度势的宏观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