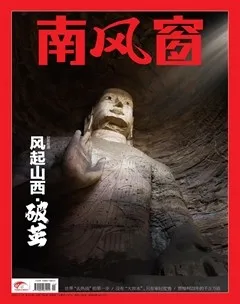舌尖上的吕梁,吃“土”也疯狂

一团拳头大小的淡黄色,在黑色瓷缸底被反复捶打拉扯,随着师傅灵活熟练的双手腾挪变换,像极了南方的手握糍粑。
这是山西吕梁一家“土豆宴”的后厨,目之所及,烈火烹油之下尽是形态色泽各异的土豆。师傅是个年轻小伙儿,面色红润,微微发汗。不一会儿,他捞出缸底的土豆,扯出一坨拇指大小,再捏成汤圆形状,装盛小碗,淋上酱油、醋和葱花及香菜,给我们浅尝。
香港美食家蔡澜说,“浅尝”是一种本事,是一种对食物细节的尊重。一股绵密的、甘甜的清香,沿唇齿下渗透。没有花枝招展的调味和辅料,也能顷刻间俘获味蕾。
在吕梁人民手下,不仅土豆,哪怕是“黄土”,也能被化为舌尖传奇。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我第一次踏足吕梁,五感皆被一股浓郁的泥土气息包裹。这里的“泥土”,不仅指漫山遍野的黄土高原景观,也指代一种贯穿天地和楼宇的平朴和厚重。
以太行山、吕梁山和黄河为界,山西被划分为三块相对封闭的区域。汾河与吕梁山相遇处,就坐落着吕梁。东卧太行山而垂,先民因形取义,见大山绵延如巨兽,“吕,骨脊也”,连在一起的山脉和脊骨,即为“吕梁”。
数千年华夏历史长河里,吕梁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阻碍了一部分外族入侵,保证了晋文化在历史上的相对完整和连续,但同时也隔绝了一部分对外发展的机会。
可恰恰就是在这么一块天生条件困厄的土地上,吕梁的饮食文化,如大漠奇葩一般,在黄土大地上世代沉淀,渐成历久弥新的瑰宝佳酿。山河表里,内有乾坤。
那一碗的承托
午饭,一只碗被递到眼前。
一只碗,精巧轻盈的,薄薄一层瓷壁。掂在手里,对着阳光,才见内壁一层青灰色的荞麦肉。碗如硕掌,把以荞麦和水为主做的面团轻轻托起来,二者仿佛合为一体。碗上方搭一把拇指长的银质小刀,用刃轻轻划开质地柔软的荞麦坨子,铺在中央底部的辣椒油沿着细缝下渗,直至浸染整只碗。
头茬辣椒、麻油、花生核桃仁制成的辣油,如雨后的盆地积水,浅浅地兜在碗托底部中央,泛着艳丽的油光。烈焰入口,却无半点辛辣刺激。再低头一看,那张扬的红色更像热情的旗帜,宣告着对食客味蕾的攻城略地。
吕梁柳林“沟门前碗团”的创始人贾旭东教我一种吃法:先将碗托中部挖开一个小圆,辣椒油会顺着圆边渗进去,第一块便是最入味的那一口。直接用小刀叉进嘴里,入口冰凉,却有着南方凉粉没有的柔韧性。
对于碗托的历史,当地流传的一种说法,最早追溯到千年前的西晋时。那时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被派去进攻都城洛阳的大将石勒,就是吕梁离石人。石勒在柳林三郎堡垒扎营,战时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导致士兵们粮食短缺,只购得一些荞麦,只好把荞麦磨碎熬粥喝。
一次,几个军士外出,误了饭时,回来后,荞面粥已凝结成块,舀不起来,只好将硬结在碗内的凉荞面块用手扒下来吃。歪打正着地,竟觉适口。
也许有当时条件艰苦的原因,但从结果来看,“碗托”的形与实,的确就这样被流传了下来。
在“十里不同音”的山西,碗托也可以叫碗团、碗凸、碗坨、碗秃。但就形而言,大抵还是“碗托”最准确。
在山西,几乎每一样如今被列入传统的食物,背后都可能铺垫着一段由实用性发育而来的民间历史。
比如一种名为“栲栳栳”的面窝。“栲”是植物的泛称,“栲栳”指用竹条或柳条编成的称物器具。和开莜面,将面团分小块蒸熟,在手掌中搓成一个“长寸许,薄如叶”的卷面筒,再整齐排入蒸笼内,形如蜜蜂的巢穴。
相传,唐国公李渊被贬太原留守,途经灵空山古寺,寺中方丈特地做了一道莜面窝窝款待他。后来,李渊当了皇帝,为感谢当年方丈的恩德,便请他去五台山当住持。方丈赴任途中看见莜麦丰收,便将莜面栲栳栳的制作方法传授给了当地的百姓。由于这种食物像极了存放东西的“栲栳”,百姓便把莜面窝改名为“栲栳栳”。
在山西不少地区人家,孩子们从小吃的酸枣面,因外形酷似黄土,就被戏称为“吃土”。
在吕梁,不少美食都有着生僻甚至相当拗口的称号。它们大多源自当地百姓的口语相传,在蹚过工业化与市场化后的现代商业社会,也未曾想着要将它规模化、标准化,这是独属于晋西大地的一份自足和自洽。
靠土吃土
老话讲“民以食为天”,在山西,民先“以地为食”。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西人民脚踏黄土,靠土也吃土。
在吕梁,“土地母亲”这个说法得到了具象化的展现。如今,仍有少部分地区人民住着旧时的泥土窑洞,冬天睡温土炕,吃黄河水。从前,许多农村媳妇生下孩子来,也是落到土里。
黄土高原的孩子对土的亲切与信赖是自骨子里长出来的,是一种温暖的天性。即便环境干旱贫瘠,吕梁人民也依然与土为乐,以土为荣。
在土做的吕梁,连食物也是“土”做的。
在山西不少地区人家,孩子们从小吃的酸枣面,因外形酷似黄土,就被戏称为“吃土”。对于“土”,山西人民所抱持的,是毫不犹豫张开手臂拥抱的深情和信赖。
中国自古信奉“天人合一”的天地哲学,对土地的敬畏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敬畏。农业社会几千年,土里长出来的小麦,是晋人在舌尖上安家的基底。
“四十里莜面,三十里糕,二十里荞麦面饿断腰。”山西人吃面,光“莜面”就有数十种形态,比如两端尖细的面食叫“抿尖儿”。将绿豆面和白面粉混合的“豆面”捏成蝌蚪形状的细条,晋中地区更为直白,呼“抿圪抖儿(蝌蚪)”。
如今,许多人家还保留着一种井字形木质床架,中间放置铁或铜制的抿床,床上密密麻麻排列着细小的孔眼。将面和成团,置于平面,再用带柄的铁“抿拐”做出“抿”的动作,使面糊从抿尖床的孔眼中穿过、成形,落入锅中。
山西人善朴,对食物的命名,多以其形直白赋之。寻常人家油炸,空心无馅、皮上有糖,长得像油糕的叫油器,真似一只油做的器具。状如面条,细绳一般卷起来的叫“馓子”。北魏时期,高阳太守贾思勰就在《齐民要术》里记载过馓子的制作方法,并称之为“细环饼”。

面粉单调,但晋地先人总能在枯燥中取趣。每一步都有“形”,亦有“神”,小麦本身的厚重和精巧技艺并存,劲道和绵密兼具,叫人品出一份山河共济。
这是对麦与谷的讲究和敬意,本质上,是对土地的敬畏。
还比如土豆。作为历来中国家常餐桌上最常见的基础食材之一,不太抬得上价。而在吕梁,土豆可以有108种做法,当地引以为傲的“土豆宴”,就囊括至少“捣、滑、溜、汆、醮、焯”等数十种细致入微的技法。
擅长用最常见、最单调的平民食材,烹调出千变万化的味觉,是山西人民在饮食上的独特智慧。这份通达是当地人民在长久以来的求存之旅中,自然探索发展而来的。而对人民及生活本身的尊重,让许许多多自历史深处沿袭下来的技法和味觉得以保存。换句话说,也许正是因为食材的单一,山西人民才在漫长的生存与开拓历史中,衍生出了不变中生万变的生存智慧,一种通变、达观的生活态度与意趣。
不变
吕梁一隅,折射出晋人在“吃”上的善朴与讲究。不过,中国传统八大菜系其实难觅晋菜身影。2001年,晋菜短暂跻身“新八大菜系”,但也因宣传力度微弱而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
在吕梁酒店餐饮协会秘书长樊益明看来,山西美食走出大山的一大阻碍,是相对生僻的民间称呼,以及“十里不同乡”的内部地缘差异。“头脑”不是脑花,而是一种用炒面、山药、羊肉等食材熬煮的“八珍汤”;土豆做成的烩菜“炒恶”,“恶”字完全是方言口语。于是,在最富丽堂皇的饭店,你也能看见“炒恶”这般字形不善的传统名菜(但在吕梁方言中,“恶”意为有能耐、有本事)。
在吕梁,土豆可以有108种做法,当地引以为傲的“土豆宴”,就囊括至少“捣、滑、溜、汆、醮、焯”等数十种细致入微的技法。
令樊益明忧虑的是,随着晋菜大师年龄老化,加上人才的职业培训几乎为空白,深有造诣的晋菜厨师渐渐后继乏人。目前,晋菜烹饪的培养仍以 “传帮带”为主,“但现在,愿意从事烹饪工作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即便学习,也有不少只是为了找份工作”。
不过,某种程度上,这反而成为了山西美食的一大吸引人之处。它并不张扬,不擅长推销自己,像一个永远驻守原地,背靠大山、脚踩大地的老翁,世世代代安居于此,沉默、笃定而扎实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山窝窝”吕梁的厚重是嵌刻在历史渊薮里的。这里走出来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也走出了抗战巾帼刘胡兰。时间浪淘里,那些真正坚韧的精气神留存下来。
在当代第六代导演贾樟柯镜头下,故乡山西有着柔情的一面。他形容自己出生的吕梁汾阳,“有着独特的光线,或许因为她地处黄土高原,每天下午都有浓烈的阳光,在没有遮拦的直射下,山川小城被包裹在温暖的颜色中,人在其中,心里也便升起几分诗情画意”。
吕梁地处黄河中段,没有湍急与壮阔的水流,取而代之的是阳光下徐徐流动的光泽和晶莹。一河之隔的那头是陕西省,同一片阳光下,土地缀连,河水流动,一股动态而温沉的气息,将两岸包裹。
天上来的黄河水,在河套平原骤转后,一路向东撞上吕梁山,南下出壶口,滚滚东去,雄峻浑阔,磅礴奔腾,而后静流退之。一静一动,勾兑出这片黄土大地独有的一份温沉和柔美。
沉甸甸历史里,提纯出来独一份的轻盈与明媚,就像以“饱”为主的食物里,也承载着一粒粒小麦的优雅与细腻,一颗颗土豆的粗粝和淳朴。
晚秋入夜早,吕梁街头的小吃摊上燃起烟火人家的星星点点。灰扑扑的挡风帘背后,透出若隐若现的“炸恶”“沾串”“合楞”,没一个词能叫外来者一眼看懂。山西人也没指望将个中奥妙张扬出去,就像脚下这块坚实平静的黄土,悠久而绵长,沉默而安然自得。
告别吕梁,我这个南方人逆着晚秋热情似火的阳光,舌尖仍然回味着这些日子流连的清爽和扎实——这两个词同时在晋地美食上存在,相辅相成,延绵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