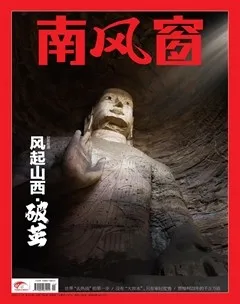风吹黄花,大同遍地生金

恒山北,太行西,内外长城之间,是北方锁钥,大同。
万马酣战之地,冯唐持节而来,恩赦云中太守魏尚;花木兰卸甲而归,于明堂叩拜天子。中原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于此,拓跋鲜卑吃肉饮酪,亦食谷蔬鲜鱼。
大同人向来是擅长在交汇之处创造的。金戈铁马之中,大同人环顾四周,捧起一抔火山土,又引来桑干河水,在过去的大同县、现在的大同市云州区,成片成片地撒下一种种子——黄花。
火山环伺,河水充沛,水与火交融之处,生出晨开暮闭的小黄花。在来自蒙古高原的朔风之中,在千年古刹的风铃声中,可入宴食用的小黄花于塞上边城摇曳生姿,成为历史书中记载的“上等佳肴”。
时间流转,600年后的今天,黄花仍然是大同云州的瑰宝,却不只是作为食物出现。在更高的维度里,它是产业,是更好的生活,是希望。
当十余万亩黄花绽放于盛夏7月的大同云州时,上至80岁老汉,下至10岁小童,都会扎在黄花堆里。采摘、搬运、杀青、晾晒或者加工,40天花期里,各家各户都有得忙。
因为这一朵鲜花,在大同云州这里,会有多种多样的可能。它会出现在茶里,饺子里,烧麦里,饼干里,甚至是酒里,或者以酱、汤料、青菜的形式出现在餐桌上。
只利用这一朵花,大同云州一个区就做出了22亿的全产业链产值,将产业人员人均收入提高至5000元左右,让入了股的贫困户领到几百到上千元不等的分红。
2012年时还在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县名单上的大同云州,如今已经跑出了15家黄花深加工企业,6家省级龙头企业。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同云州的黄花基地,了解黄花产业带领脱贫的工作成果。他指出,黄花菜也能做成大产业,“一定要保护好、发展好这个产业,让它作为人民群众致富的好门路”。
在赫赫有名的大同煤田与历史古建之外,云州开出千朵万朵黄花,让大同长出新的希望。天时地利人和汇集在城市与草甸的相接处,云州人种出一朵花,化历史中的干戈,为今日的玉帛,美美与共。
难
随机询问一个大同人,大概率会得到这样的答案:“黄花,小时候经常吃。”
大同云州,有600余年的黄花种植传统。在更长的时间段里,农户们你三亩我五亩地种着黄花,房前屋后地晒着黄花,就这么凑出了1975年时的1万亩种植面积和150万公斤的产量。这一年,云州(原大同县)就被山西省政府评为黄花基地县。
但这并不代表种植黄花是一件易事,相反,对于农户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除草施肥,干上整整一年,黄花也未必能变成口袋里的钱。靠农业吃饭,看人也看天。
比起杂粮,黄花算作一种“金贵”的作物,种黄花的人,更需要一种毅力。
“(种植黄花)前两年肯定没收益,第三年管理得好一点,能拿回一点成果,第四年就开始有产量了,一般盛产期是5 年以后。”谈起黄花特性,大同市云州区黄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一鑫给出了“至少三年培育期”的回答。
在周士庄镇黄花产销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王倾看来,“三年能打个平手的黄花,那是很好的黄花”,在更多的情况里,种植户还是需要继续贴钱,才能迎来丰收。
三年里,种植户要干的事却一件不少。3月萌芽前浇水、旋耕、施肥,6 月抽薹适度浇水追肥,7月采摘期盯着土壤潮湿程度,看天浇水,秋后再施肥积累养分。一年到头,浇水施肥和除草的活要来回干。
但这期间可能出现的干旱、冰雹和泛滥虫灾,都会要了黄花的“命”——干旱会让黄花减产,突降的冰雹会把黄花打落,而易发的蓟马、蚜虫和红蜘蛛一旦泛滥成灾,种植户就只能认下绝收这一个结果。
丰收,也是一场持久的硬仗。
难做,不意味着不做,尤其发展总是得建立在因地制宜之上。如果依靠集体的力量,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实现规模化种植?云州决定试一试。
采摘期,为了能在花蕾未开放时及时摘下,及时蒸制晾晒,不久放,种植户们常常是夜晚采摘,白天加工,24小时都呆在地里的人不在少数。“(有时候)迷迷糊糊躺下就睡,什么时候有时间就睡一会儿,习惯了”,王倾常常如此度过40 天花期。
能养人的黄花,首先靠人养,一整套程序走下来,唯有耐得住“寂寞”的人,才能以黄花致富。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对于农民个人来说,试错成本是巨大的。
难做,不意味着不做,尤其发展总是得建立在因地制宜之上。如果依靠集体的力量,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实现规模化种植?云州决定试一试。
“这个产业好发展,人们认识这个东西,历史上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有产业基础。以前是农民做,规模化种植的少,于是,云州也就选了它作为脱贫攻坚的特色产业。”张一鑫解释道。
“听别人说,都能挣钱”
王倾和许堡村俊仙黄花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薛俊仙,原来都不是种黄花的。
在2012 年大同云州将黄花产业定为“一县一业”之后,越来越多政策出炉。原本只知道黄花,却不清楚怎么操作种植的他们,才逐渐加入这个行业。
“在家没事干,想出来做点别的。当时鼓励大家种黄花,听别人说都能挣钱。”原本赋闲在家的薛俊仙开始从事黄花产业的理由非常简单,在被政府帮着找到合适土地后,薛俊仙比着周围的农户,开始自己种黄花。
到2017年,薛俊仙决意扩大自己的事业规模,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合作社。
2017年,对于大同云州的黄花来说,其实是一个关键的节点。用张一鑫的话来说,“2012年、2013年更多是农民自己做,合作社、企业和种植大户们进行规模化种植,是到2017年”。
补充上王倾进入黄花产业的契机,或许能让整个规模化种植的图景明朗一些。
2017年,周士庄镇开始大面积带领贫困户脱贫,1258个贫困户带着政府给的1000元补贴,入股刚刚成立的,由6 家黄花合作社联合而成的黄花产业联合社。王倾在这时接手联合社成为理事长,一边做散岔村党支部书记,一边埋头在地里种黄花。
“虽然种黄花有600年的历史,但不是每个人都懂。我(当时)是什么都不懂,就得学,得和周围的老百姓拜师学艺。”带着贫困户,王倾的“压力”大了些,心里想着“怎么着也得脱贫了”,于是,培育期间,王倾又张罗着种上别的作物,给贫困户创收。
如果要发展黄花产业,成立合作社或者联合社只是第一步,关键还得把种植的“后顾之忧”一一攻克才行。
“当时发展黄花种植以后,云州区专门跟省、市政府争取下来农业保险政策,现在主要是自然灾害险。每年多多少少发生雹灾和病虫害,能给种植户提供一些赔偿。”张一鑫回忆道。
解决气候灾害还不够。种植面积一大,病虫害就多,这是种植户的共识。每一个种植户,都承受不起绝收这一毁灭性打击。于是,“每个乡镇派遣至少一个农技特派员,区里统一预算,每年两次无人机飞防。2022年,区政府又聘请来甘肃庆阳市农科院的专家,特别来研究黄花病虫害问题”。
链条逐渐成型。农技员就在田间地头观察,一旦在黄花叶子里发现害虫,就上报农业局,由农业局出具监测预报,再由县统一组织或者农户个人进行害虫防治。与此同时,每年到访云州四五次的专家,也会讨论意见,给出方案。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十余万亩的黄花栽种起来,花季的抢收工作量不可小觑。恰恰,抢收只能依靠人力。因为黄花不像棉花,其花蕾的成熟时间不一,无法一次性全部采下。而目前的机械,还不能识别哪朵是已经成熟的黄花蕾。
“必须雇佣采摘工,但本地的采摘工数量不够,每年解决不到一半(黄花)。前几年就是政府出去跑,和山东、河南政府协调,把人‘调’过来,这些年(工人)自动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在张一鑫的回忆里,云州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把成熟的花蕾采摘下来,换成钞票的。
到2018年底,田间地头的事太忙,王倾辞去了书记的职务,彻底扎进黄花堆里,就这样守着这三千来亩黄花。迎着西北的大太阳,他说:“不怕,我们这儿就这样。”
田地给予了他们馈赠。2019年,靠着黄花,联合社里的1258个贫困户一人一年分到了500元,“小试牛刀,赚了点,虽然不多”,提起这段往事,王倾是骄傲的,“到2020年,黄花已经到了4年(株龄),我们就又给每个人分了1000块”。
靠着黄花,收入大幅增长,在过去几年的云州反而成了一件常事。
百亿级产业
大同三利集团的总经理庞乃东戴上眼镜,郑重地说道:“有些东西我觉得达到什么时间,你就做什么事情。”
到2018年底,田间地头的事太忙,王倾辞去了书记的职务,彻底扎进黄花堆里,就这样守着这三千来亩黄花。迎着西北的大太阳,他说:“不怕,我们这儿就这样。”
受制于气候,大同黄花一年生一季。为了能够延长产业链,云州区建起了86个加工点,50个合作社中又有近一半,拥有自己的加工设备,具备收购加工能力。但企业们做的,往往不只是收购加工。
在“产出—加工—销售”的逻辑上,企业需要思考和行动的,远多于合作社。因为,市场的目光一直在变化,黄花菜这一种产品形态已经不足以支撑企业去攻城略地。想要吃下市场份额,就得主动出击。
“企业还是得创新,”大同云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占云说道,“现在准备研发一个黄花项目,还不成熟,类似于清水黄花的项目。”
比起单纯地售出干菜、冰鲜花菜,更多的企业会把目光放在“产品”上。依靠着产地优势,庞乃东觉得可做的事还有很多。
比如,过去三利集团用黄花和小麦酿出啤酒,利用黄花的功效,撇去啤酒加重痛风的风险;又比如,根据南方市场的反馈,把黄花、松茸和羊肚菌放在一起,做成南方人最爱的煲汤汤料。
“要把黄花产业发展好,必须要产品升级。”庞乃东补充道,在这点上,三利和云萱都把目光投向了有机产品。“如果做有机,渠道和消费人群就不一样了,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种高标准高回报的模式”,在王占云心里,有机也是产业与企业的双赢。
往更广阔的天地走,也是云州的目标。
“我们市委书记提出来,要把黄花产业打造成一个百亿级产业。云州区是大头,我们一直在朝这个目标努力。”说到这里,张一鑫笑了。
产业链上的每个人都在想办法。
王倾和薛俊仙看着地里的黄花想,怎么样才能提高产量,怎么保证40天的采摘期;庞乃东和王占云则看着各式各样的黄花产品想,怎么拓宽渠道,怎么利用产地资源做出品牌价值。
作为产业服务中心主任,除了田间管理的提质外,张一鑫想的,还要更多些。
2024年,张一鑫带着各式各样的黄花产品跑了四个地方,在北京、深圳、太原和成都分别办了四场黄花推荐会,把有意向的经销商、餐饮代表都聚在一起,让黄花有更多路可销。
“过去和京津冀的联系多一些,以后希望更多往南方走。”末了,张一鑫这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