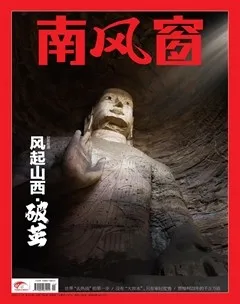文献
1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与新质生产力
赵波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
本文为赵波在北大国发院MBA讲坛第75讲
先谈谈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从1978年开始,我们的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波动,但平均增速非常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前40年里,年均增速在9% 左右。然而近些年来,尤其是从2012 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速不断下降。这既由于全球次贷危机的冲击波,也有新冠疫情和全球新一轮衰退的影响。经济潜在增速从2012年左右的近10% 降至现在的约5%。

面对这样的数据,很多人感到悲观,担心中国经济是否出了问题,是否还能按照过去的高增长进一步改革下去。因此,我们急切需要搞清楚如何才能提升经济增速,或者避免它进一步的下降。我们需要总结过去的成功经验。以前为什么做得很好?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绝大多数人会认同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头40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市场化的改革、投资驱动的发展战略、扩大开放与国际贸易、经济上财政分权等。为什么那些成功经验在当前遭遇了挑战,无法维持过去的高增长呢?部分原因是经济内在规律的作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再增加资本投入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会逐渐降低。例如,美国、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都经历过快速增长阶段,但在后期都出现了增速逐渐下降的现象。
此外,我们面临一些特殊的国内国际环境,包括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等。例如,房地产业过去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但由于2019年之后国家推行“三条红线”政策,旨在遏制房地产企业过高的债务增长,这导致房地产企业融资困难,投资大幅下降,进而影响了土地市场的拍卖,加剧了地方政府本就严峻的债务危机。同时,由于过去的房地产投资在我国整体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也导致经济中的投资需求下降得非常快,经济开始出现大幅度的增速放缓。
我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应对上述挑战的重要手段,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生产率可以简单理解为一种生产效率,它衡量了企业在相同要素投入下的产出能力。体现在宏观层面,就是一个国家整体的生产效率。为了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经济学家们采用了一系列的生产计量方法在宏观层面进行估算。生产效率的变化不仅反映了技术进步,还体现了创新能力和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
2为什么硅谷精英希望特朗普成为“美国的CEO”?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编译原文为Capital&Main
《为什么硅谷精英希望特朗普成为“美国CEO”》
科技精英的倒戈也与拜登在退选前提出的征税计划有关,他希望对未实现收益的资本部分征税,而这是压垮风投a16z创始人马克·安德森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主党)太疯狂了,他们显然想借此谋求巨额利益,”Palantir 联合创始人乔·朗斯代尔表示,“99% 的投资者都明白这将造成多大的破坏——它将摧毁我们的创新世界。”
特朗普承诺将放松监管,是吸引科技精英的另一个关键要素,这将带来宽松的反垄断执法环境,为“不受约束的企业增长”铺平道路。尽管这保障了巨头的利益,但长远看将会抑制公平竞争和创新。ITIF(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创始人阿特金森表示:“特朗普更像是一位‘CEO’总统,他倾向于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人脉来做决定,而不是通过繁琐的政府流程,譬如19次会议或四级备忘录来进行跨部门活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硅谷精英)会觉得,‘如果我们能与特朗普开一些闭门会议,我们的议程便可以落地’,这与哈里斯政府不同。”

特朗普对加密货币领域的示好也点燃了一些科技精英的热情,他承诺任命一位“建设未来、而不是阻碍未来”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暗示加密货币的监管将得到放松。尽管这会使加密货币投资者和企业家获得收益,却会让散户在已经十分动荡的市场上承受更大的风险。
硅谷里反对特朗普的力量也已集结起来,即一批觉得自己被“污名化”的科技精英们。“外界传言硅谷和科技行业正转向‘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甚至不只是右翼,而是右翼的分支,这让人感到沮丧。”他们担心,减税和放松管制带来的短期利益,可能会以牺牲长期经济健康和社会稳定为代价。正如库班所形容的,“科技精英已经到了想要自己控制世界的地步”。
3数字时代的就业风险分配:制度主义的视角
张顺 吕风光 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5期
当代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风险社会特征进一步凸显,甚至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21世纪以来的数字经济发展,使我们尤其深刻地感受到数字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和不安全感。
劳动力市场风险不断深化。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1999 年至2019 年,自雇劳动者群体占比由8.74% 上升至22.84% ;同时,2021 年个人经营、非全日制以及新就业形态等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 亿人,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性与风险性不断凸显。从理论维度看,风险社会学理论深刻分析了当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演化趋势。布迪厄认为“不确定、不稳定是21 世纪社会问题的根基”;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现代社会正从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本文从风险社会学的基本视角出发,从失业风险和收入风险两个维度,衡量劳动者就业风险并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而降低失业风险,但劳动者收入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则快速上升。这一发现可以解释为何近年经济发展增速放缓,而整体失业率并未发生明显上升,还有大量劳动者进入互联网新业态、非正规就业数量增加,劳动者职业流动速度加快、收入波动加大等现象。第二,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就业风险的不同维度具有相异的作用效果。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劳动者失业风险,但显著提高劳动者收入风险,呈现高收入高风险特征;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均能显著降低失业风险与收入风险。第三,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三类个体资本对就业风险的制度性作用大体上呈下降趋势,或者说化险性功能有所削弱。这一结论能够很好地解释“读研、读博热”及大学生入党积极性上升等现象。为应对数字时代不断加剧的就业风险,劳动者需要更为丰富的个体资本以有效规避就业风险。
综合上述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但通过技术系统路径直接影响就业风险,也通过影响制度作用空间进而影响就业风险的分化程度,并对就业风险的不同维度具有不同的影响,促使失业风险整体降低且呈收敛之势,但收入风险整体加大且分化程度有扩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