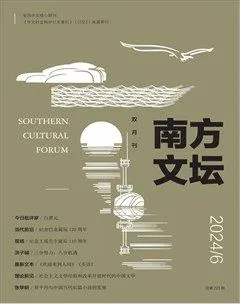社会转型、思想解放与1980年代现象级小说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创刊号以头条的形式发表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该文的发表石破天惊,迅速引发了共鸣,人们奔走相告。“读书”,这样一个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私人行为,释放出强劲的思想力,催促着“思想解放”向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转化①,同时也让民众的读书热情加速沸腾。1980年代现象级小说②诞生于一个“读书”的年代,其“现象级”的生成是写作者内在精神与外部世界互相激荡、交织互动之后的向外触着。对于写作者而言,现象级小说不仅仅是一种文本实践,更是其自我建设,与他者、与社会沟通的重要方式。凭借“一颗真诚的热烈的心”,写作者以情感内爆的方式重返现场,调动了民众的心灵世界,使得大量的情绪与感知涌出,整个社会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振。在情感共振中,现象级小说所具有的现实指向性,以及与广泛的普通民众的心意相通,又使得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互为参照,进而现象级小说所涉及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转化与呈现,现象级小说具有了中间物的性质。值得注意的是,现象级小说催生了大量相似经验图景与叙事样态的小说,而拥有虚构权力的写作者,并不愿意成为他者抑或自我的副本、衍生本,他们渴望“构造适当的富有意义的表达”③,与不断变化的经验世界保持对话,探索更多的可能。
一、“自我重建”作为出发点
处于转折期的写作者,普遍面临自我重建的问题,比如王蒙谈到“复活了的我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寻找我自己。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与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持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风格”④。但是相较于王蒙“返场”之初幸运地寻找到“意识流”,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创作主体意识,更多的写作者最初是以情感内爆的方式出现在民众的视野里。对于他们来说,最初的写作,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说话”,是将“内心话语”以“小说”的形式“说”了出来,有着浓烈的“我”的在场。不少写作者在步入写作之时并不知道什么文学技巧、方法理论,尚不能对写作应付自如,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作”。刘心武写《班主任》时“只是觉得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凭着一种真挚的责任心,一股遏制不住的激情”提笔书写熟悉的人物⑤。卢新华写《伤痕》“只是初步意识到文学作品应该真实地描绘人的感情和思想,作者应该交给读者一颗真诚的热烈的心”,从涌起创作冲动直至小说完成,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写作”,只是“一任自己的感情在纸上倾泻”⑥。同时代的其他写作者,陈世旭、何士光等也大抵如此。这种相对朴素、有着自我袒露性质的情绪表达,既是写作者自我重建的方式,同时也深深地触及了人的共有经验,是人在相似处境之下可以引申、拓展的,与生命经验紧密相关的问题。它外化形成了1980年代现象级小说最初的文本形态,一经公开,便从私人领域腾挪至公共空间,冲荡着人们的思想,使得原本就潜在的情感与经验得以照亮,混沌朦胧的心灵获得来自外部的指引,进而在人与人之间荡漾开来,扩散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彼此激荡,引发了限度之下“新时期”的群体性激动。即便某些带来感性体验的小说尚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其意义并未获得正式、公开的确认。大量情绪与感知的释放,使得整个社会沸腾,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振。
在情感的共振中,其“轰动效应”从外部近似单纯的刺激反应逐步渗入人的内心领域,成为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相创造,共同成长。写作与阅读的过程本身就是发现自我、自我与社会对话的过程,一度让写作者有了“哦!原来生活是这样,原来我对生活还有这么一段感受”的觉察⑦,周克芹构思《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自言“我是完完全全地参与了进去,我的感受在这些人们身上找到了寄托和归宿”⑧。高晓声也曾坦言《陈奂生上城》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自己⑨。对于读者而言,现象级小说亦是起着镜子的作用,人们阅读小说更倾于从中看到自己的情感与选择,陕西省电力设计院的工作人员王晓华写信询问“为何小说《伤痕》写的都是他家的遭遇,而他跟作者卢新华素不相识”⑩。有中年教员甚至直接闯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对古华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11相似的情感与经验得以被叙述激活了人的生命状态,同时也推动了社会恢复活力。
《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发表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由此引发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从此次讨论可以窥见,身处转折时期的民众普遍有着迷茫、焦灼、苦闷的心理,迫切地需要处理过去的经验,渴望得到理解,重新确认自我以及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现象级小说恰恰暗合了这一社会心理需求,其丰盈的情感使得淤积的情绪经由阅读而得到纾解。在相似经验被表达的过程中,人获得了被肯定、被看见之感,逐步对小说所提供的故事产生信任,意识到自己处于“共在”之中,那些携带私人性质的“丰富的痛苦”、焦虑、渴望同样也存在于他人,是属于人的共同情感。《班主任》《爱情的位置》《伤痕》等小说从“自我”涌动而出,之所以成为“现象级”,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其与更为广泛的人群产生了内在连接,这种连接又激活了人的感知感觉,召唤出民众自我表达以及表达他者的欲望,进而情感溢出,得以在社会流转。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表达”也意味着“自我”的获得,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在现象级小说带来的新鲜与刺激中,人获得了勇气与力量,从对故事的信任延伸为对自身的情感与经验的信任,进而逐步打破了既有的感知框架。尽管这种打破受多种话语因素的影响,是多方力量博弈之后的结果。换句话说,现象级小说鼓励与呼唤着“那个个人”,将人的注意力导向鲜活的经验世界,使得人在与人、与社会的联系中获得实在感,确认“我”的在场,发现“我”之所是。在“附近”的阅读分泌出熟悉的氛围,加强了小说所提供的经验的真实性,使得人们更加相信文本所构建的世界,进而在现实与虚构的互相参照中建立起新的认知。
不同的现象级小说,事实上,与经验世界有着不同的联结方式,提供了理解与处理经验的不同参照,以及言说自我与阐释自我的不同可能。在强烈的主体渗入中,小说中人物的痛苦与欢娱就是自己的痛苦与欢娱,小说中人物的言与行就是自己的言与行。当日常生活中遇到类似的情景,便尝试着用小说中的思想逻辑或行为方式处理自身的问题,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在文本经验的拓展与补充中,“属于我们自己的或我们希望属于自己的各种能力”12通过现象级小说得到了释放,并逐步有了实践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班主任》中张老师式的“启蒙”地位,也从文本空间延伸到现实生活,得到了确认。在民众的眼里,写作者成为拥有强劲力量的主体,几乎就是“超人”,能够解决生活、情感、事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源源不断的读者来信,向写作者倾诉心绪、寻求帮助,甚至将之视为“文化英雄”“人生导师”“青天大老爷”。写作者承担的不仅仅是写作的职责,同时也拥有了社会功能,其书写成为个人话语与社会话语双向动荡的中间物,获得来自民众的充分认可。而文学,依托着现象级小说,以“重”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二、经验的开拓与问题的转化
现象级小说生长在写作者真诚热烈之心与广泛人群的互相激荡之中,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发生联动,有着一定的公共性。其中所牵涉的问题,已经逐步溢出了文学自身的解释范畴,而与此一时期的社会语境、历史情势紧密相关。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评论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标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重新确认,以及“改革开放”作为历史大势的正式启动。受益于“思想解放”的鼓励与庇护,以及文学可以“讲述一切”的特殊权力13,1980年代现象级小说往往携带突破“禁忌”的色彩。关于“禁忌”,何平提示“禁忌不完全等于社会热点和公共议题,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国民心理、文化传统、人性底线和审美惯例等都可以是某个方面的禁忌,有人有边界有秩序就会有禁忌,有禁忌就会有突破禁忌的冲动和快感”14。实际上,对禁忌的突破就是不同经验样态与感受类型的不断敞开,这就使得现象级小说从源头上便携带“解放感”。像《爱情的位置》对“爱情”的触碰、《乔厂长上任记》对“改革”切入、《人到中年》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珊瑚岛上的死光》对“科学文艺”探索、《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对世俗观念的挑战等,是写作者对各种经验样态与感受类型的注意与发现,同时也是写作者以文学的方式转述现实需求,向国家与社会的小心试探。这种试探与时代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同构的。在不断求证、获得确证的过程中,经验域得到了不断的拓展,经验呈现出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而活生生的经验与感受正是意义生成的基石。
雷蒙德·威廉斯曾注意到“不是与思想观念相对立的感受,而是作为感受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思想观念的感受”15。也就是说,思想观念与感受并非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它们彼此联系、互相生发。转型时期,不同的话语力量事实上也处于自我重建的状态中,它们迫切地需要构建自身的合法性,建立或推广自己的意义体系,它们在“思想解放”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使思想观念发生变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正在生成或变动的思想观念“能够感受到”,因为“只有当个人周围流行的思想和价值被感知时,它(此处指情境,引者注)所提供的东西才对他或她的思想转变发生影响”16。而现象级小说提供了能感知的情境,联结了人的内心领域与公共空间。尽管这种提供或多或少受到既有思维框架的影响,也会存在认知的直接给予。
一方面,从文本本身来说,现象级小说构建了令人震颤的故事,使得“友爱”“善”“责任”等相对抽象的价值意识具有了可理解性,更新了人的视野与感受。另一方面,从文本所引发的整体性联动来说,大量现象级小说被改编成广播、影视、连环画等,对现象级小说的生成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17。由现象级小说改编的广播、影视、连环画等承担了“叙述”的功能,使得整个社会充盈着现象级小说叙述的“故事”。或者可以进一步说,这些改编之作,突破了文艺门类的边界,是作为“另一种现象级小说”而存在,进而与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发生联系,使得现象级小说在不同群体中流转、扩散,成为社会各个阶层广泛共享的文学样态。加之,现象级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强烈互动性,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扩大版的感性情境。
在这样的情境之中,现象级小说所提供的思想价值又进一步呈现出它的可感性,也即通过被改编的广播、影视、连环画等有了视觉、听觉等多方位的互动,通过现实生活中人具体的言与行变得可知可感。人所感受的思想价值已经不单单是文本本身所提供的,还包括了由现象级小说所延伸、转化、提纯出来的,那些与现实互动强烈,正进一步传递、生成的思想价值。而置身于其中的人,既是思想价值的感知者,同时也在被感知,参与了其传递、生成。有姑娘一直压抑自己的情感,直至《爱情的位置》引发热烈讨论,感受到“正面舆论的支持”,才勇敢地向暗恋对象表白,收获了爱情18。也就是说,通过现象级小说及其引发的轰动,人的爱情观发生了变化,并实现了从观念向行为的转化。通过人的具体实践,小说所提供的思想价值在现实生活中也形成了一个可感知的情境,而这种思想价值又汇入个人因子,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话语力量持有不同的动机,民众感受到的意义也有着一定的差异。对于主流意识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将“思想解放”导向现代化建设。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便谈到了“新时期”的价值判断标准,即“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在总结新时期文学之时,也是着重强调其“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积极作用19。写作者更多的是出于表达的冲动与快感,以及来自于与鲁迅、穆旦等人一脉相承的公共关怀与担当意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为关心与切身利益相关的现实问题。而文学期刊也有着自身的定位与价值诉求20。这就使得现象级小说从一开始就夹杂着多方话语力量的博弈,有学者留意到“《伤痕》的‘原意’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各种力量就介入了文本意义的生产。从修改和发表,到评论、研讨和争鸣,再到获奖和最终的经典化”21。现象级小说更像是具有了阿伦特所说的“桌子”的功能,使得不同的话语力量“围桌而坐”,激发了不同身份、立场的充分表达。这就为国家把握社会心态,调节社会情绪提供了途径。
“我写《人到中年》时,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考虑要‘揭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我只是根据生活中的感受,去写我熟悉的那些中年知识分子的理想、志趣、甘苦和追求。”22尽管谌容着意强调的是从自我真实的内心感受、经验出发,但是主流意识却注意到了小说中那些从个人出发,同时又超出个人的部分。小说中的陆文婷不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而是被释读为“新人”,提纯出“新人”的特质,汇入“社会主义新人”的谱系中,成为新时期的精神典范。像《乔厂长上任记》源于《人民文学》的邀约,且在邀约之时便指定了小说的方向“写实实在在的生活及人们在生活中碰到的阻力,要写出怎样克服这种阻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23。更何况,报刊、广播、影视等载体本身就属于体制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些“能够感受到”的价值意识,事实上,也受到国家意识的引导、筛选。
大量的价值意识,经由辨识、转译、引录,而被生发出新的意义,成为国家意识的一种表达。这种文学化的国家意识,又以“读者来信”“评论”“笔谈”“报道”“小说奖”等方式出现,向外推广为适用于更为广泛的普通民众的尺度,催促着原子化的个人向外敞开,走出自我,接近他人,重新确认或建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情感与经验、情绪与感觉的共享中,相似的经验与情感得到进一步融合,参与或被改写进正在生成的意义价值秩序中,催生着共同的事业。也就是说,现象级小说在被国家话语、社会话语、知识话语等多种话语力量充分共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现象级小说成为此一时期社会思想价值汇集的中心。在这样意义互相重叠、彼此关联的境况中,写作者自身也获得了赋权。反过来,这种赋权又形塑了写作者的良知系统与美学意识,激励着他们成为积极的行动者,以文学的方式转述社会需求,将社会问题文学化,进而文学世界与现实社会互为参照,又掀起一次次轰动。
三、“回到文学自身”:
重建文学与经验世界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当社会秩序步入正轨,国家的注意力逐步从意识形态建设层面转移开,与文学的关系没有那么胶着之时,经历了“轰动效应”,或者说,在“轰动效应”的另一边,越来越多的写作者激情消退,有了“下一步踏向何处”的困惑与思考。不断地向外开拓经验世界,事实上,成为写作者的一种蓄力或蓄势,它与写作者自身主体性的增益是一个二而一的过程,并逐步转化成“虚构”的力量,指向对文学可能性的进一步探索。对于重返现场的写作者来说,“轰动效应”自然有着它正面建设的一面,也即让写作者获得尊重感与自信心,激活了写作者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形成一股由外部而导向内部的驱动力。冯骥才便曾言及“刺激我写作的另一种力量来自读者的来信”24,来自读者的热情回应,使得冯骥才产生心灵的震荡,让他感受到“自己的写作”与普遍的素未谋面的他者“心灵相通”,进而领悟到“文学的意义”,获得了力的增益25。然而,另一面,“轰动效应”也会使得写作者自身沉溺其中,带来写作的惰性。不可否认的是,现象级小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写作者转化与提炼经验的能力,是对琐碎的、混沌的、处于生活流的经验的“问题化”。同时,现象级小说所具有的“开拓性”“创造性”,也催生了大量相似经验图景与叙事样态的小说。这些有着相同质地的小说毫无节制地涌出,使得写作逐步浮于表面,失去了其走向深处的意义。部分写作者甚至沉溺于现象级小说所带来的声誉,成为所谓的“文学活动家”。
而拥有抱负的写作者,并不愿意倚靠曾经获得的声望与权威,也不愿意重复光晕之中现象级小说已有的经验图景与叙事样态,沦为他者抑或自我的副本、衍生本。他们渴望沉入鲜活的经验世界,重新调动或锤炼把握经验的能力,保持“思想着”的状态。比如路遥,面对读者“人生导师”的角色赋予,一阵喧闹之后,路遥感受到的是惶恐,他发出感慨“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26。他将“写作”通约为“劳动”,意识到“劳动,这是作家义无反顾的唯一选择”,并为“能干些什么”而痛苦不已27。是维特时期的梦想,即“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28重新驱动了路遥,使得他获得勇气与力量,进而让路遥告别《人生》所分泌的暖融氛围,再次成为一个行动者,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写作。
事实上,在路遥之前,刘心武、冯骥才、蒋子龙等经历过“轰动效应”的写作者,就已经有了“下一步踏向何处”的思考。1981年,在给刘心武的信中,冯骥才提及与刘心武的长谈,“回想起来,谈来谈去始终没离开一个中心,即往下怎么写?似乎这个问题正在纠缠着我们。实际上也纠缠着我们同辈的作家们。你一定比我更了解咱们这辈作家的状况。这两天蒋子龙来信问我:‘你打算沿着《歧路》(《铺花的歧路》)走下去,还是依照《在人间》(高尔基)的路子走下去?’看来,同一个问题也在麻烦这位素来胸有成竹的老兄了”29。也就是说,“下一步踏向何处”成为此一时期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而对此一问题的思考伴随着对已有文学现象的质疑与分析,这恰恰意味着文学作为文学本身而被思考,写作者的创作主体意识的逐步强化,以及新的可能性的浮现。正如冯骥才所觉察到的,“作品获得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会暂时把作品的缺陷掩盖起来,时间一久,缺陷就显露出来。这样下去,路子必然愈走愈窄”30。冯骥才强调的不是不能写社会问题,而是从艺术构思角度强调不能“简单地一个个把问题抽出来写”,要让作品即使是脱离那些“社会问题”依然能保持自身的魅力,也即强调“写人生”31。
刘心武则在回信中点出,“问题在于我们有必要在新的形势下总结一下成败得失,踏上更广阔的创作道路”,进一步总结了冯骥才从“艺术角度”生发的思考,认为“注意写人生”即“把生活当作一个整体,充分认识到人的活动即人生的复杂性、丰富性、流动性,使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在作品中达到充分的‘立体化’”,并补充到“真实地反映人生,并通过作品引导读者看出人类生活的总发展趋势”32。面对像王蒙一样“重返”文坛的“真作家”,刘心武明显感受到了危机,他预感到《班主任》式“说真话”的写作路径“恐怕就很难在文坛上支撑下去了”33。相较于“轰动效应”所释放的表面诱惑,刘心武更倾于开拓文学的潜能。也正因如此,刘心武将自己从“轰动效应”所编织的束缚中释放出来,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在回顾个人的创作史之时,刘心武也是坦然地将《班主任》等一类相对朴素的自我表露之作视为写作能力不断生长的一个过程34。1982年,刘心武、李陀、冯骥才等人又以“现代派”回应文学“轰动效应”,发表了《关于“现代派”的通信》,引发“下一步踏向何处”的进一步思考。1983年,李陀和冯骥才还编选了《当代短篇小说43篇》,进行“新”的文本实践。
从上述可以看到,“变”成为写作者面对“轰动效应”的普遍共识,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想要回归文学本身,对“文学”进行重新确认,并以此充分占有经验世界,重新建立文学与经验世界的血肉联系,试图寻找到文学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平衡点。同时,对“变”的四方摸索,也逐步从对个人写作的驱动延伸为对整个文学发展的驱动。而写作者整体上生发“变”的行动,以及呈现“变”的形态之时,已是1980年代中期。此一时期,文学的整体氛围,以及所置身的社会场域,已经有了新的质地。拥有“虚构权力”的写作者,并不愿意在已有的话语图式中进行重复的表达,沦为意义象征体系中漂浮的符号,发出单质的声音。他们渴望调动想象力,在“怎么写”中重获“言语的力量”,寻求相对独立的叙述品格与精神立场,以实现限度之下更大程度的言说自由。同时,也试图呈现经验世界本身的复杂形态,给予新鲜的感知体验,锤炼把握经验世界的能力,培养人对丰富性、差异性的理解与尊重。诚如王蒙所言,“一切形式和技巧都应为我所用”35,“怎么写”只是作为一种方法。而“一切形式和技巧都应为我所用”,以及“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复杂化了的形式”36“人类生命是一种神秘和极度复杂的东西,是一种需要用思想能力和能够表达复杂性的语言才能接近的东西”37又生发出对“新”38的渴望。冯骥才便表现出对“新”的迫切需要,“没有新东西刺激我,我就要枯竭。新生活,新思想,新艺术,都要!”39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东西,形塑了写作者的感知方式与情感结构,使得文本呈现不同的审美特质,而具有辨识度的审美特质正是写作者彰显“自我”,是否具有“强力”的体现。《棋王》的独特性,便缘于阿城与时代潮流相异的知识结构、文化构成涵养了其特殊的感知与表达40。也就是说,文学形塑个人的感知方式与情感结构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尽管按照杜威所言,“我们不可能恢复到原始的淳朴状态”,但是他也提示通过一种“严肃的思维锻炼”可以获得“一种在眼睛、耳朵和思维上被培养出来的淳朴状态”41。从一定意义上讲,现象级小说正是思维锻炼的方法,构成了写作者“介入”的具体行动。语言与形式本身的使用也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成为文学与现实生活互相撞击、彼此激发的重要一环,具有了让意义迸发的重要作用。写作者们争先恐后地进行各种各样的艺术实践,引入新鲜的知识与经验,对“现实主义”进行梳理与转化,使得“现实主义”在1980年代有了新的“变奏”。而不同知识构成、情感结构、美学意识的写作者,其具体的路径以及作品本身呈现的审美形态也略有不同。
现象级小说作为一种与经验世界保持对话,在叙事与美学(或者说公共性与文学性)之间“思想着”的文学,实际上起着改变认知、重塑情感的作用。它激活了鲜活的“感”,唤醒了民众自我表达以及表达他者的欲望,使得情绪与感知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培养着个体对自身经验与思想能力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思想的“解放”。这种个体维度上的意义参与了正在生成的社会主要价值秩序,也因此,1980年代现象级小说深深地嵌入时代,成为勘探1980年代文学史、社会史、心灵史的重要刺点。
【注释】
①朱正琳认为“读书无禁区”是直接针对普通民众的“解禁”。参见朱正琳:《老字号的老》,载王世襄等《我与三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六十周年纪念集:1948—200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第87页。
②关于“现象级文本”的提出及其研究实践,可参见何平自2022年1月起至今,在《小说评论》主持的《重勘现象级文本》专栏。在专栏中,何平多次强调现象级文本的现实指向性,认为现象级文本强调“文学性”,“但它更重视文本和读者,文本和文学生活,文本和更广阔社会生活等等相关联的历史感和整体性”;指认文本的“现象级”,“会综合考量它所关联的——或公共议题、或读者参与、或审美哗变的公共性和社会性等等”;“无论怎么说,现象级文本应该是被国民广泛传阅,在相当大的读者群引起反响,成为文学的公共事件的那部分文学作品”。参见何平:《主持人语:时间之流的文本浮标》,《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③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王成兵、乔春霞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25页。
④36王蒙:《我在寻找什么?》,《文艺报》1980年第10期。
⑤刘心武:《班主任·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第254页。
⑥卢新华:《要真诚,永远也不要虚伪》,《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⑦王蒙:《漫谈短篇小说的创作》,载彭华生、钱光培编《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第350页。
⑧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创作之初》,《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⑨高晓声:《且说陈奂生》,《人民文学》1980年第6期。
⑩钟锡知:《小说〈伤痕〉发表前后》,《新闻记者》1991年第8期。
11古华:《闲话〈芙蓉镇〉:兼答读者问》,《作品与争鸣》1982年第3期。
12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161页。
13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5-6页。
1420何平:《主持人语:改革开放时代文学的欲望表达》,《小说评论》2022年第3期。
15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141页。
16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许殿才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5-6页。
17何平:《主持人语:时间之流的文本浮标》,《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18刘心武:《让我们来讨论爱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第82-83页。
19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209、208页。
21刘复生:《为什么非得是〈伤痕〉?》,《小说评论》2022年第1期。
22谌容:《写在〈人到中年〉放映时》,《大众电影》1983年第2期。
23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账》,载《不惑文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第52页。
2425冯骥才:《激流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第2、5页。
262728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载《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第5、7、7页。
293031冯骥才:《下一步踏向何处?》,《人民文学》1981年第3期。
32刘心武:《写在水仙花旁》,《人民文学》1981年第6期。
3334刘心武:《我是刘心武》,团结出版社,1996,第123、183页。
35王蒙:《王蒙致高行健》,《小说界》1982年第2期。
37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生活》,丁晓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47页。
38这种“新”,并非进化论意义上新旧之新,更倾于是有着区别性特征的“新”,套用冯强的话来说这种“新”侧重于“更新感知”,“只要有助于更新感知,它完全可以激活旧传统”。参见冯强:《文明论“文学性”发微》,《当代文坛》2023年第5期。
39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给李陀同志的信》,载《我心中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第41页。
40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22-23页。
41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26页。
(陈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