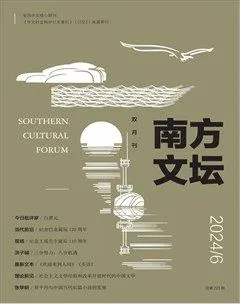从场所意识营造到自然的“复魅”
一、沉浸式交互艺术:科技时代的人文回响
在当今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艺术的表现形式正在不断地演变和创新。沉浸式交互艺术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至90年代逐渐走向成熟,是一种交叠时空、多重感知、融合媒介的当代艺术形式,具有偶发性与非现实性的艺术特点。这种艺术形式通过构建非真实的空间场域,在参与者体验的时段内令其可以短暂地逃离现实的束缚,使其意识与思想可以在其间自由驰骋。
沉浸式交互艺术借由打破作品场域和真实空间的界限,构建出全新的感受和体验,满足了观众对独特记忆共情的需求,成为当代艺术展览与公共艺术形式的议题焦点。但也正因这种艺术形式关注表现手段、注重体验效果的原生属性,其在人文特质上的不足渐而显现。我们亟须反思:沉浸式交互艺术作为一种极富前瞻性的当代艺术形式如何回应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永恒命题。笔者试图以美学理论指导艺术实践创作的论述形式,从人文性的角度切入,探讨通过重塑沉浸式交互艺术中的参与方式和体验过程,进而打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实现科技与人文的有效融合。作为一种依托于科技媒介的复合型艺术形式,沉浸式交互艺术以“沉浸性”、“交互性”与“跨媒介性”的三重特性见长,正是这些特性的加持使得沉浸式交互艺术打破了传统艺术中心化的表意方式,鼓励观众与作品建立共生关系。
沉浸式交互艺术通过精心设计的空间布局,巧妙地引导观众的游览动线,创造出一种探索与发现并行的感知体验。无论是在物理空间还是虚拟空间,沉浸性均被定义为一种多感官体验,它能够将观众“传送”至一个不同的时间、地点或情境。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提出的“沉浸”(flow)状态,是理解沉浸式交互艺术的理论基石。“当观众全身心投入当前情境,忽略时间流逝和环境因素,达到一种忘我的沉浸状态时,才能感受到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与思想交流。”笔者认为:沉浸式交互艺术借由其“沉浸性”的本源属性需逐步演变为一场心灵的深度旅行,在拓展感知边界的同时,赋予其重新审视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契机,进而令体验者获得思想的启迪。
与传统艺术不同,沉浸式交互艺术是在创造“行为”与“体验”。交互指代了一种交流的关系,而交流的主体是人;广义上讲,人与自然、人与事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皆可视为“交互”。交互性是沉浸式交互艺术的核心特征,它通过多元化手段和表现形式使观众成为艺术作品的参与者。交互性在改变观众与艺术作品关系的同时,拓展了艺术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在公共场域中,这种交互性不仅增强了个体的体验,还创造出一种集体的参与感。沉浸式交互艺术开启了集体互动体验的崭新向度,在带来集体感知的同时,引出了作品宏大叙事与群体观众之间一种微妙的“互文关系”。
沉浸式交互艺术是多重媒介的艺术表达,通过结合视觉、听觉与其他感官的表达营造出符合情境构思、具有强烈沉浸感与交互性的场景,激发观众的多重感官体验,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融入作品及其情境中。与传统艺术形式中透过玻璃观看架上作品的形式相比,沉浸式交互艺术消解了艺术展的“第四堵墙”①。它利用空间结构的开放性,创造出一种模糊边界的独特感知力,使观众不再仅仅是被动的观察者,而是艺术作品积极的共创者。这种跨媒介性的互动,不仅丰富了艺术的表现手段,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参与和感受方式,实现了感官的全面激活。媒介的多样性赋予了艺术多元的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使观众徜徉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奇幻之中,也令沉浸式交互艺术本身越发成为当代艺术中创新性和独特性的代表。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数字化浪潮的席卷,当代艺术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趋势。沉浸式交互艺术作品通过沉浸性、交互性、跨媒介性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全方位体验。然而,这类作品也逐渐显露出局限性。过度依赖技术和一味追求感官刺激的创作倾向,使得许多作品忽视了应有的精神深度,导致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和感官麻木。在这种艺术创作背景下,在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愈发渴望本真世界的回归。与数字模拟中的赛博世界形成鲜明对比,“自然”是最为原始、最为纯粹的语言。倘若沉浸式交互艺术以其复合型的手段,将“自然”作为创作的视角,在模拟自然体验、还原自然感受的同时,辩证性地引发体验者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势必会为艺术创作带来全新的人文性、美学性价值。沉浸式交互艺术的自然视角,是科技迷雾中奏响的人文哨音,它追寻艺术的本真,在科技与自然之间寻找平衡。借由这种方式,艺术家们不仅展现了技术创新,更传递了深刻的人文关怀,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再次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科技关系的契机。
二、场所意识与感官体验
场所意识中“场所”的定位,是相较于“空间”而言的,在海德格尔的著作《筑·居·思》中首次被提出。“场所”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象征着人们在其依附关系中的共有情感,具有相对封闭且较强的叙事属性。场所意识不仅囊括了场所自身的固有特征,也包含了人们对场所独特的“场所依附”(place attachment)。例如,人们对“家”这一场所具有强烈的依附感,而特定环境中的光线、声音、色调、气味等元素,也同样给予场所以清晰的勾勒。美国当代著名环境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在其论著《环境美学》一书中表示:“通过身体与‘场所’的相互渗透,我们成为了环境的一部分。环境经验调动了我们的整体人类感知系统,因此,我们不仅仅‘看到’周遭的世界;而是漫步其中,与之共同活动,并与其产生互动。”如此,对场所的营造是通过我们所处可感知范围内的面积、质量、体积、深度等信息,往往借由其存在状态、运动形式与我们的身体悄然相遇。同时,笔者认为场所意识在创作表达中应该作为一种“情感”的投射,叠加身体与场所的相互渗透感予以呈现。
在沉浸式交互艺术设计创作中,“场所意识”不应异化为某种场所经验的表达。当代较多艺术创作均尝试对自然进行数字化表现,这不应是简单的复现,而需要作为重拾对场所美好感知的尝试。人与场所之间的关联形成“联结的交点”(joint association),创作者由此会将“场所”视为人与自然秩序的一种整体融合。在这种融合关系之内,人与自然秩序是相互作用、互文往复的关系。自然秩序是有生命的主体,场景中的参与者通过自己的身体进入其中,自然秩序也像身体一样与参与者同在。
具有依附感的场所不仅在感官上提供了丰富的互动体验,更在精神和情感层面上建立了深刻联系。作品中艺术家尝试唤起观众对自然的亲近感和归属感。观众与场所逐步建立情感连接,进而激发出对自然和自我关系的反思。对场所意识的营造,不仅丰富了艺术作品的层次,也使观众在再现自然中感受到一种回归和共鸣。在诸多再现“自然”的沉浸式交互艺术作品中,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天气计划》无疑在知名度与艺术造诣上极具代表性。埃利亚松出生于冰岛,这里有着纯粹而本真的自然环境,喷泉、瀑布、湖泊众多,气候多变且植被丰富。这些自然和环境因素所带来的深刻感受,逐渐成为埃利亚松作品创作的灵感源泉,从而引发他对自然与人类共生关系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辨意识通过“沉浸式”的交互模式,产生了一种绵延不断的感受,深深触动观众的身心。
三、从静观美学的突破到自然复魅
早在20世纪60年代,艺术史中便提出了“观众参与”(viewer participation)的概念,这一观念催生了交互艺术的发展,使观众成为作品完成的一部分。从人文角度研判,笔者认为,交互艺术是“参与美学”在实践领域的一种延伸,强调了参观者在艺术品实现和接受中的角色。“参与美学”由阿诺德·伯林特明确提出,是对传统静观美学的重大突破。传统静观美学以艺术为主要审美对象,以人为中心,以视觉、听觉为主要审美手段。而“参与美学”无论在审美对象、审美手段抑或是审美范式上均有了极大扩展。美学与环境在其理论中需在一个崭新的、拓展的意义上被重新思考。“参与美学”强调自然语境的多元以及由此而生的感性体验的多元,主张消除主客体二元对立的传统束缚,倡导缩减人们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在“参与美学”的框架之中,审美价值呈现出一种弥漫性与持续在场性,所有感知形式的全面参与性则呈现了一种“联觉”②的状态。
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在其著作《审美经验现象学》中以“审美客体”“审美知觉主体”“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的和谐关系”3大部分阐释了“参与美学”的思想。这与交互艺术创作中主体(指代艺术家/创作者)、本体(指代作品)、访客(指代观众/用户)三者的内在联系不谋而合,也为交互艺术创作者针对三者辩证关系的内在理解提供了清晰的范式表达。在杜夫海纳与伯林特理论的交叉并行间,艺术作品无法单独存在,审美的知觉主体需通过呈现阶段、表现阶段和想象阶段的“进阶式跃迁”方能被感知。这些“参与美学”的思想对于交互艺术设计创作的逻辑性创建、情感化表达、体验感提升均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沉浸式交互艺术在结合主体、作品和观众的基础上,塑造了一种更为递进的审美体验,包含身体各感官的全方位参与,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实现了对静观美学的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身体化”取代了静观美学中的“无利害性”,“连续性”取代了静观美学中的“分离”。“沉浸式”交互模式强调了身体的全面参与和感官的充分介入,超越了传统的“如画式”鉴赏。身体图示不仅是在体验中建立的结果,也是在感知世界中对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在沉浸式交互的体验过程之中,空间、时间、体积、质量、色彩、光线、气味、声音、触感、秩序等要素共同作用,构建了多重维度的审美感知。以此,也引出了下文“连续性”的特征。连续性的突破在其交互方式不再是单方面的连续,而是多种维度和面向。在阿诺德·伯林特的理论中,他倡导多种连续性观念,尤其是“感官经验”的连续性和“感知方式”的连续性。“感官经验”的连续性是指在作品中,不同感官之间的体验是连贯的、相互交织的。“感知方式”的连续性指观众的感知不是片段式的,而是持续体验且连贯生成的。由此构建了一个完整且连贯的艺术体验范式。
以埃利亚松《天气计划》和兰登国际《雨屋》为代表的沉浸式交互艺术作品通过最纯粹的艺术语言带给观众震撼心灵的体验。回看这两件作品不难发现其作品强调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通过技术手段传达的人文渊涵。作品之间蕴含着对自然“复魅”的趋势。事实上,从对自然的“祛魅”到对自然的“复魅”是人类从驾驭自然到敬畏自然迈出的关键转向。“祛魅”源自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它诞生于工业文明时期,认为人是“度量世界、征服自然”的唯一尺度。这一思想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主宰了当时的生活秩序和精神文明。在“祛魅”中,自然失去了神秘感和亲和力,成为人类征服的对象。这种异化的生存方式,使人类生活的意义流于不断膨胀的欲望和物质享受之中。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发展时代,人们需要对工业文明时期自然“祛魅”思想做出重大跃迁。据此,“复魅”应运而生。
自然的“复魅”并非回归到对自然“赋魅”的盲目神化,而是对“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归属并栖居在自然之中,应对自然抱以敬畏之心。人类的创造性不应凌驾于自然界的创生力之上,而应合理地融入自然的生成过程之中。“复魅”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亲和关系的重建,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语境下,“复魅”是一枚需注入创作者血液中的觉醒药剂。
四、结论
沉浸式交互艺术作为融合科技与人文的前沿艺术形式,不仅突破了传统静观美学的桎梏,更需为科技时代注入崭新的人文内涵和美学价值。本文从场所意识和参与美学的理论观点出发,剖析在沉浸式交互艺术之中观众与环境的情感纽带,以及身体性与连续性的美学突破。这一创新性的艺术实践拓展了艺术体验,重新探讨了当代艺术的本质和边界,进而为创作和欣赏开辟了一种新的向度。
本文以自然“复魅”的视角,唤起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在技术主导的当代语境下,这一视角不仅是对传统自然观的创新诠释,更是对数字时代人文精神的切实思考和有力回应。通过将自然“复魅”理念与沉浸式交互艺术相融合,提出全新的艺术体验范式。这一范式结合了现代技术优势与艺术美学,唤醒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和亲近之情,为解除当代社会中人们对于自然的疏离提供了具备启发性的艺术解决方案。沉浸式交互艺术的美学实践尝试打破横亘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隔阂,呼唤、培育每一位参与者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创造者。
【注释】
①第四堵墙,原为戏剧术语,是指一面在传统三壁镜框式舞台虚构的“墙”。它可以让观众看见戏剧中的观众。
②联觉(Synesthesia)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σ<P:\南方文坛\2024年\2024-6\图片\11.tif>ν(syn),意即“共同”,和α<P:\南方文坛\2024年\2024-6\图片\22.tif>σθησι<P:\南方文坛\2024年\2024-6\图片\33.tif>(aisthēsis),意即“感觉”的组合,指“共同的感觉”。它表现为不同感官之间的感觉信息相互交织和关联。
(董瑀强,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陈娱,清华大学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