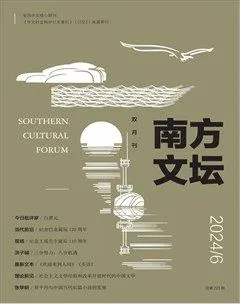在边缘处打量
白惠元是我的小师弟,他入师门时我已毕业工作,所以并没有多少共同研学的校园往事可供追忆。犹记得初次相见,是2010年秋天,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办的某个国际研讨会会场,有一个穿着浅灰色小西装的男生笑语盈盈地跟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他是陈晓明老师新招的直博生。其时,他还在读大四,应该是已经通过了推免考试,即将成为晓明老师名下的第一位直博生。起初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是个性张扬光彩夺目的那一个,而是在北京大学经常能见到的某一类男生,斯文清俊,温和安静。
后来听我另一位师弟刘伟说起,2007年,他作为一名博士新生参加中文系的迎新晚会,小白师弟作为本科新生担任了主持人,当他听到小白说“下面有请温(儒敏)爷爷……”时,瞬间觉得自己“老了”。可以想见,喊出那声“温爷爷”的小白当时是何等青春无忌。后来我在他的访谈中读到,尽管这位学霸一路以年级第一考入北京大学,但是在应试教育阶段仍然倍感压抑,直到大学才开始了迟到的青春期。青春的小白遇到了青春的北大,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我想北大是适合小白的,尽管学业的竞争依然激烈,但是“卷”绩点这样的事想必难不倒他。在自由的氛围中,他度过一段“最好的时光”,他不断培养、激发、探索着自己的各项兴趣与潜能,多方面的才能在这个大舞台上得到尽情地施展与发挥。
借用我师母陆波女士的评价:“小白真是没有浪费一点上天给他的才华。”迎新晚会上的表演或许只是牛刀小试,顶着文艺之星之名出道,他唱歌、编剧、演戏,样样尝试,样样在行。如今在网上还能看到他当年参加“北大十佳歌手大赛”复赛时的一段演出视频,在吉他手的伴奏下,他吟唱起张艾嘉的那首《春望》:
冬天已去,冬天已去
春天在睡梦里向我们招手
你再不要忘记神话里的童年的幻想
你再不要忘记那甜蜜的成长
你再不要忘记母亲怀里童谣的歌唱
有一天它将会再回到你身旁
较之原唱,小白的演绎突出民谣风格,更显疏朗,尤其是结尾那一串“啦啦啦啦”,既有忧愁而甜蜜的缅怀,也有朝向未来的畅想,每一句咏叹的仿佛都是歌者“虽迟但到”的青春啊。身着格子衬衫、牛仔裤,留着半长头发的他,身体随乐律轻轻摇摆,叠印着记忆(或想象)中的北大校园歌手的形象。
他对戏剧也投入热情。充满实验性和人文性的校园戏剧从艺术上和思想上滋养了他,有一段时间,戏剧创作甚至成了他的“主业”,他与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组成了“枫丹白璐”戏剧团体,这两位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他的谈话中。记得他曾发过他写的剧本给我听取看法,对戏剧基本门外汉的我自然提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只是感觉到他那时的剧作中已有对动物、性别、阶级等社会议题的自觉思考。他编剧的《ROAR!ROAR!》《末路狂鸡》等作品不仅在北京大学剧星风采大赛上斩获殊荣,还受邀参加校外的各种戏剧节。
运动场上也有他灵动的身影。他拿起球拍练习网球,随着球技的突飞猛进而成为北京大学网球队队员,经常参加校际比赛,得过名次。总之,无须再举例赘述,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小白已经把自己“养成”了一个北大式的文艺青年,一个妥妥的“斜杠青年”。
毕业后,他先是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做博士后,出站后入职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成为一名青年教师,2023年被聘为副教授。其间,他还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总之,一切看起来都是新一代青年学者、青年批评家的“标准”成才进阶路径。最近看他的朋友圈,在与毕业研究生的合影里,真分不清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他一身白T恤、短裤、球鞋,俨然是时尚男大学生的标准穿搭,简单、随意中也不乏精致。想想距离2010年与他初相识,14年时间已悄然流逝,让我不禁又陷入中年式感伤怀旧:时间真的已经过去那么久了吗?
这些年,我们分散在偌大京城的不同角落。京城居大不易,我们各自都搬过几次家,有时离得近,有时离得远。最近时,住处不过隔几条马路。这些年,我们见过很多次面,吃过很多次饭,甚至不时私下约会,交流近期“八卦”信息,兴高采烈叽叽喳喳,相互提供情绪价值,又或者针对某人某事冷嘲热讽,但皆无中心、无主题,只图一时爽,事后都如过眼云烟。我们也相互交换过秘密,但那涉及个人绝对隐私,“无意在此占用公共资源”。我们也许还谈论过学术?对此,我不是很确定。不过,小白提醒我,我们曾在十里堡的“漫咖啡”谈论他要写的论文,就是后来发表于《文艺研究》的那篇《哪吒之死:镜像、幻想与缝合——近年中国少女电影的文化症候》,文中论及我们都很喜欢的电影《七月与安生》。“我当时问你,题目究竟是该叫‘叛逆者之死’还是‘哪吒之死’,你说必须是‘哪吒之死’。”小白很肯定地告诉我。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终于提交了博士论文,连夜要来找我吃饭,以慰藉写博士论文时受的伤、吃的苦。谁不曾被博士论文折磨过、伤害过?作为过来人,我会心一笑,连声应允。他便大老远地从北京大学跑来找我。我们坐在十里堡北里路口的路边摊吃烤串,喝了饮料或是啤酒。我们聊了他的论文或者没聊?那晚的氛围照例是轻松愉快的,他满是解脱之后的轻松。当然,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神”,这篇论文后来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为他9年的北大求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认真地读他这篇博士论文,便是后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一个中国当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生怎么会选这么一个有些偏门的论题做博士论文?放在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这或许并不奇怪,尤其是在中文系,这种自由氛围更为突出,当代教研室的几位老师研究方向各异其趣,晓明老师更是出了名的宽厚包容。孙悟空形象学看起来并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但是正如晓明老师多年前就敏锐指出的,尽管“文学”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或是作为一门强大学科的存在遭遇了巨大的危机,然而,文学的“幽灵”正在其他文化类型中显现,不论是电影、电视、新闻报道,还是商业广告、娱乐节目,甚至是在高度“仿真化”的日常生活中,文学的“幽灵”无孔不入,文学性的思维和语言文本无处不在,想象的逻辑被消费的、娱乐的、数码的,乃至存在的规则暗中接纳。当小白的论述在小说、戏曲、影视、网络文学、动画、游戏、流行歌曲等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穿梭游走时,他事实上一直在敏锐地捕捉那只猴子的“幽灵”,它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媒介的转换中,呈现为不同的形象,询唤着不同的主体,他的论述致力于发掘形式与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研究方法,小白用起来得心应手。他熟练操练着福柯、詹姆逊、德勒兹、德里达、竹内好等人的理论,自如运用批判理论,条分缕析,行文潇洒灵动。
贯穿论文的问题意识是孙悟空形象再现与“中国故事”的同构性,这自然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小白也有诸多精彩论述。不过,最打动我的,还是其中最与己相关的部分——这个“己”是指小白,也包括一部分的我,毕竟相差了十余岁的我俩并不完全共有同一种成长经验和与之相关的“情感结构”。从中,我也更加接近了解了小白的那个“自我”。围绕全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当初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和后来保护唐三藏西天取经的孙悟空之间的形象断裂性,如何解释或缝合这种断裂,呈现出了不同的文化症候。在白惠元的读解中,今何在的《悟空传》试图论证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的必然性,他给出的答案是:成长。于是,“闹天宫”的孙悟空成为叛逆青春期,“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才是成熟状态,这是彻底取消了反抗的合法性。由此我也联想到小白的成长路径。
2014年3月29日,张曼菱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将北大学生的高考成功评价为“压抑的胜利”:“并不是你们真的比你们的同学优越,聪明,用功,有天才,有前途,你们才坐在这里。而是你们比你们的同学更能够接受压抑,配合压抑,与压抑你们的学校和家庭,老师和家长配合,服从,压抑了你们青春的个性,是这种对压抑的服从,是你们通过了考试机器,使你们得了高分,进了北大。”在小白的自述中,他也是靠着一定程度的自我压抑才考上北京大学的,所以他说,青春期在上了北大之后才开始。在兼容并包的北大校园,他开始摸索着“成为自己”,如前所述,种种光鲜亮丽的才华标识可能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那个真正的独立的自我的生成——在小白看似温和乖巧的外表下,其实埋藏着一颗叛逆之心。现代意义上的自我一定包含着向外的批判精神和向内的自我反思意识。在小白的成长路径中,社会机制的压抑看似无可避免,但反叛机制或者自我取消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选项。一如他当初是以一种“压抑自我”的方式完成发现自我与反思自我的论文,也一如当代学术机制这个庞然大物的压抑下,他以学术的方式去“反学术”。
论文讨论的是“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也是小白的自我超越。小白自有他的方法与策略。首先便是他从孙悟空那里学来的“七十二变”,尤其是“自我收缩”的“释厄之道”。小白在书中写道:“孙悟空自知‘不变大的’,却‘变作小的’,诸如各种飞虫,语气中还透着骄傲,可见,他的‘自我收缩’绝非被动策略,而是一种自觉的方法。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认为,取经师徒面对的困境更多是概念性的,而非物质性的,于是克服困境的方式也往往是抽象的:‘破除包容魔力的方法不是依靠自我扩张,反而是仰仗自我收缩。’面对困境时,孙悟空的‘自我收缩’具有东方哲学意味,这与西方超级英雄式的力量扩张是完全不同的,其背后的文化逻辑差异也就更加引人深思。”这令我想起小白最喜爱的波兰网球名将A.拉德万斯卡。在当今世界女子网坛,她不以力量著称,却因超高的球商和充满技巧性的打法,被人称为“Hot shot女王”。我不打网球,也便没有机会一睹小白在球场上的风采,但想来,他在球场上可不就应该是这副模样吗?小白的收缩怀柔之法与聪慧机敏之心,使他尽管寄身在这个压抑机制内,却仍然保持了本真的批判力与反思性。
这就是小白。
他总是站在边缘处打量、观察、思考。小白最新的论文以青蛇形象为主题,经由被主流话语压抑的“妖话”,去分析一种边缘性的话语生产,从而提出了所谓“妖怪政治学”。这无疑是他对自身立场位置的自觉表达与学术推进。作为一个兴趣广泛且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斜杠青年”,小白显然不会满足于单一的工作、单一的职业乃至单一的社会身份,他不断地跨界、破圈,去实践他所钟爱的德勒兹的“解域”。他也不会安于炮制那些四平八稳的论文,仅为稻粱谋,为职称谋,他不能忍受没有创造性的简单重复,不能忍受脱离了感性经验与本真动机的“学术”。同时,他对消耗性的“内卷”也保持着一份警醒。我想,小白的“道路”或许不是主流(他也未必想成为“主流”),却一定是年轻一代学者可以参考的重要方向。
(饶翔,光明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