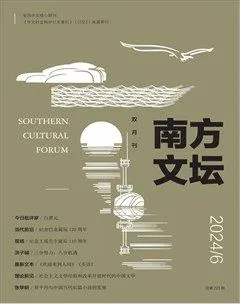从历史到文学
一、小说不是历史的文学改编本
“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新旧两代人的冲突为框架,代表父辈的高老太爷、叔叔们是没落的守旧者和残酷的压迫者,觉慧、觉民等新一代青年是反抗者和革命者。此外,还有两个群体:梅、瑞珏、鸣凤、蕙等牺牲者,女学生为主体的同盟者。后者是觉民、觉慧等人的同盟军,渐渐成长为“新青年”,在小说中承担同样的输出作者声音和价值观念的职责。“激流”世界中,新生力量取得标志性胜利便是女学生的成长、独立甚至冲出旧家庭。
“激流三部曲”中的“女学生”以琴、淑英、淑华三个人为代表,她们都是大家庭中的“小姐”,通过抗争获取个人自由。三人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差异,成为“女学生”受到的阻力也不一样:琴,通过抗争和坚韧实现个人目的;淑英是在觉民兄弟的帮助下逃离大家庭;最年轻的淑华,变成女学生则是水到渠成……巴金通过三位旧家“小姐”成为“女学生”的经历,写出五四前后中国社会观念的变化和女性解放所走过的道路。
“琴”是“激流三部曲”中贯穿始终的人物,她在家庭中的身份是高家姑妈的女儿、年轻一辈的“表姐”;她的社会身份是青年学生,“在省立一女师三年级读书”①。在小说中,她主要承担四重叙述功能:第一,争取个人进一步受教育的权利,由一位“女师”的学生,想进一步进入男女同校的“外专”,接受更为开明的教育。第二,争取个人的婚姻自由,与觉民从自由恋爱到举办新式婚礼。第三,与觉民一道,从事社会团体的活动。第四,在家庭中,作为其他年轻女性的启蒙者、引导者而存在。借助于琴、淑英、淑华的经历和视角,巴金笔下的“女学生”表达出这些具有五四精神特征的行为,如主张男女平等,要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反抗父权,争取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这些都是巴金通过人物所表达出来的一些价值和观点,熟悉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的人不难看出,它们并非来自巴金个人,而都是五四前后讨论比较热烈的社会话题。
“激流三部曲”如实地传达了五四时代知识精英的启蒙主张,是这个时代的忠实传声筒。它有着明确的历史纪年、具体社会运动为叙述背景,再加上内容与作者本人家族故事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顺理成章被当作自传体小说,以致让不少人认为它的文字就是纯粹的写实文本。小说中对女学生的叙述,与中国现代女性解放的道路基本吻合,很多细节其来有自。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方法对于文学研究的渗透,对于《家》《春》《秋》这样具有年鉴意义的作品又有了另外的研究视角。如《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中,作者试图“重新建立巴金小说中的戏剧性故事和激发了小说创作的真实城市生活间的联系”。由此认为:“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不断影响着人们对五四时期的中国的认识。它仍然是对20世纪初的几十年中‘父权制家庭’和‘传统中国社会’最有力的描写。……作为小说家,巴金创造了引起广泛共鸣的鲜活角色。他成功地用富有情感的叙述方式展现了历史时代,同时还创造出很多令人同情的角色,这些都不断地吸引着读者。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的‘激流三部曲’也生动鲜活地描写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冲突,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但是,作为引人入胜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必然简化了历史,特别是简化了那个时代中国城市变迁的多面性。”②这个“但是”,是由历史学的原则来评价“引人入胜的小说”,这把尺子用得恰当吗?
将文学作品作为历史或社会学文本加以研究,是近年学术界较为热衷的方式,比如从《水浒传》中看宋代社会世俗生活,从《金瓶梅》中看明代人的消费等,这些研究都是将虚构的小说作为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素材和实证材料,从而扩大了它们的研究范畴。然而,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这是否大大简化作品的内涵,削弱了文学的想象力,缩小了文学功能呢?仿佛一本文学作品其作用不过是一份高级社会文件。这种研究思路的进一步发展是有的学者以小说中的细节与历史史实相衡校,比如有研究者注意到巴金修改《家》中删掉小说中提到王尔德的《遗扇记》,小说表现的那个时期的《新青年》在成都尚不流行,人们还不知道王尔德和《遗扇记》,原来那么写,是作者犯了“常识性错误”。当时,人们根本就看不到中文版的《复活》,巴金便让觉慧去读英文版。研究者又质疑:在成都能买到英文版的《复活》吗?一个“外专”二年级的在读生有阅读它的外语水平吗?吴虞任教成都“外专”,《家》中给提前了一年。男女生同台演出《终身大事》,也被作者提前了几年,“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③。于是,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由时间叙事的混乱性,再延伸到历史叙事的混乱性,这便是作为现代文学经典的《家》,始终都难以消除的巨大缺憾。”④还有很多类似的研究,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原型探究,反过来解读小说中的人物。——原作者尽管小心翼翼处理某些细节,还是左右都是错。在这些言之凿凿的论述中(都是有实证依据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被强行遗忘了:这本是小说的虚构世界,很多现实世界的逻辑在这里可以是被打破和重组的,作家不一定要处处对位历史,反而有权建构小说中的历史世界。小说中的世界是由作者以文本构建起来的,它并不能等同于现实世界,即便“历史小说”也并非严丝合缝的历史事实的文学“改编”。手执《三国志》去说《三国演义》“太离谱”,虽然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但未必这是原作者“一个天大的笑话”,毕竟,读者和研究者还得尊重小说中的“现实世界”的独立性和自足性。
其实,巴金自己已主动为某些研究者提供了批评炮弹呢。在《家》的第十二章,提到《前夜》时,巴金特意加了一个注:“《前夜》,屠格涅夫(1818—1883),沈颖译,这个译本本是1921年8月上海出版的,我在这里把它的出版提早了十个月的光景。”⑤也就是说所谓的“时间叙事的混乱性,再延伸到历史叙事的混乱性”,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作者已经留意到这种时间的错位,他没有弥合,为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内心发展的需要,有意“提早了十个月”。文学没有义务与历史百分百对位,它不是历史的文学改编本,而是另外一个层次上的艺术。巴金曾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是在写小说,“不是在拍纪录片”,举例便是小说中的大哥觉新的结局与现实中原型人物不同:“我曾经说过觉新是我大哥的化身。我大哥在一九三一年春天自杀。这才是真的事实。然而我是在写小说,我不是在拍纪录片,也不是在写历史。”⑥在另外的谈创作的文章,巴金认为:“屠格涅夫在《父与子》里面记错了人物的年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面也有把时间弄错的事。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去改正这些‘错误’,而且那两部伟大作品也并不曾因此减色。我即使在这些小节上花了很多功夫,也不能使我的几部作品成为杰作。一部作品的主要东西在于它的思想内容,在于作者对生活、对社会了解的深度,在于作品反映时代的深度等等。”⑦这里的“主要东西”,其实谈到了文学作品欣赏的核心到底在哪里,我认为有必要:将文学文本作为文学来研究的问题。——这不是绕口令,也不妨碍一个文学文本作为其他功用而被研究,但是笔者想强调把小说作为文学文本来解读始终是阅读、欣赏、研究小说的根本出发点。即便将文学文本移作他用,比如采取所谓的文史互证的解读方式,也应当注意边界,不可过度阐释,以免产生对小说美学和文学创作规律的伤害。
二、文学,在历史框架的外逸之处
从小说艺术而论,沦为“传声筒”的小说并不高明。的确,仅仅简单地将历史事件或相关细节搬到小说中,写不出好小说。“激流三部曲”能够打动一代代读者,必有他独特的魅力,而不是简单的“传声筒”。巴金的能力在于他把这些时代的声音融进了人物的行动、言论和观点中,形成了富有情感富于表达力的情节,或者说,作者将历史的声音人格化、故事化,并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物命运之中。从历史到文学,逐渐看清的是一个个具体的面孔,一个个更加清晰和独特的人物面孔。由此,再反观“传声筒”的作用,它反而体现出巴金敏锐的历史感和巨大的社会概括力。从家庭出发,新与旧的冲突,父与子的冲突,婚姻,爱情,家庭,青春,等等,这些在五四时代中最为人们期望的话题,小说中都有涉及。“女学生”这个话,它既是那个时代先锋的、时尚的、为社会所关注的话题,同时也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女性谋求解放的思想成果的积累和显现。这是一个焦点问题,而且还在延伸、辐射,巴金抓住这些,表现在作品中,无疑会牵动社会各层面尤其是“新青年”们的关注。巴金的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是这样,主题虽然简单,却鲜明,针对性、概括性强,与那个时代的读者关注的呼应感也强,这样的小说能够得到青年最热烈和最迅速的呼应也就不奇怪了。
达到这个效果,不是占了题材的便宜,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创造力,他得有能力把那些抽象的观念自然而然地编织在他的故事之中,形成完整的叙述编码。这不是简单的观念的传达和集合,作家要有相当的故事编织和叙述能力,关于女性的那些价值观念,通过琴、淑英、淑华等女孩子的人生和命运表达出来,它们融在她们的生命和情感中,就不是漂在水上的油,而是融入水中的盐,水乳交融才有感染力。文学的魅力恰恰在此,它既容纳了价值、观念,历史、现实,又有逸出的部分。逸出常规之处,正是作家匠心所在。
以对于琴这个人物的叙述为例。那些提供给学者做思想分析的历史声音传达部分,是一部小说构成的基础,而一部小说精彩之处,恰恰是这基础未能容纳的溢出部分。比如,作者没有把琴写成一个作为观念符号的女英雄,反而真实地表现琴的犹疑、软弱和怯懦。琴的奋斗和抗争,都面临来自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习惯思维的压力,加上再顾及守寡多年的母亲张太太的感受,很多时刻,她更是难以做到“一往无前”。剪发,在观念上琴早就接受了,但是在行动上,她总在观望。许倩如的勇敢让琴自惭形秽,却难以打消她的顾虑,以致质疑自己:“我的确是一个没有勇气的女子。我自己建立了一个希望,我下了决心要不顾一切地向着那希望走去,可是一旦逼近那希望时,我却有点胆怯了。顾虑也多起来了。便不敢毅然前进了。”她想到母亲:“我想她苦苦居孀把我养育成人,而且平日又是那样地爱我,体贴我,到了如今她应该享福的时候,我反而给她招来更大的苦痛,如社会的嘲笑,亲戚底责难,她自己底希望底破灭。这个打击太大了,她实在受不住的。为了她我宁肯牺牲了我自己。”这“牺牲”的逻辑,岂不是与觉新同出一辙?然而,觉新又是她们平时劝慰和批评的对象。在强大的五四话语下,作者还为琴保留了一丝“私心杂念”,实属难得。这种难解的矛盾,让人物更真实、生动,它们也增强了小说人物内在的张力。
兵荒马乱时,作者写到琴的无助和绝望,并特别强调,新青年并没有天赋神力,跟其他一样“没有力量”:“这时候什么新思潮,新书报,什么易卜生,什么爱伦·凯,什么与谢野晶子,对于她都不存在了。……她疲倦了,她绝望了,她这时候才开始觉得她跟梅、瑞珏这些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她实际上是跟她们一样也没有力量的。”“……她看见了自己的真实面目。……然而这时候她才发见自己是一个多么脆弱的女子。”⑧对于未来的前途,琴总归还要寄希望于觉民——从女权的角度而言,“女权”居然要依托男权而存在,这是对女权的伤害,然而,这是赤裸裸的现实:“她相信觉民,而且也明白觉民是在为她打算。”⑨这个寄托会不会像鸣凤的梦一样渺茫呢?
对于琴的现实处境和羁绊,作者叙述得比较充分,而不是将她从尘世间超拔出来,使这个人物逃离符号化的先天预设。琴没有父亲,是在寡母带领下生活,这样父权的控制比较弱,如同丁玲《母亲》中的曼贞没有丈夫,少受夫权控制一样。琴的母亲也说:“你父亲早死了,剩下你一个,把全部责任都放在我的肩头上。我不曾要你缠过脚,小时候就叫你到舅父母家里跟着表兄弟们底先生读书,后来你要进学堂,我又不顾一切地把你送进了学堂。”⑩琴温柔娴静,没有张扬恣肆的革命面孔,反而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与长辈的关系比较融洽,容易为各方面所接受。琴以自己的言行让那些开明的长辈觉得“女学生”并非人们传说中的洪水猛兽,觉民的继母周氏说:“我觉得进学堂并没有什么不好。譬如你琴姑娘,你进过学堂你就比别人懂事情。说老实话,我素来就喜欢你。可见你进了学堂也并没有学坏。”11在琴的身上,甚至能看到中国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一面:
“你不要急,等我慢慢讲。”他(觉民——引者)忽然想起一件事又换过话题含笑问道:“你明天不走了。你说过明天亲手做菜请我‘消夜’,算不算数?”
琴温柔地笑起来:“当然算数。”她充满爱情地小声说:“为了你我还有什么不肯的?”12
当然,巴金对于“女学生”的叙述和思考并非止于琴,在他丰富的创作中写到各种类型的“女学生”,并就她们从“家”里走出来、走到社会上又如何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尤其是抗战后期的创作中,巴金的作品涉及女性解放过程中不能回避的诸多社会问题,比如经济独立、职业选择、工作与家庭关系等问题,也对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等话题进行了反思。这些问题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本文想通过巴金笔下“琴”这样的“女学生”形象之塑造,探讨在此背后的小说之叙述策略。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琴这个人物在表面上是由两个层面构成的,一是来自她生活历史的时代声音,她是这些价值观念的承担者。二是来自一个人的人性的特点,她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个独立的人物。
三、巴金创作中的观念性统摄
“女学生”来自哪里?
不仅是女学生,“激流三部曲”中的年轻一代的女性,很难在巴金家族的现实生活中找到明确而清晰的原型。“在女人方面我也写了梅、琴、鸣凤,也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也有三个不同的结局。至于琴,你还可以把她看作某某人。但是梅和鸣凤呢,你能够指出她们是谁的化身?自然这样的女子,你我也见过几个。但是在我们家里,你却找不到她们。”13对于可以看作“某某人”的“琴”,巴金又强调:“琴出现了。不,这只能说是琴的影子。……我知道我们那样的家庭里根本就产生不出一个健全的性格。”14他的现实生活中最多只能找到“琴”的“影子”:
这是我的一个堂姐的影子,我另外还把当时我见过的少数新女性的血液注射在她的身上。我这位堂姐就是我在前面提过的三房的六姐。在我离家的前两三年中,她很有可能做一个像琴那样的女子。她热心地读了不少传播新思想的书刊,我的三哥每天晚上都要跟她在一起坐上两个钟头读书、谈话。可是后来她的母亲跟我的继母闹翻了,不久她又跟她母亲搬出公馆去了。虽然同住在一条街上,可是我们始终没有机会相见。三哥还跟她通过好多封信。我们弟兄离开成都的那天早晨到她家里去过一次,总算见到了她一面。这就是我在小说的最后写的那个场面。……可是环境薄待了这个可爱的少女。没有人帮忙她像淑英那样地逃出囚笼。她被父母用感情做铁栏关在古庙似的家里,连一个陌生的男人也没法看见。有人说她母亲死后,父亲舍不得花一笔嫁女费,故意让她守在家里,不给她找一位夫婿。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见到了她,她已经成了一个干枯的“老太婆”了。其实她还不到四十岁。我在小说里借用了她后来写的两句诗,那是由梅讲出来的:“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她像一朵没有盛开就枯萎了的花。她那一点点锋铓终于被“家庭牢狱生活”磨洗干净了。她成了一个性情乖僻的老处女,到死都没法走出家门,连一个同情她的人也没有。15
琴的性格、命运绝不是这样,作者仅仅借助于“一个堂姐的影子”,琴并非像高老太爷和大哥觉新来自一个完整的人物原型,反而是“当时我见过的少数新女性的血液注射在她的身上”。更有意思的是,《家》中所写的觉慧与琴清晨告别的场景,巴金记忆中是与这个堂姐“总算见到了她一面”,事实是,堂姐过于伤感,没有应声出来跟他们相见。这是巴金翻看大哥1924年3月2日的书信才找到的确证16。——由此也证明了,作家在写作中记忆、想象和叙述预设经常交织在一起,难分彼此的,这本来是小说家惯用的手法。质言之,琴这个人物根本上来自作者的创造,而非现实中某个具体的人。巴金在另外一篇文章还说道:“到了《春》和《秋》,琴就完全是虚构的人物了。但是她的性格已经形成,她的影响逐渐在扩大,她可以靠自己活下去了。……我很想把我青年时期见到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全加在她的身上。但是她不需要。她仍然是一个平凡的少女。”17很显然,作者还试图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更多美好的情感。
《春》中的淑英也是“虚构的”:
我当初计划写的那本小说并不是《春》。淑英的故事是虚构的,连淑英这个人也是虚构的。我所说的“真实的故事”是我在日本从一个四川女学生的嘴里听来的。这位四川姑娘有一次对我谈起她自己出川求学的经过,她怎样跟她父亲进行斗争。她自杀未遂,逃亡又被找回家,最后她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又得到哥哥的帮助,顺利地离开了家乡。她的话非常生动,而且有感情。我说我要把她的故事写成长篇小说,她并不反对。18
借用了一个听来的故事:“应当首先提到的人是淑英和蕙。……这两个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我也并非完全无中生有,凭空创造。我在我的姐姐妹妹和表姊妹们的身上看到过她们的影子,我东拼西凑地把影子改变成活人。”19从“影子”到“活人”,依靠的是作者“东拼西凑”(提取,综合)。他还提到一位“四姐”,被二叔嫁给成都南门的首富的儿子:“淑英可能就是我那位堂姐。其实论性格我的四姐完全不像淑英。在我的记忆中四姐好像是一个并不可爱的人。但是关于四姐婚姻的回忆帮助我想出来《春》的一部分的情节。从这里我创造出周伯涛这个人物,我也想出了高克明的另一面。”“淑英不是四姐。但淑英的父亲高克明却是我的二叔,也就是四姐的父亲。”20现实生活里的鳞爪被作者组织起来,才有了一个独立的作品人物。他们一旦脱离作者之笔,便很难再与现实一一对应起来,这才有作者这样的交底:“淑英可能就是我那位堂姐。其实论性格我的四姐完全不像淑英。”
统观巴金的自述,那些敢于反抗旧家庭、充当时代先锋的新女性,在巴金的现实家庭中很难找到明确的原型。那个时代的旧式大家庭中,很多女孩子只能在家塾中读书,很少有机会去社会上的新式学校,完全走出大家庭在社会上独立生活的更是凤毛麟角。出生于1897年的苏雪林,比巴金大七岁,她的求学经历略早于“激流三部曲”中人物生活的时代,但是她付出的代价与小说中所写的背景大体一致。1915年,为报考安庆省立初级女子师范,苏雪林“这不算是请求,简直是打仗,费了无数的眼泪、哭泣、哀恳、吵闹,母亲虽软化了,但每回都为祖母或乡党间几位顽固的长辈,轻描淡写两三句反对论调,便改变了她的初衷。愈遭压抑,我求学的热心更炽盛地燃烧起来。当燃烧到白热点时,竟弄得不茶不饭,如醉如痴,独自跑到一个离家半里名为‘水口’的树林里徘徊来去,几回都想跳下林中深涧自杀……”——回到巴金的创作上,可以总结一句:他作品中的“女学生”多出于虚构,为巴金的创造。
通过“女学生”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领略巴金的叙事策略:记忆和观念的结合。前者比较直观,尤其是巴金经常给人以在强烈的情感驱动下完成创作的印象,他的自我表述也很多。巴金另外一面却很容易让人忽略,即他还是一位观念性很强的作家。他不断地提醒我们他有“信仰”,信仰是什么?它不仅是作家的灵魂,而且也是他观察、叙述世界的视角和出发点,这种观念也会改写个人记忆,以服从整体观念的需要。即便巴金激情燃烧下的创作,他创作中的方向、视角早已在“信仰”影响下有了具体的指向。这是一种隐含的结合和隐形的力量。而无政府主义长期以来不为社会所容,巴金本人闭口不谈,这就造成不少读者、研究者只看到巴金作品的外表,看不清它的内里。其实,巴金对社会早就有明确而系统的看法。1930年7月,巴金还出版过一本《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的政论著作,虽然巴金曾说这部书中的理论多袭自国外的革命家,然而,它署名“芾甘著”而不是“芾甘译”,这种高度的“改写”,至少浸润了巴金对这些理论观点的认同。该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今日”,写的是他对当前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全面批判。内容涵盖工钱制度、法律与政府、失业、战争、教会与学校、专政与革命,以及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历史。第二部是“安那其主义”,阐释了作者对此的全面看法。第三部是社会革命,这是作者主张的以安那其主义改造社会的主要方式,包括工团革命的基本原理与实行、社会的消费和生产、革命的防卫等内容……尽管巴金也曾一再强调,文学创作不是信仰的宣传,但是如果说一个作家的信仰与他的创作完全绝缘,这现实吗?作家的信仰至少会影响甚至决定他认识世界、观察生活的视角。这是潜伏在作家创作中的先天基因。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和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等人的理论著作,充分证明,巴金开始文学创作之时,已经对身处的社会有着非常明确和成熟的看法,包括对社会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指向,比如他提出的理想的“安那其社会”的蓝图:
在安那其共产主义的社会中:——
在政治方面,人不承认任何权威,也没有什么权威来压制,人强迫人。政府是废除的了;
在经济方面,谁也没有权利把生产分配的机关以及生活的必需品占据为私有,不许别人自由使用,自己享受。私有财产制是废除的了。
简单地说安那其共产主义的意义乃是废除政府,废除强权及其所有的代表;共同管理社会财富,各人可以自由地,平等地参加共同的工作以谋共同的福利。21
巴金的社会观念不是朦胧的,而是具体的,有理论依据的,有行动措施。在现代作家中,有这样的明确的社会纲领和看法的并不多。后来,巴金有意识地回避这些问题,随着时间推移,读者和研究者对此也越来越陌生,巴金创作中众多独有的观念便淡出人们的视野。于是,人们对巴金作品的认知中只有热情、悲情、忧郁这些感性的部分了,完全忽略了巴金是一个观念性极强和拥有理论自觉的作家。“激流三部曲”中有人们可见的作者个人情感记忆,也有潜伏着对于家庭、社会、人性的观念性叙述和塑造。
由此,可以说巴金笔下的很多在生活中找不到原型的人物,更大一部分来自作者的观念,观念塑造人物的灵魂。在谈到《爱情的三部曲》中李佩珠这个人物时,巴金说:“李佩珠这个近乎健全的性格要在结尾的一章里面才能够把她的全部长处完全显露出来。……这个妃格念尔型的女性,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写她时,我并没有一个‘模特儿’。但是我所读过的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22“近乎健全的性格”“妃格念尔型的女性”,他明确交代出自“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是阅读和研究,让他建立起对某一类女性观念性的认识,它们反过来带动他去构建笔下的人物形象。异国女革命者的精神、气质,成为他锻造他笔下的新女性的思想和形象的资源。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其中女主人公叶莲娜不顾世俗眼光大胆追求爱情,这样的性格和举动,经常也被巴金赋予他笔下的女性。屠格涅夫说:“像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类人物都是……新生活的预言者。”23他笔下的女学生也是时代的预言者。巴金还为俄罗斯十位女革命者写过一本传记《俄罗斯十女杰》,里面都是他敬佩和大力倡扬的女性,她们的经历、个性、主张也默默化作巴金作品中女性的人生底色。比如谈到苏菲亚·柏罗夫斯加亚,巴金说她是“一生最敬爱的人中的一个光荣的女杰”,总结她的性格:“苏菲亚诚然是一个温柔可亲,而且有一颗爱人类的黄金似的心的女子;但同时在做事的时候,却又是一个阴谋的天才。她是下列三种特性的混合体:一,深远广大的能力;二,热心激烈的性情;三,钻石一般的意志。”他还引用克鲁泡特金的话,赞扬苏菲亚“热烈的勇气、灵敏的智慧与仁爱的性情”24。在巴金的作品中,我们不难找到这类女性的身影。
就表现力而言,琴等人算不得“激流三部曲”中塑造得极为传神的人物,在复杂性方面,尚显单薄,尽管作者极力挖掘她们的内心,可是人物基本上都是“扁形人物”。这也是观念性创作的硬伤吧,观念性的写作要获得丰满的血肉是需要作者有着理性与感性间的平衡力的。在这一点上,巴金做得不算成功,他笔下的女性,理想性的成分往往大于现实成分,始终没有达到一种自由的状态,这是观念束缚了她们自由发展吧。
四、家族小说,还是国族寓言?
由“女学生”探讨巴金的叙事策略,可以进一步追问:“激流三部曲”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作者写它的动机是什么?不妨以《家》为中心,重探这个问题。
用人们习惯的观点来回答,《家》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家族小说,有人还把它与《红楼梦》、与福克纳的家族小说做比较。但是,从巴金叙事策略的角度看,我更倾向于将《家》看作是以家族小说为外壳的国族寓言。《家》以及它的续作《春》《秋》,一方面写了一个在历史转换时期的大家庭走向衰败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家”带有强烈的隐喻性,隐喻着一个专制王国的最终灭亡。无论是描述现实中的“家庭的环境”,还是阐述小说《家》的主题,作者曾反复使用同样的词句:“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25“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是害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我的确憎恨过他。”26“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更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拿旧礼教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27“家”的意象是“黑暗”,“黑暗”是专制的隐喻。——这是1930年代的巴金真切的生活感受,也来自他对社会的认识。《家》写出了专制对人性的戕害以及人们为了争取独立、自由的抗争。家族故事,仅仅是它戏剧性的外表,作者要表达的是超越之上的观念和价值。《家》呼吁丢掉阻碍国族的黑暗包袱,呼吁国族现代化。它是与“青春是美丽的”相呼应,青春,既是年轻的生命状态,也是对青春中国的呼唤和渴盼。
写过《吃人与礼教》的吴虞还写过一篇《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吴虞也被巴金写入《家》中,成为小说中的人物。写大“家族”,为的是反专制,这才是巴金的真正目的。巴金的信仰中,反专制、争自由,是他最根本的追求。立足于巴金的叙述策略:他不仅仅是一个借助回忆的感性的抒情作家,他更是一位对社会、国家有着成熟和系统看法的观念性写作者。《家》的写作,与其说是指向过去,是为了回忆,不如说是为了现实和未来。特别是1930年代,复古思潮卷土重来,专制的囚笼越来越严密,作为“五四之子”的巴金,捍卫社会和个人追求的价值便成为他的重要使命。他曾说:“有人把路分为两条:一条通自由,一条向专制,但后一条并非必经的。事实上我也给人指出了一条趋向自由的路,至于什么时候才能够走到尽头,那却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但那条到自由的路不会在我的眼中脑里变成模糊,却是我可以断言的。”28他的这些作品,正是通往“自由之路”的思想桥梁。
巴金为什么需要借助一个外壳呢?除了文学创作的技术因素,也不能不注意现实的原因,写《家》的时代,外部的舆论和出版环境是这样的:
1930年4月,国民党公布全国主要城市邮件检查办法。
1930年10月,国民党下令取缔左联,通缉鲁迅等成员。
1930年1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国民政府之出版法》,限制出版自由。
1931年1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凡以文字、图画、演说作宣传活动的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931年10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出版法施行细则》并查禁书刊228种。
当时种种状况,使鲁迅不得不对朋友发出“而于是乎文网密矣”29的感慨。
事实上,巴金也面临各种。他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书,印行一版后即被国民党政府以“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罪名通令查扣。1933年10月,出版不足两个月的小说《萌芽》被“中央明令查禁”。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令查禁的149种文艺图书中,《萌芽》也赫然在列。书业同人两次呈文申辩后,当局又把查禁图书分五类处理,《萌芽》在“先后查禁有案之书目”,“应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30。1934年1月,出版不过五个月的小说《新生》也被国民党政府以“鼓吹阶级斗争”查禁。1933年年底,《文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稿子送审时,巴金的小说《雪》被抽出;散文《新年试笔》,刊物主编为避免麻烦将署名“巴金”改为“比金”发表。而小说《电》在刊物最初送审时,被禁止发表,巴金不得不将之易名为《龙眼花开的时候——一九二五年南国的春天》,署名欧阳镜蓉,换了刊物才得以发表……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巴金不得不调整叙事策略,在小说创作上,他拿外国的事情、历史故事来表达现实感受,如《海的梦》《罗伯斯庇尔的秘密》;也写起了“童话”《长生塔》。“家族题材”小说虽然酝酿已久,但它从最初就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家族的故事,大家庭记忆、社会批判、国族寓言,这几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在那个时代,家庭才是专制的重灾区、“黑暗王国”,这么写顺理成章。更重要的是,家庭伦理比社会伦理、政治呼吁更具有隐蔽性,可以成功地躲过当时的书报检查制度。这样的叙述策略确实取得了成功,即便是在上海沦为“孤岛”后,《家》的话剧还创下连演100多场的纪录,成功地穿越了不同的历史云烟。
当然,这种叙述策略难免造成《家》长久的被误解,连曹禺的话剧改编都集中在家庭伦理、儿女私情上。后来,大家都谈“反封建”,抨击了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与作品内容也算贴切,作者也立即予以追认。然而,作者最早在后记中曾说,他描写的是“一个正在崩坏的资产阶级的家庭底全部悲欢离合的历史”31,显然与我们后来理解的“封建”不是一个概念。时迁世移,“家族制度”与“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也淡化了,“封建礼教”也许又有了保守主义的价值,作者的本意被丢在时间后面。人们不再关注,作者强调的“反封建”,在反对包办婚姻之外,总是与反专制、争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近年“孝道”盛行,人们再以人情伦理来解读《家》,觉得祖孙关系,不必弄得那么紧张嘛,还证之于现实认为本也不是那么紧张。大家又忘了,巴金是把高老太爷作为专制王国的头子来写的,超出具体的个人和人情伦理,而整部小说,它的隐喻性和象征意义更不应再被遮蔽。
2022年7月2日于上海酷暑中
2024年8月26日改毕
【注释】
①⑩巴金:《家》,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第18、39页。此本是依据开明书店1933年5月《家》初版本排印的。
②司昆仑:《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何芳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第4、231页。
③④宋剑华:《巴金为什么要反复地修改〈家〉?——由“开明本”与“全集本”的对读说起》,《南方文坛》2018年第2期。
⑤⑧⑨巴金:《家》,载《巴金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101、212-213、411页。
⑥17巴金:《谈〈秋〉》,载《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440、456页。
⑦181920巴金:《谈〈春〉》,载《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429、423、430、432页。
1112巴金:《秋》,载《巴金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545、435页。
1314巴金:《关于〈家〉(十版代序)》,载《巴金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445、451页。
1516巴金:《谈〈家〉》,载《巴金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350-351、350页。
21巴金(芾甘):《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香港文汇出版社,2009,第149页。
22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载《巴金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38页。
23涅·纳·纳乌莫娃:《屠格涅夫传》,刘石丘、史宪忠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157页。
24巴金:《俄罗斯十女杰》,载《巴金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303、325、328页。
252627巴金:《家庭的环境》,载《巴金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398-399、399-400、400-401页。
28巴金:《我的路》,载《巴金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第30-31页。
29鲁迅1933年12月20日致郑振铎信,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05页。
30转引自倪墨炎:《149种文艺图书被禁的前前后后》,载《现代文坛灾祸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200页。
31巴金:《家·后记》,载《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第427页。
(周立民,上海巴金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