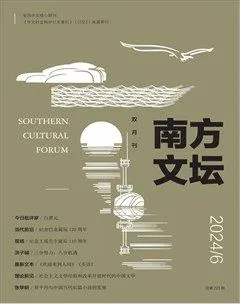再论巴金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巴金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经历了阶段性的起伏,从民国时期《灭亡》的影响、《家》的声誉到新中国文学史上“鲁郭茅巴老曹”的大师定位,《随想录》既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又在文学多样化时代被疑作的技巧的缺乏,“讲真话”被判定为肤浅,以及坚持终生的“反封建”被批评为陈旧等,可谓是潮起潮落,与世浮沉。不过,不管巴金一度遭遇怎样的疑问,有一点却从来没有被人怀疑过,那就是他的存在和姿态始终都被誉为是中国文学的“良心”。打开百度搜索,输入“巴金”“良心”几个关键词,出来的信息有上万条之多,有消息,有访谈,有论文,有著作,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仿佛巴金的历史形象天然就与这样的描绘联系在一起。当然,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也不再重拾这样的话题。但尘埃落定,无疑也给了我们真正沉淀和反思的机会,今天巴金,一时不再可能引发更大的学术热点了,我们正好可以冷静讨论:巴金和“良心”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我们把“良心”这个词用在巴金身上,它究竟表达了什么?为什么普遍认可这样的定位,其学术判断的合理又在哪里?我们不妨再作探讨。
一
“良心”这个词,一方面早已经进入大众日常口语,被作为基本的道德性表达自由使用;另一方面就其伦理道德的内涵而言,显然又可以追溯到中外历史的深处,并且提炼出对人类从古到今的发展都不可替代的重要规范来。当代的学人怀着景仰之情谈论巴金的人格风范,显然不是对一般生活用语的简单征用,而是包含着对巴金精神姿态和文学取向的特殊的认同。那么,这一认同的实质指向是什么,能否恰当地反映文学家巴金的志业呢?
良心,作为我们汉语里的词汇,其使用最早出自儒家。《孟子·告子上》有云:“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於木也。”朱熹为此做注:“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谓仁义之心也。”①这个解释非常清楚,所谓“本然”,就是一个人天生就具有的,人生而有之,不需要学习、教育就能够获得,这就相当于《三字经》里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就是在我们的天性当中就有一种被称为是善良的这样一种心性,这个就是良心。作为人性的最初的自然特点,儒家所强调的“良心”也就不会是中国文化的独有,事实上在西方文化最早的典籍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表述。英语中的conscience,意大利语的coscienza,法语中的conscience,它们均源自拉丁语conscientia,它的词根是sci,指“知道、认识”,con是指“共同、一起”,conscience通常被用来形容人的道德观念和内心感受,意思是“共同的道德观念与内心感受”;德语的良知为Gewissen,Gewi的意思是“确定性”;希腊文的suneidhsiV的意思是“一种与本己行为活动相关的知识”,尤指道德方面的知识。良知问题是古希腊哲学很早就开始思索的话题,苏格拉底在那场著名的审判中,宁死不屈,慷慨赴死,他听从的就是自己内在的良知。在古希腊时代的思想发展中,“良知”以中性的姿态与人的知识联系在一起;笛卡尔之后,“良知”从概念上融合了内在道德与自我意识;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康德特别提出一个善良意志、义务意识、内心法则的问题。另外一位20世纪的重要哲学家叔本华也特别论述了一个所谓道德的自我决定。他认为道德感不是别人强迫我们的,不是别人要求我们的,不是这个社会规定的,是发自于我们内心的,叫道德的自我决定。
总而言之,无论是中国的儒家,还是西方从古希腊时代开始的思想家,他们都注意到了人内心深处有着一种道德的内在意识。它与那些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出现的又变动不居的思潮有所不同,属于人最基本的知识,也与自我的意识密切相关。
作为精神现象,良知往往与人最本能的心理状态有关。特别是在中国文化的伦理传统中,它常常就是我们最基础性的道德选择,是人生在世的底线,所以中国人习惯有谓“天地良心”之说。
“良心”在心理上身居我们自我意识的底层,属于最基础的心理现象,在表现上则出现在我们人生的日常,是最普通的、最平实的态度选择。它并不代表某种思想境界的至高标准,就是人们必须坚持却常常不断放弃的日常操守;“良心”所处理的也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经天纬地的国家民族大事,也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人和人类社会内部的一些基本关系准则。处理这些问题的最大特点恰恰是它们十分平常、平淡无奇,但对于每个人来说却是普遍存在、随眼可见的。而且完成这样的日常琐碎更需要付出和坚持,需要更加持久的耐性。所有这些精神品质的综合——内在的、基础的、本能的、日常的、细碎的、底线的和持久的道德追求,就可以被我们称作“良心”。
巴金出现在中国文坛,从一开始就不是基于探索中国文学的艺术方向,而是在致力于社会改造于社会革命过程之中的思想表达。也就是说,文学艺术本身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并不是他关心的主要内容,如何改变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探索人类理想的生存才是他矻矻追求的目标,文学不过是这一社会理想的自然表述。
1921年,巴金在成都参加了“均社”,接近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从此“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②。在以后的一生中,这样的信仰深深地扎根在了他的灵魂,成为思想和情感的基础。“无政府主义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假若我一生中有一点安慰,这就是我至爱的无政府主义。在我的苦痛与绝望的生活中,在这残酷的世界里,鼓励着我的勇气使我不时向前进的,也是我所至爱的、能够体现出无政府主义之美的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们。对于我,美丽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就是我的唯一光明,为了它,我虽然受尽一切的人间的痛苦,受尽世人的侮辱我也甘愿的。”③巴金的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沐浴在这样的信仰的光辉之中,他笔下的青年革命者常常就是这些理想和信仰的化身。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因为巴金这样一个作家对无政府主义理想是那样真诚和忠实。他笔下许多革命者的原型曾经是他的无政府主义朋友;更重要的是,在他写作这些作品时,他确实深信无政府主义者是唯一真正的革命者。”④
应当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始终从属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现代社会改革与思想革命的诸多理想都曾经为中国现代作家所接受,也都在他们的文学世界里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在所有这些理想形态中,无政府主义的最大特点是将乌托邦式的社会改造蓝图融入个人的信仰修养形式,民主主义的理想是实现现代民主社会的制度化构建,共产主义的理想是通过大众参与的社会运动完成从制度到思想的崭新改造,而无政府主义的现实革命则主要依赖革命者的修养、信念和自我牺牲,这就带来了它们信仰表达的特殊状态:激情化、情绪性和浪漫主义,并且直接诉诸人的内心世界的倾诉。不难看出,这正好都是巴金文学特别是早年小说的基本特征。他总是将大量的篇幅置放在主人公心灵激情的表述上,对行动和故事关注的细腻程度远不及对其内心情绪的抒发,而且主观抒情式的渲染更重于对精神世界微妙细节的深度挖掘,抒发的内容则常常涉及人的道德和理想。“良知”就是他笔下人物自我表白的关键词,例如《秋》中写觉民等人的小团体的活动:“他们真心相信自己有强大的力量,不过他们并不拿它来谋个人的利益,他们却企图给黑暗世界带来一线的光明,使得不幸的人得到温暖。他们牺牲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特殊地位,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安适生活,只怀着一个希望:让那无数的人们都有这样的安适生活。”⑤或者《灭亡》中杜大心:“但是她一旦离开了他,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便感觉到剧烈的良心上的痛悔。”⑥而张为群的心理也是:“他是一个天真的人,虽然已经成年,却还有孩子气,还没有失掉赤子心。正因为有赤子心,所以看见不平、不公道的事,就要出来说几句,叫几声;看见别人底苦痛,他也要流眼泪。这样他就不能以自己小小的幸福为满足了。在不到一年以前,他信仰了杜大心底‘社会主义’,要用革命的方法推翻人世间一切的不平,创造出一个美满的世界来。”⑦天真、孩子气、赤子心,巴金本人和他笔下的“安那其主义”的革命者一样,时时都倾诉着真挚的心声,这就是“良心”的表白。巴金的文学世界,从早年的《灭亡》《家》到晚年的《随想录》,首先为我们营造的就是一个“二十世纪文学良心”的浓郁抒怀。
二
巴金一生的文学创作,不仅反复倾诉着一个从真诚的信仰出发传递人间良心的基本情怀,而且他在一系列文学目标上的执着和坚持也是基于一种不愿放弃的信仰和理想。就如同他早年对安那其信仰的大篇幅渲染可能会为一些艺术“讲究”的读者所挑剔一样,在后来巴金的各种“固执”也是引发质疑的主要原因。但是,人们所质疑的可能正是在日常行为中所忽视了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这一切在巴金的理想价值中恰恰可能是不能退守的底线,是人生在世的良心的一部分。
巴金的“反封建”的执着和艺术“无技巧”的信念都与这样的良心密切相关。
“反封建”就是巴金坚持一生的良心。从早年的“激流三部曲”、中年的“人间三部曲”到晚年的《随想录》系列,“反封建”是他贯穿始终的文学主题。他知道在别人眼中,这可能就是一个陈旧的话题,有点不耐烦。但是,某些读者的质疑并不能阻挡他坚持不懈的意志。他说:“我多么希望我的小说同一切封建主义的流毒早日消亡!彻底消亡!”⑧是啊,他说得很重。“我”也不想天天说《家》,“我”也不想天天说《激流》,但是只要当时中国存在封建主义,中国人就离不开《家》!至于晚年的历史反思,他也为自己的坚持而辩护:“要反封建主义,不管它穿什么样的新式服装,封建主义总是封建主义,衙内总是衙内。”⑨
我们质疑巴金对“反封建”的执着,在很大的程度上乃是出于从历史学知识出发的一种学术概念的准确性,中国学界所定义的“封建”与19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有关。斯大林、布哈林等认为,当时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仍占据优势,应当进行民主革命。反封建就这样成了现代革命的重要内容,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史理论则广泛运用苏联关于社会发展的“五形态”说。于是,“反封建”就成了对我们现代历史使命的权威解释。新时期以后,历史考察的视角和方法在多元化的方向上展开,更多的学者从中西历史的普遍性出发,重新提出了对“封建”的界定,“封建”一词有了具体的经济与制度的含义:在中国的西周,它指的是“封邦建国”,在西欧中世纪,feudalism是指“领主法律”。无论哪一种形态,实际上都与秦汉以后建立和主导的中央集权制大为不同,中央集权之下已经不容许诸侯国的存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⑩。这就是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郡县制。“秦至清的两千余年,政制的主位是郡县制,封建制不过是辅助性的偏师,郡县制与封建制两者均归于专制君主中央集权政治的总流之下。”11中国社会“封建”性质认知的调整反映了历史学界在学术视野与学术方法上的发展、探索,问题在于,当史学界的“新声”陆续传来的时候,巴金却继续着对他的“反封建”追求,这是不是一种思想的落伍呢?
事实可能还没有这么简单。学术史的探索和巴金的创作表达之间,是不是同一问题同一策略的差异?或者我们是不是就从概念的不同认定巴金和史学家讨论的是同一回事,巴金是不是有他自己的感受和所指?当我们不假思索地将巴金的“封建”概念比附于历史学界的问题之时,很可能在事实上遗忘了巴金信仰的准则。在巴金的人间情怀中,概念的准确性必须让位于现实体验的准确性。不管历史学界如何定义既有的社会制度,现实的不平等关系依然存在,而他所谓的“封建”并不是在纯粹史学的意义之中,与分封制度无关,与诸侯分治无关,而是与人间的压迫和不平等有关,甚至与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有密切的关系。在巴金心目中,反封建就要“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12,“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的进化和人性的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努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13。无论是在现代化已经起步的民国还是极“左”思潮之下,巴金都的确面对了这样的制度,也拥有这样的反抗的权利,都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只要他心中的理想社会依然没有褪色,只要追求人间平等和幸福的初心不曾改变,那么就有理由对种种的不合理现象予以揭发和批判,如果这样的压迫关系明目张胆地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又为什么不能继续揭橥反抗的大旗呢?在历经现实悲剧的文学家巴金看来,“封建”存在与否,“反封建”必要有无,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不是学术的问题,归根结底这是敢不敢于面对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基本的求真求实和捍卫人的基本权利的问题,也是维护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基本价值理想的问题,“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五四运动的年轻的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着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天地”14。它并不需要诉诸太多的智力,也不是什么更高境界的特殊要求,其实不过就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人类道德基本底线,所以凭“良心”说话和表达就足以完成。只有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不难感受到他对一些细微的扭曲缘何如此愤怒、不愿轻易放过的执拗,也不难理解他何以要在1980年代反复唠叨极“左”时代。因为,正是从他坚持一生的良心出发,他不能忍受我们社会存在的“底线”的破防,也不能接受基本原则的撤销,他要以自己固执的坚守来抵抗不断崩溃的道德堤防。
三
巴金对于文学创作的“讲真话”与“无技巧”追求的坚持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良心的表达。
“讲真话”与“无技巧”,表面上看是巴金追求的两个方面,其实严格说来就是一个思想的不同方向的阐述。“讲真话”就是直截了当,没有遮挡和掩饰,这就是“无技巧”的一种生动表现,而对文学“无技巧”的辩白则可以看作是“讲真话”的一种。总之,人们曾经的疑问在于,文学求真是应有之义,为什么还要被巴金反复申说?这是不是一种老生常谈的饶舌?是不是属于对文学发展无话可说的姿态?甚至有人还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一再被主流批评家所称道的‘讲真话’精神,也只能称为‘文革’时期知识分子懦弱脊梁、萎靡人格、颓唐心理的代名词。”15至于20世纪文学的发展本来就一度出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学技术的手段层出不穷,有人质疑:怎么还会退回到19世纪初年批判现实主义时代的理念和诉求?
与我们囿于史学的“封建”之论来挑剔巴金的思想相类似,基于文学发展的当代动向来质问“讲真话”与“无技巧”,同样属于文不对题,因为,这完全漠视了巴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基本状况的评估和抉择。
“真”的确是我们谈论文学的起点,但是这个起点其实同时又是最大的难点。没有哪个作家公然宣布文学可以而且应该说假话,即便说了假话,他也要说他说的是真话。中国所谓的文学之“真”,并不仅仅就是人生经验的真实记录。从孔子“删诗”的时代开始,文学之“真”就不再是作家经验的再现,它必须经过“道统”的规范和约束,一句话,经验开始得服从儒家经典的解释,符合了解释方成为“诗经”,不能合于解释的即不再为“真”。历经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规范,中国文学的真实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很多时代都不得不偏离作家的真切人生经验,以迁就国家政治的需要。巴金一生,见证了民国政治的黑暗,也目睹了极“左”时代的文学表述,所以他对文学“讲真话”的渴望来自现实世界的惨痛教训,是着力推动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更新的真诚呼吁,也是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历史的反省和自我的批判。巴金以他持续的求真,警醒人们不可忘记了那个是非颠倒的时代:
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我念念不忘的是这样一件事:读者,后代,几十年、几百年后的年轻人将怎样论断我呢?他们绝不会容忍一个说假话的骗子。16
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个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17
“十年浩劫”绝不是黄粱一梦。这个大灾难同全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是不搞得一清二楚,作一个能说服人的总结,如何向别国人民交代!18
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真话的人。我提倡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也在走向死亡,所以在我眼前“十年浩劫”已经失去它一切残酷和恐怖的力量。19
巴金“讲真话”的强烈诉求之中,更包含着他自己深深的忏悔,而促使他勇于忏悔和反省的恰恰是我们已经失落甚至开始消失了的“人”的原则和良心:
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20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登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作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21
五卷本的《随想录》,它才是我的真实的日记。它不是“备忘录”,它是我的“忏悔录”,我掏出自己的心,让自己看,也让别人看。22
在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的还是一种现代良知与人格底线的力量,这就是巴金通过自己“讲真话”所努力挽回的中国人的生存底线。
文学当然需要技巧。但是在那个内焦外困的为生存的底线而挣扎的时代,技巧恰恰也可能成为某种自我掩饰的手段。巴金以他多年目睹“文学江湖”的教训揭示了这样一种极端性的现象:技巧成为躲避人生真相的借口和装饰,或者打击那些无法理解的人生真相的理由。例如,隔着境内外的社会差异,最早攻击巴金“无技巧”的是一群香港大学生,他们对动乱年代的中国悲剧难以感同身受,为此,巴金在《〈探索集〉后记》中回应说:“最近有几位香港大学学生在《开卷》杂志上就我的《随想录》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是严厉的批评吧:‘忽略了文学技巧’、‘文法上不通顺’等等,等等。……我冷静地想了许久,我并不为我那三十篇‘不通顺的’《随想》脸红,正相反,我倒高兴自己写了它们。……我从来不曾想过巧妙地打扮自己取悦于人,更不会想到用花言巧语编造故事供人消遣。……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鼓舞他们前进。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23
在巴金看来,20世纪中国可能还没有足够的理由成为“为了文学而文学”的时代,如果我们在事实上无法从诸多生存世界的困扰中解放出来,那么“直面惨淡的人生”可能比许多炫耀技艺的华丽要切实得多。应该说,对文学技巧问题的审慎也是巴金正面迎接生存挑战的良心之选,显然,这样的选择并不仅仅属于他自己,在现代中国,包括鲁迅在内的能够严肃地面对生存真相的作家都有过类似的理解和主张。正如学界已经发现的那样:“迄今为止,鲁迅作品之得到中国读者的重视,仍然不在于它们在艺术上的成功……中国读者重视鲁迅的原因在可见的将来依然是由于他的思想和文化批判。”24现代中国很少“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家,很少作家把自己的探索集中于纯文学的领域,他们涉及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不仅文学,更包括了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几乎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不少人对现代自然科学也同样有很深的造诣。这一切必然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体现到他们的思想、创作活动和文学作品中来25。
巴金说过,自己早年创作小说就是“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而晚年的随想录也“是为着同敌人战斗。那一堆‘杂货’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武器,我打仗时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着,我都用上去”26。这正如鲁迅的文学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晚年的杂文也被人斥作“缺乏文学性”,但是,鲁迅却多次表示:“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27最终“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28。巴金和鲁迅显然有着高度的共识:
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29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巴金对“良心”的坚守和执着归根到底是来自新文学诞生之初的基本理念,这就是陈独秀所论:新文学精神的起点是伦理的革命。
《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是陈独秀发表在1916年《青年杂志》一卷六号上的重要文章。在陈独秀看来,自明清以降,近代以来,经过器物、军事、政治等诸“觉悟”之后,“伦理的觉悟”就是新文化运动所要推动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彻底之觉悟”。何谓“伦理”?其实就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包括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所谓“伦理的觉悟”也就是对人之为人的这些基本道德责任问题展开自觉的反思与建构,而现代意义的伦理建构也当对传统的反省与批判为起点的,所以陈独秀首先提出了自己思考的结论:“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30五四新文学—新文化运动重新确立了“人”的基本理念,而将中国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旧思想称为“封建伦理”“旧礼教”,予以猛烈的抨击和批判。这里的思想批判已经不着眼于“封邦建国”的经济/政治内涵,而是另有了思想伦理的全新内容。巴金所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五四新文化,他的反封建—讲真话—无技巧追求都是五四新文化传统在历史进程中的延续和发展,他努力以此构筑起现代文化新伦理的良心和底线。
【注释】
①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一,载《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331页。
②巴金:《〈火〉第二部后记》,载《巴金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374页。安那其(anarchism)即无政府主义。
③巴金:《答诬我者书》,载《巴金全集》第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179页。原载1928年5月《平等》月刊第1卷第10期,署名芾甘。
④奥尔格·朗:《西方思想对巴金的影响:无政府主义与民粹主义》,载张立慧、李今编《巴金研究在国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第493页。
⑤巴金:《秋》,载《巴金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124页。
⑥⑦巴金:《灭亡》,载《巴金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109、98页。
⑧巴金:《关于〈激流〉》,载《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687-688页。
⑨巴金:《衙内》,载《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654页。
⑩语出《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今通常写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11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第93页。
12巴金:《关于〈寒夜〉》,载《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690页。
13巴金:《写作生活的回顾》,载《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556页。
14巴金:《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载《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66页。
15惠雁冰500233ec3ff8622c244ac5c4a48d54e034ed56791b3f3d8043865e79f5e8a345:《意识形态粉饰下的平庸:巴金〈随想录〉》,《二十一世纪》2007年12月号,总第104期。
1619巴金:《“没什么可怕的了”》,载《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254、254页。
1723巴金:《〈探索集〉后记》,载《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274、272-273页。
18巴金:《写真话》,载《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241-242页。
20巴金:《怀念胡风》,载《无题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174页。
21巴金:《解剖自己》,载《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398页。
22巴金:《致树基(代跋)》,载《巴金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第613页。
24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十一)》,《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2期。
25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方法》,《读书》1986年第3期。
26巴金:《我和文学》(《探索集》附录),载《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268页。
2728鲁迅:《华盖集·题记》,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5页。
29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05页。
30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1卷6号。
(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