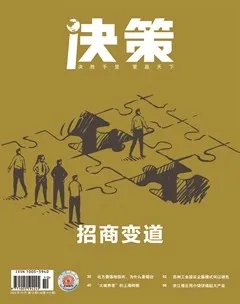裹脚布(下)
四
失明女孩的救助并不顺利,其过程一波三折。先是在省立医院碰到了问题,收治她的医生在全面检查之后,认为她不适合做手术,一家人悻悻而返。我得知情况后感觉非常遗憾。
有人向我推荐北京一家大医院,称该院眼科是业界权威,何不往那里试试?我把情况告诉患儿父亲,他拒绝了,称非常感谢我,但是他们已经认命。我明白这家人更多的担忧是花费,以及竹篮打水。我向他们保证可以提供有力帮助。
经反复劝说,患儿父亲同意再试一试。我通过多方联系,为他们安排了北京行程。动身之前患儿父亲再次变卦,不想去了。
深入一了解,原来他们从未出过省,一想起走那么远就心里发悚。问清情况后我决定抽空亲自带他们前去。到北京后又几经周折,最终该女孩被确定可以手术,只须排队等待可供移植的角膜。
但是这件事很快成为问题,在检查期间被要求做出说明。有人就这女孩的手术提出看法,认为我与女孩家人可能有瓜葛,涉嫌假公济私。
我向检查组组长段仁杰解释了全部情况,承认对这位女童格外关注,但是并无私利。女童的救助经费基本出自社会募集,我本人来往北京也不使用公款,那一趟机票与差旅费都是自掏腰包。我向他出示了保存的票据,他表示认可,问:“你为什么呢?”“我总是爱岗敬业。”我自嘲说。
段仁杰是一位重量级检查组长,刚从市中级法院副院长位置上退二线。适逢本市进行市直部门工作大检查,他奉命率组检查若干单位,市残联为其中之一。
他安排了一个下午时间跟我谈话,一起谈话的还有检查组副组长和一位组员,谈话在会议室进行,很正式。段仁杰主谈,另两位负责记录,各有一个笔记本,需要时可互相核对笔录,确保无误。
谈话开始前,段仁杰特别指出:按照检查日程,今天下午是与残联领导班子个别谈话。由于目前残联理事长因病离岗,又没有其他班子成员,因此谈话对象仅我一人。整整一个下午,时间非常充裕,可以谈多一点,谈深一些。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让我做出说明。那些问题是他们通过问卷、意见箱、举报信和个别谈话等方式,从各方面搜集了解到的,搜集范围包括本单位人员、本单位服务对象、离退休人员、上级领导等。
经检查组梳理的问题大体分工作、个人两大类,有关失明女孩的问题既是工作,又涉个人,却显然不是他们想要了解的主要事项。
段仁杰提到了裹脚布:“请你也谈谈吧。”我感觉不解。他解释,只要有反映,他们就需要做些了解。不要太在意,如实说明就可以。
我相信他有备而来,很大可能是奉梁茂华书记之命,这块布始终是个问题,并没有因为我“工作需要”就消失。我告诉他裹脚布是一种纺织物,估计以土法编织为多。迄今为止我还只限于资料阅读,从没见过实物,哪怕一条裹脚布。
段仁杰说:“曹理事长,你应当很清楚我们要了解什么。”我即席略做发挥,认为裹脚布的要害不在长短,而在气味。如果它洗干净并经曝晒,散发着阳光的气息,超过五米无妨。如果它臭不可闻,短于三尺也能令人作呕。“咱们还是谈谈其他的。”他说。
他提到了吸烟室。我告诉他我不吸烟。当然他也知道,在吸烟室里吸烟并不违反规定,问题不在吸烟。“那么在哪里?”我问。“你如实说明就可以了。”
我不觉得吸烟室有什么问题。他追问,既然没问题,为什么不能说一说?我承认他说得很对,而后即做思考状,缄默不语。
这一次谈话与岳晓峰那次个别谈话有别,此刻回答的每一个字都将被记录在案,需要特别注意。段仁杰和颜悦色,劝告我端正认识,实事求是。他让我不必纠结裹脚布,市尺还是公尺并不重要,无关紧要。
我说:“感谢段组长提醒。”我点点头,微笑,一言不发,没有更多补充。
五
我们磨了整整一个下午。段组长作为一个老资格法官,也是法官领导,专业水平很高,耐心也足够。他可以两眼盯紧,一声不吭,观察我的表情,等我开口,一等半个小时,不显出丝毫着急。
我对他抱以微笑,很理解,也不着急,始终不再开口。应该说我俩都很成熟,修炼都不错。如此相对枯坐哪会不尴尬不痛苦?几分钟足矣,撑一个下午实有如受刑,我们却都撑住了。
既然我不说话,段仁杰为什么不能早点中止,让彼此都轻松些?我估计他跟我一样面对同一份记录。如果记录上没什么内容,那么只有时间可以表明他们绝非草率,一直在努力劝导,为了听我一说,非常有耐心。
下班时间到,谈话程序按计划完成,段仁杰宣布今天就谈到这里。他要求我回去好好想一想,准备准备,需要的话他会另找时间跟我再谈。他特别强调,本次大检查非常严肃,接受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好好配合,否则会有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待另两位收起记录本离开,段仁杰又说:“曹理事长有点意思。”我告诉他,根据北京传来的消息,由于各方面共同努力,本市那位失明女童已经等到了志愿捐献的角膜。不出意外的话,手术很快就将进行。我一直保持密切关注,感觉跟裹脚布什么的比起来,这事情更有意思。
“听起来像是有些感慨?”他问。我承认。人突然碰到意外情况,免不了感觉失落。这种时候特别需要做些事情,觉得尚有可为,把自己从失落中打捞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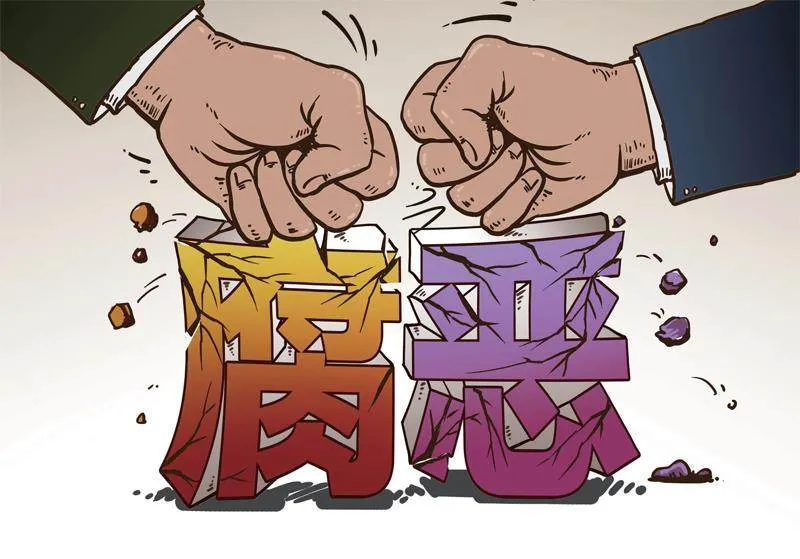
这位盲女让我颇有感触,我思忖自己如果徒有目光炯炯,哪怕眼神如刀片一样锋利,其实不辨真假不知善恶,那实在不如瞎眼。通过努力帮助她恢复视力,看清眼前事物,我会有一种成就感,也觉有所安慰。
段仁杰很敏感:“别有所指吧?”我说:“是真心话。”“我还是希望听你谈谈敲钟。”我笑笑说,“没有更多补充。”其实何须我多补充,他们早都知道了。什么叫做“敲钟”?段仁杰是拿我自己的话来提醒我,有如裹脚布。
那一回,李大章问我,梁茂华书记的这份五米长稿是不是我参与研讨的?我告诉他是政研室搞的,我没参与。一旁另一位说,他注意到讲话里提到了太平洋中心,看来事态最终平息了?另一根烟枪插嘴,太平洋中心有些啥?那就是一条大海沟,一大坑,太平洋中心其实就是太平洋大坑。“三四五”怎么说都不要紧,财政的钱可不能那么弄,不可以拿去扔海里填那个坑。
李大章插嘴表示反对:“你去捞几张钞票上来看看,哪一张印着‘财政’?”另一位说:“需要那么印吗?明摆的。”我感觉他们又踩线了,话题比较敏感,笑着再次提醒:“诸位,敲钟了。大领导目光炯炯,日后再研讨。”
那仨烟鬼听从劝告,不研讨了,各自在烟灰缸按灭烟头,起身离开吸烟室。大家分别从不同边门溜进会场,如老鼠沿墙角悄然而迅速闪过,窜赴各自位置落座,继续聆听、记录领导重要讲话。
所谓“太平洋中心”是个什么?简而言之,那就是一个大型造城开发项目。这项目搞砸了,疑似上了几个跨国骗子的当。类似项目初起时总是很诱人,该中心听起来曾经像个微缩型上海浦东,资金因而趋之若鹜,直到被席卷一空。当这个中心引发动荡,情势显得严重之际,有一家公司果断介入,接下盘子和巨额债务,投入大笔资金理赔,让事态渐渐趋于平静。
出手救场的是一家上市公司,底子是本市市属企业集团,主管是本市国资委,经几轮打包和资产重组上了市。这家企业近年经营不善,屡现贫血,市里通过各种途径为其输血,帮助其撑下去,企业的钱虽然没有印着“财政”两字,实有赖于地方政府。
为什么已经贫血还要跳入太平洋?因为那个大坑项目原本是梁茂华书记亲自招商、亲自拍板确定的,不能听任不救,哪怕背上巨债。这件事机关内外议论不少,于本市属于敏感事项,所以我对吸烟室那三位敲钟叫停。
这才是裏脚布后边的要害。如果仅是那快臭布,哪怕再加上个懒婆娘,即便对滔滔不绝的市委书记有所冒犯,也不至于让他那般气恼。裹脚布实只在表面,里边还包着一个坑,那个坑才深不可测,有如太平洋的马里亚纳海沟。
事实上,吸烟室里的这个坑与那块布一样,跟我基本无关,却显然被姓“批注”了,所以才有梁茂华目光炯炯,把我拖出来当一只鸡砍了,以诫众猴。
为什么事后岳晓峰与段仁杰又先后要求我谈情况?估计梁茂华心里或许有些生疑,要听听我怎么讲。这种事大张旗鼓严加追查影响未必好,只能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这尤其让我无法接受。
类似情况要搞清楚又有多难?无须劳驾包公穿越,让分管领导悄悄把几个当事人分别叫去问问,稍加比对,自会真相大白。为什么不先搞清楚就雷霆万钧,草率处置曹某?退一万步说,即便裹脚布和太平洋大坑都姓曹,那又算什么?就应该被一刀砍了?显然不对。
在木已成舟之后,如果我喊冤申辩,或者遵命向岳晓峰、段仁杰提供我所知情况,也许有一些好处,立刻反转“工作需要”,官复原职可能性不大,至少不会陷于没完没了。但是这么干于我有障碍。
考虑到他们未必就相信我,且洗刷自己同时肯定得举报他人。我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发展,只能走着瞧。
六
半年多后,梁茂华荣调省城任职,离开本市。履新的第三个月他突然出事,名字登上“打虎榜”,成了涉案被查官员。关于其涉案细节有众多传说,包括太平洋大坑,据说其家人在该项目审批中获取了巨额利益输送。
如此看来,他为那个吸烟室大为光火实有隐情。
我因为传闻纷纷的“批注”与“工作需要”被办案人员注意到了,他们把我请到办案组驻地,让我谈谈所知情况。我告诉他们,因工作所限,我并不掌握梁茂华涉案情况与证据,我在吸烟室除了敲钟叫停,没有参加任何研讨,并无出色表现。裹脚布什么的与案情无关,无须多说,或称“没有更多补充。”
此后裹脚布渐渐归于尘土,至今我还不知道自己被谁“厚爱”了。相信查实不难,只是懒以为之,与其追逐臭气,不如寻求光明。
我所帮助的女童经成功手术,已经得见天日,两只大眼睛闪闪发亮,波光粼粼,炯炯有神又含暖意,令我欣喜不尽,觉得这种事值得多做。
偶尔我也会有些不平与失落,幸而都能自我排解,毕竟强如梁茂华书记都到牢子里让人“批注”去了,我还能做点好事,闲来笑谈“裹脚”,不挺好吗?
(原文刊载于《湖南文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