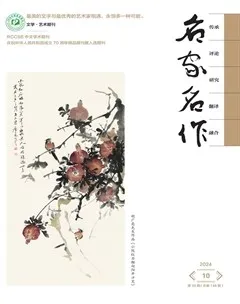以孙悟空为例探究跨媒介形象的经典化路径
[摘 要] 经典形象的确立往往伴随着丰富的相关文本,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文本的介质也体现出多元性。文学作品影视化作为长期存在的文艺现象,为人物形象提供了一条成熟的媒介形象经典化道路。影视化过程中文本的增殖印证了热奈特承文本性的关系论述,体现了原文本形象在叙事和意涵上的延伸。文本增殖依托媒介载体,也伴随着媒介增殖进行。形象实现跨媒介增殖的背后是再媒介化过程的体现,文本形象也在媒介物质基础和传播规律的作用下得以再造和传播,由此产生新的审美体验,完成经典形象在新媒介环境下的更新与确认。
[关 键 词] 媒介形象;文本增殖;媒介增殖;再媒介化;孙悟空形象
一、问题缘起
文学作品影视化是长期存在的文艺现象,也是影视作品创作的重要来源和途径。从默片时代《一个国家的诞生》对托马斯·狄克逊《同族人》的改编,到如今各类经典名著的影视化呈现,文学作品一直是影视作品的重要蓝本,改编也一直是影视创作的重要途径。在这一过程中,原本的文学作品得到了跨媒介传播,文学形象在异质媒介间得到再现或重塑,实现了形象的“增殖”。这一过程是持续进行的,这种形象的生产方式呈现出增强、增多的趋势。[1]其中,孙悟空作为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形象在影视作品中得以增殖,成为最典型的跨媒介形象。无论是六小龄童饰演的“美猴王”,还是后现代主义艺术下的“至尊宝”,一个又一个影视形象完成了文学形象的经典化,又在增殖的过程中塑造影视形象的经典,让文学与影视在异质媒介的再造中互相滋养、互相成就,从而形成一座文艺世界的“高峰”。
孙悟空形象的跨文本增殖是西游学界的传统研究视角,影视作品作为孙悟空形象增殖的重要媒介也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以孙悟空为例,媒介时代的文化艺术生产被概括成一种以文学形象为根源性、共同性因素的相关艺术文本的生产模式。但这一模式下,孙悟空形象何以在异质媒介中完成经典化?本文将从文本与媒介两个角度探析其中的路径。
二、经典的重要特质:构建高度互文的文本网络
经典作品本身具有典型性。经典作品作为文艺作品中超越时间的典范,实现了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融合,为后续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可阐释性,在后世的不断改造和摹仿中,完成了与受众期待视野的确认和平衡,成为历久弥新的文艺高峰。经典作品中的经典形象则作为作品意旨的集中体现,承载着经典创作的核心价值,在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中与群体性的期待重合,成为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形象化存在。以孙悟空形象为例,经典化的孙悟空寄托着时代与大众的精神呼唤,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无畏、敢于斗争等精神品质的形象化体现。
经典化是一个意义生成的过程,是正在进行时的建构,体现出活态的审美文化。[2]除了自身的典范性,文艺作品的经典化还离不开后世的确认。这种确认来自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以及受众的期待视野,反映在跨文本性的文本世界中。经典既要接受历史和社会的考验,也要体现其典范意义,为后世提供鉴赏、研读并可供改造和摹仿的价值。因此,经典往往伴随着数量庞大的衍生作品,编织起高度互文的文本网络。经典作品《西游记》在纸和屏幕、书报刊和电子媒介、戏曲和影视等不同的艺术类型的媒介中得以再现,孙悟空也成为后世解读、演绎及改造的重点,在不同作品、不同媒介中幻化出各种各样的形象,活跃在不同类型但高度互文的文本网络中。
三、文本增殖:形成文本网络的途径
(一)承文本性的泛用
文本的创作往往是相关相承的,具有不同程度的联系。文学创作者难以避免地受到前人作品的影响,从而在创作时表现出对已有作品的借鉴、参考、掺杂乃至模仿。20 世纪 60 年代,学者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就文本间的关联性问题提出了“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概念,揭示了文本之间相互关联的内在属性。随后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从诗学维度提出“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的概念,将“所有使文本与其他文本发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称作跨文本性,并划分出跨文本性的五种类型: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副文本性(paratextuality)、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y)与广义文本性(architextuality)。在五种类型中,承文本性是热奈特重点论述的对象。
在热奈特的论述中,承文本是在蓝本基础上嫁接而成的、与之具有非评论性攀附关系的派生文本,是一级文本衍生出的二级文本。承文本性就是对这种关系的描述。在承文本性中,蓝本是关系存在的前提,承文本是承文本性的载体。对承文本性的研究,就是在以蓝本为前提、承文本为载体和核心的基础上分析文本的派生,进而阐释文本二次创作的表现和意义。[3]热奈特对承文本性的论述是在诗学领域范围内的,但对泛文本类别下作品间关系的思考有借鉴价值。学者李宁在《增殖的美学:论文艺高峰的文本世界》中,根据热奈特跨文本性的论述,将现实文本世界划分为对应的几种文本类型,并将文本类型的界定拓展至更加广阔的文艺空间。[4]在多种艺术形式的文艺作品相互关联的网络中,原文本的核心地位得以强化,实现了文本跨媒介的增殖,从而筑起文艺世界中的“高峰”。
(二)影视作为承文本的“增殖”
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是由来已久、数量庞大的承文本现象。以《西游记》为例,其作为我国经典著作,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与审美空间,其故事和以孙悟空为代表的主要人物为诸多文艺作品提供了创作母本。从 1926 年的短片《孙行者大战金钱豹》到 2015 年的《大圣归来》,中、日、韩、美等国在九十年间至少拍了 85 部相关电影,2016 年就有 9 部有关“孙悟空”的电影上映。电视领域也不乏改编作品,央视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最典型,他身披黄金战甲、头戴金鸡翎、手舞金箍棒,被亿万观众称作永远的“美猴王”、永远的“齐天大圣”,凝结着几代观众的共同记忆,塑造出国人心中孙悟空的基本形象。可见,数量庞大的影视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再现着原文本,构成了类型内容纷繁的承文本网络,实现了文本的增殖。
在文本增殖的同时,形象本身的意涵也得到拓展,实现了叙事和意义上的增殖。同为《西游记》改编后的影视承文本,孙悟空的形象在不同的作品中大相径庭,体现出作者创作意图、观众期待视野以及更宏阔的文化语境的融入与影响。《大话西游》系列电影中,孙悟空由神变成山野强盗至尊宝,完成由“神”到“人”的巨大转变,影片解构了数百年来老少皆知的人物形象和情节体系,将故事的时间线定位于《西游记》前传或后传的后现代版本,塑造了一个失去神性而找寻自我的至尊宝形象。[5]而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在《大话西游》的无厘头后现代主义解构上更上一层,通过大圣形象反映了年轻人勇敢无畏、敢于战天斗地的不羁态度,而后被江流儿释放的孙猴有被束缚时的落寞,也有逆境时的坚强崛起。对许多观众来说,孙悟空不再是六小龄童演绎的那个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而是一个拥有尘世凡人“贪嗔痴恨”的矛盾个体,深刻地折射出一种人性关怀。在此意义上,以《大话西游》系列电影为代表的影视作品,不仅完成了文本的增殖,也在叙事上架构起新的故事线索和内容设定,从而让原文本在承文本性实践的过程中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语境结合,让作品原有的意涵得到延伸与拓展,从而印证了原文本作为经典的典型性。
四、媒介增殖:实现文本增殖的载体
(一)媒介增殖的本质是再媒介化
美国学者杰伊·大卫·博尔特和理查德·格鲁辛正式提出“再媒介化”的概念。在二者合著的《再媒介化:理解新媒介》(Remediation:Understanding New Media)(1999)一书中,博尔特与格鲁辛曾运用“再媒介化”概念来分析新媒介对传统媒介进行改造的方式,认为再媒介化是“一种媒介在另一种媒介中的再现”。它们通过举例电影《末世纪暴潮》(Strange Days,1995)进一步指出“去媒介性”(immediacy)和“超媒介性”(hypermediacy)是“再媒介化”的双重逻辑,以此来表征媒介发展过程中新旧媒介不断重塑自己与对方的作用力,“作为一种革新,再媒介化的目标是重建或重塑其他媒介”。相比于麦克卢汉以时间顺序来界定媒介化的先后过程,再媒介化理论进一步厘清了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新旧媒介关系。新媒介使旧媒介得以重塑,这是新媒介对旧媒介再现与再造的过程,也是旧媒介重塑自身以适应新媒介出现的过程,新与旧此消彼长、难解难分,旧媒介不会消亡,而新媒介也以确定或不确定性的方式依赖着旧媒介。[6]
(二)影视文本的媒介增殖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 (André Bazin)在其《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一文中,提出了一条审美原则,即“摄影的美学特征在于它能揭示真实”。巴赞认为相比于其他艺术,电影艺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纪实的特征”,摄影克服了人的主观性,隐藏了创作者,满足了人们对自然的直接感知。电视剧作为电影的“姊妹”媒介,具有同源而相近的纪实性,兼具纪实编码。从小说到影视的再媒介化中,影视纪实的一面得以放大,通过塑造视觉形象,将文字内容可视化,尽管填补了文学作品提供的想象空白,但影视既定的视觉形象带给受众更直接、真实的审美体验,凸显其作为新媒介的去媒介性。影视制作依赖于复杂的装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拍摄、剪辑以及其他形式上的规范,从而让它看起来是连续不断的,以此来消除媒介的痕迹。尽管如此,影视创作的最终产品呈现为快速连续的图像,又唤起了人们对其美学、时间和形式中介的注意。影视在对旧媒介的再造中体现了再媒介化的双重逻辑。作为再媒介化的产物,活动影像在意图性和明确概念的层面上显然弱于文字的表达,但它提供了视觉感受的直观性和意义生成的开放性,影视在对旧媒介有所存续的基础上,也在视听系统延长了原有文本的表意空间。
(三)再媒介化带来的审美增殖
在多样化的媒介世界中,每一种媒介都以其独特的表现力和沟通方式传递信息、表达情感,这些独特的媒介特性能够赋予文艺形象特定的审美特征。电影作为一种视听媒介,融合了视觉与听觉元素,以其时间性、空间性的特点为电影艺术创造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视听体验,从而塑造了不同于文字叙述的文艺形象,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沉浸式的审美体验。正如上文中对孙悟空形象文本、叙事和意义增殖的论述,异质媒介的再造为原文本提供了延伸的空间。在这个媒介空间内,原文本的典范性得到巩固和确认。《西游记》改编电影众多,其中孙悟空的联系与差异均直观地表现在视觉形象上,带给观众截然不同的审美体验。这样的声画表达是原文本的媒介增殖,表达所带来的是作品审美意义的增殖。孙悟空再媒介化后的影视形象依托于电影媒介的物质基础和传播机制,也深受社会语境的影响,形成了“媒感”基础上的“美感”。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演进,艺术家被赋予更多的创作可能性,同时观众的审美体验也因技术的介入而发生改变。从印刷媒介到数字媒介,每一次技术革新不仅推动了艺术形式的创新,同时促进了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的转变和跃迁,从孙悟空这一形象上便可见一斑。时至今日,孙悟空的形象愈加多元化和人性化,不断被时代和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所塑造,突出了个体的情感表达,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切实反映出网络时代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与对自我价值的探索和突破。数字艺术和网络文学的兴起极大地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和维度,也为审美接受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艺术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不再受限于时间与空间,艺术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紧密频繁,促进艺术更好地走进大众生活。
五、结束语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在艺术手段上实现了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变;在媒介手段上呈现出异质媒介的跨越,既为影视提供了文本的根源,也为文学拓宽了视与听的表意空间。而在数智时代下,技术变革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更让文艺作品赖以存续和传播的物质基础发生了转变,文艺也面临着数字化生存的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由于物质介质差异性的消磨,原有文艺作品成为可供任意解码、传输和重新编码的数字语料,为新的创作提供了基础,衍生出即时性、参与式、碎片化的数字文化生态,使作品能被快速地传播和分享,同时被分解为更小的单元,满足人们日益多样的审美需求,从而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互动。数字时代的文艺正逐渐成为更加开放、互动和多元的文化生态。经典作品在“高峰”稀缺的文艺世界里勾勒出人类艺术成就的“天际线”,但也面临着数字化的文化语境。影视媒介对孙悟空形象的增殖是一条文学形象在异质媒介中再现与传播的成功路径。数智时代语境下,经典形象也应挖掘新媒介背后的物质基础和传播规律,在媒介增殖基础上实现符合传播特征的文本增殖,从而使经典形象与时俱进、因时常新。
参考文献:
[1]阎怀兰.从孙悟空看媒介时代文学形象的增殖[J].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7,37(5):91-96.
[2]孔朝蓬.数字时代经典电影的文化记忆延伸与再媒介化[J].当代电影,2023(7):96-102.
[3]王金涛.浅谈热奈特跨文本性中承文性的概念、存在条件及实践类型[J].名作欣赏,2024(9):71-74.
[4]李宁.增殖的美学:论文艺高峰的文本世界[J].中国文艺评论,2021(10):50-58.
[5]周兰,周文.神·人·妖:论孙悟空的影视形象演变及其社会文化动因[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40(11):98-102.
[6]党东耀.媒介再造:媒介融合的本质探析[J].新闻大学,2015(4):100-108.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