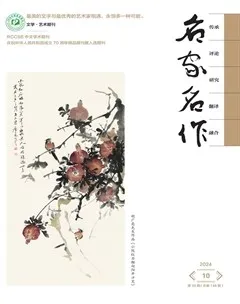《功夫》中的沉重与轻盈:周星驰电影的叙事手法与风格分析
[摘 要] 在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中,“周星驰无厘头喜剧”风格是一股清流,不仅重振了本土电影的活力,更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独特的艺术标杆。作为周星驰的代表作之一,《功夫》在商业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主题表达、人物塑造以及风格形式三个方面深入分析影片中沉重与轻盈的共存,探讨喜剧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批判与人性思考。
[关 键 词] 周星驰电影;无厘头喜剧;《功夫》;叙事手法;风格
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在广东话语境下具有“无目的、无中心”的随意感,这种幽默形式强调无厘头的荒诞和毫无逻辑的情节发展。2003年《时代周刊》将周星驰誉为“中国的卓别林”,在电影史上,“无厘头”风格与卓别林的默片喜剧有某种共鸣。《功夫》作为“无厘头”的先锋之作,以喜感的方式表达出更加高级的喜剧技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无厘头”风格以幽默为表,但喜剧的内核往往是悲剧,周星驰饰演的角色阿星从小受尽欺辱,长大后依然是个一事无成的混混,试图通过加入“斧头帮”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处处碰壁。在这个过程中,阿星经历了现实与虚幻交织的“猪笼城寨”的冒险,最终领悟到功夫的真正意义。
一、主题表达:解构现实权威,歌颂纯真爱情
(一)黑白不分的时代权威
情感冲击通过剪辑产生,而思想上的碰撞则是通过对比画面、声音与节奏的相互配合实现的。爱森斯坦认为,不同镜头的相互碰撞可以引发观众对影片背后深层含义的思考。在《功夫》开篇的平行蒙太奇中,导演不仅展示了黑帮的暴力和社会的混乱,还通过对比巧妙地展示了贫困社区暂时的安宁。通过这种对比的剪辑,观众在直观感受到黑帮残酷压迫的同时,也得以反思社会底层的复杂局面。这种交替剪辑的手法正是爱森斯坦所主张的,即通过镜头的对立来激发观众的思维活动,进而传达出电影的社会批判性。同时,黑帮出场的音乐多由西洋乐器演奏,带有神秘浑厚的即视感,增强了情节的紧张感与节奏感,引导了观众的情绪波动。最后引出一段上与下对立矛盾的文字:“这是一个社会动荡、黑帮横行的年代,其中又以‘斧头帮’最令人闻风丧胆,唯独一些连黑帮也没兴趣的贫困社区却可享有暂时的安宁。”可见当时隐于时代的小人物独享的片刻安宁是暴风雨前的平静,黑帮和这些贫困社区将在此后有重要的剧情交集,推动了后续的剧情发展,创作者巧妙地将前后因果完美融合,也渲染了时代的压抑感与权威感。通过将荒诞与压抑并置于荧幕之上,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让观众意识到自己在欣赏影片,使观众保持一定的理性思考距离。
为了让观众“无痛”接受黑暗社会的残忍,电影巧妙地将血腥镜头利用场景中真实存在的柱子对肉体遭受惨烈伤害的情景做出遮挡,让这部片子不至于过于暴力血腥。这种叙事策略也体现出电影作为“第七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视听的双重冲击,迅速将观众拉入血腥压迫的情境之中。
(二)洁白无瑕的无声爱情
在电影《功夫》中,爱情的表达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融合了个人风格和功夫电影的传统语境。电影中的爱情并非通过直接的语言或传统的戏剧冲突呈现,而是通过细腻的情感暗示与隐喻手法,使得情感表现更加含蓄且具有层次感。这种表达方式不仅符合东方美学的特质,也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功夫电影中常见的阳刚与暴力主题。
电影《功夫》中的爱情表达是隐晦而非外露的,采用了情感暗示的手法。相较于传统爱情叙事中情感的激烈宣泄,《功夫》中的爱情更多通过视觉符号和细微的互动予以呈现,通过面部表情、肢体语言和环境氛围等元素传达出比言语更丰富和细腻的情感层次。当阿星追忆起过去自己的善良和纯真时,棒棒糖成了他和哑女的羁绊,也成为这段无声爱情的符号,在特定的语境下承载和传达出“爱”的情感、观念与记忆。
阿星初登场时在造型上的不修边幅、凌乱发型与女孩身穿白裙的纯洁形象形成鲜明对比,随着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成长,阿星逐渐从落魄的小人物转变成黑帮中的马仔,又在打通任督二脉后实现了重生,身穿纯白的功夫服,也代表他已经脱胎换骨,完成了身份上的重大转变。但在最后与哑女重逢时,阿星换上了普通的店员服装,这个阶段的他则是从英雄向普通人的身份转换,回归平凡。[1]人物服装上的三次转变,也是其在心态、情绪方面的重大转变,将视觉符号和内心情感表达相结合,可见导演和服装设计师的深厚功底。
阿星对哑女表现出的不同态度也从侧面体现了阿星的成长:从童年时期的保护弱小,到成年后因挫败感而选择欺凌,直至最后功成名就后试图弥补昔日的过错。周星驰导演通过哑女这个角色以及她与阿星之间复杂而微妙的情感纠葛,巧妙地平衡了影片的暴力、血腥,为观众呈现出一个深刻、富有层次的叙事世界,为暴力底色的暗黑社会增添了一抹淡然的轻逸,为电影的叙事架构提供了更丰富的维度,使其在功夫电影类型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与哲学思考。
二、人物塑造:反英雄与反传统的草根边缘角色
(一)人物群像和草根式主角书写
拉康的“镜像理论”在电影的创作和鉴赏领域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主要用于描述婴儿在成长过程中如何形成自我意识的过程。“镜像阶段”的概念来自法国心理学家瓦隆。拉康认为,婴儿在出生后的6至18个月之间,会经历一个称为“镜像阶段”的发展过程。在此阶段,婴儿第一次在镜子中看到自己的形象,并且将这种外在的形象认同为自我,镜像是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是通过观察婴儿对镜像的反应来确定自我意识的发生。[2]
首先,在周星驰的电影宇宙中,草根人物形象无疑是观众“二次同化”后理想中的人物,草根人物形象就如同镜像一般,使观众看到一个与自身境遇有相似之处但同时被理想化的角色。主人公出身低微、生活悲惨,而观众可以将自己的现实困境投射到这个草根角色身上,形成一种“误认”,将角色的奋斗和成功视为自己的理想化自我。主角阿星从最初的失败与妥协,到最终成为正义使者并击败火云邪神,展现了个人成长的历程。这不仅是电影中的情节,还成为观众自我认同的一个“镜像”。观众在观看阿星的奋斗和胜利时,会将这种成功的幻想投射到自己身上,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借助主角的经历满足自己对身份认同和自我实现的渴望。
其次,影片中的功夫并不是主角特有的个人能力,而是融入了一场集体叙事框架,展现出浓厚的集体主体精神,这是群像的特色表达。“猪笼城寨”作为武林高手的聚集地,成为中华民族集体主义的精神缩影。在面对邪恶势力时,众人团结一致抵御外敌,展现出强大的集体力量,也触动了观众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归属感。在这个过程中,“功夫”超越了个人技艺的范畴,而是成为连接个体与集体、传统与现代、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传递了跨时空的文化价值观,共同制造出中华民族集体主义的感动气氛。
周星驰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是玩世不恭的街头混混,他们的言行举止粗俗,颠覆了传统英雄形象的既定框架。这种颠覆性的塑造不仅打破了观众对英雄角色的固有认知,还引发了对社会边缘群体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凸显出“反英雄”与“反传统”的艺术特色。《功夫》中的阿星没有能够立足江湖的本事,唯一被“斧头帮”看上的“开锁”技能也是小偷小摸的类型,他还带着小弟在大街上混吃混喝、撒泼打诨,这种草根式主角的塑造也体现出导演对边缘人物、小人物的怜悯情怀。影片通过喜剧的方式传达了潜藏的悲哀与社会批判,在欢笑之中也带有情感的深度和现实的沉重感。
(二)人物台词与“梗文化”
“梗文化”是指在网络文化和大众传播中,某些特定的词语、句子、图片、视频或事件等被反复引用和传播,逐渐形成固定的表达方式或符号,成为一种集体认同的文化现象。《功夫》作为周星驰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各种台词的“梗”更是被人津津乐道,成为跨时代的文化记忆符号。影片通过鄙陋但不失幽默的语言外壳,巧妙地包裹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实现了“大俗即大雅”的艺术效果。这种语言风格的运用,不仅贴近了观众的日常生活经验,也激发了观众的共鸣与思考。例如,“你想学啊?我教你啊”这句台词不仅在影片中反复出现,成为关键的笑点,也在电影上映后迅速在网络上流行,成为观众引用的“梗”。这种语言上的重复与反讽,不仅提升了影片的喜剧效果,也使得这些台词在网络文化中得以广泛传播。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用戏谑的方式反应心酸和苦涩,用喜剧的形式消解沉重感,这种处理方式不仅体现了周星驰电影“笑中带泪”的美学风格,也契合了后现代文化中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讽刺。
《功夫》中的许多场景直接借鉴了武侠片和功夫片中的经典元素,并对其进行了夸张和戏谑的处理。例如,火云邪神作为反派,带有典型的武侠片反派特质,他使用的“蛤蟆功”既是对武侠经典的致敬,又通过夸张的表现手法成为全片的一个重要笑点。观众对这些经典场景的熟悉感,使得这些“梗”成为与观众互动的媒介。
三、风格形式:颠覆逻辑的喜剧“漫画式”戏仿
(一)“无厘头”的喜剧风格
鲁迅提出了“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独到见解,揭示了喜剧艺术的本质内涵。可以说,喜剧是用戏谑的笔法揭露惨烈的现实,触及社会批判和人性洞察的层面。《功夫》作为这一理念的生动实践,片中笑点密集,阿星单挑猪笼城寨居民、小跟班的飞刀、阿星与包租婆的追逐战等众多笑料百出的无厘头情节,把不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插入重要情节中,在悲剧的底色上铺陈了一层戏谑的笔触,与观众的日常生活形成夸张的反差,而让观影人在这种反差中高度集中并发泄心中的无奈。
在影像风格上,看似与现实逻辑脱离的桥段,并非娱乐元素简单堆砌,而是导演精心设计的叙事手段,是用一种超现实的手法,将观众从日常的琐碎和平淡中抽离出来,对日常生活进行夸张与扭曲,从而创造出一种强烈的反差效果。例如,包租婆的追逐战场景,通过慢镜头和快速切换的镜头语言,刻意放大了人物的身体动作,达到了滑稽且不合理的效果。观众在视觉享受的同时,也通过这种极端化的影像风格体验到无厘头式的荒诞感,进而从中感知现实生活的荒谬性。
周星驰电影成熟时期的作品多以现实主义题材著称,主人公贫穷、自卑,导演用喜剧化的夸张手法在艰难的生活中暴露人性弱点,通过外貌、服饰等视觉性语言反映人物的心理特征和社会属性[3],用喜剧包装悲剧性的精神内核,形似尼采的“日神精神”,即在美好的面纱遮盖下触及深刻的悲剧社会。
从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的角度看,《功夫》中的“无厘头”喜剧不仅是对传统戏剧形式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反思,普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江湖始终是江湖人的战场,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简单的人生哲理用戏剧性、喜剧性的形式进行表达,让观众想参与其中,从中获得审美娱乐的快感,同时引发现实关注、思考。影片赋予观众超越现实的想象空间,寓教于乐,为观众提供了一次深刻的文化体验与思想启迪。
(二)漫画式的致敬与戏仿
《功夫》中充满了对漫画式元素的致敬与戏仿,这种手法不仅增强了影片的视觉冲击力,还为其“无厘头”的喜剧风格注入了更多的表现张力。周星驰在影片中频繁运用漫画的表现技巧,如夸张的动作、极端的表情和不符合现实逻辑的打斗场面,营造出一种超现实的戏剧效果。这种漫画式的致敬与戏仿通过将传统的武侠叙事和英雄形象进行解构和重塑,带来了一种新鲜且具有颠覆性的视觉体验。在《功夫》中,人物的动作设计往往带有极强的漫画化风格,夸张且富有戏剧性,超越了现实的物理法则。例如,在阿星打通任督二脉后,他的动作不仅具有超现实的力量,还融合了传统功夫片和漫画中的表现手法,如腾空飞跃、超高速打斗等。这些动作场景借助慢动作、快速切换的镜头以及夸张的视觉特效,创造出一种脱离现实但令人捧腹的视觉体验。
大拼盘式的背景音乐形成了周星驰烙印的风格,同时其背景音乐也兼具戏剧性、民族性、经典性,在紧贴剧情的同时,赋予观众多重感官享受。[4]其中的配乐、桥段对许多经典的乐曲和影视、文学形象进行戏仿,也就是“拟象”。打斗时使用的音乐《十面埋伏》《东海渔歌》等,不仅营造出了浓郁的民族氛围与战斗激情,还巧妙地带领观众开始了一段跨越时空的怀旧之旅;同时,李小龙的功夫形象、金庸笔下的“神雕侠侣”等经典的隐喻性引用,构成了一种跨媒介的拼贴式艺术组合,让影片充满怀旧色彩,丰富了影片的文本内涵,唤醒了中国观众的集体记忆,也削弱了现实主义的直接性,赋予影片梦幻般的超现实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后现代”的表现手法也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依赖对既有文化的拼贴和戏仿,虽然能够迅速激发观众的共鸣与认同,但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原创性以及思考的深度,也与前文所提到的“梗文化”不谋而合,是快餐式消费与文化复制的现象,往往侧重于娱乐性和传播效率,而忽视了内容创新和深度挖掘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创作者应该在以消费者为靶向的商业性和艺术表达的创新性中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四、结束语
电影是观众的一次想象性满足体验活动。周星驰导演的艺术创作,深刻体现了以轻盈叙事技巧承载厚重社会意蕴的精湛艺术手法,是他能够创作出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的重要思想内核,也是其艺术思想的鲜明标志。他在喜剧风格的框架下融入对现实社会的洞察与批判,通过精巧的叙事结构和幽默风趣的表现手法,将沉重的社会议题转化为大众易于接受且乐于讨论的艺术形式,在笑声中传递出深刻的社会思考和人文关怀。这是一种含泪的笑,这种审美体验是对悲剧元素的温柔消解,也是在观众心中留下深远回响的艺术张力和悠长余韵。
参考文献:
[1]杜厚平.电影《功夫》:影像造型与文化分析[J].人文天下,2020(24):57-59.
[2]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82.
[3]杜衣杭.周星驰电影的角色造型语汇研究[J].当代电影,2021(5):75-80.
[4]李祖玥.浅谈周星驰喜剧电影的悲剧性[J].名作欣赏,2022(26):173-175.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