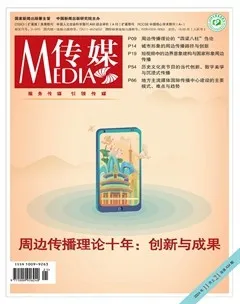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
摘要:汉语言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传承、历史积淀,在历史上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了东北亚国家特别是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本文从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现象和遭遇的挑战出发,提出了当前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的路径优化策略,以期推动东北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关键词:汉语言文化 周边传播 东北亚文化共同体
一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需求、在世界文化舞台和文化市场上的地位,显示了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形象。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各国政府对文化软实力的争夺异常激烈。它们通常都会以语言推广为先导,以语言文化传播为内容,达到增进相互了解和经济文化交流的目的。在此背景下,笔者以周边传播理论作为研究视角,从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现象出发,分析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途径与当前遭遇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路径优化的新思路。
一、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的四个阶段
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历史实践不断证明:“语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和国家地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语言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彰显国家地区影响力的同时,也会带动其经济文化的发展。”汉语言文化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传播,是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经典案例。笔者梳理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历史,总结出萌芽期、发展期、弱化期和振兴期共四个主要发展阶段。
1.萌芽期。对于汉字进入朝鲜半岛的时间,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我国学者敖依昌等人认为,早在周武王分封箕子到朝鲜时汉字便一并传入,因为箕子在朝鲜半岛的教育启蒙活动,离不开语言、文字等施教工具。也有学者认为汉字是汉武帝征服朝鲜政权后建立汉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时传入的。
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相对较晚。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东汉光武帝赐给倭国国王的金印上刻有“倭奴国王”字样,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汉字在日本的证据。南朝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百济人段杨尔将“五经”传入日本,进一步促进了汉语言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2.发展期。公元668年,朝鲜半岛的新罗联合唐朝灭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三国。新罗景德王时期全面引进盛唐文化及先进官制,使汉语言文化在朝鲜广泛传播。公元935年,新罗被朝鲜半岛的高丽国取代。高丽建国伊始就创办国学、讲授中国儒家经典;公元958年,高丽举行科举制,专设讲授、传习汉语的机构;公元1391年,高丽设立“汉文都监”,编印《老乞大》《朴通事》等汉语教科书,培养大量汉语人才。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后势力扩张,与邻国的交流不断增多。此时日本向隋朝派遣遣隋使,文化交流日渐增长。至盛唐时期,日本遣唐使络绎不绝,唐人也不断东渡。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颁发改革诏令,设立太学与地方学校,太学设置明经道和纪传道等科目,学习汉文儒经,这对日本的政治与伦理产生深远影响。唐朝开元年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携130卷《唐礼》返日,促进了日本典章制度的完善。同时,其他种类的汉文书籍也大量流入日本。
3.弱化期。李氏朝鲜时期(1392—1910年),统治者亟须创造一套属于本民族的文字系统。世宗李裪在位期间(1418—1450年)颁布《训民正音》,创造朝鲜民族文字——谚文。
谚文初创时并没有得到迅速普及,上层社会和士大夫仍然使用汉文。当时朝鲜的一些贵族和士大夫认为,使用谚文是摒弃先进的中国文化,使自身成为夷狄之邦。1895年,朝鲜政府颁布“使用国汉文混合体”法令,正式废除汉文。二战后,朝鲜、韩国纷纷进行去汉字化运动,从此汉字在朝鲜半岛使用频率日趋减少。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倡导“全盘西化”,崇尚效用西法,主张放弃汉学。据《日本杂记》记载:“其改政之初,几欲废置汉学,国中所有中国书籍皆贱价出卖,又多为中国人购回,如《太平御览》,一部价才十余元。”虽然日本汉学家不愿放弃汉语,但十九世纪末日本“西化”的政治需要,决定了汉语言文化在近代日本的逐渐没落。
4.振兴期。改革开放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备受海内外关注。截至2023年底,全球已有81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8万多所国外大学与培训机构开设中文课程。
东北亚周边国家相继成立多家孔子学院,加强对包含儒家经典在内的汉语言文化知识和理念的学习。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设立。截至2024年10月,韩国已成立24家孔子学院和5家独立的孔子课堂,数量位居亚洲首位;日本也先后成立了12家孔子学院和2家孔子课堂。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东北亚地区的发展注入新活力,周边国家民众主动聚焦中国,走近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这为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再度振兴搭建平台、打通渠道,亦有利于东北亚地区构建开放、包容的汉语言文化交流格局。
二、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途径
周边传播理论认为,宇宙万象,传播方式多种多样,但一切传播都可以概括为“三体传播”(人体、物体和媒体)。而无论是“三体传播”中的哪一种,其传播模式都首先遵循或者应当遵循能量或信息由原点向周边、由中心向边缘、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圈层式扩散的基本规律。
笔者通过对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历程的梳理,总结了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的“三体传播”途径,具体有移民传播、官方交流、贸易往来与书籍传播等。
1.移民传播。由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毗邻而居,因此民间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其中,移民对汉语言文化在朝鲜半岛的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马韩、辰韩、弁韩)中,辰韩、弁韩均为秦朝百姓躲避苦役逃亡至朝鲜定居所形成,其语言、风俗与秦朝人极为相似。我国汉朝、唐朝、元朝都曾经征服朝鲜半岛,并将其置于我国封建王朝统治之下。汉武帝征服朝鲜半岛后设置乐浪等汉四郡,采用与内地郡县相同的行政体制。
隋朝攻伐朝鲜半岛时,不少士兵无法还乡而滞留于此,新一轮移民热潮带动汉语言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唐朝联合朝鲜半岛的新罗消灭高句丽、百济后,一度将朝鲜半岛置于其统治之下。1283年,元朝征服朝鲜半岛后设置征东行省,从此历代高丽王即位时都要接受元朝的任命和册封。政治统一和两国人口的频繁流动,直接促进了中朝两国文化的交流。
明朝初期,由于东北战乱,包括辽东流民、漫散军、海上漂流民在内的汉民移民涌入朝鲜,并融合到朝鲜族普通民众中。朝鲜对这些汉民移民实行收容安置并给予优待政策,同时进一步吸收中国文化和科技,汉语言文化也得以广泛传播。
2.官方交流。朝鲜与日本都曾经与中国互遣使节,这些政治活动除了强化中国对东北亚地区的影响之外,还直接推动了汉语言文化在朝鲜、日本的广泛传播。
隋唐时期的遣隋使、遣唐使、来华留学生、僧侣等群体,是汉语言文化在朝鲜、日本广泛传播的重要媒介。从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至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的近300年间,日本先后4次派出遣隋使、19次派出遣唐使(实际成行的遣唐使团为12次)。使团的规模最初在百人左右,后来增加到600余人。来华使节团中除大使等官员外,还有一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日本还多次派遣地位崇重的公卿出使中国。例如,第11次日本遣唐使回国时,就迎请律宗名僧鉴真(688—763年)与弟子同行,后来鉴真和尚在日本传播佛教,谱写了中日友好交流史上的光辉一页。此外,日本留学生在中国政府资助下,潜心研究隋唐文化,熟读中国典籍,接受中国儒家文化教育;学问僧主要来中国学习佛法。这些人回国后均积极参与母国政治文化活动,对日本社会变革发挥了重要作用。
3.贸易往来。早在秦朝时期,我国就与朝鲜半岛开辟了“东洋航线”。唐朝同日本、朝鲜半岛间的贸易往来迎来高峰期,大量丝绸、陶瓷等货物由宁波或蓬莱出发,到达新罗的庆州;日本遣唐使团也带来砂金、银等货物与唐人交易,同时购回大量中文书籍、香料等物品回日本出售。此外,日本“唐通事”等机构的设立也促进了中日贸易往来与汉语的传播。
宋元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海上丝路”贸易达到鼎盛。中国延续此前与日本的贸易传统,日本也鼓励本国商人与中国进行贸易。中国向日本出口墨砚、书籍等,而日本向中国出口东京锦等,两国商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媒介。
明朝时期,中日两国在1403年签订《永乐条约》,官方交流得以恢复,亦为汉语言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提供助力。
4.汉籍传播。历史上,汉籍输入朝鲜半岛曾出现过三次高峰: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和明朝初期。其中,明初汉籍输入朝鲜的范围和数量都已远超前代,此时朝鲜王朝不仅大量进口《训蒙字会》《新增类和》等汉文书籍,同时让朝鲜名儒编写各类辞书,以此教育国民、维护国家正统思想。
汉文书籍在日本的传播源远流长。奈良、平安时期,日本文人就有阅读汉诗汉文的风尚。除经史典籍,《搜神记》《冥报记》《长恨歌传》等中国文学作品在日本也广受欢迎。日本人认同汉语言文化且热衷收藏、阅读汉籍,因此前往日本的中国商船经常携售大量书籍。平安时代,日本大臣大中臣辅从北宋商人手里购买《唐音》《玉篇》《白氏文集》等书籍,并进献给朝廷。江户时代,中国商人钟圣玉曾运载93箱、总计86种11000余册书籍到达日本。
三、当前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遇到的挑战
虽然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同属于汉语言文化圈,在文化上有诸多相似之处。然而,随着历史不断发展演进,这些国家将本土文化与汉语言文化、西方文化进行融合、贯通,逐渐形成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系统。不难想象,当前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会遭遇一系列“挑战”,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1.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环境不稳定。首先是各国发展道路不同。在社会制度上,日本和韩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和朝鲜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天然形成东北亚地区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诸如行政实施、法规制定、道德规范、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直接影响这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此外,东北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日本是发达国家,韩国是经济次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朝鲜则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各国发展道路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其在心理认知层面的距离,进而影响东北亚区域一体化发展,也对东北亚地区的语言文化认同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是语言文化属性不同。虽然日语文化汲取了汉语言文化精华,后来又合理吸收、借鉴欧美语言文化的特点,但是它更多地深植于本民族文化中,因此日语文化与汉语言文化存在诸多“文化差异”。例如,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中国语言文化中被解释为“君主按照礼节来使用臣子,臣子以忠诚来侍奉君主”;而在日语文化中却被解释为“家臣必须为自己的君主奉献出全部生命”。孔子所说的“忠”字,在日本被解读为“一种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忠诚”。在此背景下,东北亚地区不同语言文化间所产生的“文化折扣”现象,无疑影响了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效果。
最后是价值观念取向不同。自古以来,日本就深受中华文化影响,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行为方式与社会制度等。明治维新后,日本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不仅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也全盘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浸染。这虽然造就了日本文化的兼收并蓄特点,但亦使日本人在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面前无所适从。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造成日本国民矛盾性的主要原因是它对不同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借鉴。由于当前日本文化的多元与西化,汉语言文化在日本的周边传播必然要面对文化差异与中西方价值观念冲突,难以达到预期传播效果。
2.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内容待整合。首先,汉字的演变与发展、汉字的文化要义、汉字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与独特文化特征等内容,尚未在东北亚地区得到充分挖掘和揭示,导致东北亚周边国家民众对于汉语言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出现偏差。
其次,我国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时,需考虑目标受众对汉语言文化的真正需求。我国对外汉语教学者习惯使用一套“统编教材”。千篇一律的传播内容使汉语言文化难以被完全理解和接受,导致传播效果不佳。
最后,我国在加强与东北亚地区国家的经济领域交流合作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各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当前的一些文化交流项目存在着形式老套、缺乏新意的问题,难以在东北亚地区国家受众中引发情感共鸣。
3.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途径不畅通。第一,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传播的主要途径仍是报纸、广播、电视、书籍等传统媒体渠道,其单向度的传播方式缺乏反馈与互动机制,导致东北亚地区民众参与度较低,难以实现周边传播目标效果。
第二,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应力避灌输式、倾倒式、说教式的宣传思维,力避忽视海外受众的实际信息需求、接受心理,力避造成“传而不通”的结果,唯此方能使汉语言文化的东北亚周边传播达到预期效果。
四、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周边传播路径优化
周边传播理论认为:“万物皆有周边,万物之间的关系都是引力与斥力、传播与被传播的关系。和被周边传播现象一样,向周边传播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及媒体之间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对待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工作,我们要处理好传播理念、传播主客体、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渠道等问题,以汉语言文化为契机,促进东北亚地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
1.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所谓“文化共同体”,是指隶属于相同或相似文化区的人群以某一共同关心的文化现象为纽带结成的文化群体,其中包含“经济文化类群”和“历史民族类群”。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周边传播现象,更多体现出“历史民族类群”特征,即特定区域的居民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性、长期联系和相互影响,形成了相同或相近的文化日常生活特征。
中国与日本、朝鲜半岛国家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而居,在宗教信仰、伦理思想以及社会价值观等方面均具有共性。数千年来,东北亚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互影响、取长补短,同属于儒家文化圈,因此各国文化虽然具有一些差异,但并不是完全对立。
笔者认为,构建“东北亚文化共同体”不仅有利于增进东北亚各国人民间的情感联系和相互理解,还能为汉语言文化的周边传播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推动东北亚地区不同文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2.官民并举驱动汉语言文化传播。一方面,以政府为主导传播汉语言文化。政府统筹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资源与力量,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当前,我国亟待制定一套科学、系统、全面的政府驱动顶层设计方案,通过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引导,整合现有文化资源和行政资源,推进汉语言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广泛传播。
另一方面,以民间力量为辅传播汉语言文化。作为官方渠道的有效补充,民间力量亦是汉语言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可以通过国际会议、经贸交流、互访、游学等方式,在东北亚地区团结更多文化群体,面向东北亚地区民众“讲好中国故事”,使民间力量成为传播汉语言文化的中坚力量。
3.运用融合媒体进行多样化传播。一方面,以传统官方媒体为主传播汉语言文化。传统官方媒体是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重要力量。在汉语言文化的周边传播中,官方媒体应以其权威性、公信力和专业性,准确、及时地传递汉语言文化的核心内涵,让海外民众全面了解汉语言文化魅力,亦使汉语言文化传播更加体系化、制度化。例如,为满足海外汉语言文化学习者需要,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联合中央电视台于2002年共同开办汉语竞赛综艺节目《汉语桥》,以赛促学,开设“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在竞赛中加强各国汉语言文化热爱者间的交流。
另一方面,以社交媒体为辅传播汉语言文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全媒体为汉语言文化周边传播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和更加丰富的形式。首先,运用社交媒体平台,如微博、抖音、小红书等,打造汉语言文化的线上传播矩阵。其次,利用视频平台和线上平台,如B站、YouTube等,发布关于汉语言文化的纪录片、教学视频和综艺节目等,如《汉字五千年》《字从遇见你》《史说汉字》。这些节目利用视频平台讲述汉语言文化的演进历史,让广大网民深刻感受到汉语言文化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4.大力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事业。首先,加大对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注重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师队伍;积极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开展国际中文教育合作,拓宽交流渠道;建立健全科学的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并持续改进。
其次,鼓励国内普通高校与国外语言文化机构加大合作深度与广度,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切实增加我国高校人才输出的份额占比。
最后,为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特别是应届毕业生志愿者,提供充分、完善的就业保障措施,帮助完成外派工作的志愿者顺利实现二次就业,为其创造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
(作者郑敏系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东北亚周边传播研究院院长;赵一潇 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周边传播理论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17ZDA28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肖潇.“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北亚地区汉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
[2]陆地.周边传播理论在“一带一路”中的应用[J].当代传播,2017(05).
[3][日]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M].徐世虹,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
[4]陆地.周边传播理论范式的建构和深化[J].当代传播,2021(03).
[5]韩志斌,马云飞.国家建构、政治文化与政治危机——中东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三维考量[J].西亚非洲,2024(03).
[6]戴蓉.孔子学院与中国语言文化外交[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7]敖依昌,樊菀青.汉字在朝鲜的命运与朝鲜人价值观的变化[J].湘潮(下半月)(理论),2007(02).
[8]董明.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M].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2002.
【编辑:曲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