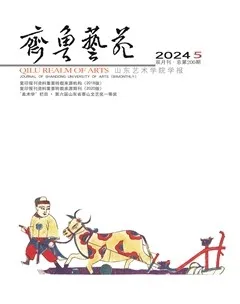论当代跨媒介艺术的触觉参与特性
摘 要:后/疫情时代,艺术需要发挥参与功能。艺术的参与功能与怎么参与艺术有着紧密的联系。当代跨媒介艺术以触觉感知为中介,让观众作为活跃的主体参与艺术生产,在触觉式参与路径中,艺术通过对艺术欣赏整体的建构,参与到社会、自然和生态关系中,发挥艺术的影响力。触觉审美在行为、感知与情感上的特性内在地通向生态意识的具体内涵,在审美视域下触觉关系和生态关系呈现耦合状态。
关键词:跨媒介艺术;艺术参与;触觉审美;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36(2024)05-0113-08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人类所关注的主题。在后/疫情时代,艺术更加需要施展参与功能,在生态公民的重塑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代艺术发挥参与功能的方式,与传统的艺术参与方式表现出很大不同。以当代跨媒介艺术为例,当代艺术在与艺术欣赏者的合作过程中实现参与功能。由于对多种媒介的运用,当代跨媒介艺术作品往往要求艺术欣赏者更多感官知觉的共同参与,通过和艺术家一起创造艺术情境来“在艺术事业中持有权力或承担份额”[1](P5),从而实施艺术的社会功能。这种审美范式的转换意味着艺术把目标转向了艺术欣赏者,通过对艺术欣赏者整体的建立,参与到广泛的社会、自然和生态关系中。在艺术欣赏者的中介作用下,“艺术参与什么?”与“怎么参与艺术?”有了紧密的联系。重要的是,通过艺术欣赏者中介,当代审美范式的转换与亟待解决的生态意识培养之间产生了隐秘的联系。当代跨媒介艺术激活观者主体,对观者进行重塑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让触觉加入审美活动。当代跨媒介艺术通过触觉进入观众的整体存在,观者也通过触觉加入艺术生产。艺术与观众或者公众在以生态关系为指向的艺术中,通过触觉共同承担生态责任,参与生态意识建设。由此,我们试图从触觉的客观属性——行为、感知和情感三个层面进行阐发,进而发现触觉的参与内涵,敞开一条艺术参与的道路。
一、触觉的行为特性及参与内涵
在艺术史中,对视觉和听觉的推崇远高于触觉。直至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家们,重新审视人类感官经验的多重性,让人们意识到对视觉和听觉的过度信任,和对其他感官知觉的忽视。这一突破性的思考在艺术中也有反映。赫尔德在其1778年出版的《雕塑论》中把雕塑界定为触觉的艺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同样认为雕塑和绘画需要从感官上进行区分:“前者叫做塑性艺术(雕塑),后者叫做绘画。二者都使空间中的形象成为理念的表述:前者使形象对两种感官成为克制的,亦即视觉与触觉(虽然对后者来说意图并不在于美),后者使形象只对于视觉成为可知的。”[2](P335,336)李格尔从知觉方式上,重新考虑艺术史,把“触觉”引入艺术史的研究。他认为艺术史不能局限在视觉艺术,在《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一书中,他的艺术发展史划分方式是:“触觉——近距离观看(古埃及)→触觉—视觉——正常距离观看(古希腊)→视觉——远距离观看(罗马帝国晚期)。”[3](P3)
无论是赫尔德、康德还是李格尔,都是基于传统艺术的感知方式对触觉进行强调。因而,“触觉”在他们的理论中是与视觉相对立的一种感知,更加地从视觉无法达到的直接触摸的意义上使用触觉。而当代跨媒介艺术中的触觉已经超出了直接触摸的含义,是在一个开放性的意义上使用触觉。正如加令顿所认为的:“触觉应该理解为一个开放性的词汇,用来指涉下列一种或多种体验:触摸(人类皮肤、皮下组织、脏器和相关神经末梢的主动的和被动的体验)、运动感觉(身体对自身运动的感觉)、本体感受(身体对自身的空间位置的感觉)以及前庭感觉(依赖于内耳的平衡感)。”[4](P16)因此,当代跨媒介艺术的知觉方式呈现的是身体实践的整体性,其中不仅包括触摸的动作,还包括身体实践的行为姿势和身体动态的统一性感觉。当代跨媒介艺术是从广义的触觉定义基础上,在艺术中展开对触觉的运用。
任何艺术类型和艺术作品都需要审美活动加以实现,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当代跨媒介艺术中,行为不是在艺术作品之外,而是直接以身体实践本身为审美对象。这意味着艺术欣赏者通过行为直接参与艺术作品的意义生成,而当行为本身成为审美对象时,艺术欣赏者获得的审美体验也有了区别于其他艺术的意义。跨媒介艺术的行为参与方式让人从文字和图像的世界暂时脱离出来,恢复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实践方式,在活生生的感知状态下,呈现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在关系,这是当代跨媒介艺术通过触觉参与到生态意识建设的主要路径。
其一,利用行为的情景特性,当代跨媒介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字导致的意义与语境的分离,唤起数据和文字中的行为意义。行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相对于文字更加亲密。行为能够把文字重新放回情境性、操作性的空间里,让人在生活的基础上考虑文字的意义,而不是相反。跨媒介艺术作品通过当下直接的艺术反馈,让语词从思维信号转化成行为方式,这一过程实现的是从认识“生态”到体会“生态”的转变。例如,交互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和地质学家米尼克·罗辛(Minik Rosing)共同创作的公共艺术品《冰上守望》(Ice Watch,2014,2015,2018)。他们向公众展示了来自格陵兰岛努克外围峡湾的80吨冰块,在公共广场上,十二大冰块在公众的触摸和守望中逐渐融化。冰块融化的过程,是气候挑战的数据在艺术欣赏者头脑中逐渐演变为清晰的感官感受的过程。触摸冰块的感觉带来的寒意,无法留在城市的广场中,一切人类对冰川带来的伤害都在滴水声中,声声入耳。正如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所说:“让我们欣赏这个独特的机会——我们,世界,现在能够而且必须采取行动。让我们将气候知识转化为气候行动……使以前看起来相当抽象的东西更加现实。”[5]触觉行为的直接参与特征让艺术欣赏者能够尝试着贴近认知对象,在“与之共处”的情况下达到与之产生共鸣和认同的境界。让文字不仅仅呈现为某个概念,而有可能从自身的角度去考虑其中的意义。作品中“冰川”“融化”等概念,就比文字和数据更加真实地体现在艺术欣赏者的感知中。这种更加真实的感知,让人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人类对地球造成的影响,体会到人类作为宇宙生态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和采取的行为。
其二,跨媒介艺术借助行为的实践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视觉逻辑所导致的人与真实世界的第二次分离,呈现行为的真实效应,并在揭露人类行为无法忽视的影响基础上,把人的行为效应推到极限让人们看到它背后残酷和杀戮的可能。由此,还原我们与世界的真实的、本质的和纯粹的联系。只有在这个联系上,生态得以被具象化,而生态与我们的意义才能够在血肉而不是图像上被认知。
我们已经生活在信息与真实世界的第二次分离的世界,也就是“拟像”(simulacrum)世界。“所谓‘拟像’就是没有原物的摹本。”[6](P34)鲍德里亚说:“图像与任何一种现实都没有关系:它只是自身的纯粹的拟像。”[7](P34)“拟像”不同于表象,虽然它们都是被附着意义的视觉形象,但是“拟像”无法回到再现和表现的世界,它不可能在“真实世界”里找到其中的所见之物。“拟像”世界意味着人与“真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如何在“拟像”世界的压迫中重新与世界建立本质上的联系,是生态意识建构的重要问题。在《知觉现象学》中,梅洛-庞蒂提出了一个方法,就是将主体由意识还原到知觉,知觉是具有身体性的,在身体性的知觉中人与世界具有一体性。“本已身体在世界之中,就像心脏在机体之中:它持续地使可见的场景保持着生命,它赋予之以生机并内在地滋养之,它与之形成一个系统。”[8](P281)
当代跨媒介艺术所诉诸的触觉审美得以实现的前提就是承认参与者的身体存在,用运动感官或触觉感官来补偿视觉逻辑,在实际处境中让“拟像”的依据在参与者的审美活动中消失。注重在作品中体现时间意义的新媒介交互艺术家珍妮弗·霍尔(Jennifer Hall)的作品——《世间果实的针灸疗法》(Acupuncture For Tem-poral Fruit,1999)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作品用由西红柿、电动机、针灸用针和用来检测观众距离的声纳设备组成的许多电子装置单元来记录艺术欣赏者的动向,当艺术欣赏者进入作品范围时,声纳设备会感受到然后触动发电机带动针刺进西红柿,当观众距离单元越近时,针就会越激烈地穿刺西红柿,经过一段时间后,水果会变瘪,并且会夸张地长出霉丝。这个作品让人联想到生命、伤害等内容,西红柿生命状态的变化记录了艺术欣赏者进入这个空间所留下的轨迹,就好像是他们在这个空间的时间导致了西红柿“血液”的流失。时间在这里作为一个清晰的事件标示着艺术欣赏者的存在。在进入作品的过程中,参与者没有和自己的身体分离,或走向虚拟的图像世界。他们通过身体行为与作品产生联系,在交互活动之后,参与者得到的“仅仅是他的身体,而他的身体是针对某个世界的能力”。通过身体所生发的所有触觉的整体感官,参与者在作品中不仅获得了知觉的某种还原,更重要的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上得以产生新的解释。在审美意义上,世界对于参与者来说不是客观空间,而是身体的家园。他们通过熟悉的活动,把身体安顿在周围环境中,在其中产生实在的行为效应。艺术的世界对标的就是客观的世界,甚至是更为真实的世界。当参与者用身体和触觉感受与作品的联系之时,通过艺术的诠释和审美的效果人类与环境和生态之间得以在生命的意义上产生共鸣,而这是生态意识得以发出光亮的时刻。
其三,跨媒介艺术触觉行为的情景特性和实践逻辑,内蕴着一条通向中国艺术家进行审美体验的方式和中国艺术精神的线索。在这条线索之中,艺术欣赏者得以使用中国艺术“以身践道”的审美体验方式,参见中国艺术精神包含的“天地境界”,认识到“在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大全的整体,就是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还是宇宙的一个成员。就社会组织来说,他还是一个公民;但他同时还是一个‘天民’,或称‘宇宙公民’”[9](P295,P297)。
跨媒介艺术的行为参与方式恢复了艺术生产的原初过程,让艺术欣赏者用艺术家的方式去体验世界,在一个诗意的关系上体现人与世界的互动。艺术的世界是一个灿烂丰富的世界,所谓“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10](P109),“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灵想之独辟,总非人间所有”[11]。但,艺术的境界,不是凭空出现在艺术家的心灵之中。宗白华在谈到艺术境界时,一再强调心灵与自然、世界、宇宙的沟通,他说:“美与美术的源泉是人类最深心灵与他的环境世界接触相感时的波动。”[12](P81)
在中国艺术中,“美”不是空泛的理想化状态,不是科学实验中取极限值的完美状态,而是寓居于生活中的一种与自然相通的“合适”状态,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在生活中的展现。艺术家的审美体验是直接的,但是他们通过作品与观众的沟通,却需要经历媒介的编码和解码过程。艺术家在审美创作之前的审美体验中是用身体实践,但是在艺术作品中却把身体实践压缩在视觉和听觉的空间中。这个现象在西方艺术中表现得极为明显。黑格尔在《美学》中明确提出:“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13](P48)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跨媒介艺术的触觉行为方式,以身体为媒介,取消了视觉和听觉符号的二次编码,在具体的行动中调节了灵与肉的紧张关系。徐复观提到,老子和庄子“所说的道,若通过思辨去加以展开,以建立由宇宙落向人生的系统,它固然是理论的、形上学的意义(此在老子,即偏重在这一方面),但若通过工夫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认,则将发现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这一直要到庄子而始为显著”[14](P29)。可见,无论是在审美创作之前的体验,还是审美创作之后的体会,艺术精神的追求都是从身体实践开始,最终归为身体实践。当艺术欣赏者用艺术家的审美体验方式去开展审美活动时,更加接近的不是理论的、形上学的审美意识,而是现实人生的审美境界。
身体的行动可以达到与自然无碍的状态,以身体感官与自然相遇相知,最后归为和谐,归为合一。“万物一体本是人生的家园,人本植根于万物一体之中。”[15](P337)中国艺术精神支持身体实践的艺术性,并且把身体实践放到万物之中,以回归自然为目的。艺术欣赏者可以通过身体实践体会更为深远广大的爱,这是以天地为立足点的大爱。生态意识的最佳解释就是中国思想家追求的“大爱”。
二、跨媒介艺术的感知特性及参与内涵
跨媒介艺术诉诸行为和身体感官不单是为了寻求艺术表达方式上的突破,其目的在于通过触觉的感知特性,让生命之间有更多共鸣。在当下,我们需要对生态环境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保护。而采取措施的根基在于人类的生态意识。建立良好的生态文明所需要的生态意识,必须完成从个体的自我意识向共生的生命意识转变,回到自然和宇宙整体之中,重新思考人的存在方式的合理性。在这方面,触觉的感官特性具有通向生态意识的优势。
触觉具有独特的“双重性”,即触与被触的双重统握,“同样的触感觉,既被统握为‘外部’客体的特征,又被统握为躯体—客体的感觉”[16](P122)。触与被触的交织,为总是指向自身的意识内在性找到一条通往外部世界及世界中他人的道路,打破沉思者的孤寂。触觉的双重性从主体能力方面保证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这个主体能力不同于“反思性的判断力”。在“反思性的判断力”中,人类看似个体的审美经验通过能够反思到愉快情感的判断力获得共通性,但客体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就是客体存在的不可侵犯。可见,反思性的判断力所指向的通向他人的道路是抽象的。从反思推到他人,所强调的是设身处地地“想象”,目的不在于对他人处境的主动关心和操劳,而服务于对他人之心的客观认知和理解。
触觉的道路通向具体的人和物,在没有距离的相互遇见中,触觉面对的是整体的人,包括人的不完美,人的伤痛和苦难。最重要的是,触觉没有中心,物与我之间在触觉的交织 中没有主客。在触觉之上,物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是平等的。因为,在触觉之中,“事物进入我们,我们同样也进入了事物”[17](P153)。人在大自然中的一切活动,正如触觉活动一样,是相互的。人对大自然进行研究,展开实践,大自然也同样给我们带来影响。可以说,人存在于世界之中,与万物共同存在的证据,在触觉这里最为明显。在触觉模糊的情感中,人不需要区分出一个独立于世界之外的我,不需要依靠与他物清晰的边界来具体化、实体化自我的概念,触觉给予人类的就是万物的直接存在,是自然给予的人类的原初存在感觉。这也是触觉被称为“元觉”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触觉的直接性与生命具有内在联系。在狩猎和采集时代,感知能力与生存机会密切相关。原始人可能具有相当敏锐的嗅觉、视觉和方向感。因为,感知信息对于他们来说是事关生存的信息。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说,“在现代生产条件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的堆积”,而“景观不是影像的堆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的社会的关系”[18](P3,4)。在当下媒介技术更为成熟的社会,人的所有都被投射出去,变成了抽象的符号和虚拟的影像。生命的体验和存在的实证性,从拥有走向了显现。在苍白的表象和景观之下,媒介物的中介作用已经变成了一种杀戮的力量。因为,媒介把直接地经历的一切,我们所有的生活都转化成了表象。生命失去了应有的现实基础,人们无法承受生命的重量,便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对他人的悲哀只留下抽象的悲悯,更遑论其他生物的伦理关怀。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需要寻找解决的办法,而突破口就在于触觉。居伊德波在书中提到,景观社会两重根本的罪恶——缺乏时间感和取消地方性。触觉恰恰需要真实的时间和地点。“触觉直接地无需中介地通向真实性”的特性,能够让人在“活”的状态中体会“生”。触觉获得直接性的保证在于,触觉可以脱离中介物的束缚,人只要有意识就有触觉。其他,“光线、黑暗、声音、气味都不能对躯体施加作用”[19](P63)。视觉需要光线,听觉需要声音,而触觉可以目盲、耳聋,感觉的真实本质却不因此而丢失。相反,当我们闭上眼睛、堵住耳朵,站立于世界之中用触觉去感知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更多关于世界的言语。例如,大地的坚实、风的速度、空间的大小、空气的温度等等,这些都是空洞的符号无法复制的。由此,触觉可以消除符号、影像的控制,让人得以从个人的镜像世界走出来,毫无顾忌地拥抱真实世界。而当我们,以纯粹的身体拥抱自然、宇宙之时,我们就不以单薄的个人面对上帝。我们身后是与我们同为一体的自然和宇宙。
触觉还具有多重感官特性。多重感官共在是跨媒介艺术的共同特征。跨媒介艺术不仅需要观者触摸、运动感觉和本体感受,还运用了视听媒介,允许观者进行多感官的共同参与。多重感官共同作用是活动的基本要求,虽然艺术时常根据人的感知方式被划分为视觉艺术和听觉艺术,但任何艺术欣赏活动都需要多重感官的参与。在以往的艺术理论中这种感官的共同协作会被归到“通感”的领域。“通感”并非感官实际接受信息产生反馈,而是建立在联想和想象基础上的感觉,或者说“联觉”。“通感”的效果不需要实际的身体作用,更类似于幻觉。
多重感官共在在艺术活动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真实共在。有学者称之为“共感知”(polysensoriality),“指向的是各种感官知觉之间的综合、共存和统一性,也指向对感官等级制或中心论的结构,以突显各种感官知觉及认知之间的平等性”[20]。跨媒介艺术中多重感官共在的性质显然偏向“共感知”所指向的含义。跨媒介艺术让身体在场,利用身体对空间和时间的接受性实现审美体验的整体性。跨媒介艺术的场景生产机制,把艺术空间变为“容器”,能够容纳观者希望放入的内容,包括物、装置和语言,艺术欣赏者可以在其中获得真实的感官信息和行为反馈,使用体感交互技术(动态捕捉)和无限惯性体感技术的跨媒介艺术可以反馈行为的更多信息。跨媒介艺术感官共在的真实性,还隐含着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审美特性。跨媒介艺术让感官停留于在场的场景,试图达到的是让身体与场景之间的联系脱离意识形态上的想象关系和日常生活的有目的性的占有关系,从整体性的感官中重建审美体验和存在经验。借用媒介技术,跨媒介艺术中身体与场景的感知方式,不仅局限于刺激-反应或符号互动,而是扩展到现象身体一体化的探讨,对感官平衡的重新强调,以及世界与个人之间联系方式的扩展或回归。
对此,我们以兰登国际(Random International)在MoMA美术馆展出的《雨屋》(Rain Room,2012)为例加以说明。《雨屋》运用体感交互技术,通过天花板上的装置,进行人体数据与像素的采集。对像素信息处理过后,得到人体的位置坐标,接着控制顶部水流喷头的开关,完成人体动作对水流的控制这一系列的效果。当艺术欣赏者进入其中又通过物体感知技术让雨滴避开人体时,既感受了一场雨,又隔离了下雨的直接感受,不用担心衣服被雨淋湿,不用担心感冒,不用担心雨的冲击。艺术欣赏者只感到雨的亲切和熟悉,沉浸在一片雨声中,漫步在无边的丝雨中,仿佛那句诗“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一般(秦观《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尽情地享受这雨带来的所有情感,所有愁思。
在这里,人与场景之间的互动取消了日常生活场景中自我展现的身份定位,以及规范自己的行为去适应各种不同角色所应该具有的行为标准。作品中下雨的场景不指向打伞和躲避,不意味着寒冷和危险。身体的决定权从场景定义转向了艺术欣赏者,人们在雨屋中跳舞、打闹、奔跑,甚至亲吻、拥抱、求婚。这种全身心的参与,在符号、技术所规定的社会实为罕见。艺术欣赏者在跨媒介艺术场景中体会到的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场景意义的解放,是人类对他物的关怀不再以利用为目的,而是一种纯粹地欣赏,是对万物存在的极度尊重。正如海德格尔对“人的自由”的定义——“自由不意味着自我的无任何限制的通行证,而是人类此在具备‘让万物成其所是’而不是仅仅把他们当做工具的能力”[21](P246)。
如果说,跨媒介艺术通过“行为”参与了宇宙生命整体的建立,那么跨媒介艺术通过“感官”参与了存在者整体的建立。触觉的双重性、直接性和共感知性,在跨媒介艺术中塑造的是对他人和他物具有包容性和接受性,对生命具有敬畏,与自然无限亲近的艺术欣赏者。相应地,此类艺术欣赏者对人类在地球的位置有着更加清晰的认识,对人类的生态环境有着更多的关怀,对人类的行为有着一定的反思。而这些是生态意识的基本内涵。跨媒介艺术作品通过激发出艺术欣赏者的生态意识,发挥了艺术的参与功能。
三、跨媒介艺术的情感特性和参与内涵
“旧有的过去了,将能取而代之的却依然悬而未决。”[22](P446)詹明信曾把“情感的消逝”称为后现代文化的第三个特征。这个词背后蕴含的是他对“社会的‘他物’(other)不再是大自然了”,且极为可能在后现代被界定为“科技”的担忧。[23](P448)詹明信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这个“祛魅”的时代,艺术的处境十分复杂。艺术是否还有“灵魂”?艺术是否还需要情感?如何激活情感?这些问题是今天必须面对的。而对这些问题的根本回答,不能简单地进行否定和肯定。情感是艺术的灵魂,但是情感是被建构的,“情感的消逝”既与人类过于关注主体的主动性和超越性情感相关,也与文化对情感的建构方式有着直接的关系。跨媒介艺术在此时参与情感的建构,其被动性体验和结构化时间的身体实践,所建构的是不同的情感内涵。
人类的主体性一直建基于主动性之上,而“当人类身上那些本质性的主动能力(认知、意志、欲望等等)都日渐被人工智能所操控和捕获之际”[24],人类对机器唯一不能复制,却依然以主动性为依据的情感必然产生动摇和怀疑。正如人类失去了孩童时期情感体验的纯真,就开始不相信情感的存在。因此,“情感的消逝”的根源从来不是情感是否存在,而是人类体验情感的方式是否正确。在后人类时代,艺术重获生命所需要的情感体验方式,不是主动性的和超越性的,而是被动性的。因为,被动是承受。“从根本来说,这就是生命的重量;它是生命对于自身的体验。正是由此,生命得以面对自身而处于彻底被动的地位。……生命在一种苦痛以及此种苦痛之苦痛(a suffering of this suffering)之中承受(undergoing)此种体验,此种苦痛要比任何自由都更为强大。”[25]
触觉可以让身体的被动性体验实实在在且直接地实现。触觉本身就是被动性的。在“精神性盲”病人施耐德的陈述中,他提到,在生活中“我感觉到各种动作是处境的结果,是各种事件本身之连续的结果;可以说,我和我的各种动作只不过是整体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我几乎意识不到自愿的主动性,……一切都完全独自运行”[26](P153)。这是在把身体交给世界之后,所获得的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建立在生活中身体与物体之间的被动性关系上。被试者面对熟悉的剪刀、针和工作,不是在认知的条件下去调动身体,在客观空间中找到针和线的联系,而是在面对它们时,已经被剪刀或针的知觉调动起了相应的能力。正常人可以用想象来减轻身体处境所给予的意向任务,被试者却不能离开身体所处的空间和处境给予的习惯性和具体性的任务。被试者的身体承受着世界给予的一切,正如梅洛-庞蒂所说,“他仅仅是他的身体,而他的身体是针对某个世界的能力”[27](P156)。
跨媒介艺术试图达到的正是把身体放到实际处境中的效果,是真实的感知和生命重量。如,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作品《介导运动》(The Mediated Motion,2001)。作品通过控制湿气制造“雾”的天气效果。在大雾弥漫的空间里,艺术欣赏者的感官失去了指向,一切都被雾所掩埋,只呈现出虚无。人们消失在“雾”中,能看到的只剩下自己的身体,但反而得到了更多。因为,这种虚无具有悲剧的力量。人在虚无中无所适从的时候,才会去怀疑感官的真实性,世界的真实性,最后必然会回到哲学问题——存在的真实性。这种怀疑产生的结果,在艺术欣赏者这里,肯定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在对他人的呼唤中再次对世界和自我的肯定。其中蕴含的是,从取消自身到确认自身和他人、世界的整体性存在的心理过程。可见,处境给予身体的,是思考无法达到的整体性存在。艺术欣赏者在身体参与的基础上,感受到的不是个人的情感,而是个人与他人和世界之间无法分离的集体感和归属感。在后人类时代,人类需要的正是与其他人类和非人类存在者的无法分割的联系,如此才能在“存在者整体”和“宇宙整体”的意义上,参与公共生活。
另外,情感的内容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詹明信提到的“情感的消逝”在社会的层面上,其本质是文化作品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对身体使用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习性的断裂。“情感”是实践的堆积,是历史留在我们身上的痕迹,无“时间性”和“深度感”的情感就是历史时间在当下的精神文化中被隔离,无法在我们的身体惯习上体现,如积聚民族和时代传承的习俗与禁忌,对某些事物的莫名敬畏和熟悉,这些事物在我们的生命中不再产生历史意义,即布尔迪厄称之为身体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通过结构化时间和空间建立信从关系的过程被干扰。在孩童建立原始信念的过程中,这个干扰过程呈现出实质性。“处在孩子和世界之间的是整个集团”,孩子处于物体的世界中,“物体的世界类似于一部书,在这部书里,任何东西都在用隐喻谈论所有其他的东西,而孩子则在该书中阅读世界。而且,这部书是用身体阅读的,不但是在造就了物体空间的、且由该空间造就的运动和位移之中被阅读,而且要借助这类运动和位移来阅读”[28](P119)。
习性的断裂和情感的“无深度感”现象,本质上是用身体阅读物体世界的方式被改变,也就是在文化作品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对身体的使用方式的改变。结合詹明信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将“无深度感”和当前社会以“形象”(image)及“摹拟体”(simulacrum)为主导的新文化形式相联系的观点,以及他在《文化转向》中所说“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着形象生产”[29](P137)。可以认为,后现代文化集中于视觉形象的文化生产方式,例如电视、电影、手机等以形象生产为主的技术设备,改变了人们接受文化作品的身体,技术媒介作为人的延伸,被纳入人的感知系统中,身体与技术媒介组成了新的身体结构,这种新的文化与身体的关系消解了情感的深度。
触觉审美通过对身体的安排,把时间结构化为身体状态,重新将情感放到社会的重大关系中。艺术分类把声音艺术放到时间艺术当中,因为声音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旋律。实际上,相比于声音的时间性,身体在空间中的实践把时间化为身体状态,形成实践时间之实在性。实践时间的身体化是物体世界的隐喻,是宇宙结构本身予以物体的结构化产物。在跨媒介艺术中可以看到艺术家极力将宇宙结构放到身体的时间安排上,试图通过结构化时间,让身体阅读宇宙隐喻的努力。奇点艺术科技艺术家打造的《千里江山图》沉浸互动艺术空间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结语
经由前文的缕述和论证,我们可以初步达成三个基本的结论。
首先,触觉加入审美体验,是应对符号关系思维和技术理性所营造的审美幻象的有效手段。在此之上,触觉本身的感知特性也是重建人类关系的可行方式。虽然,触觉在西方文化中一直被排除在审美活动之外。但,触觉可以重建感官连续性。触觉审美也内在地支持“生态中心主义”,而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至上宗旨相违背。由此,当跨媒体艺术作品以生态问题为主题时,触觉体验,相对于其他感官来说,能够更大程度地引起艺术欣赏者的共鸣,保证作品与艺术欣赏者之间的平等关系。
其次,触觉行为成为审美对象,亦得以把人类意识与行为的联系揭露出来,并在无媒介介入的情况下,展现行为和真实情景之间的互动,以及行为者应该承担的行为责任。行为的力量得以对抗思维的冷漠。触觉审美呈现出从西方视觉艺术中有距离的静观转向中国艺术中“以身践道”的倾向。而中国艺术家的审美体验方式内接的是亲近自然和天地的中国艺术精神。当代跨媒介艺术家,把触觉行为放进艺术创作的考虑中时,必然要面对行为对象、行为环境和周围世界,由此从中国艺术中获得更多的启发,以天人自然和谐的关系为最终目的。
最后,当代跨媒介艺术的触觉感官,不仅以被动性重拾艺术体验之丰富,在苦痛和承受的基础上回顾主体性的根源,用体验之力回应生命之思,找到基于生命联系的归属感,回到自然和宇宙的家园;而且触觉结构化时间的身体实践方式,给予体验之力深刻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内涵,把图像所见证的人类最深刻的经历,展现为身体状态,让人类情感落实在时间长河的积淀中。
参考文献:
[1]Suiti Bala.The Gesture of Participatory Art[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18.
[2]李秋零主编. 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 实践理性批判 判断力批判[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3]李格尔. 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M].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
[4]Abbie·Garrington.Haptic Modernism:Touch and the Tactile in Modernist Writing[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3.
[5]广场上的圆形冰块艺术装置[EB/OL].(2022-03-19)[2024-01-30].https://mooool.com/ice-watch-2014-artwork-by-olafur-eliasson.html.
[6][7][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 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8][26][27][法]梅洛-庞蒂. 梅洛-庞蒂文集(第2卷) 知觉现象学[M].杨大春,张尧均,关群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9]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修订译本)[M].赵复三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10]俞剑华编著.中国历代画论大观(第6编)[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
[11]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EB/OL].(2024-03-08)[2024-04-08].https://www.163.com/dy/article/H45D4LED0521BMH5.html.
[12]宗白华. 艺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3][德]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4]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5]张世英. 哲学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6]胡塞尔. 现象学的构成研究——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7][法]梅洛-庞蒂.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 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8][法]居伊·德波. 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9]苗力田主编.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0]赵奎英.当代跨媒介艺术的复杂共感知与具身空时性[J].文艺研究,2021.
[21]Michael E. Zimmerman.Heidegger, Buddhism, and Deep Ecology[G]// Charles B. Guigno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23][美]詹明信,张旭东编.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明信批评理论文选[M].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4]姜宇辉.艺术何以有“灵”——从米歇尔·亨利重思艺术之体验[J].学术研究,2020,(10).
[25]转引自姜宇辉.艺术何以有“灵”——从米歇尔·亨利重思艺术之体验[J].学术研究,2020,(10).
[28][法]皮埃尔·布迪厄. 实践感[M]. 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29][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文化转向[M]. 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杜 娟)
作者简介: 张玉青,女,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媒体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