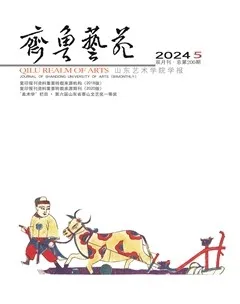潜隐的力量:宋代女性之于绘画艺术的形塑

摘 要:古代女性是我国艺术发展中的一股容易被遮蔽却非常关键的力量。本文立足两宋绘画发展的历史语境,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传统学科相交叉的研究范畴,说明宋代女性主要是以两种形式融入于绘画艺术发展之中,而后分析在两宋绘画发展历程中这两种形式不可忽视的意义及作用,最后以艳艳女史为案例进一步阐释宋代女性与绘画艺术的紧密关联,明晰宋代女性之于绘画艺术发展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宋代女性;艺术传播;艳艳女史
中图分类号:J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36(2024)05-0057-07
古代女性是中国艺术发展中容易被遮蔽的群体。迄今为止,现可见传世画作的创作者大多为男性,体现出各异的男性视角;现存的文史典籍、诗词题跋中各类艺术品评,亦大多为男性所撰,反映出男性主体的自我意识。值得思考的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中,难道只有男性群体进行艺术创作或者予以效果的反馈?古代女性群体之于艺术又是如何理解、如何反馈的呢?由此,本文基于宋代绘画历史原境,通过对宋代女性群体的考察,阐释其作为绘画创作者与观者对于绘画艺术观念和技法传播的深刻意义,以期为中国艺术发展与女性群体关联性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宋代女性介入绘画艺术发展的两种形式
通览史料不难发现两宋绘画艺术与女性群体之间存在深层互动,以及在两宋绘画艺术发展中宋代女性存有两种面向。
第一,宋代女性作为艺术创作者与观者,她们较多参与到各类艺事之中,亦会进行绘画实践与品评。宋代擅画女性的绘画实践、审美思想体现出所属阶层的特点;宋代女性观者也会赏画品画予以反馈。宋代女性,无论是宫廷女性、官宦女眷抑或平民女性在经济能力和社会交流层面都具备接触绘画作品的可能。宋代女性的自由程度虽不及盛唐,会受到社会伦理道德束缚,但其整体社会地位仍旧有所提升。宋代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宋代妇女享有很大的财产权[1](P5)以及继承权位次的提高,她们对于各类艺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些艺事也往往是她们闲散时光中的消遣。宋代女性也存在较为便利地获得知识的可能,如《女孝经图》中一位女子的案几旁放着若干卷书籍,取之翻阅。再如刘松年《博古图》中描绘出女性参与艺事之景,她们随心交流,赏鉴古玩。可以说,宋代女性对于绘画作品具有不同的审美偏好与传播方式。宫廷女性和平民女性(风尘女子)所为通常带有“社交性”目的。而闺阁中的官宦女眷则不同,她们大多出于“自我中心性”表达。如蔡绦在《西清诗话》记载的“朝奉郎中丘舜诸女,皆能文词”[2](P416)。她们普遍有一定学识,热衷享受绘画创作的自由,随性挥毫。
第二,宋代不同阶层的女性作为题材内容的情况愈发多见,市井妇女、淑女闺秀均被纳入其中。两宋时期表现女性日常生活的图像频频出现,而且南宋时期从事女性题材绘画创作的画家多于北宋。宋人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不同阶层女性,既有表现劳作场景的平民阶层女性作品,如《纺车图》等;又有表现闺阁庭院等较为私密场所中的女性题材作品,以团扇的绘画创作为例,宋代女性普遍存在的用扇情结,在诗词与绘画当中都有描绘:诗词中,如苏轼《贺新郎》“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晏几道“玉阶秋感,年华暗去。掩深宫,团扇无绪”,柳永《少年游》中描写歌舞女“娇多爱把齐纨扇,和笑掩朱唇。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称在风尘”,甚至宋代普通村妇也用扇掩面,如徐积在《贫女扇》诗中写道:“妾有一尺绢,以为身上衣,团团手中持,朝携麦陇去,暮汲井泉边,无人不看妾,不使见峨嵋”,绘画中,如南宋刘松年《仕女图》中的少女手持纸扇追逐嬉戏,南宋陈清波《瑶台步月图》侍女持扇等。进言之,团扇所代表的小品画形制,也彰显着绘画风格向含蓄温婉、精致典雅的优美境界,团扇在无形之中成为女性受众艺术接受的中介之物;相对地,两宋女性是团扇的主力消费者,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代小品画的发展。
概言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宋代文人常将女性题材看做被人观赏的对象,处于次等地位。如米芾将仕女画列于末端,其《画史》说:“仕女翎毛,贵族戏阅,不入清玩”,这也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佛像、故事、山水、竹木水石、花草、仕女、翎毛的排序位置一致。可见女性题材绘画在当时地位不高。诚如两宋女性题材绘画一样,两宋女性在艺术史中也被置于从属地位。回溯画史,女性书画家比例很低。比如《宣和画谱》收录6396件作品,所藏231位画家,只有3位女性画家画作,比例甚低。她们受到父权社会之禁锢被时人忽视,反之男性在艺术史中地位常被当作一种顺理成章的存在。
二、画家/观者:宋代女性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外塑力量
分析史料可知关于宋代女性画家的记录较为零散。在《宣和画谱》中记录三位女性画家:五代童氏、宋代曹氏、王氏。曹氏为“雅善丹青”的皇家宗室,她被宋内府收藏的绘画作品有五幅:《桃溪图》《雪雁图》《柳塘图》《牧羊图》和《蓼岸图》。王氏是功臣后裔,“以淡墨写竹”,她的二幅《写生墨竹图》被御府收藏。之后,南宋邓椿《画继》也记录了六位女性画家(曹氏和王氏不在其中),分别是李夫人、文氏、方氏和国夫人王氏、章煎以及任谊之妾艳艳女史。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画继》中介绍的六位女性分属于不同的阶层。再至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又记录14位宋代女性画家,他是在《宣和画谱》和《画继》基础上,又补充了六位,共14位,分别为擅画竹的胡夫人、汤夫人、卢氏、翠翘、苏翠和擅画人物的刘夫人。最后,清代杨漱玉编撰的《玉台画史》是第一部女性画家专辑,记录31位宋代女性画家,除上述14位外,又补充17位,分别为擅绘竹菊题材的李清照、朱淑贞,织绣名家韩希孟,常州女史朱氏、鲍夫人,妓女画家琼华、绿华和延平妓,擅绘罗汉像的王氏女,擅绘山水画的仁怀皇后朱氏和清音道人,以及一部分仅存画名,但未标示出所擅题材及画风特点的女性画家:蔡国长公主、度宗皇后全氏、宁宗恭圣皇后妹杨妹子、郭昭晦女郭氏、谭文初妻谢夫人、祝次仲女、天台营妓严蕊。再如邓椿《画继》中专设一节《贵胄妇女》侧面说明女性对绘画已产生一定影响。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淑女闺秀和具有较高艺术素养的才女,在宋代绘画艺术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如同文人士大夫阶层一般,具有独立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判断,对艺术的追求中饱含着主体意识的觉醒。她们的绘画艺术风格也具有个性特色。例如,闺阁女子文氏,受文同“浓墨为叶,淡墨为背”的墨竹画影响,笔墨浓淡相宜,注重写生;汤夫人与其父亲汤叔雅风格类似,汤叔雅是画家扬补之的外甥,所画梅竹松石,自出新意。再如,国夫人王氏绘画上自出新意,《画继》记载:“和国夫人王氏,显恭皇后之妹,宗室仲輗之室也。善字画,能诗章,兼长翎毛。每赐御扇,即翻新意仿成图轴,多称上旨。一时宫邸珍贵其迹。”[3](P364)宋代女性拥有较多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使得一些个人天赋较高,善于拈翰弄墨的女子,成为善诗词、精书画、工声律、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才女”。这些“才女”分布在各个阶层之中,“上自皇室、贵族、士大夫之家的妇女,下至宫人、尼道姑,侍儿、婢妾、樵女、娼妓等等,为数可观”[4](P507-513)。即是说这些不同阶层的女性都具有接触绘画的可能。宋代宫廷女性被要求学习女德和文化典籍,宋高宗曾说:“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惟妇女亦不可不读,读书则知自古兴衰,亦有所鉴戒。”[5](P237)这些宫廷女子的日常学习也包括“游艺”,琴棋书画等。如宋神宗第九女蔡国长公主六岁就能作画、仁怀皇后朱氏、南宋高宗贵妃刘夫人、杨妹子等。官宦家的女眷常在家中,琴棋书画成为消磨时光的手段,以至于书画的爱好可以得到延续。宋代的狎妓之风盛行,婢妾娼优可以在教坊中进行专门的学习,她们在与文人的交往中也会得到浸染;良家女子亦可选择在私塾、道观或跟随专业技师学习。
究其原因,第一,宋代是尊重知识、普及知识且社会风气较为宽松的时期,使得宋代女性可以较为自由地学习知识。首先,宋代书籍流通于各个阶层人群之中。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对刻书业产生深远影响,加上书院与州县学的设立,使文化知识传播渐渐普及于民众,在各种文献中看到社会上很多人都可以方便的获取过去很难阅读的书籍,就连妇女、牧童、樵夫都可以阅读经典,引用古人言语。[6](P169)美国学者柏文莉(Beverly Bossler)统计过《华阳集》《曾巩集》《二程集》《浮溪集》《攻魄集》等16种宋人文集中119位女性墓主的墓志铭、行状等,从中筛选出识文断字者35人,占总数的29.4%。[7]其次,作为舆论领袖的文人群体对于女性学习并不排斥,甚至较为推崇。比如,宋代理学家比较重视“女教”。如司马光言:“妇人专以柔顺为德,不以强辩为美。”可以说,柔顺贤德、端庄沉静是宋人士大夫眼中的女性典范。文人士大夫群体,如司马光、朱熹等认为女性应多学儒家经典,以规范女性行为。此外,宋代社会认为有文化的女性对于家族兴旺有利。如永嘉学派叶适所言:“妇人之可贤,有以文慧,有以艺能,宜其家室而已。”[8](P264)可推测,相比前朝,宋代女性的文化水平较高,而文化素质的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艺术修养的提升。即那些通晓吟诗作赋、擅长书画的女性,必然接触并学习过相关知识,而后有一定的艺术创作或赏鉴能力。
第二,两宋绘画艺术传播活动较为频繁,加之宋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她们可以较为容易地接触到绘画艺术作品。一方面,两宋经济水平长足进步,大众物质水平的提升,画作会以商品的方式在艺术市场中流通;社会文雅之风盛行,宋代女性在物质消费之余,也醉心于精神层面的消费,如闲暇时光对文字书籍、绘画作品的消遣。另一方面,朱熹在《小学》中引用《礼记》中的“男不言内、女不言外”,这种约定俗成的“男治外事,女治内事”思想,常见于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家庭之中。在宋代社会政治环境中,在男外女内的权力分配下,女性虽不求功名,却可自主参与家中活动,在《开芳宴》《梳妆图》等墓室壁画中可见。这些壁画既反映了富裕家庭中女性的地位,也见到了中下阶层女性生活情境(婢女、乐妓、厨娘等)。宋代女性在处理完“内事”后,也会读书、品画、赏花、出游乃至诸多“外事”活动。这些“外事”,譬如“东土饥荒,孔氏发家粮以赈,邑里得活者甚众,生子皆以孔为名”[9]。宋代女性慈善活动,有救济灾民、收养孤儿等等。这使她们得以接触到真实的大千世界,也为她们接触先进艺术思想、流行绘画题材、风格提供了可能。如周密著《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记载女性出游的场景:“都城自过收灯,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至禁烟为最盛。龙舟十余,彩旗叠鼓,交舞曼衍,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歌欢箫鼓之声,振动远近,其盛可以想见。”[10](P376)但宋代女性大多还是在闺阁家中,常在与家人友人的交流之中赏鉴佳作。她们对于绘画的学习和热忱使得她们会积极地参与到绘画创作与传播之中,如怀仁皇后、杨妹子、艳艳女史等。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宫掖女子、闺阁女子抑或风尘女子,她们都有接触绘画的渠道。譬如,南宋夏珪《山水十二景》中标题因有皇后单龙玺钤印,被认为是杨皇后亲笔,这可能是杨皇后的拟定之命题,也可能是她观后的亲笔。另外,诸如欧阳修、苏轼等人都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风尘女子比较欣赏,他们时常交游;那些对绘画热忱的婢妾娼优以及普通官宦女性或也有机会,从其“知己”或夫父之处得以欣赏佳作。比如,李夫人的外甥黄庭坚常参加雅集艺事,每次遇到佳作便借给李夫人临摹。《画继》记载:“作一横绢丈余《着色偃竹》以贶子瞻,过南昌,山谷借而李临之。”[11](P361)风尘女子王英英与名士蔡襄、梅圣俞交往甚密,得名师指导。《宋人轶事汇编》卷九记载:“英英,姓王氏,楚州官妓。学颜鲁公书,蔡君谟教以笔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尧臣赠之诗曰: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亲传笔法中郎孙,妙尽蚕头鲁公体。”黄尚书田之妻胡夫人作为名门之后,自幼受家门艺术风气熏陶,“精于琴画” [12](P481)等。可见艺术传播过程也就是传播者与受众双方的生活经验空间互相交叠、由此达彼的过程。女性在与文人的交往交流中,她们可以有机会观赏到雅集之中的佳作,或听闻文士之于书画的真知灼见,甚至有机会得到他们笔墨方面的点拨。
闺阁女子和风尘女子,教育环境没有宫掖女子好。她们大多接触的是流行的题材,较为单一,如花鸟竹石,她们艺术接受范围基本是耳濡目染,或外聘“擅画者”。而宫掖女子创作的题材更广泛,侧面证明了艺术接受的丰富性,既有善绘山水花鸟的曹氏,又有善绘山水的怀仁皇后朱氏、越国夫人善绘烈女人物等等。但是这些女性绘画作品非常稀少,而且在男性文化价值体系的笼罩下,其艺术风格与审美意趣基本趋同于男性。
三、对象/内容:宋代女性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内化力量
宋代女性不仅作为艺术创作者或观者助力绘画艺术发展,而且亦作为一类艺术主题或表达对象内化于绘画艺术演进中。
宋代女性作为视觉对象常出现在图像、文本和历史情景中。第一,就绘画表现对象而言,一类是淑女闺秀之形象。大多文人士大夫秉持“内外各处、男女异群”伦理观点,朱熹在他的《小学》中引用《礼记》中的“男不言内、女不言外”,这种约定俗成的“男治外事,女治内事”“妇人无故,不窥中门”即已明确了淑女闺秀的交往范围。另一类是市井妇女之形象。她们多是在公共场所中抛头露面,全然不符合士人心中女性应有的克制贤良、知书达礼的完美形象。正如宋人胡颖笔下记载:“大凡街市妇女,多是不务正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三五成群,专事唇舌。”[13](P506)这两类女性群体均曾出现在两宋绘画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淑女闺秀往往处于宫闱之中,在公众视线之外,生活和社交空间相对封闭,如北宋末年佚名《文姬归汉图》,高墙之内的妇女们,与熙熙攘攘的市井人群形成鲜明对比。而市井妇女则大多出现在反映风土人情或现实生活的画作之中,她们为生活所忧,囤于生活琐事之内,如北宋王居正《纺车图》、南宋李嵩《市担婴戏图》、南宋刘松年《茗园赌市图》等中的女性形象。
第二,从绘画表现内容而言,宋代绘画中存在大量女性下棋、梳妆与赏景的场景,同时这些表现内容均是基于男性视角。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女孝经》中一位女性案桌旁放着书籍、苏汉臣《妆靓仕女图》中梳妆打扮的女子等等。又如,周肇祥旧藏的宋仕女梅妆镜的镜背上绘有女性读画的场面(《艺林月刊》第五十期);宋代墓葬壁画中也存在女性的读写形象,如平陌宋墓墓室下半部西北和东南壁画,[14](P41-54)另如河南新密市平陌村的宋墓的两幅壁画,考古报告中《书写图》和《读书图》就是展现女主人生前读书弄墨的场景。诸如此类图例不胜枚举。进言之,宋代女性作为绘画表现内容,主要是附庸于主流意志或男性喜好。如现存黑龙江省博物馆南宋《蚕织图》,其每帧画下面都有宋高宗吴皇后题写说明,描述道德教化、农业纺织相关问题。[15](P31)这些题记说明吴皇后参与了这幅画的创作,而且应该是在南宋楼璹(1090—1162)将其《耕织图》及其配诗呈现给宋高宗后,宫廷后妃观赏后的启发之作。又如,宋代女性普遍喜用“团扇”,如苏轼的《贺新郎》中“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女性作为团扇使用的主要人群,应该会接触到类似的女性人物题材的团扇,同时也会是画家的绘画对象。如刘松年《仕女图》、佚名《招凉仕女图》、陈清波《瑶台步月图》中具有持扇的女性形象,矜持而典雅。宋代团扇中女性形象“得闺阁之态”,汤垕《画鉴》中说苏汉臣仕女“知其又所思”是男人欣赏的对象,属于仕女画的范畴。再如,南宋《女孝经图》,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讲述了女性道德箴言。在符合政治和伦理的规约下进行创作,皇家女子对于此类女性题材是支持的。宋高宗的吴皇后、刘贵妃,以及之后的杨皇后可能都通过参与了此类题材的创作,一方面可以展示她们的艺术修养,另一方面也表明她们对儒家伦理“妇德”的理解。
可以说,绘画艺术是在接纳、吸收和合并宋代女性群体的绘画风格与审美方式的情况下,逐步形成宋代绘画艺术的整体风貌。进一步而言,宋代女性对绘画艺术发展的内化之力,即是以宋代女性作为绘画对象与内容固化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认知,并逐步成为一类经典的艺术题材。
究其原因,从宫廷审美到文人诗情和民间风俗,从艺术的功用性质到艺术的赏玩性质,再从北方笔墨的变异与南方景致的融合,这些似乎都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主体——受众”所奉行的审美旨趣,宋代女性多以附庸的方式参与其中。其实在两宋时期,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个人还是群体都有他们的所属阶层。具有知识权力的人在不同场合彰显的不同身份,在本质上还是属于上层艺术受众,男性与女性均是“郁郁乎文哉”的社会缩影;但也存在另一面,下层艺术受众的成长,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壮大,表现为绘画艺术受众扩大到市民阶层以及延伸到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中,仿佛并未在意主流文人士大夫的态度。如《市担婴戏图》中的妇女头梳简易发髻、身材丰腴怀抱婴儿在街边哺乳,并未在意货郎的目光。这也许说明理学思想并未渗透至下层受众之中,或是下层妇女疲于生活。由此,宋代绘画表现对象与内容得以丰富与拓展。
四、宋代女性之于绘画艺术发展的具体阐释——以艳艳女史《花鸟草虫图卷》为例
宋代女性之于绘画艺术发展存有外塑和内化两种进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群体也如同文人士大夫阶层一般,她们对绘画艺术亦具有自觉的审美判断与实践认知。
以南宋艳艳女史《花鸟草虫图卷》为例。据邓椿《画继》记载:“任才仲妾艳艳,本良家子,有绝色。善著色山水。工真、行书,其夫北宋名士,工于山水竹石,艳艳盖得其笔法。”[16](P364)通过艳艳女史的生平资料可知,她是任谊(神宗、哲宗时人)之妾。任谊,字才仲,北宋画家宋迪外甥,他亦擅长绘画,曾有协律郎,后通判澧州官职。南宋邓椿《画继》记载:“(任谊)又取平生所见兰花数十种,随其形状各命以名。皆小字隶书,记其所见之处,邵氏名曰香圃。有南北江山图、平芜千里图、四更山吐月图、唐功臣图、斗山烟市图、松溪深日图传世。”宋佚名《画录》记录艳艳女史所绘《潇湘八景图》册言:“细润清远,足以名世。”可知艳艳女史的画作应大体呈现笔法细腻、设色雅润的风格。而她的此幅作品画风雅致、笔法细腻,体现出两宋画院“宣和体”的特点。任谊与艳艳女史都喜绘画,艳艳女史很有可能耳濡目染任谊艺术观点,甚至技法的直接传授。应如《画继》中说,艳艳女史“盖得其夫笔法”。
通过对画作中的石头、花卉和蝴蝶等艺术元素分析,至少有三点可以说明女性画家之于绘画的贡献。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单国霖先生曾多次考证《花鸟草虫图卷》,他从该图的风格内容、笔法特征、印鉴款识,结合对作者艳艳女史生平考察并曾详细阐述了此图的真伪鉴定过程。本部分参照单国霖先生之于艳艳女史的研究成果。第一,树石部分。她画石头的是用渲染,与徽宗画院画风一脉相承;而坡地画法水墨皴染后,辅以细密苔点,苔点中点染石绿,称之为“嵌宝点”。“嵌宝点”最早约出现于两宋之交,南宋江参《林峦积翠图》和马远《观瀑图》中,坡地和松干上都有“嵌宝点”。第二,动物部分。蝴蝶的画法非常工细且翅膀弧度呈圆润的弧度。明显与唐代刁光胤《写生花卉册》中蝴蝶画法不同,与北宋赵昌《写生蛱蝶图》相近,更贴近南宋《海棠蛱蝶图》。第三,植物部分。有学者注意到她画花卉之时,白色部分的是“留白”,而偏黄的部分是绢的本色(留底),而后加以白粉与其他颜色晕染,如林椿(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年间画院待诏)《海棠图》、马远(南宋宋光宗、宋宁宗两朝画院待诏)《白蔷薇图》中淡黄色就是“留底”。就技法风格分析,这幅画异于“黄家富贵”风格,而是与北宋末、南宋初重彩工笔花鸟画风格相似,其多重视生活的细微观察,以自然与人、生活为体验,使观者在画面上容易有相似的感受。而艳艳女史作为北宋任谊之妾,她应是北宋人。以此,推断她应接触过相似风格画作,或接受过院体画师的指导。且早于南宋画院这些画家掌握此类“留白”技法,故可将绘画史之花鸟画法中的“留白”之法推向更前,甚至可以说她一定程度上创造了绘花卉可以“留白”的先河。而这种“留白”之法,就是她之于绘画艺术发展的贡献。某种意义上而言,绘画艺术史中女性画家或观者所存有的“遮蔽性”,造成我们对艺术发展理解的单一化,而恰恰对于这种“遮蔽性”的重审才是艺术创新性发展的活力源泉。
可以说,虽然宋代女性处于政治权力的边缘,却在日常家庭或宫苑生活中享有一定权利。她们在作品中表达心绪与见解,对于艺术的学习、接受与鉴赏更为纯粹,在男权社会中寻求精神解放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诗词绘画无疑是适宜的窗口。身处家庭内闱之中的女子,她们对于艺术作品的“观看”与“创作”并非社交性、公共性的行为,而是充满自娱性和隐私性的行为;相应地,这种艺术“行为”则是出于对艺术本体的切实“感知”与“反馈”。
不可置否的是,两宋社会环境的开明性、丰富性与多元性,使得女性具有学习绘画技法、接触绘画作品的客观条件,并一定程度上影响宋代绘画传播和发展。宋代女性画家在主流的艺术语境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绘画品评和风格上多以男性为参照,恰如黄庭坚评李夫人画“健妇果胜大丈夫”等,亦再次说明宋代女性画家绘画技法、审美旨趣与男性画家类同。
结语
本文以宋代女性视角介入两宋绘画艺术研究,明晰女性在绘画艺术实践和风格形塑过程之中的真实情状。通过一系列考察可知宋代女性以两种形式介入绘画艺术发展之中,一类是作为画家或观者,一类是作为绘画表达对象或主题内容;同时,作为画家或观者的宋代女性对绘画艺术发展具有外塑之力,而作为绘画对象或内容的宋代女性对绘画艺术发展则具有内化之力,以此共塑两宋绘画艺术发展之路;最后,通过对艳艳女史《花鸟草虫图卷》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两宋绘画发展过程中被遮蔽的女性力量,明确女性之于中国艺术史的重要意义与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1][美]伊沛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2][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3][11][16][宋]邓椿.画继[M]//潘运告主编.图画见闻志·画继.米田水译注.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
[4]郑必俊.论两宋妇女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贡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7]Beverly Bossler. Women’s Litera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Preliminary Inquiries[G]//本书编委会.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8][宋]叶适.叶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1.
[9][宋]范成大.吴郡志[M]//中华书局编辑部.宋元方志丛刊(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外四种)[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2][清]佚名.书画史[M]//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13][宋]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4]郑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郑州宋金壁画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5]林桂英,刘锋彤.宋《蚕织图》卷初探[J].文物,1984,(10).
(责任编辑:刘德卿)
作者简介:宋芳斌,男,博士,南京理工大学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传播。
项目来源: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艺术学评价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21ZD11)、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青年项目“吴门画派赠礼画研究”(21CF184)、江苏省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艺术传播视域下两宋时期绘画艺术研究”(22HQB5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