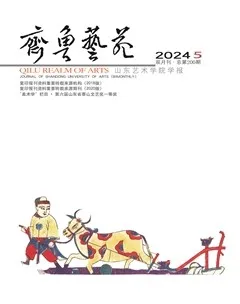口述史视域下德州李氏陶埙的传承实践与反思





摘 要:德州李氏陶埙源于清光绪元年(1875)的举人吴浔源,传承至今已有四代,笔者与其第二、三、四代传承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2009年,“李氏陶埙制作工艺”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第三代传承人李钟汾为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李氏陶埙从家族传承到高校教育传承的转变过程,传承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高校的介入,使非遗传承的链条得以加固,为传承保留了火种,同时,在此转变过程中,既要合理解决“非遗”项目的课程设置、学分、经费等具体问题,还需要抓好传承人培养工作中“点”和“面”的问题。
关键词:德州李氏陶埙;传承实践;口述史;高校教育传承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236(2024)05-0004-07
陶埙是我国特有的闭口吹奏乐器,也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乐器之一。清光绪元年(1875),举人吴浔源偶得埙,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并著《埙谱》传世。居住于德州五里庄村的李氏陶埙创始人李雨村与吴浔源有亲缘关系,吴浔源曾赠与他手制陶埙和《埙谱》。他于20世纪20年代初复制出五音孔梨形陶埙,开启了李氏陶埙的传承之路,历经四代,由兴趣到热爱,由自发到有意识,由家族传承到学校教育传承的不断转变,使陶埙这件古老乐器在德州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2009年9月,“李氏陶埙制作工艺”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第三代传承人李钟汾为省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笔者与李氏陶埙的第二、三、四代传承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第三、四代传承人李钟汾、李峥嵘父子,与他们相识相交已有40余年。可以说,我从开始对陶埙的懵懂初识到体会其起伏与衍变,再到将李氏陶埙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无论是以亲历者身份的直接参与,还是采访者角度的田野工作,都见证了李氏陶埙在德州的传承和转变过程。
一、德州李氏陶埙的家族传承
吴浔源(1824—1902),字棠湖,是清代光绪年间河北吴桥县的文人,祖籍宁津县小店乡王庄,后迁居河北省吴桥县旧城。他博学多识,涉猎广泛,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书法家、雕刻家、画家、音乐家。他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依据考古发掘的殷代陶埙实物,复制出梨形五音孔陶埙。值得注意的是其撰著《埙谱》一卷,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是我国迄今仅有的一本埙谱。
李雨村(1885—1951),德州市五里庄人,酷爱音乐,与吴浔源有亲缘关系,是李氏陶埙创始人。20世纪20年代初,他复制出了褐红、红、灰、墨黑等大小四类五音孔梨形陶埙,底部用篆书或隶书刻有“建安六年”“隔津天泉”“李雨村制”“桃园老人李雨村制”等字样。20世纪30年代,李雨村所制陶埙参展山东省博览会获得奖章和奖状,现存于山东省图书馆。他制作的陶埙在当时影响广泛,其将调音较为准确的陶埙通过德州教会学校博文中学王景文校长,赠给北京燕京大学、济南齐鲁大学图书馆、德州某教会医院的美籍医生等社会机构与人士;音准较差的则赠给附近各寺庙的和尚、道士、民间乐户(吹鼓手)及济南、天津、北京的亲友当作古玩欣赏。5pLkD9yTXLeCudNTKhN7WQ==1986年,德州棉纺厂老工人董玉水曾依据其陶埙复制出梨形五音孔黑陶埙。
李雨村的儿子李孟才(1914—2000)是李氏陶埙的第二代传人。1930年冬,李孟才先生赴北京读书,在北京市中小学的文艺汇演中用陶埙吹奏了昆剧《紫钗记》中《折柳》的一支曲牌【北寄生草】,第三天登了报纸,引起当时社会各界的关注。1986年9月,中央电视台《话说运河》摄制组在李孟才先生的居室内拍摄了德州陶埙的演奏片段,李孟才和其次子李钟汾用五音孔陶埙和铜制洞箫吹奏了古曲与《话说运河》主题歌,作为《话说运河》德州部分的一项内容。
李钟汾(1938— )是李氏陶埙的第三代传人,他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化学系,系德州学院化学系退休教师。他自幼对制作和吹奏陶埙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五音孔陶埙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索,成就突出。李钟汾按照祖父李雨村当年制作陶埙的工艺程序,经多次改进,制成了八孔、九孔陶埙和易于演奏和传播的“哨埙”,在推动几千年古陶埙进化过程和改革中国古老乐器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2009年9月,“李氏陶埙制作工艺”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李钟汾为项目传承人。
李钟汾的长子李峥嵘是陶埙的第四代传人,他自幼随父亲学习了陶埙的制造工艺和吹奏技术,曾发表《说埙》参见:李峥嵘.说埙[J].乐器,1990,(2)。一文,在成功申请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文字材料收集与整理工作。
德州陶埙经过李氏家族四代人的努力传承至今,体现出了民间艺术顽强的生命力和民间艺人的传承精神。传统非遗传承方式多种多样,其中,家族传承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它通过血缘关系代代相维系,以家族内部的教授和培养来保证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发展。但是,这种家族传承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是“父子相传”的负面效应造成传承人的断档。“口口相授”一直是家族传承的主要教学方式,这种方式建立在子女甘愿顺应家学的基础上。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一方面,子女更加独立,对家长有着极大的逆反心理,对传承非遗项目有着强烈的排斥心理;同时,当前的学校教育使孩子们的人生有着更多的选项,他们很难追随父辈的道路。尤其是中学或大学毕业有了其它工作后,生活的压力迫使他们无力从事这种传承。李峥嵘幼年也随父亲李钟汾学习陶埙制作和吹奏,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小学任音乐教师。按照我们的设想,他应该最有条件成为李氏陶埙的传承人。但是,他对此一直没有太大的兴趣,为此,李钟汾先生也是无能为力。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和审美价值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年轻人更热衷于现代生活方式,如使用社交软件、网络购物、电子游戏等,他们对民间传统技艺逐渐失去了兴趣。
其次是家族式传承模式虽然保证了埙的制作、演奏及创新的“嫡脉”,但也有着动力不足的局限性。陶埙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制作出一枚外形精美的作品已是不易,而我们需要的是音高准确且符合音律要求的专业演奏埙,要达到这种要求则需要众多专业技术和音乐知识的强力支持,这也是李氏陶埙在推广普及过程中发展迟缓的因素之一。
二、德州李氏陶埙的高校教育传承
李氏陶埙的家族传承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生活观念、就业理念、个体兴趣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甚至陷入濒临失传的境地。在这种状况下,高校教育传承的介入为李氏陶埙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高校教育传承是指充分发挥高等学校教育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事业中的作用,充分利用高校师资及科研资源,成立一支集教学、科研与创新于一体的团队。德州学院建立了“鲁北地域文化研究中心”,设有专门的陶埙制作工作室,开设陶埙制作及吹奏课程,让学生亲身体会到陶埙及传统文化的魅力。自2010年开始,德州学院每年邀请李钟汾举办关于陶埙的学术讲座,效果颇佳。很多学生对陶埙制作和吹奏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成立了李氏陶埙课题研究小组。小组成员利用课余时间学习陶埙制作工艺,赴梁子黑陶陶艺馆观摩,并开展陶埙手工制作、陶埙包装设计等实践活动,形成了李氏陶埙最早的一批成果,作为特色礼品成为我校对外文化交流的亮丽名片。
2011年,德州学院音乐学院获批山东省艺术科学“十二五”重点学科“地域音乐文化”项目,并把“李氏陶埙制作工艺”作为重点研究内容之一,申请山东省文化厅文化艺术重点课题获得成功。
2012年,学校正式开设“李氏陶埙制作与演奏”课程(选修),特聘李钟汾先生授课。第一届选修陶埙的学生共10人,课程设置在第五学期,每周两节。授课内容包括陶埙制作和演奏两部分。这10名学生均为竹笛主项或者副项学生,在陶埙演奏学习上较为顺利,但在陶埙制作的拉坯、调音和烧制三个环节受挫颇多。但经过李钟汾先生的精心指导和帮助,半年间他们先后制作出20余个品相和音准均基本达标的陶埙。同时,学生们开始在民乐队中承担埙声部的演奏任务,民乐合奏《大同梦》第一部分深沉悠扬的陶埙音乐已成为历届陶埙演奏学生的必学曲目之一。
2013年,“李氏陶埙制作与演奏”课程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和总结论证,确定了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将陶埙课程调整到第三学期,并将学时延长为一学年,正式纳入音乐学院的人才培养方案。“陶埙制作与演奏”课程(选修)的设立为陶埙的进一步传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李氏陶埙制作工艺”的传承得到有效保证,从而解除了李氏陶埙传承的后顾之忧,充分体现了德州学院音乐学院“以课堂为平台,学生为传承主体,让更多的德州民间音乐走近学生、走进课堂”的教学理念。
2016年1月,德州学院音乐学院为了解决李氏陶埙的师资传承问题,同时也为了学科专业的良好发展,在征得李钟汾先生的同意下,特别推荐新引进的优秀青年教师徐琦博士作为李氏陶埙的第四代传承人,开启了李氏陶埙从家族传承到高校教育传承的转化。
三、德州李氏陶埙传承过程中的故事
前文简要叙述了李氏陶埙在德州的传承发展历程,笔者与李氏陶埙的几代传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以至于影响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民族音乐学的海洋里畅游至今。现在回想起来,虽没有取得卓著的成果,但在这一过程中也感到非常充实和惬意,受益匪浅。
(一)初识李氏陶埙
李氏陶埙的四代传承人分别是:第一代李雨村,第二代李孟才,第三代李钟汾,第四代李峥嵘和徐琦。其中,第四代传承人李峥嵘是我认识李氏陶埙继而进行研究的关键性人物。
李峥嵘是李钟汾的长子(次子对陶埙不感兴趣),与我是同学关系,而且是小学、初中乃至高中的同班同学。李峥嵘高中时期学手风琴,我学琵琶,一起参加了艺考和高考,他最终考入德州师专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德州学院音乐学院前身),毕业后分配至德州黎明小学任音乐教师至今。他性情敦厚平和,对待李氏陶埙这门家传技艺一直抱着随性而为的态度,也学习其制作与演奏,在李氏陶埙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过程中付出甚多,做出重大贡献。申报成功后,由于非遗传承是一项费时、费力且费钱的事,对此他一直缺乏足够的兴趣。我曾多次劝说他继承这门家传技艺并将其发扬光大,只是人各有志,终不得遂愿。正因如此,为了将传承了近四代的李氏陶埙制作技艺更好地延续下去,同时考虑音乐学院学科专业建设发展问题,征得李钟汾先生同意,2016年优选新引进的青年教师徐琦博士举办传统拜师仪式,确立了李氏陶埙第四代传人,将这项省级非遗项目真正落户高校,同时,也开启了音乐类非遗项目由家族传承到高校教育传承新模式的转变。
(二)李孟才先生印象
在我的印象中,每次去峥嵘家都看到身材瘦小的李孟才先生安静地坐在床边看书或者在书桌上写作。开始觉得好奇,就悄悄问峥嵘:怎么每次看到你爷爷都在看书写字啊?他说:我爷爷就是一位沉默寡言、喜爱看书的老人。李钟汾也说他父亲虽然是地主出身,但在历次社会变迁中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均得益于他的老实勤勉和小心谨慎。他自幼因学习中医而习字,从背《汤头歌》《黄帝内经》到学习四书五经等经典,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后去北京读新学,就读于金鱼胡同小学和中学,高中一年级时因“一二·九运动”返回德州,曾在济宁一个禁烟办事处和德州教育部门当过职员,建国后先后在德州建筑公司、济阳县卫生院和德州市造纸厂工作。离休后(1983)在德州市文联《德州文史》编辑部从事写作和文献整理工作,写作了《德州历史沿革》《中国古老乐器——陶埙在德州地区的复制发展》等文章24篇,分文史、名人轶事、事件见闻、杂考及音乐五类(表1)。其中,《中国古老乐器——陶埙在德州地区的复制发展》一文是德州陶埙传承发展理论研究的最早成果。李孟才先生曾在德州五里庄的民间乐队拉“龙头嗡子”(一种雕刻龙头的自制二胡),对德州及周边的民间乐曲较为熟悉,其《百年来德州民间乐曲概述》一文也是对德州地区民间乐曲研究整理的最早资料,被收录于《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东卷》(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4.08)。
(三)聪颖多才、“不务正业”、执着坚韧的李钟汾先生
李孟才的次子李钟汾,1963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化学系,曾任德州师专化学系副教授,是李氏陶埙的第三代传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乐陵第四中学任化学教师,曾兼任音乐教师,1978年调至德州师专化学系任教。李钟汾对音乐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和音乐天分,童年时先后自学竹笛、箫、箎、埙、二胡、三弦等民族乐器且能熟练演奏,工作后又自学了风琴(在中学兼任音乐教师的需要)、手风琴(李峥嵘是手风琴专业方向)、小提琴、钢琴、电子琴等乐器,后来又学习了简谱和五线谱。我高中和大学期间经常去峥嵘家串门,有时碰到李钟汾先生在家里拉坯制作陶埙,感到很新奇,便不断地向他请教。他看我对陶埙有兴趣也非常高兴(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对他制作陶埙均不太在意),我又是民族器乐专业的(琵琶),所以每次李钟汾先生都像遇见知音一样兴致勃勃地向我展示其祖传的陶埙、铜制洞箫,及他自己复制的箎、三弦等乐器,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了这些以前在只是在书本上才能看到的乐器实物。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的交流为我从事民间音乐的研究播下了一颗勃勃生机的种子,也是自己后来克服重重困难将李氏陶埙引入大学课堂的原动力所在。他常说自己水平很业余,就是“玩儿”。但其可贵之处在于“玩儿”的高兴,“玩儿”的有模有样,“玩儿”的实实在在。记得第一次请他为音乐学院学生做陶埙知识讲座时,他将陶埙、哨埙、竹笛、铜制洞箫、三弦等乐器依次展示和演奏,一次次获得了学生们的热烈掌声。我正准备致结束词时,没想到李先生看到旁边有钢琴,又兴致盎然地表演了一段钢琴弹唱《骏马奔驰保边疆》,洪亮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及熟练的钢琴伴奏(虽然不怎么规范)震惊了我和所有师生,将现场气氛又一次推向了高潮。
李钟汾作为我校化学系副教授,多年来,除了认真完成教学科研任务外,业余时间都给了陶埙,并发表了相关论文《关于古陶埙的源流和九孔埙的研究成果》。我和他聊天时曾说:您当时选错专业了,应该学音乐才对,现在是“不务正业”啊。他一笑了之,表示当时想考音乐却无从下手,且家里对以音乐为职业也不太认可。我想这可能是李钟汾内心的一个遗憾,让儿子李峥嵘学习音乐也是间接圆了自己的音乐梦。
李钟汾先生对于陶埙传承的执着与坚韧是非常令人钦佩的。他在祖父的制作工艺基础上制成了方便吹奏、音阶齐全的八孔陶埙和九孔陶埙。2006年,李钟汾研制的陶埙参加了“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奖”展览会,获得好评。之后又成功研制出造型和传统陶埙相似,且简单易吹、适于普及的“哨埙”。2009年9月,“李氏陶埙制作工艺”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李钟汾为项目传承人,2010年被山东省文化厅授予“山东省文化行业高技能人才”称号。退休后被聘为我校音乐学院教授,先成立了“李氏陶埙制作与演奏”研究小组,在陶埙纳入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后承担“陶埙制作与演奏”课程的教学。2014—2015年间,李先生身染重疾(癌症)仍坚持授课,不过,他对李氏陶埙的传承忧心忡忡,多次催促我选择年轻教师接替他的教学。徐琦博士2015年来我院工作,辅助他进行陶埙制作与演奏课程的教学,2016年1月,经李钟汾先生同意于我院举办拜师仪式,徐琦成为李氏陶埙第四代传人,先生终于得偿所愿。
(四)踏实勤奋的传承人徐琦博士
徐琦本科是竹笛专业,硕士是中国音乐史专业,博士则是音乐教育专业,2015年7月入职我院任教。他在入职面试时展示了陶埙演奏,这也是能够录用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时期,李钟汾先生已经查出身患癌症,很难继续承担陶埙课程的教学任务。徐琦入职后承担竹笛教学及民乐团排练工作,并依托我院山东省文化艺术重点学科“地域音乐文化研究”(“十二五”重点学科为“地域音乐文化”,“十三五”重点学科改为“地域音乐文化研究”,特此说明),选择李氏陶埙作为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他首先担任了李钟汾先生的陶埙助教,在拜师后,更加积极虚心地向李钟汾先生学习,并承担起了李氏陶埙教学传承的重任。经过潜心学习,他深得李钟汾先生制埙技艺真传,对练泥、拉坯、阴干、修形、抛光等陶埙制作要法都得心应手,在教学实践中孜孜以求地不断探索着陶埙的奥秘和真髓。自2015年9月承担德州学院“陶埙演奏与制作”课程教学以来,每年教授学生20余人,至今已经培养学生300余人。2019年建立德州古埙工作室,2020年被评选为德州市非遗传承人,2022年晋升为副教授。
四、德州李氏陶埙传承实践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国内对“口述史”的关注逐渐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民族音乐学和传统音乐研究领域极为重要的研究方式,使笔者对于德州李氏陶埙的诸多传承问题及今后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启发和认识。通常“口述史”是研究者运用录音、访谈、叙事等相关方式,搜集整理调查者的口传记忆、口述材料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进行整理还原的历史。[1]笔者非常赞同与欣赏臧艺兵先生的观点:“他们的叙述只想对世界说出一句话:笔者们也活过。尤其重要的是,口述历史会更让个体生命的灵魂得到独特而充分表达。这会使历史更细腻、更入微、更深刻、更生动、更确切、也更方便地让人们进入历史的时空中去立体地感受历史的存在。口述历史就是人类呈现自己发展历程的一个有效方式,重要的是这个方式对于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体现了一种生命存在的公平。”[2]每一位传承者都是一粒种子,你不知道将来会有哪一粒种子在世界的任一角落生根发芽,支撑起一片新的绿色。李氏陶埙的创始人李雨村便是吴浔源先生撒下的众多种子的一颗,其发芽结果,将陶埙技艺传承了四代,是为典型案例。吴浔源、李雨村、李孟才、董玉水、李钟汾、李峥嵘、徐琦以及学习陶埙制作和演奏的学生们,他们都是小人物,做的都是极为平凡的小事情,但他们对民间技艺的坚守和标准是值得研究者们重视与关注的。
以口述史的视角审视德州李氏陶埙的传承实践案例,首先是高校介入非遗传承的必要性问题。高校介入是非遗传承的众多路径之一,之所以重要且必要,在于高校具备固定的教育平台和教育资源,一旦将非遗项目纳入到教学体系中,可以使其传承活动得到有效保障。相当数量的非遗项目如果以家族传承方式继续下去,很有可能会随时中断,李氏陶埙便是典型的案例之一。因此,高校介入使非遗传承的链条得以加固,为传承保留了火种,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当然,高校介入非遗传承也有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实施过程中的课程设置、学分、经费及重视程度等问题。非遗项目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虽然可以使教学活动得到保障,但同时会受到一定制约。人才培养方案有/Io07+t1wdxXwkOW8Ri7qm8bUc1YoiQD1YC/oqXQ8G0=着相对固定的模式和板块,主要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大类,非遗类课程作为特色课程一般只能纳入选修类课程板块。而选修类课程一般开设年限为一学期,最多两学期(主修专业选修课除外)。以陶埙课程为例,2012年最初开设在第五学期(大三第一学期),每周两节课,但一学期的选修很难让学生达到熟练制作成品的水平。2013年改为开设在第三学期,开课时长延长为1年。2016年至今,“陶埙制作与演奏”课程调整到第一学期,开课时长1年,第二学年与器乐选修课相结合,学生实际学习时间为2年。
另外,目前大学教学管理制度为学分制,陶埙制作课程只有1学分(不能随意加分),制约了学生选课的积极性。经费问题是指开设陶埙制作与演奏课程所需要的场地、设备、耗材(胶泥)及烧制等所需的费用,均需要学校层面的大力支持。很多非遗类课程因属于特色课程,在建设过程中的经费支出会陷入教学和科研相互矛盾的尴尬境地。当然,这些都是细节问题,但处理不得当也会制约其教学效果和发展质量。关键在于校院领导是否真重视、真支持,很多学校领导表面是重视的,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缺乏切实具体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最后是关于传承人的培养问题,这里涉及传承者和传承人两个概念。简单说传承人一定是传承者,而优秀的传承者才是传承人。纵观李氏陶埙传承历程中涉及到的众多传承者,李钟汾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李氏陶埙的传承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提升作用,正因为如此,才被评为省级传承人,这是国家对于非遗优秀传承者的肯定与标志。笔者认为,要想搞好非遗传承工作一定要抓好“点”,做好“面”。抓好“点”是指抓好优秀传承者的培养,做好“面”是指非遗传承者的培养普及工作。只有形成良好的非遗传承社会环境,有更多的人加入到非遗传承的工作中来,才能不断涌现出更多的优秀传承者。同时,优秀传承者也是可以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重点培养的,家族传承人的培养有一定的限制,而高校教育传承则可以充分发挥国家体制的优越性,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人选进行重点培养。徐琦可以作为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他在进入李氏陶埙传承教学短短5年间便成功获批“李氏陶埙制作工艺”市级传承人,目前正向省级传承人迈进。
李氏陶埙由家族传承到高校教育传承的转变过程只是众多非遗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传承方式,不是唯一,也不一定最好,但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阶段,这种模式对一些濒临灭绝的非遗项目确实能起到起死回生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2]臧艺兵.我们也活过:以口述史为证——论口述史在音乐学领域的运用[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7,(1).
(责任编辑:李鸿熙)
作者简介:段 文,男,博士,德州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教学与研究。
徐 琦,男,博士,德州学院音乐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研究方向:民族器乐。
项目来源:本文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研究专项“省级非遗‘德州古埙制作技艺’传承创新研究”(2022-2XLC-3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