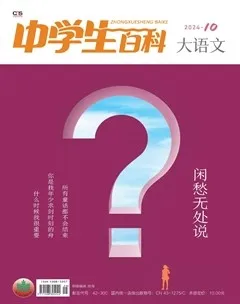土地里长出来的房子
在读《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这本书之前,我有一种迫切的执念——特别想拥有一幢带院子的房子,而且这房子最好是在田野里或者森林中。
符合我想象的,是学校北边、高铁站南边的几幢本地房子。它们是农村自建二层楼房,有宽敞的阳台,最令人羡慕的是,门前春天时有大片的油菜花,夏天里有青绿的水稻。这些房子就像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那么水灵自在。
我总是幻想在那样的房子里养猫养狗,在门前晒太阳,去油菜花地里跑。在院子里,会有爬了一墙的粉色蔷薇,角落里种着结香,门前是两棵云蒸霞蔚的樱花树。挨着墙边的地方,我会栽满珍珠绣线菊,剩下的空地就全用来种菜,韭菜、西红柿、豆角和生菜。
收到这本书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读了《引子》,读到最后,眼泪不知怎么就流出来了。我想是因为作者申赋渔在引言里解读了我的这种执念。我为什么在这个年纪有了这样的执念?曾经,我是喜欢高楼大厦的,是喜欢双脚离地不再沾土的。
“一个朋友说,当你忧郁痛苦不能自拔的时候,你就在心里回想最美好的事情。只有美好的回忆,才能治愈残破的心。每当这个时候,我想起的竟然是童年的茅草屋,屋门口围着竹篱笆的小院子……”
我也是啊,我常常回想自己童年时故乡的院子,那里有从春天开始播种的蔬菜,有一棵结瘦弱果子的樱桃树,有我强壮的父亲在自己搭牛棚,还有过两条长寿的狗,都是我取的名字,而且都叫里更。我还清晰地记得,我放牛时光着脚丫,记得泥从脚趾缝里挤出来的感觉。
我走过很多地方,但对任何一个地方的留恋都如申赋渔所说,是“虚情假意”。如此看来,我似乎终将回去,回到土地里去。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申赋渔是在南京的郊外买了那所房子。在很多年里,他国内国外流浪,但最终还是一个人回到了这里,按照自己的期待打理并居住在那所房子里。他和房子外的白鹭相互对望,提防着野猫,留恋着房子外乌桕树下的河水;他曾遭遇一只狗的死亡,与一只猫守岁,关心一只斑鸠的命运。与他来往的人,由文人墨客变成了石匠、木匠以及木匠有病的妻子,还有水电工老刘、承接工程的李师傅。作为新闻记者,他曾经投身于一个宽广复杂且伟大的世界,然而现在这幢房子,连带这幢房子里的蜘蛛、蚂蚁,屋外的雨点、喇叭,方圆三里的地方就成了他的新世界。他一直期待一场大醉,而醉后的自己仿佛变成了蛛网中的一粒尘土。

申赋渔引用了庄子的话,“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机”是细小的粒子、精微的能量,也是琴弦上振动的吹开百花以及万物的微风。世间的一切,来于尘土,归于尘土。读到此处,我恍然大悟,原本我就是一粒尘土,对土地的执念只是我基因的天性欲望。我是从泥土里长出的孩子,我的基因里流动的是泥土的魂魄,我一直敬仰那片泥土上跳跃的卑微生灵和愚昧无害的人们。
是谁在呼唤着我的归去?我不知道,我只是无法控制。我是一直在被城市驯化的孩子,而土地一直在以深沉的低吟试图唤醒我。可是我真的还能回去吗?
天黑的时候,我看向学校外的那几幢“梦中房”,觉得它们好孤独、好冷清,仿佛是被世界遗忘的虚无。我对自己说:“别再有什么执念,其实你已经回不去了。”
“每一片森林都是从一粒种子开始的,就像每一段人生都是从一个意念开始。”这是申赋渔写在引言前的话。那么,我这只山雀懂得了另一只山雀吗?我在这本书的最后,如此写道:你的眼睛很好,能看到那么细,看到流水的波纹、鸟的羽毛和猫的眼神,不像我,已经失去了眼神。你也爱土地,却不像我,对土地有着逃离却不被驯服的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