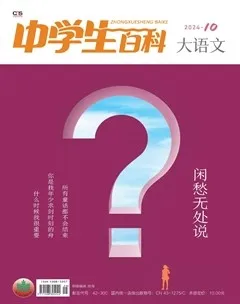你是我年少求剑时刻的舟
▲
安隽站在窗前,觉得今年秋天比往年来得要早一些。风从四面八方涌来,灰喜鹊从草地上起飞,天空蓝得惊心动魄。她对秋天的感知是从空气里嗅出来的,一种只属于这个季节的气味。
经过三次手术,安隽脸上和颈部烧伤的痕迹已经不甚明显,但皮肤的末梢神经没有恢复,瘢痕所至的整片区域麻木得很。她感觉不出这风急不急、凉不凉,甚至,感觉不到有风。
安隽今天出院。这次复查一切正常。
林然本要来接她的,安隽知道他在忙留学申请的事情,坚定地告诉他不必来。她自己收拾东西,办理出院手续,在医院门口打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家里地址,然后靠在后座假寐。来医院太多次了,这些事她早已轻车熟路。
一路上,安隽几次微微抬起眼皮,发现司机有意无意地从后视镜打量她。安隽戴着墨镜、口罩和围巾,把脸和脖颈捂得严严实实。一定很奇怪吧,这个天气,有人戴这么大的墨镜和这样厚的围巾。
▲▲
到家时黄昏已近,放下东西,安隽不着急准备晚饭,静静地在沙发上坐了很久。她喜欢黄昏时的光线。暮色给她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荒芜、空旷,但是安全。这个时候,她的心安静得像一座秋天里颓败的废园,没有麻雀和灰鹊,没有一点人声,有的只是那些自生自灭的植物和植物上面流过的一寸一寸光阴。她在这暮色中可以顺流而下,自由地烫烫记忆的褶皱。
这房子是母亲留给她的,父亲再婚后就搬出去了——这是安隽同意父亲再婚的条件。母亲在安隽18岁时因病去世。安隽不拦着父亲开始新生活,但这是曾经也属于母亲的房子,是她长大的地方,她曾在这里有一个完整的、幸福的家庭,因此绝不允许其他人介入,或者说打扰这段回忆。
父亲同意把房子给安隽。带着安隽去办过户手续那天,他说:“爸爸工作太忙,关心你太少,对不起你和你妈,以后爸爸会好好照顾你。你自己住我也不放心,你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这里你随时想回来都可以。”
安隽从小不缺钱,因为父亲在经济上总是尽量满足她。她缺爱!成年后她尚未明白这世间每个人本就孤独的道理,只知道以后生活的路得自己走了。
她笑了笑,说:“不了,爸爸,我想自己住。”
▲▲▲
林然接到安隽的邀请时非常诧异,并且莫名其妙。他不知道安隽为什么会突然回学校参加舞蹈学院的汇演,她明明还在休学中。他本想打电话问她复查的情况,没有打通,后来也只收到一条孤零零的信息:“国风专题汇演有我的节目,请你来看。明晚7点,学校文汇楼一楼。”
林然是安隽同校不同院系的学长。说起来,他也算是安隽的救命恩人。
一年前,林然去做兼职,路过学校边上的虔江,只因不明所以地转头多看了几眼,就注意到在江边低头徘徊的安隽。对这个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女生,他凭直觉判断她可能情绪不对。你看,有些事真是说不清也道不明。
林然不远不近地跟了许久,直到安隽也察觉到自己被人注意。之后的故事,没有任何的过渡。安隽突然转过身来,歇斯底里地质问林然为什么要跟着他,然后号啕大哭……
虽然并没有做傻事,但哭出声来后的安隽还是有种死里逃生的错觉,又或者说是痛觉。这种痛,像烈焰一样灼烧。稍稍冷静一些后,她茫然地看着林然,又转头望向远方。夕阳把整个苍青色的天烧红,把落满积雪的枯树烧红。她仿佛看到林然陌生的脸正与这雪地和枯树慢慢融化在一起。a1c27950a2e76d1e2fabe3e3d1017371f71efc42d8e65293648704b5de35a638
一切来得太突然,以至于林然什么都不敢问。倒是安隽先开了口:你是谁?林然简单介绍了自己,然后很小心地告诉她,自己为什么会一直跟在她身后。安隽眼前的那张脸逐渐清晰起来,年轻光洁,神色温柔,带着关切与担忧。
他怕她说话费力,微微歪头,与她靠得更近一些。
安隽笑了。那个笑容,在林然眼里有种怪异的割裂感:一半柔美苍白,是打磨后浸在水里的和田玉料,还存留莹润的光泽;另一半瘢痕累累,是粗糙砂纸上再写半幅惨剧,仿佛顷刻就要枯槁。
他下意识转过脸去,不忍卒视。他大概猜到了,她之前经历过一场与火有关的劫难,或者是类似的劫难。至于真相如何,他不问,她也没说。
▲▲▲▲
安隽从不知道,原来重新穿起这身舞衣,也需要莫大的勇气。眼前的裙子布满褶皱,不曾熨烫,像一张哭皱的脸。
这条裙子原本是她的最爱,现在忽然变得可怖。白色织物上流淌着生冷而陈旧的气息,像上世纪苟延残喘的历史遗物,像锦缎生了霉,像生铁起了锈。
她笨拙地展开它,穿上它,抚摸它。她忽然紧张起来,好像身上穿着的并不是一条白色的裙子,而是一件银色的铠甲。她穿着这铠甲,带着生铁的气息慢慢向镜子走去,不敢朝镜子里看。
身段还是那个身段,脸却已不再是那张脸。
那天安隽拨通了辅导员的电话,告诉辅导员自己想参加汇演。安隽办理休学后,老师、同学的关心没断,只是好几次想上门慰问,都被她拒绝了。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她主动联系老师。老师自然忙不迭地答应,并且很快安排妥当。
这支舞安隽练了很久很久。
从得知毁容的那一刻起,安隽就再没奢望过继续学舞,甚至一度对人生绝望。她深知,所有台前的艺术类职业,都多少需要美貌加持。
但她还是想再跳一次,一是为自己,二是为林然。她要为自己跳一支舞,好记得自己曾经美丽的样子。她要为林然跳一支舞,让他记得,他未曾见过的样子。
▲▲▲▲▲
林然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毫不吝啬自己的善意与温暖。那次在江边相识,他要了她的联系方式,对她关心有加。后来熟悉了,他时常去看她,去的时候还会带些吃食,吃完后两个人窝在沙发上聊天。
安隽问,你知道我为什么那时候特别想不开吗?因为我没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在某一天变成这个样子……我完全没有准备,也接受不了。林然轻轻握住她的手,那只手纤细、冰冷、微滑。他知道这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是在讲厄运的吊诡与人生的无常。
林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害怕你做傻事吗?我曾有个妹妹,7岁时在河边玩水,一脚打滑,掉进了河里……那年我11岁,什么都不懂,懦弱胆怯,不敢上前,眼睁睁看着她被水吞没。我很伤心,心里从此有了阴影。就算十多年过去了,做梦梦到她,我还是会哭。
她望着他年轻而充满生机的脸,心想生活令人厌倦的一点就是它总让更懂事的人来承担糟糕的感受和结果。
他说:“我妹妹跟你同年,如果好好长大,也已亭亭。”
他眼神亮而专注,偶尔闪烁一下。安隽明知道他在怀念一个遥远时光里的人,可又似乎在望着眼前的她。
她有种错觉,与隐忍又热切的喜欢有关。
▲▲▲▲▲▲
林然站在礼堂一侧的走廊里,望着前方舞台上烟雾迷蒙,怎么也无法将记忆中的那张脸,同台上的安隽联系起来。
他到的时候已经没有座位,站着看完了整场表演。
夜色如流淌的绸缎,音乐像水一样沿着绸缎浸漫,她自水中悠悠浮现……
意似近而既远,若将来而复旋。雾绕骨峰,江起肩胛,皮肉沉雨,经久不歇,仿佛山海丰腴,她便永不枯寂。
林然从不知道,原来她这样美,原来她的舞,跳得这样好。他忽然有一种感觉,人生际遇不可知,离合天注定,而他们注定会相遇。
汇演结束之后,林然在门口等安隽出来,然后送她回家。
那天,他们在楼下作别。她站在那里,望着林然离开。天上有一弯寒瘦的月,正别在梧桐的枝丫间,如落在巢中,像是它从来就长在那里一般。
那天月色如雪,林然也像跋涉在雪地里一样脚步滞重,一步一回头。
安隽忽然怀念起她那沉寂安宁的黄昏,只有在那样的时光里她才处之泰然。她也想偷黄昏的酒与他不醉不归,可又怕自己刚举杯他已走。
安隽不知道,如果有些话说出来,他们能不能短暂地依偎,像两只在冬天偶然遇见的松鼠。她只觉得,纵然醉梦极美,也难以长过蔷薇,那就不必!
他自有鸿鹄之志,终要去山高水远,不可能长久待在这里。那支舞跳尽了万字的挽歌,致无言的爱恋,假装写过壮阔的情诗,送给陌生的人。
安隽觉得林然之于她,就像她爱的一首歌里所描所绘的:他是她年少求剑时刻的舟,是孤旅者不眠夜燃的灯,你以为稳固长久,其实不是的;又像那天上的月亮,落在河畔的波光里,你以为它离你很近,其实不是的。
她萌生过一种爱的错觉,其实不是的。
安隽朝林然使劲挥一挥手,意思是:走吧,快走吧!
▲▲▲▲▲▲▲
林然顺利通过了留学申请,去英国。他走的那天安隽没有去送他。
安隽在第二年复学,申请转了专业,留两级,等于要从头开始学起。人生也仿佛重写了曲谱。过往已是过往,那个跳舞的少女留在了昨日。
她在重新入学之前,去了一趟英国旅行。她没有告诉林然自己也降落在了那个国度,独自去看了他描述过的山峦、河流、森林、湖泊。
城市车马喧嚣,建筑并不高耸,彩色的玻璃反射着阳光煞是好看,穿戴夸张的乐手坐在街边拉着古老的手风琴。
原野空旷寂静,山坡上一排排矮房被刷成薄荷叶的颜色,小小的方窗透出温暖的光。苍蓝的夜空下,有人在门口挂星星。
安隽在旅行中听了一路的歌:你是我年少求剑时刻的舟/载着一生的平凡美梦/搁浅在岸头/也算看过了许多星海苍穹/却各自奔流……后来我单枪匹马去听春风/去看错过的世间种种/每一座山峰/要这千里迢迢相逢/幸而来日无穷……
特约评析 | 宋雨霜
成都文理学院文法学院写作教师,讲师
有些相遇、相守不是结局,相互救赎已是最好的意义。读完《你是我年少求剑时刻的舟》,我轻轻念出这句话。黄昏、独处、陪伴、救赎、舞蹈……青橄榄般的青春故事跳跃在经由文字建构的画卷上。
全文内容并不复杂,讲述了一个丧母、毁容的独居女孩被学长鼓励,重拾信心回到校园的故事。作者善用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法讲述,错杂交织的时空画面增强了阅读趣味,提升了审美效果。行文长短句错落,善用四字句,对称映照,富有美感。如“意似近而既远,若将来而复旋。雾绕骨峰,江起肩胛,皮肉沉雨,经久不歇,仿佛山海丰腴,她便永不枯寂”,把安隽重返舞台的表现描摹得生动灵性,具有想象张力。文中的一些比喻也值得咀嚼,如“眼前的裙子布满褶皱,不曾熨烫,像一张哭皱的脸”,把裙子比作脸,角度新颖,本体和喻体之间巧妙的对应亦与全文的意蕴主题相扣。
“刻舟求剑”是寓言演化而来的成语,人们对它的认知存在刻板印象。小说借同名歌曲《你是我年少求剑时刻的舟》为题,赋予“剑”与“舟”新颖意象,形成生动的意境,也有几分悬念,引人思考——到底是怎样的你我?“舟”与“剑”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掩卷回味,林然是载着安隽走出心灵暗河的那条“舟”。安隽克服心理障碍穿上舞衣,重回舞台,她举起了心中的“剑”,对着那压抑、自卑、绝望的坚冰砍去。
男女主都有着苦难悲伤的遭遇,相遇如一抹阳光照亮晦暗的心房,救赎彼此。其实再细想,救赎他们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呢?林然守护江边独行的安隽,是对懵懂无知失去妹妹的救赎;安隽重回舞台,想给自己和林然全新的印象,是向自卑压抑的自己告别。而结局是开放式的,故事中的他们是否重逢或者相守已不重要。曾经相遇,温暖过彼此,已然足矣。情意如“舟”,曾载着女孩越过万重山,渡过千重浪。这条“舟”永远摇曳在生命长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