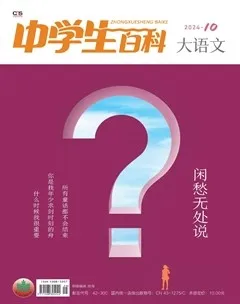从鲁迅的中年腔说起
我查了一下“腔调”的含义,一是戏曲表演中的曲调,一是说话的声音和语气。一个人有腔调,一篇文章也有腔调。说人有腔调好懂,装模作样的,惟妙惟肖的,声嘶力竭的,这些都跟腔调有关。腔调好让人赏心悦目,写文章如果腔调正也会让读者如沐春风,沉浸回味。
讲解鲁迅的《呐喊·自序》,我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感受这篇文章的腔调。一个人的腔调是一举手一投足的显现,是细节、动作、声口的表达。一篇文章的腔调感,毫无疑问得看第一句第一段。不妨看看《呐喊·自序》的第一段: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读文章的时候不喜欢咬文嚼字,换句话讲就是读得很快。但是,读鲁迅得小心谨慎,因为他笔下的字句所牵扯出的感觉非其他作家可比。放在聊“腔调”的语境里,我的问题可以细化为:这是一个多大年纪的人写的文章?大家都能回答得出,是一个中年人,而且是一个经历不简单的中年人。
正所谓“中年哀乐损天真”,鲁迅在这第一段就已经定下了全文的调子——他想跟你说说他的寂寞心事,并且已经决定打开往事的闸门。不过,虽然打开了闸门,河水也并不汹涌,你不仔细一点还不一定听得明白。
这篇文章我之前讲过很多遍。这一次解读,我在第一句话上停留了几秒钟。“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我在想鲁迅写的时候为何加上“也”字。他大概是想说,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做过很多黄金好梦,只是别人都还记得,还很宝贝,而他渐渐忘了。这个“也”是在说和别人的不同吗?
鲁迅文章的腔调感非常好。这篇文章写于百年前,百年后的读者读这一段话,很明显的感觉是:有一点跟现代白话不太一样的鲁迅式表达,而且要说一个不讨喜的话题——寂寞;这个“寂寞”看来也不是一个小寂寞,总有一点欲说还休的味道。你看,他的腔调透露出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中年男人”。
文中有一段对话把这个中年人的沧桑感推到了高潮: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新青年》杂志的钱玄同(金心异)问他钞古碑有什么意思,鲁迅说没有。虽然没有意思,但按照鲁迅的想法,他还是准备再钞。钱玄同最后劝他给《新青年》写点文章,貌似有点理不直气不壮。这段对话看了很多遍,我发现鲁迅真是极度缺爱,掉在冰窟窿里好久,心里未尝没想着有人拉他一把,但是冰窖里待得太久,恐怕生出了“外面不见得好,这里未必差”的感觉。
这种叙事腔调的把控真是炉火纯青,字不多,有分量。如果换了我们来写,恐怕会写成这样: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地跳动。他劝我为《新青年》写点文章,我犹犹豫豫答应了。

如果真写成这样,就是毫无腔调。桑兵老师在《如何提升史学论文的文字表现力》中说,现在史学系学生的文字表现力已经差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文字表现力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没有腔调。他们不懂得如何营造腔调,所以语言是大众的、平凡的。如果说语言是最直观的,是那池塘里若隐若现的鱼儿,腔调就是跃出水面的塘鲤鱼——关键是那瞬间得以呈现的活蹦乱跳。
既要写语言,又要注意营造腔调感,看上去不简单,不过我们可以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就是下笔第一句话一定要慎重。
延伸阅读
■一个词:中年哀乐,意指中年人最容易动感情,常触景生悲或生欢,出自《晋书·王羲之传》中王羲之与铁哥们谢安的对话。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谢安曾经对王羲之说:“人进入中年以来,容易为喜怒哀乐所伤,与亲友分别后,总要难受好几天。”王羲之回答得很直接:“年在桑榆,自然至此……”翻成大白话就是:老铁啊,都老成这样了,不很正常吗?此处的桑榆比喻垂老之年。王羲之还跟谢安透露了一个小秘密。“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意思是说自己近来正靠音乐排遣忧闷,还总担心被儿女辈发觉,影响欢乐之趣。陶写,即怡悦情性、消愁解闷。
■一个人:钱玄同,即鲁迅所写的那个“偶或来谈的老朋友金心异”。为什么叫金心异呢?是因为林纾曾写过一篇小说《荆生》,痛骂文学革命的提倡者,借小说中的人物金心异来影射钱玄同。钱玄同早年留学日本,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五四”时期参加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在他的敦促下创作的。1917年8月,为劝说周树人给《新青年》杂志写稿,钱玄同去了补树书屋,在一棵老槐树下与周树人进行了一场石破天惊的谈话。最终,周树人被打动,决定走出隐默,并在次年4月写出了振聋发聩的抨击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时署名“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