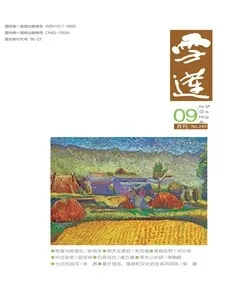杜梨树下的土地
【作者简介】齐未儿,原名李冬梅。有作品散见于《散文》《山花》《四川文学》《黄河》《黄河文学》《中国校园文学》《胶东文学》《当代人》《散文百家》《北方文学》等刊。出版书籍有《秀丽的家园》《二十四节气果蔬》。
1
在母亲的讲述里,杜梨树是一棵老树,根深叶茂。谁也不知道它是从何时植根于这片土地的,唯一肯定的是比我们落地生根更早。我的祖籍山东,早年,先辈背井离乡闯关东,没想到,半路发现一座村子,留了下来。反正到哪里都是为着填饱肚子,到哪里都要勤忙肯做才有饭吃。
坐在母亲身边的我,安心听故事,想着树缘自于哪里呢?是一颗什么样的种子萌芽抽枝展叶而长成了树的形象?种子是被鸟带过来的,还是粘在小兽的皮毛上不经意甩落到这片弹丸之地?树的童年少年,在历史的哪个节点?它第一圈年轮里,留下了怎样风霜雨雪的信息?它要捱过多少个四季流转,冷与暖的迭换,旱与涝的锤炼,才能够长得挺拔高大?
它的枝丫奋然向上,探向远天。每一片叶子都像小船,游弋在季节的河流,与日夜擦身而过,晃亮每一颗星星的灯盏,再摇醒日出的响铃。那个站在地上的生命,并不苍老,它有一个向上的灵魂。鸟儿是树的信使,携长风万里,扶摇直上,托着满树叶子的呼喊,落到云端探问消息。于是云接受邀请,飞临树枝歇一歇,眨眼间,留下满树玉白花朵。雨脚停在树上,滴滴答答,像是在说着什么悄悄话。雨收了,花谢了,果子初孕。
杜梨只有个指甲盖大,圆圆的,一嘟噜一串串悬在叶间,晃呀晃呀,叶子也绿,果子也绿,谁会在意?只有叽叽啾啾的鸟们,不厌其烦地透露着各种消息,给谁听呢?果子不声不响地,把日子晃老,一天天翻了篇儿。夏日嘹亮。阳光陡然暴烈如金芒,铺天盖地泼洒,叶子显得蔫头耷脑,每一颗果子都没心没肺地继续在风中摇晃。于是,秋风赶跑了热浪,顺手把满树叶子的水分抽走,绿沉下去,赭黄窜上来。杜梨毫不掩饰地亮出暗黑色外皮,等着淘气的孩子攀上去采摘。熟透的杜梨软烂,涩味淡了,酸味显得缠绵,一直流连在舌尖。
耕地在杜梨树下,以此为名,叫作“杜梨树底下”。祖祖辈辈繁衍,村里人口越来越多,把地块儿按人口分给不同人家耕种。
这么分呀分呀,谁知道哪一年呢,杜梨树消失在这片以它为名的土地上了。等到我出现的时候,只能在想象的浓阴下,遥想几个人合围的大树该多么气势不凡。乌鸫飞过来,喜鹊也来,树变成了杨树和柳树,不是站在田间地头,而是在通向田地的路边。
2
“去杜梨树底下”,人们呼儿唤女下田做活儿时这么说。街坊邻居在村巷里遇上,言语里也是“去杜梨树底下看看”。地在村南,既不高,也不低。和周边其他地方没什么差别,都是盐碱滩。阳光照在盐花儿碱花儿上,银亮亮的,闪闪发光。如果下了雨,地皮湿透,黑乎乎的,种什么呢?大多是抗盐碱的水稻。春天育秧的土,是别处运来的,做几个畦,秧苗被小心呵护着长大,绿得茁壮。等到把它们移栽到水田里,青绿迅速褪去,叶子发黄,萎蔫,像是少了骨脉,倒伏在水面上。父亲说,是被碱拿的。捱过去,脱胎换骨,从芯里萌出新叶,算是活过来了。捱不过,空出个落脚之地,再找来秧苗补上。时令不等人,渐渐入了夏,抽薹展叶,拔节扬花,再于秋日里成熟,或稀疏或稠密,好歹解决了一年的口粮。
这是我印象中的杜梨树下,早年见过的土地。
后来人们发现,种水稻的地,竟然也能种其他庄稼,于是田里的作物摇身一变,换成了玉米和高粱,也有豆子和花生。护秋的人住在窝棚里虎视眈眈,一点也不影响我们钻进田间,找那种叫“小鸡乐”的高粱秆。这个品种与其他高粱不一样,个子矮小,铁秆,剥掉外边的叶子,劈开硬硬的外皮,咬一口青绿的瓤,汁水丰足,一直甜到心里去,不比甘蔗差。
还能打乌米,长长的苞叶包裹着剑一般的一截穗子,劈开苞叶,粉白的皮露出来,咬一口,是黑色的没长出颗粒的穗,口感绵软。这些乌米,可不让大人欢喜,是长瞎了的粮食。有人用乌米熬酱下饭,我家没尝试过。结乌米的高粱个子高,不是“小鸡乐”。还有一种糯米高粱,秸秆高有两米,抽出的高粱穗疏松散乱,披垂向下。姥爷整理扦下来的高粱穗,一副慎重样子。辗过高粱米的穗子做笤帚、做炊帚,用处多着呢。糯糯的高粱米,用作食物的需求倒在其次。
这几年高粱的销量明显不如玉米。糯玉米等不到秋天,就青枝绿叶着装到袋子里卖给了收货的人。玉米养生,是连村里老人家也津津乐道的话题。日子好过了,胖子满街都是,还吃什么细粮吃什么肉呀?烀玉米吧。去田里的年轻人少,中老年人多,如今做什么都有机械帮忙,种地不像之前一个汗珠掉地上摔八瓣了。犁地有旋耕犁,下种有播种机,锄草有喷灌的药剂,浇水施肥有潜水泵,用不上两天就完成了。余下的时间,清闲了,像孩子们一样端着手机,抖音、快手换着看,玩游戏的不多,也能把手机用到烫得慌。有人窥到商机,在网上开个直播小店,卖粮食,卖海鲜。快递可不挑剔海边还是树下,只要有需要,开着车疾驰而至。发货、送货都能上门,热情服务。刚入冬那会儿,七十多岁的姑姑来看我妈,带来一件毛绒衣服。她抖开,让老嫂子看面料,又让试试,穿着压风,正好天寒地冻的时候套在衣服外边赶集上店儿,短款,利索。母亲拿钱要给我姑,她笑着摆手,哎呀,没花多少,不用给不用给。你看,我这一身儿从上到下,都是抖音直播间买的,有便宜处理的才下手。我一天一天举着手机不停看,哪家店里便宜,有数儿。我买的,价钱少,穿着实惠。现在我可是一会儿也离不了这智能手机,交电费,交保险,都从这里划。方便,还快。
孩子们放假回家,用笔记本电脑给母亲放电影电视剧,也给父亲放综艺戏曲和相声,看得津津有味,一个劲儿感叹网络方便。更多时候,母亲还是里里外外走走,在阳光和暖的晌午头儿,把院子里拾掇清爽。父亲仍是闲不住,天还没亮透,他就出去,九十点钟,必定推着一车柴禾回来。林子里的树枝,旱田里的秸秆,沟塘里的大苇子,轮换着载。炊烟袅袅热炕头儿,才是父母半生的稳妥。
去年秋末冬初,我跟着父亲去村外拾柴。一路之隔,路北种了大片玉米,粮食已经收获,秸秆横七竖八。风东刮一场西刮一场,枯黄的秸秆越发凌乱。羊在稍远的地方,耐心十足地啃吃秸秆上残留的叶子。放羊人坐在不远处闭目养神。路南看上去一片荒芜,衰草连天。地当然还是不肥沃,杂草们却从来不嫌弃贫瘠。小时候我常想,要是稻苗长得像稗草一样旺盛,就好了。现在,这里看不到一根稻茬,大部分土地承包给了专门种俏货赚钱的人。今年这些地倒没有承包给外地人,南街住着的大顺找到村委会,把地给包下了。
我和父亲把小推车放在地头儿,一步迈进田里。我弯腰把长的短的秸秆放在一起。父亲并没停下脚步,径直往深处走。他转过头喊我过去,秸秆果然很多,攒一攒,就是一小堆。我们一起把小堆再凑到大堆上。眼见着够独轮小推车装的,我尾随父亲走到路上。这是一条被枯草掩蔽的田间小路,来的时候,父亲在前边推车,我跟着,并没发现路被草镶得面目不清。
站在那儿,抬头望去,由近及远,除了牧羊人和我们,再看不到其他人影。几只灰色的鸟,拍着翅膀起来又落下,它们需要落在地上的玉米粒充饥。
低下头,才注意到,路对面连片都是花生秧,枝子上已经没有几片叶子,却一点不影响对我目光的牵引。我深觉诧异,秧子还仔仔细细长在地上,花生还没锄走?父亲摇摇头,踢踢近旁的枯枝败叶,让我拔起来看看。那些花生角,兴兴头头在根部摇头晃脑,好像在说,你看,我们都在呢。
环顾四周,远处看不分明,近处的地面上东倒西歪着不少花生秧。怎么不收呢?这也太糟害东西了。父亲说,雨水大,收秋的时候,连三并四下了好几场,站到村外,大水泼天,一片汪洋,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看不出路,也辨不出田。过了两天,水下去些,路上能驮住人,承包地的大顺和媳妇提着铝盆到地头儿。推着盆在泥水上挪,拔到哪儿推到哪儿,花生果被泥镶上了,半天也没拔上几撮,枝子拔下来,花生大多留到了泥里。大机器进不来,人力拔不起,雇人做活儿,花生钱不够给工钱。父亲种了大半辈子田,看着庄稼不能收,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不住地长吁短叹。母亲说,后来父亲自己去过,泥里水里的,捡了一些花生回去。连九牛一毛也谈不上。
父亲一边说,一边指给我看。另一侧不远处,明显有块台地略高,父亲和母亲每年来种大葱,有两年收成好,葱长成了仙鹤腿,一大截葱白,几枚绿生生葱叶,戳到地上,跟我个头差不多。雨水也败了葱的兴致,虽然赖于台地的高度,没有全军覆没,却长成了营养不良的样子,挺起腰杆都费劲儿。剥掉外皮,内里的葱身,没有小指头粗。
即便是各种农具变得现代化的年景,农民,仍然需要靠天吃饭,风调雨顺,才是保证收获的先决条件。
花生在土里,泡过水之后,外皮发了毛,果粒变了色,本来红艳艳的,现在躺在我手心的,已经霉变,成了棕黄色。我似乎可以看到陷在土里的花生,一颗挨着一颗,沉默地,等着上了冻,在春风和暖的时节,跟着返了浆。一冻一消,它们腐烂成泥土的一部分。冬天到了,田鼠会来把它们搬回巢穴吗?会有饿肚皮的小兽来刨冻土之下的果实吗?我到田里转了一圈,地面上有散落的,捡起来剥开,没有一颗颜色正。放到齿间,味道似乎没什么变化。可是父亲说,霉了,要不得。
我看到大顺在街上骑着摩托车疾驰而过,又去做木工收拾船了。他媳妇端着盆,穿着厚厚的棉服,起早贪黑跑到养了扇贝的人家里,剥扇贝肉。她手快,每天都赚个两三百。
面对一片折损了那么多粮食的土地,我和父亲,除了哀叹几声,又能做什么呢?
父亲指着身边的草,要我走在前边,他推车跟着,免得歪到路边的沟里去。我问父亲,挂在车把上的布包里有没有小绳,系在车头,我拽着,他推车轻省些,也容易跟。他果然翻到了几米蓝色的胶丝绳,比不得麻绳好用,总好过没有。小路上的荒草不断碰到我的腿,脚下的路面凹凸不平,我慢慢向前,步步稳当。
拽着小绳,我还能跟父亲闲聊几句,这样一来,脚步明显放慢了。父亲并不提醒,我不急,他也没啥急的。恍然回到少年时,吵着嚷着帮忙。父亲还年轻,我装模作样地在车前拽着小绳迈大步。不大一会儿,绳子被甩到车上,人跑没影儿了。